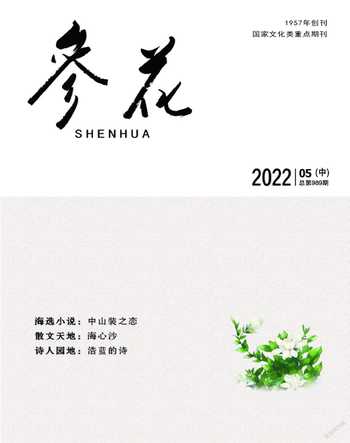“詩是我的寄托”
若阿西姆·杜貝萊于1522年左右出生于安茹的里雷市,是岡諾勛爵讓·杜貝萊和蕾妮·夏博的兒子。他十歲時父母雙亡,杜貝萊跟隨哥哥熱內·杜貝萊長大,然而兄長并未給予應有的照料。少年的杜貝萊身體孱弱,性格孤僻,常獨自在樹林里或盧瓦河邊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他過早地經歷了人世間最殘忍的骨肉分別和親人的疏離。提及自己的青春年少,詩人說道:“我的童年時代和青春期最美好的時光是多么無用……”“無用的”青春年少造就青年杜貝萊細膩敏感的性格,詩歌創作成為他自撫創傷的良藥。
一、為詩而狂的青年時代
杜貝萊出生于大家族,但生活并不闊綽。1546年左右,杜貝萊前往普瓦捷大學學習法律,在那里結識了拉丁詩人馬克·安東尼·穆雷和薩爾蒙·馬克林,學習了古希臘文和拉丁文,萌生了對文學的熱情。次年,他結識了龍沙,兩人決定加入巴黎的科克勒學院的文人圈子。在科克勒學院院長、希臘語老師讓·多拉的影響下,組成了一個名為“詩隊伍(La Brigade)”的詩人團體。1547年,在另外四位成員的加入后,“詩隊伍”更名“七星詩社(la Pléiade)”,詩成了安茹青年的“惡癖”。
而在十六世紀的法國,希臘語和拉丁語依舊占領語言高地。“七星詩社”力圖推廣法蘭西語言進行文學創作。1549年3月,27歲的杜貝萊執筆并以大寫字母I.D.B.A.署名,發表了人生中第一部作品——《保衛和發揚法蘭西語言》。作為“七星詩社”的宣言書,該文將法蘭西語言與法國文學命運相聯系。來自安茹的青年詩人搖旗吶喊:“不應褒揚一門語言,又貶低另一門語言”,因為“它(法語)具有與其他語言同等的生殖能力”且“并非不能探討哲理”。法蘭西語言的貧瘠應歸咎于“對它有保護之責的人們犯有過失,沒有充分的耕耘和栽培它”。宣言抨擊法國文壇輕視、拒絕用當時被稱作是“俗語”的法蘭西語言寫作的風氣,主張取古希臘羅馬語言文學之精髓以滋養本國語言,對法國文學批評和詩學發展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其實,《保衛和發揚法蘭西語言》并非是法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用法語創作并發表的為法蘭西語言和文學下注的作品。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頒布維萊科特雷法令后,法蘭西語言作為法律和行政上的第一用語地位被全面確立起來。彼時,對語言極其嚴苛的神學領域也陸續出現了法語譯本的宗教作品,在法國社會,尤其是在法國文人中,對民族語言的呼聲漸高。約1548年6月底,有巴黎書商開始發售名為《法國的詩學》的作品,盡管未署名,但沒過幾天作者便浮出水面:托馬斯·賽比耶。這部先于杜氏公開發表的作品也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篇用法語創作,并公開發表的關于法語文學創作的論著。賽比耶建議年輕人以克雷蒙·馬洛及其門徒,那些“優秀古典主義作家們”為榜樣,從他們身上汲取靈感,進行法語詩歌創作。他的出現引得科克勒學院側目。大約8個多月后,杜貝萊執筆的宣言面世,激起法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論戰。
宣言分上下兩卷,上卷圍繞如何豐富法蘭西語言這一問題進行論述,提出“模仿”的必要性。杜貝萊強調各種語言之間的平等性,認為“法語并非如認為的那樣貧瘠”“翻譯作品不是唯一和足夠的做法”,而因“絕大部分的藝術手法蘊含在模仿之中”,所以要“向希臘和拉丁最優秀的作家學習”,并且“鉆研出一個屬于自己風格的文學形式”。詩歌作為中世紀以來備受推崇的文學形式,其創作者們被賦予了這項捍衛和豐富法蘭西語言尊嚴的崇高任務。下卷著墨于詩人與詩歌,探討如何撰寫詩文,重點言及韻律、自然天性與寫作技巧之間的關系、詩歌體裁、新詞的發明、節奏、詩歌當中運用的一些古代技法、詩句的發音和詩歌藝術中需要的其他技藝等內容,提出今人在模仿的基礎上超越古人的傳統。宣言著成之際,杜貝萊尋得三樣護身符:一是將宣言致敬給親戚讓·杜貝萊,以為處女作增添無上榮光,二是請科克勒學院院長讓·多拉批準以院章加持,三是以寫字母縮寫署名I.D.B.A.發表,營造集體宣言之感。杜貝萊的一鳴驚人實非偶然,盡管很難將他的體弱多病與慷慨陳詞聯系起來,但他在宣言中多次提到“不朽(immortalité)”,他積極出世,認為詩人身份的最高企望是創作出不朽的作品和博取不朽的名聲。出生名門,半世坎坷,初登文學舞臺,杜貝萊便實現了名垂千古的愿景。
二、被誤解的法蘭西詩歌捍衛者
宣言的成功給杜貝萊飾以愛國者的偉大形象,但這部最重要的代表作自發表以來卻飽受爭議。1549年底,賽比耶首次做出回應。在自己翻譯的古希臘悲劇家歐里庇得斯作品《伊菲革涅亞》的卷首獻詩中,他將杜貝萊比作“放肆的批評者”。然而兩人觀點與其說相左,實則大同小異。駁斥賽比耶《法國的詩學》的同時,杜貝萊又展現出對對方觀點的吸收:他們都認為應該將所有語言一視同仁,翻譯是有必要的,詩人須效仿古人,認可靈感在創作中的重要性,推崇十四行詩等。賽比耶贊美馬洛特使用的法國古典傳統詩歌形式,讓龍沙和杜貝萊這樣的年輕詩人不能茍同,他們要求革去自己民族的傳統詩歌,于是在宣言中,杜貝萊有如復制粘貼再重新編輯了賽比耶的清單,留下了代表古希臘羅馬傳統的十四行詩、哀歌、頌詩、牧詩、史詩、悲歌及喜劇,將“雜詩”驅逐出境:“未來的詩人,請你再三閱讀,日夜翻閱希臘和羅馬的經典范本,然后替我將這些陳舊的法語詩留給圖盧茲的花賽詩社和魯昂的詩歌評委會:回旋體詩、三聯韻詩、兩韻詩、十音節誦詩、歌謠體詩,以及其他雜詩,他們敗壞了我們語言的美感,除了為我們的無知作證其他并無裨益。”“七星詩社”企想擯棄法語傳統詩歌形式、創造新的詩學、歸還法蘭西語言美感與優雅。相較之下,賽比耶更像一個純粹的法蘭西語言和文學傳統捍衛者——他維護了在十五世紀由法國修辭學派和里昂派制定卻被杜氏宣言驅逐出境的法國本土文學傳統,對意大利傳統詩歌形式也采取包容采納態度。杜貝萊似乎與自己的愛國衛士形象相悖,“它一方面極力主張提高法語的地位,宣稱今人絕不亞于古人……另一方面它又主張模仿古人,要人們日夜翻閱希臘拉丁的著作;它一方面提倡用法語寫民族的新詩,另一方面卻蔑視本民族的文學傳統……”,甚至有學者認為“杜貝萊在保衛和發揚雄心壯志下,掩藏的是一顆在意大利文化面前無地自容的心”。也確實能在宣言上卷第二章看到詩人承認“祖輩因為風俗粗野而被希臘人稱呼為野蠻人”,全文多次使用“俗語(vulgaire)”一詞(該詞本就帶有些許貶義,表示“通俗的,大眾的”,甚至“粗俗的”之意),而表達“法語”這一概念的方式有多種,用“法語”(le fran?ais),“法蘭西語言(la langue fran?aise)”“傳統語言(la langue traditionnelle)”等。
宣言在謀篇布局的不盡人意和自相矛盾,不禁讓人們疑惑:為何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中展現出一種熱情有余而嚴謹不足?興許是因青年詩人散發出的那份對民族語言的熱切愿景,故而讓人讀來有身臨精彩的“即興演說”之感;興許僅是文本體裁之故——這是一部宣言書,代表那個時代的一群新興法國詩人對民族語言和法國本土文學的呼喚。縱使稍顯倉促和馬虎,但這部“七星詩社”眾星捧月而出的宣言也應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即興演說”,它并非作者恣意筆墨的隨性而作。在杜貝萊看來,當時的法語不論是詞匯和表達方式都不能與希臘語和拉丁語比擬,更無法作為高級詩歌形式的媒介,但通過適當的培養,法蘭西語言可能會達到古典語言的水平。出于“對祖國天然的愛”,杜貝萊將語言與民族認同聯系起來,呼喚“保衛”和“發揚”法蘭西語言,建立法蘭西詩學新傳統并力求超越古人。此外還應該看到,杜貝萊面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慚鳧企鶴,除去他自身便受希臘、拉丁語啟蒙之故,還因“羅馬人的雄心和貪婪對所有相鄰的民族極具蠱惑性,讓他們蔑視自己的語言文化變得更加低劣無恥”,在長久的語言文化入侵下,杜貝萊也無可避免地受“蠱惑”,但在這樣的“蠱惑”之下,隱藏的應是一顆企望弘揚民族文學的心。
在賽比耶回應后,宣言遭到紀堯姆·德·奧特爾茲和巴泰勒米·阿諾的輪番攻擊。在1908年,法國學者皮埃爾·維利的發言引起了對杜貝萊作品原創性的討論。他指出宣言直接翻譯了意大利作家斯佩羅勒·斯佩羅尼代表作《語言的對話》中的部分段落,“《保衛和發揚法蘭西語言》的原創性遠不及我們所認為的那樣。實際上,它什么也沒有。不再是拾起一些古代回憶的問題,必須承認它所有的觀點都是借用的。”皮埃爾沒有直接指控杜氏抄襲,措辭時使用了emprunté(借用的)一詞,沒有直接說杜氏的作品是“一部抄襲斯佩羅勒《語言的對話》的法蘭西語言捍衛宣言”,自此,關于1549年宣言的原創性質疑聲不絕于耳,普遍認為杜氏這部作品中的內容確與同時期已出版的多部詩歌、書信以及著作前言在內容上雷同。劇作家莫里哀在面對指控他將西拉諾·德·貝爾熱拉克劇作中的一整幕搬到自己的作品中時說:“我不過就地拾起了我的東西”,杜貝萊拾起了斯佩羅勒和賽比耶的作品,和同伴一起審視它,為了創造不朽的法蘭西文學,去了他們認為的糟粕。應該看到,杜貝萊所處的時代是經歷了沉重壓抑的中世紀之后百廢待興的時代,理應正視它對法蘭西詩學和文學批評的推動作用,它出現的意義高于原創性的討論。正如V.L. Saulnier所言,“《保衛和發揚法蘭西語言》屬于那種稀有的作品,即使每個細節在獨創性或價值方面都存在爭議,但整體是有意義的。對這類作品來說,基調甚至比內容更重要,因為它們是用來攪動和更新氣氛的”。
三、以詩慰藉的暮年時光
杜貝萊一生發表詩作數余部,如1549年出版的《橄欖集》《抒情詩》和獻給瑪格麗特公主的一部詩集,早期作品帶有強烈的彼特拉克風格。《橄欖集》發表后,他因積勞成疾患上嚴重的肺結核,臥床休養兩年,不幸于1552年耳聾。次年隨親戚讓·杜貝萊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創作了《悔恨集》,《羅馬懷古》和《村戲集》,還用拉丁文撰寫了一部詩集。詩集的名字也反映了詩人的心境:失落,懷古,這一時期的作品擺脫了初期的模仿作風,寫出了內心的郁結和悲傷。看不慣佞臣,他創作出《宮廷詩人》(1559),關心法蘭西人民疾苦而寫下《關于法蘭西王國四個等級呈國王的時論詩》(1559)。
在杜貝萊的詩作中,《悔恨集》最為成功。現實中不復往昔的羅馬讓詩人感覺似被流放,就像羅馬詩人奧維德創作《憂郁集》時一樣,《悔恨集》是《憂郁集》的十六世紀版本,而杜貝萊就像是另一個奧維德,他也被流放在外,背井離鄉,盡管二者所處環境截然不同,但杜貝萊仿照了《憂郁集》中的一些元素。《悔恨集》的191首十四行詩描寫了遠離故鄉的憂郁,其中最著名的是《尤利西斯的幸福》,安茹詩人哭訴旅居羅馬的無聊。他本希冀借助意大利語言復興典范,為法蘭西語言重生助力,早在《橄欖集》中就匯集了模仿彼特拉克風格而作的十四行詩,盡管他宣稱這種模仿是出于對彼特拉克風格的嘲諷,但十四行詩在法國的興起確是由他點燃。羅馬在杜貝萊心中的輝煌無可比擬,他對羅馬始終懷有憧憬。可來到意大利之后,他見到的是羅馬的隕落,失落難捱,在《悔恨集》中寫下《詩是我的寄托》:
現在我原諒那種甜蜜的狂熱,
它耗盡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
這漫長的謬誤結果是空虛一場,
除了拋擲光陰我毫無收獲。
現在我原諒這愉快的勞作,
因為只有它撫慰我心中的創傷,
而且由于它,我一如既往,
不會在暴風雨中喪魂落魄。
雖然詩是我青年時代的惡癖,
但它也是我暮年的慰藉:
它曾是我的瘋狂,它將是我的理智,
它曾是我的創傷,它將是我的阿希爾,
它曾是戕害我的毒液,但我的沉疴
只有這靈驗的蝎子才能救治。
這首十四行詩描寫了看到日薄西山的羅馬現實,杜貝萊無比痛心的心境。理想與現實巨大的差異勾起了詩人心底濃重的憂郁,他明白羅馬最后的廢墟很快就會化為灰燼,羅馬成為一個傳說。夢想破滅的煩憂和失望讓他無時無刻思念自己的故鄉,唯在詩中能找到慰藉,獲得療愈,重拾理智,“只有它撫慰我心中的創傷”,讓他“不會在暴風雨中喪魂落魄”。如果時間摧毀了羅馬,那只有“詩”能夠救治他的“沉疴”。1558年,他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安茹,但身體的疲乏加上心力交瘁,次年末,杜貝萊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四、結語
杜貝萊是十六世紀偉大的詩人,盡管文學成就不及龍沙,但他呼吁法蘭西語言改革,撰寫的《保衛與發揚法蘭西語言》讓他千古垂名。創作《橄欖集》后雙耳失聰,客居羅馬多年,然而這座僅由廢墟構成的城市最終讓他生出厭惡,面對曾經的夢寐以求,深深的失望從心底彌漫,散結成解不開的郁結。英年早逝總是讓人唏噓,杜貝萊的溘然長往不能只用“悲劇”二字感喟,因為詩人業已實現“不朽”之愿,他有詩為伴,心有珠璣。
(作者簡介:戴艾,女,碩士研究生,樂山師范學院,助教,研究方向:法國文學)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