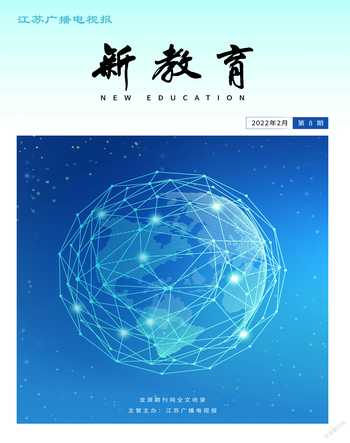探究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不同之處
摘要:一直以來,民間文學在中國文學中占據重要位置,并被稱作為文學創作搖籃,是文學創作的靈感來源,并在我國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時代都有著其獨有的價值。作家文學同樣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從文學角度來看,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同時也存在很大不同。基于此,本文對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展開研究,分析兩者不同之處,以供參考。
關鍵詞:民間文學;作家文學;不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浪興起,“文化”一詞被大眾所關注,并成為人們生活討論的焦點[1]。在大眾討論文化時,卻常常被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所困擾,即:何為文化?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是要對其進行詳細解答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關學者就提出了百種見解,有的學者認為,文化離不開人類,文化就是人類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對自己價值觀念的一種體現,是人類自己所創造的一種文化價值。這種文化價值通過某一介質實現傳播,在傳播過程中衍生出外在與文化有關的產品,同時也對人們的思想帶有著很大影響。這種對文化的定義不但突顯出了文化實質,還表明文化就是價值觀念的一個實踐過程。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同屬于文化的一種,從名字上來看,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都同屬于文學范疇當中,只不過是不同的文學樣式。通過對兩者之間的關系和不同進行分析,對推動我國文學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一、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相關闡述
在很早之前,民間文藝被劃分到文藝的名義下,但民間文藝與書本文藝、文人文藝存在很大差。在文藝學與作家文學的基礎下,建立了民間文藝學[2]。再后來,民間文學作為一門課程進入到大學校園當中,也推動民間文學理論體系建設,也使得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成為理論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在對民間文學的研究時離不開作家文學的支持。但隨著有關學者對民間文學的進一步研究,人們發現民間文學具有明顯的獨立性,其并不依賴于作家文而實現自給自足。并且民間文學有著很強的生活化特點,這與作家文學存在很大差異。站在文學角度來分析,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雖然有所差異,但兩者并不是相互對立關系,可以將其稱作為文學中的兩種不同文化現象。我們可以將民間文學看作為生活本身,也可以將其視為生活的一部分,是人類用來傳播自己價值觀的一種工具。而作家就是文學作品創作,創作就是其主要目的。民間文學來自于人們生活當中,其并不是以創作為目的,而是通過口頭講述的方式進行交流,這充分說明兩者之間有著很大不同。
二、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不同之處
1.直白與婉轉
由于民間文學是口頭講述,所以其主題向相對更加直白,對比之下,作家文學主題則更加婉轉[3]。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在主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兩種不同形態,主要是因為兩者有著各自追求。民間文學更加注重文學作品的教化效果,所以主題都非常直白,給人一種開門見山的效果。而作家文學則更加注重審美效果,所以主題表現比較含蓄,給人一種霧里看花的感覺。就比如說,在《包青天》這部民間文學作品中,這部作品就有著濃厚教化色彩,主題也是以開門見山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陳世美的批判,并憐憫秦香蓮被考上了狀元并且被選為駙馬的丈夫所拋棄。在作家文學作品中同樣也有癡情女子被愛人所拋棄的故事,但是在表達方式上卻要比民間文學更加委婉。就比如說在《鞋》這部作品中,主人公守明就是一個非常癡情的女子,作者通過描述其在為未婚夫做鞋時的心理過程來襯托出這個姑娘的善良、對待感情專注又純粹,但是當她為自己的未婚夫做好鞋之后,他卻拋棄了守明去當煤礦工人。其實這里的女主人公的故事和秦香蓮的故事非常相似,都是對女子癡情、真誠、善良的贊美,對男子薄情地批判。但與民間文學不同但是,這部作品中更為凸顯的是作者的審美意識,通過對守明心理活動的細致描寫,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通過自我感悟來體會守明姑娘的人物形象。所以,作家文學以委婉的方式來凸顯作品審美效果。
2.社會心理層面與社會意識層面
有學者認為民間文學就是一個表演過程,這種表演是以口頭的形式呈現出來的[4]。還有學者認為,民間文學是由廣大人民群眾創作的。民間文學研究學者將其視為一個口頭表演過程,這也就代表其會受到物質與制度文化的影響,還和行為文化有著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的關系。詳細而言,在民間文學展演時,需要運用到一些道具、配合相應場景,并且需要滿足展演者和觀眾物質方面的生產與生活需求,而這些內容都是物質文化層面。此外,在展演過程中,展演者和觀眾雙方都應當嚴格遵循這個時代的社會制度和規范,否則就無法順利推行展演活動。當然也會涉及到一些特殊的展演內容,如:祭祀活動等,需要展演者和觀眾能夠遵循一些特殊的要求,如:雙手合十祈禱等等。展演者的動作、神情等都要符合這個地方的風土民情或是禮俗,這樣才能通過眼神和動作與觀眾進行交流,使觀眾能夠快速心領神會。就比如說在《老少配》這部民間文學作品中,三妹子他娘和大寶他爹的展演者就通過眼神交流將這部作品中的贛南行為文化完美的向觀眾傳達出來。如果展演者之間的眼神含義沒有被觀眾所理解,觀眾就無法將自己心領神會的氛圍傳遞給展演者,那這樣的民間文學展演就是失敗的。可以說,民間文學就是對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真實寫照,對人民群眾內心情感的表達也沒有經過藝術加工,而是以直接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方式表達出來,因此民間文化是一種社會心理層面的一種文化。
與民間文學有所不同,作家文學則是社會意識層面的一種文化。社會意識層面文化主要是指藝術、文學、哲學或者是宗教活動等等,是不同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其他內容。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其雖是一種意識形態,但其是與眾不同的審美意識形態。作家文學是專業的創作者,有目的性的創作文學作品,并享有作品的知識產權與署名權。文學作品的好壞與創作者的個人創作能力、思想水平、審美能力以及文學積累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在我們生活當中,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名創作者,但要想成為文學作品創作者,就必須要付出努力和行動,并接受專業培養。從這一層面來看,作家文學是一種經過加工的社會意識,并通過文學作品的方式來呈現出來。這也是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的一大不同之處。
3.單一化與多樣化
按照作品數量來對比,民間文學作品數量相比作家文學作品數量要更多。對這些民間作品進行研究對比后,可以發現民間文學作品都大致相同,這些相同之處主要體現在作品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形式等等,很多作品的故事內容都存在雷同的情況。所以,可以說民間文學作品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相同的特點。而導致民間文學作品“相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在于,民間文學的創作主體并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某一個群體,可以說民間文學作品是由多個人創作出來的,他們之間的關系也并不一定是緊密的,但這些人在某些地方一定有著一定相同之處。例如,創作群體可能有著非常相近的愛好,或是有著非常相似的人生經歷,或是思想價值觀念趨于一致,又或是他們對于作品有著非常相近的創作動機。正是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定相同之處,在文學作品創作中不自覺地就形成了相同的意識。此外,民間文學能夠獲得廣泛傳播,也正是因為其在受眾群體中引起強烈共鳴。通常情況下,受眾群體對民間文學作品的共鳴越強烈,作品的影響力就越大,傳播范圍也就越廣泛,進而可以被更多群體所了解和認可。當然在傳播過程中,也會產生一些模仿效應,產生強烈共鳴的群體也會被作品所感染,在作品的啟發下成為創作者。只不過在這種情形下所創作出了的民間文學作品,大多是模仿,創新元素比較少,這也是導致民間文學具有“相同”特點的一個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作家文學更加追求不同,這種不同可以理解為創新。作家文學作品創作者希望為讀者帶來與眾不同或是另類的審美體驗。作家文學在作品中表現的不同是多方面的,這種不同不僅體現在創作內容的不同,還體現在創作形式的不同。相對于民間文學,作家文學在作品形式上的呈現更加多樣化,創作者所投入的精力也更多。要知道,無論是民間文學還是作家文學,其都是由兩個部分所構成,分別是內容和形式。然而大眾對創作內容和創作形式缺乏全面地認識,甚至存在一些錯誤認識。很多人誤以為作品內容會直接決定其創作形式,創作形式對內容創作有著輔助作用。這種認識提高了內容創作的重要性,忽視創作形式的價值。其實,創作形式在作品中的價值要遠高于創作內容。主要是因為創作形式對于創作內容并不只是簡單的服務,這種服務具有主動性,并且可以反作用于創作內容,對文學作品創作內容進行拆解與重組。所以,注重作品創新的創作者,其在創作過程中更加注重創作形式的不同,通過別致的創作形式來為讀者呈現出獨特的作品。
總的來說,在我國文學領域,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同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兩者雖看似獨立,卻有著密切關系。可以說作家文學離不開民間文學的滋養,為作家文學創作活動帶來源源不斷的靈感來源,推動作家文學不斷創新。但同時,兩者之間有存在很大不同,這種不同體現在多個方面。在文學作品主題表達方式方面,民間文學更加直白,而作家文學更加委婉;在社會層面方面,民間文學屬于社會心理層面,而作家文學屬于社會意識層面;在創造形式和內容方面,民間文學存在一定相同性,而作家文學追求不同。當然,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之間的不同不僅局限于本文所述的幾點,在價值方面、功能方面等都存在很大不同。在文學觀視野下,應當認識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之間的關系與不同,使二者可以取長補短、相互促進,以推動中國文化發展。
參考文獻:
[1]安德明.在對比中進一步探討民間文學的獨特屬性[J].民間文化論壇,2019(05):1.
[2]楊晗.民間文學對作家文學的影響解析[J].邊疆經濟與文化,2017(07):81-82.
[3]王娟.當代民眾生活中的民間文學——兼談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關系[J].民俗研究,2016(02):90-98+159-160.
[4]朱家英.《三言》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略析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之關系[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4,30(11):54-56.
作者簡介:
楊德娥,女,白族,云南省大理市,1986年3月,碩士研究生,民間文學,講師,云南藝術學院文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