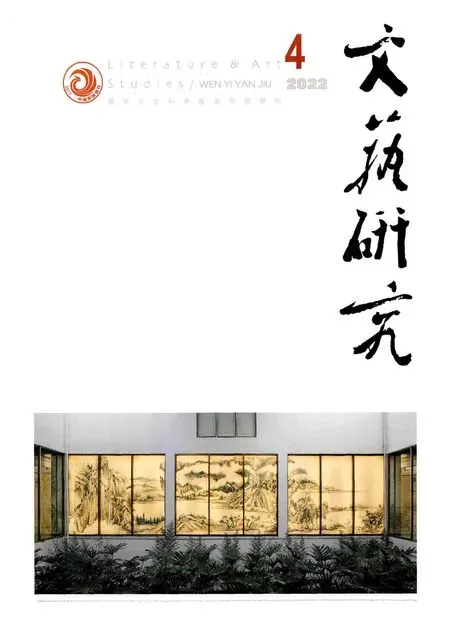作為戲劇美學概念的“暗示”
——薩特在中國戲曲演出中看到了什么?
趙英暉
薩特曾三次在演講或訪談中以中國戲曲為例闡述自己的戲劇主張。他使用了“暗示”(suggérer)一詞描述中國戲曲的表意方式及與現實的關聯模式。這個詞也出現在20世紀流派分殊、志趣各異的其他西方戲劇人和理論家的筆端,如馬拉美、阿爾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讓·莫雷阿斯(Jean Moréas)、羅蘭·巴特、阿道夫·阿皮亞(Adolphe Appia)和格洛托夫斯基等。盡管他們對該詞的具體解釋有別,但它總是作為新戲劇的特殊表達方式被提出,以反對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藝術對經驗之真的直白復現。如果說法國古典戲劇理論最熱衷探討的是規則(règles),啟蒙時代的戲劇以社會學家的目光審視時代,浪漫主義正劇(le drame romantique)表現出對個體內心世界的無限興趣,那么,暗示或多或少能代表西方現代戲劇的一個共同趨向,即對風格與表意、能指與所指之間關系的權衡。而在此之前,“不論是拉辛、雨果和克洛岱爾這樣的詩人,還是高乃依或哥爾多尼這樣的情節大師,都更重戲劇行動而非風格”。
誠然,從中國戲曲美學的真正意涵出發來看,薩特所謂戲曲的“暗示”性表演,與諸多西方人對戲曲的解讀一樣似是而非,不過是把戲曲變成了西方文化投射自身的幻想空間。然而,薩特是法國乃至西方20世紀的一面思想旗幟,他的寫作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寫照,因此,他在西方現代戲劇理論中的“暗示”概念與中國戲曲美學之間建立的關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是怎樣的思想語境使20世紀西方戲劇人對中國戲曲的關注和借鑒成為可能。如所周知,中國戲曲西傳史在20世紀初出現分水嶺:此前,西方人對中國戲曲的藝術價值普遍并不關心或給予負面評價,西方戲劇中的中國元素主要是一種異域想象,與中國戲曲本身關系甚微;此后,中國戲曲美學被西方戲劇人青睞、神往、轉化、吸收,即便是誤讀,也源自他們對戲曲美學特性的深切矚目。在克洛岱爾、梅耶荷德、阿爾托、布萊希特、熱內等人的目光或想象中,中國戲曲呈現出與西方現代戲劇理想的契合。這條分水嶺的出現,一方面與中國戲曲演出的對外輸出有關,另一方面也與20世紀西方的戲劇理想分不開。解讀薩特劇論中“暗示”一詞的含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描繪出這個中西戲劇美學交匯點在20世紀的西方得以萌生的精神土壤。
一、一種“暗示”戲劇
1954—1955年間,薩特與中國文化有過較為集中的密切接觸。他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影集《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1954)題寫前言;于1955年10月受邀訪華,隨后在《人民日報》《法蘭西觀察家》()和《新政治家與國家》()等報刊發表文章與訪談,介紹自己對新中國的觀感。
薩特與中國戲曲的相遇也發生在這一時期。1955年6月,他在巴黎的莎拉-伯恩哈特劇院(Théatre Sarah?Bernhardt)觀看中國藝術代表團首演,演出內容除中國傳統舞蹈、音樂之外,還包括《三岔口》《鬧天宮》《霸王別姬》《斷橋》《秋江》《雁蕩山》等京劇劇目。此后,他在1958年、1959年、1960年的三次演講或訪談中談及中國戲曲。并且,不同于波伏娃對戲曲全面但外在的介紹,薩特將戲曲作為論述自己戲劇思想的有力支撐。
1958年,薩特在題為“戲劇與電影”的講座中說:“在感傷電影中,風景是一種精神狀態,能創造自己的表演者。電影描繪的是在世界之中并由世界決定的人。而戲劇的情況正相反:貝克特和啞劇。電影的布景是抓住人,毀滅他或拯救他。在京劇中,河、船、危險、黑夜由動作暗示(suggérer)出來。因此戲劇是將人的行動展現給作為人的觀眾,同時也通過該行動展現這個人的生活世界和這個人自身。”
1959年,薩特接受《民眾戲劇》()雜志的訪談時說:“在戲劇中,不應把事物作為客觀現實而將觀眾的注意力過分吸引于其上:觀眾很清楚它們不存在、是假的。在電影中,事物既更真實又更不真實:它們被一整套幻覺游戲呈現給我們;我們一旦進入這個游戲,就可以認為它們是真實的。……在戲劇中,演員的姿勢(geste)比事物更重要。確切地說,事物誕生(naissent)自姿勢。讓-路易·巴洛(Jean?Louis Barrault)說模仿爬樓梯就是創造(fait na?tre)樓梯,他說得對。……中國戲曲中也是如此。事物不必在場。事物是多余的。姿勢在使用事物的過程中產生(en?gendre)簡潔的事物。”
1960年,薩特在題為“敘事性戲劇與戲劇性戲劇”的講座中說:“只需把道具減少到幾乎為無。幾年前,我們在中國戲曲演出中見過許多這種情形。幾乎什么都不用就能讓人看到(évoquer)河和船;如果你掌握了這樣的藝術,即中國人演艄公的藝術,你也能用迷人的方式讓人看到。我還見過更精彩的……聚光燈下,所有燈都亮著,兩個中國戲曲演員用啞劇創造(créer)出黑暗……他們互相找不到對方,不時出現二人險些發現對方的情況,比如,他們背對背,或是一個叉腿站在另一個上方等等。說來話長。他們本是朋友,這個故事就因為是行動才有意義,決斗是行動,二人都想殺了對方,這個行動充滿沖突和矛盾,只在黑夜里才有意義。結果大家都看到了黑夜。”
可以看出,薩特在回顧自己觀看過的中國戲曲時,總體上是在解釋中國戲曲中動作與物的關系。他連接主語(戲曲動作)與賓語(物)時使用的動詞,按照詞意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créer、faire na?tre、engendrer、naissent,意為“創造”,薩特通過它們指出,在京劇中事物誕生于動作。第二類是évoquer,意為“使在某人頭腦中產生”,即創造的結果。第三類是suggérer,意為“通過影射使人受到啟發,從而產生某個想法或采取某個行動”,它既包含第一類動詞的含義,即在京劇中事物是被動作創造出來的,也包含第二類動詞的含義,即這一創造的結果;同時,它還描述了事物被動作創造出來的方式,即戲曲動作提示、暗示、引發對實物的想象,而非直接呈現實物。它的反義詞是donné,即“給出的、給定的”。為論述方便,本文將suggérer譯為“暗示”。因為“暗示”包含另外幾個動詞的含義,能夠涵蓋它們所體現出的薩特對戲曲動作的認識,所以以下分析主要圍繞“暗示”展開。
首先,“暗示”等動詞體現出薩特對戲劇假定性的肯定。在第一次談及戲曲時,薩特根據布景與人物的關系,將京劇、啞劇、貝克特的《無言劇》()歸為一類,將電影看作與它們形成對照的另一類。在前一類作品中,暗示是一種創造活動,人物動作以暗示的方式創造出世界;而在電影中,布景(世界)決定人。在第二次談及中國戲曲時,他依然將戲劇與電影在布景與人物的關系這一問題上的表現對立起來,認為它們各自與經驗真實保持著不同的關系:在戲劇中,觀眾的注意力不應被吸引到道具的實物本身上,而應被吸引到它所代表的意涵上。道具本身并不重要,只要符號意指過程能順利完成即可,而這靠的是動作的創造性。在第三次談及戲曲時,薩特借助的顯然是《秋江》和《三岔口》的例子,他進一步解釋了在戲曲中人物動作怎樣“產生”和“創造”世界,以此支持他減少甚至取消布景的主張。
薩特的這一主張,與西方戲劇人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對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戲劇的批評一致。啟蒙以來,實證主義思想在西方社會生活各領域日益堅實,戲劇中逐漸形成對復現現實經驗之真的追求,甚至混淆藝術與現實的界限,將藝術之真等同于經驗之真。19世紀下半葉,馬拉美、雅克·科波(Jacques Copeau)、雅里、阿爾托、愛德華·戈登·克雷(Edward Gordon Craig)、梅特林克、奧斯卡·施萊默(Oskar Schlem?mer)、梅耶荷德、布萊希特,都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戲劇提出批評,比如梅耶荷德譴責它們所追求的經驗真實將戲劇帶入了“俗不可耐的泥潭”。直到20世紀中期,對戲劇之“戲劇性”(théatralité)、戲是戲而非現實的呼吁仍未間斷。比如,薩特的戲劇生涯引路人夏爾·杜蘭(Charles Dullin)反對自然主義戲劇追求逼真、否定想象和抽象的風氣,他在東亞戲劇風格化而精準的藝術中找到了精神共鳴,主張戲劇藝術是對現實經驗的“轉置”(transposition),即通過對經驗的加工、綜合、轉化、重構,實現對現實的理想化,以藝術的豐富來彌補直白的現實所不可避免的貧瘠。薩特曾為其文集撰寫長篇序言的熱內,也坦言西方戲劇逼真的“表達方式在我看來過于粗俗”,他夢想的戲劇是“富有活力的符號構成錯綜復雜的關聯體,它向公眾說的那種語言什么都不說明,但一切都能被預感”。薩特也明確反對現實主義風格,認為“大部分當代戲劇力求讓我們相信臺上之事是真的在發生的事(réalité),但對其真相(vérité)究竟如何卻毫不關心”,只求“讓我們靜心等待、讓我們害怕最后那聲槍響,若能震聾我們的耳朵……那就‘行了’”,所以他“不常看戲”,因為“太差,令人掃興”。
其次,“暗示”等動詞也體現出薩特對中國戲曲的認識是基于他對人物動作的觀察。他對戲曲的觀察角度與其他外國戲劇人或普通觀眾有所重合,即關注造型性而非戲曲的其他方面。《世界報》在中國劇團首演后刊登的報道,可以代表普通觀眾的反響:一方面,不懂唱詞影響了對劇情的理解,他們也不太能接受如“鳥雀啁啾”的“過高”調門;另一方面,人物造型和一招一式的動作令他們“大飽眼福”。外國戲劇人也是如此,克洛岱爾的文集《認識東方》中的“戲劇”篇和梅耶荷德有關戲曲藝術特點的談話,體現出同樣的關注傾向:前者不談情節,只詳盡描繪舞臺和演員的表演;后者關注戲曲演員如何將日常的舉手投足轉變成有“精細節奏感”的“舞蹈”。
以上兩點,是“暗示”等動詞體現出的薩特與諸多西方戲劇人對中國戲曲認識的共通之處。除此之外,薩特還對“暗示”有進一步的解析,這涉及他的幾個重要戲劇概念:“姿勢”“普遍性”和“戲劇性戲劇”(théatre dramatique)。
二、暗示與戲劇的“姿勢”
如上文所言,“暗示”包含“創造”之意,表示一種創生、締造的過程,通常由主語所指的事物產生出賓語所指的事物。薩特談及中國戲曲的這三段文字,在解釋戲劇是否需要真實物件作為道具這一問題的同時,更強調動作的創造性。動作的創造性取消了真實物件在舞臺上存在的必要。薩特稱具有創造能力的動作是姿勢:“姿勢是什么?姿勢即非行動(acte)的東西。是一個并不以自身為目的的行動,是一個旨在展現其他事物的行動或動作。”在薩特看來,戲劇動作是姿勢、意指活動(signification)和展示(présentation),它代表的是另一事物而絕非它自身。雖然可以將薩特的“姿勢”與通常所說的“假定性”“程式性”聯系起來理解,但薩特尤其看重姿勢的創造性。姿勢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一種對自身的否定和超越,即一種創造,并且既創造人物自身,也創造人物的環境。
一方面,姿勢創造人物自身。在薩特觀看的中國戲曲演出中,觀眾都可獲得劇目簡介手冊,因此,他應該可以提前對臺上的故事有所了解。但在他關于京劇動作的討論中,并未提到這些準備工作對他了解人物身份的幫助,而是強調人物動作創造出人物身份。他還以法國演員馬德萊娜·雷諾(Madeleine Renaud)為例來進行說明:已過中年的“雷諾演一個20歲的寡婦,絲毫不令人覺得不妥。因為,重要的不是成為那個20歲的寡婦,而是扮演那個20歲的寡婦。美麗?青春?雷諾都沒有。她用的是姿勢表意(signification des gestes)。這不是在場,而是缺席,是捕捉不到的幻影;缺席的事物被包裹在姿勢中,讓人以為它一直都在場”。雖然其他一些堅持戲劇假定性的戲劇人也舉過類似的例子,但他們的側重點主要落在演員是否應進行體驗式表演、感人物之所感的問題上,比如狄德羅的《演員新解》(,1773)。而薩特強調的是動作的創造性,“動作創造人”體現了他在早期著述《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和《存在與虛無》中就已形成的思想:人是“自為的存在”,并無預先確定的本質,而是通過行動不斷超越自己、造就自己,超越性和創造性構成了人的存在,“人除了是自己的創造外什么也不是”。
另一方面,姿勢也創造出道具布景,“說到底,道具毫無用處,布景毫無用處,毫無用處,絕對如此。……產生事物的唯一方法,是姿勢”。艄公的動作創造出他的活動環境,即船和水;《三岔口》中打斗的人通過動作創造出他們的活動環境,既包括物理環境,即漆黑的夜,也包括心理環境,即兩人間的敵意。薩特還舉出演員喝水的例子:喝水這個動作是為了展現人物喝水,杯中是否真的有水并不重要。“行動”的意思是人做這個動作的意圖就是這個動作本身,喝水就是為了喝水。但在戲劇表演中,無論演員做的是一個真動作(真喝水)還是假動作(杯中無水),它都是姿勢,都是意指活動(表示喝水)。薩特失望地發現當時法國舞臺道具方面的一個變化:以前杯中無水,喝水完全是姿勢,近年來杯中有水,演員真的喝了水。他認為這種做法扼殺了戲劇的創造性,忘記了戲劇是姿勢而非動作,忘記了道具應由表演創造出來。
薩特所說的“布景”還包括人物活動的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他說,“行動在戲劇中是姿勢”,因為戲劇通過“人體的行動”,是要“呈現具有決定意義的情形、呈現結果和方式”,姿勢“將行動作為其第一意義來展示,也通過行動將世界作為其第二意義來展示”。這里所謂“具有決定意義的情形”和“世界”,即薩特著述中頻繁出現的“情境”(situations)的同義語。“情境”指“人生的客觀物質條件的集合”,包括身體、家庭、階級、國家、種族等。人是情境中的存在或人是“在世存在”,指的是人是歷史的和真實的存在,“在世存在”是人的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本質在決定人的行動。并且,人的行動的結果也將形成人的情境,人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創造了情境。關于情境對人的決定作用,薩特早期和后來的認識有所不同: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認為人在任何情境下都能自由選擇,情境并不完全決定人的存在,但后來他更加承認“事物的力量”(la force des choses)對人的左右,“某種東西,它不是我的自由,它從外部掌控我”。盡管如此,薩特始終認為人是情境中的存在,這是人的境遇的基本事實,情境化的人才是“人的存在整體”。就藝術而言,“每一幅畫、每一本書都是對人的存在整體的一種找回”,而“一切……都來自姿勢”的戲劇,也應通過姿勢暗示出動作,暗示出包含、決定這個動作并使之有意義的情境,唯其如此,才能完整地展現世界。
薩特在中國戲曲中看到的姿勢,是否與布萊希特的“姿勢”(gestus)概念有關?布萊希特的“姿勢”概念在法國的傳播情況并無確切史料記載,但可以推斷這種關聯是存在的。薩特觀看京劇演出的前一年,即1954年,布萊希特的柏林劇團在巴黎進行了首演,這次演出在薩特、巴特、貝爾納·多爾(Bernard Dort)等一批有志于改革戲劇的思想家和戲劇家心中燃起了“一場大火”、照進了“一束光芒”,他們都曾多次撰文分析布萊希特戲劇,希望在布萊希特的榜樣中找到振興法國戲劇的力量。薩特首次提到布萊希特是在1955年,自此,布萊希特便成了他戲劇論著中最頻繁出現的名字。
布萊希特最早于1929年使用“姿勢”一詞,《戲劇小工具篇》《辯證的戲劇》《演員的藝術》等文均對該概念有所涉及。布萊希特也稱姿勢為“社會姿勢”,因為姿勢在一定程度上由人物所屬的社會階層或團體決定,并且發生在人物之間,“人物相互采取的態度,我們稱為姿勢”,姿勢可以是“身姿、語調和表情”,可以是“一系列的行動、身體動作,也可以是(更常見的是)一人或數人對另一人或數人說的話”。布萊希特認為人物互相謾罵、恭維、教訓,甚至完全私人的動作、表情(如病痛)都可以是姿勢,只要它們能表現做出姿勢的人對他人的態度,并且這種態度能體現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聯。例如大膽媽媽接過買主遞來的硬幣后用牙咬以驗真假,官僚在文件上龍飛鳳舞地簽字,這些都是姿勢。姿勢“介于行動和性格之間”,“它展現社會實踐中的人,所以是行動;它展現個體獨有的特征,所以是性格”。
在布萊希特看來,戲曲表演也是姿勢。觀看了梅蘭芳1935年于莫斯科的演出后,他在《關于中國戲劇藝術的看法》(Bemerkungenüber die chinesische Schauspielkunst)等文章中提出“這樣一種演出模式,其原則能否為西方舞臺所用”的問題,認為可以學習梅蘭芳的姿勢。他寫到,“這位演員(梅蘭芳——引者注)區分了姿勢和作為面容的眼睛”,他“像使用白紙一樣使用自己的面容,他的身體通過他的姿勢在這張紙上覆滿符號”,“他不時轉向觀眾,像是對觀眾說‘難道不是這樣嗎’?他也觀察、引導、控制自己的胳膊和腿,最后甚至可能表揚它們。公然朝地上看一眼,評估一下有多大空間供自己施展身手,這對他來說都不會干擾幻覺”。布萊希特在1936年的《中國戲劇表演藝術中的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o in der chinesischen Schauspiel Kunst)中第一次使用“陌生化”概念,即指面容與姿勢的分離、身體與表演的分離。因此,有學者認為姿勢是“陌生化”概念的組成部分。
薩特不完全贊同布萊希特的陌生化理論,他并未在京劇姿勢中看到陌生化。薩特注重的是姿勢與時代的社會現實相關聯的一面,他將布萊希特的“姿勢”與自己的“情境”概念結合,認為布萊希特的“姿勢”是情境化了的人的動作,布萊希特戲劇“要展現個人行為,也要展現制約個人行為的社會姿勢,他想展現任何行為中存在的矛盾,同時也要展現產生這些矛盾的社會制度”,既凸顯一個意義,也呈現該意義的產生環境。薩特針對的則是當時法國流行的資產階級戲劇(théatre bourgeois),其中的臺詞、動作、服裝脫離了社會和歷史,只關注個人情感,甚至只為嘩眾取寵。
行動創造人,也創造人的整體生存情境,戲劇應展現情境中的人,即人的存在整體。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用姿勢創造人物身份、布景道具、人物關系、行動環境的京劇,呈現了薩特認為的戲劇之所是。
三、暗示與戲劇的“普遍性”
薩特還強調中國戲曲暗示表演所具有的“普遍性”:“我們也可以用風格化、圖示化的布景道具(‘貧困戲劇’的意思即是如此),因為布景道具只需被動作提示出來就夠了,這樣的提示是普遍性的,我們從布景道具中看到的總是普遍性的東西。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提倡人工性(artificiel)的意義所在。或者說,突出人的存在、真正圖示化的布景總是普遍的布景。”暗示性的“動作創造出的是普遍而非特殊。坐到椅子上的方式沒有五花八門,將要顯現出來的那把椅子是任意一把椅子而不是某把特殊的椅子。用叉子的方式沒有五花八門,這是一把絕對普遍的叉子”。
首先,將戲曲表演的風格化、抽象性、暗示性與事物的普遍性聯系起來,這體現出薩特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思路:將思考集中于共相而非個別事物的偶然性,明確區分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存在和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更實在、更根本的存在,并以后者解釋前者。薩特的文藝批評常常體現出這一特點,例如在評論賈科梅蒂繪畫時,薩特尤其注意輪廓線的消失和斷續、人物與周圍的虛空之間的關聯。他認為在賈科梅蒂的繪畫中看不出虛空自何處始,人的身體到哪里是邊界:“賈科梅蒂沒有畫鞋的輪廓,不是因為他覺得這鞋沒有邊,而是他想由我們給鞋一個輪廓。事實上,鞋就在那,沉重、堅實。要看到它們,只要不真的去看它們就行。”所有身體部位、服飾都在那里,盡管并未被線條框定起來,只需一種不那么實在的目光,就像“我們有時候構思清晰而完整的概念,并沒有用詞語表達出來”。薩特區分了實在給定的和未給定但更實在的東西,把后者稱作具有“超確定性”的“純粹真實”,把實現“純粹真實”的藝術手法稱作“去物質化”(dématérialisation)。他在面對中國戲曲時也是如此,只有當真實事物不在場,當行動變為姿勢時,產生的事物才是普遍的,才能實現“純粹真實”。
薩特所說的“普遍性”也是他一貫追求的戲劇的群體性、公共性。他認為“戲劇是產生集體影響的社會藝術”,這一想法萌生于他早期的戲劇經驗。根據波伏娃的回憶,她與薩特曾癡迷于德國巴伐利亞南部小鎮上阿瑪高(Oberammergau)演出的耶穌受難劇。這部劇留給薩特的印象“可能比任何一部他觀看過的劇作都深刻”。這種已傳承了三百年的上阿瑪高的傳統演出,“給薩特印象最深的是儀式、生動的畫面、龐大人群的運動、緩慢的節奏、非專業演員的參與”。后來,薩特于1940年在戰俘營中自編、自導并參與演出了《巴里奧納》(),這次演出的一切工作都由戰俘完成,觀眾也是戰俘。這是一部關于耶穌受難的神秘劇,但將戰俘們的生存情境融進了情節,寫這部戲就是在跟戰俘談他們的狀況。演出過程中,看到戰俘們全神貫注的表現時,薩特明白了“戲劇之應是:即一個宏大的集體和宗教現象”。后來,有了更多在各個領域的創作經驗后,他說,“一般而言,戲劇觀眾各種各樣:行商的和教書的,男的和女的,各有各操心的問題。這種狀況對劇作家是挑戰”,“只有實現觀眾的統一才有戲劇”,而“能將如此不同的社會群體結合起來的聯系只能是非常普遍和抽象的”。在薩特看來,群體性是戲劇的基本屬性,如果沒有普遍性,而是將個體生活的千差萬別都通過細節體現出來,則無法實現群體性;能夠集合大眾的只有普遍意義,非實在、非物質的姿勢是實現戲劇普遍性的基本單位、基本要求。
薩特的這一主張與20世紀初的歐仁·莫海勒(Eugène Morel)、羅曼·羅蘭、菲爾曼·吉米耶(Firmin Gémier),以及與薩特同時代的讓·維拉爾(Jean Vilar)、巴特有頗多相似處。他們都將戲劇視為營建和團結共同體的方式,都努力呼吁改變戲劇的形式和內容,以讓盡可能多的人觀看、參與戲劇。薩特的看法更為徹底,他認為一切戲劇都應是民眾的,除民眾戲劇之外別無戲劇:“民眾戲劇……于我而言意思是一切戲劇。”他批評維拉爾領導的國立民眾劇院在劇目設置、演出推廣等方面并未真正走向民眾,其受眾仍是小資產階級。
若繼續追根溯源可以發現,民眾戲劇運動的參與者們用戲劇實踐或批評來闡述戲劇理想時,找到的重要參照是古希臘戲劇,他們希望恢復戲劇在古希臘發揮的凝聚城邦的力量。例如《民眾戲劇》雜志的創辦者和編輯之一巴特在《古代悲劇的力量》中指出古希臘悲劇“排除個體激情”,“借助極具普遍性的劇情”,通過引發“平民集體落淚”而實現“對他們的最高教化”,這才是“古代悲劇原初的純粹性”,巴特惋惜地說,在他的時代能夠引發群情激蕩的參與精神的只有運動會了。薩特對戲劇普遍性的肯定中也充滿對古希臘傳統的向往,他將實現了普遍性目標的戲劇稱為“神話”,“我們認為戲劇若描摹個體人格則有違自己的使命,即便描摹典型(如吝嗇鬼、恨世者或戴綠帽子的丈夫)也是如此。因為,戲劇若要面對群眾、對群眾言說,則應跟群眾談他們最普遍關心的事,用他們每個人都能明白和深刻體會到的神話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思慮”。薩特認為,細膩刻畫以強調特征、突出個體性,除了能引起贊同這種特征或者本身就具備這種特征的觀眾的共鳴之外,在人物與其他觀眾之間、部分觀眾與其他觀眾之間制造的都是隔閡。觀眾應是統一的,或者說戲劇-神話應當在它演出的這段時間內創造出統一的觀眾,“它必須創造自己的觀眾,它必須在心靈深處喚醒一個特定時代和一個特定集體中所有人都關心的東西,由此把所有不一致的元素融為一體”。
在看過梅蘭芳的演出后,布萊希特在最初的筆記中贊嘆,本以為這樣一種富含程式和規則的藝術只有懂行的學者看得懂,沒想到它也能被平民大眾廣泛接受,戲曲竟能“培育出一種需要學習、提高和演練的觀眾藝術”。巴爾巴在今天仍然沒有解釋清楚,為什么包括中國戲曲在內的“非常風格化,非常矯揉造作”的藝術,“雖然很做作,有時卻感覺比現實更真實”。對此,薩特嘗試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中國戲曲動作能撇開特殊的經驗對象,穿透事物具體的“是”,把握事物的之所以“是”,通過暗示性的姿勢創造出普遍事物,寫就以普遍的方式進行表達的“神話”。
四、暗示與“戲劇性戲劇”
薩特使用“暗示”“讓人看見”“創造”等動詞,強調戲曲動作作為符號如何完成意指過程,達成表意:一方面注意動作本身的各種特征,另一方面堅持認為戲曲動作并非它自身,而是一個不在場的人或事物的表征,是某一意義的介質,比如要讓人明白這里是一位艄公在劃船,那里是兩人在黑夜里打斗。
費舍爾-李希特在《行為表演美學——關于演出的理論》中區分了觀眾對演出的兩種接受方式:符號學的和非符號學的。前者“只專注于理解一部藝術作品”,作品的構成材質雖受關注,但其中每種元素都被視為可被賦予含義的介質,觀眾關注它們的目的只在于透過介質看到意義,透過外在看到內涵,作品的構成材質始終被視為載體,是形式/內容、外在/內在、能指/所指、物質/精神、現象/本質這一系列二元對立中居于次要的一方;后一種接受方式中,分析和理解退居其次,作品的物質性或曰“形體外在性”超出其作為意義載體的功能,比如人物的動作,“動作不自然而然產生所加予它的意義,動作要先于每種嘗試對它做出的解釋”,這時,觀眾注意的是演員身體、布景、聲響等的物質性,而不將之視為表意的符號,不對之進行符號化解釋。
薩特對戲曲及其他戲劇或文藝作品的接受,在總體上屬于第一種方式。他指出了戲曲動作的暗示性,這雖是在強調戲曲動作本身的物質性,即要求載體應當是風格化、抽象、普遍的,但這些動作是作為意義載體而存在的,必須暗示出意義。薩特在對其他戲劇的關注中也同樣持這種符號學的接受態度,米歇爾·貢塔指出,即便在生活劇團(The Living Theatre)、開放劇團(The Open Theatre)或彼得·布魯克的戲劇中,薩特注重的也不是演員、身體等戲劇材質本身,他不相信導演、服裝和布景的重要性,在他看來,那不過是對舞臺機械裝置的經營,是他最不關心的事。薩特只肯定他們的“集體創作”,認為這與自己有關戲劇的集體性、社會性的構想不謀而合。
薩特對戲劇中物質載體和被表征物之間的暗示關系的認識,以及對戲劇中意指過程、理解過程的認識,源于他的“戲劇性戲劇”主張。簡言之,薩特提倡的“戲劇性戲劇”是介于布萊希特的敘事劇和資產階級戲劇之間的戲劇。他認為,觀眾理解一件藝術作品(或者說符號完成表意過程),就是發現一件藝術作品與自己相關,而一旦理解,就會有“參與”(participation)發生,即觀眾沉浸其中,一任情感隨之起伏。如同人在鏡中照見自己,觀眾在藝術作品中看到自己的“映像”(image)。資產階級戲劇,就是觀眾能一下子自發理解并完全沉浸其中的戲劇。
在薩特看來,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是將熟悉的東西變陌生(或者說符號無法完成表意過程),即讓一件藝術作品所表象的內容對觀眾而言完全成為客體(objet),以此來阻礙觀眾的自發理解,阻止參與(布萊希特稱之為“共鳴”)的發生,從而引導觀眾理解并引發他們的批判意識。陌生化就是要“呈現、解釋、讓觀眾評判,而不是讓觀眾參與”,如布萊希特本人所言,“阻止發生共鳴”,使觀眾“不理解”,“讓觀眾或迫使觀眾不僅對所演出的事件,而且對演出本身采取批判甚至反對的態度”。
薩特對資產階級戲劇的態度是兩面的。這些戲劇展現給觀眾的是映像,這不會給符號學的接受方式制造任何障礙。于是,一方面,觀眾沉浸于這些戲劇展現的情感之中,任憑演出的法力左右,完全失去自由;另一方面,只有映像(而非客體)“才能產生普遍化作用”,因為觀眾只有將臺上發生的事當作映像理解(對它進行符號化闡釋)時,才會把它普遍化。比如,觀眾只有理解了臺上的人物處在絕望狀態,才會由人物的絕望聯想到自己的絕望,進而聯想到時代的艱難。
薩特對布萊希特敘事劇的態度也有兩面。一方面,薩特認為布萊希特的陌生化對自發理解的阻礙不能維持,布萊希特并不能真正實現他的目的,因為“參與是戲劇深刻的本質”。觀眾的自發理解肯定會形成,因為理解必然隨著解釋而發生,一旦理解發生,完全的“客體”便不復存在,也因為布萊希特賦予自己的戲劇一個重要的社會歷史使命:“既要展現個體行動,也要展現構成個體行動的條件的社會行動,他要展現一切行為中的矛盾,同時也要展現產生這些矛盾的社會制度,所有這一切包含在一部戲劇中。”社會共同的條件既是戲中人的生存條件,也是觀眾的條件,如此,共情、參與和映像的發生便不可避免。世界不可能被完全陌生化,觀眾自發的符號化理解,也即對意義的尋求也不可能被消除。客體化只是認識過程的開始,最后一定是對映像的參與。另一方面,他認為若要對抗資產階級戲劇通過心理情感對觀眾的俘獲,就必須像布萊希特那樣造成一定程度的理解障礙,阻止觀眾切近的情感參與。戲劇中距離的存在應是絕對的,“不得低估該距離;從事戲劇工作,無論是作為作家、演員還是導演,都不應減少距離”,“戲劇的起源和意義是以一種絕對的距離、不可逾越的距離、將我與舞臺隔開的距離來呈現人類世界”。
資產階級戲劇追求幻覺沉浸,是純粹的映像;布萊希特的敘事劇追求完全的陌生化,想制造純粹的客體,只有兩方面結合,實現觀眾在映像和客體間的“遲疑”,才能取得戲劇的成功。薩特以百老匯的一出名劇為例來說明這一點。該劇在閣樓里上演,觀眾最初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已經入場,不認為這座閣樓、這些人和物是表意符號,而是將它們看作其自身,這就是費舍爾-李希特所說的物質性的凸顯和符號化解釋的消隱,也是布萊希特所說的陌生化和距離在發揮作用。但隨著演出的進行,觀眾逐漸明白這是演戲,于是發生了情感代入,由臺上人物的境況想到自己的心境,從而建立起兩者間的普遍關聯。
在薩特看來,京劇表演正契合了這種恰當的距離,因為觀眾只能憑人物的動作來理解人物和劇情:“所謂與人物有距離,意思是我們只能通過人物的動作了解人物,除他的動作外我們沒有別的方式了解他。”并且,距離最終不會影響理解的發生,“結果是:大家都看到了黑夜”,也明白了兩名打斗者之間由于誤解而生的敵意。這種介于資產階級戲劇和布萊希特敘事劇之間、客體與映像之間的戲劇,正是薩特提倡的“戲劇性戲劇”,是“既觸動情感也不忘理智”,在非幻象與幻象之間、疏離與沉浸之間的戲劇。這樣的演出既能引發足夠的陌生感(距離),也不會阻礙意義的呈現。面對中國戲曲,作為觀眾的薩特在觀看過程中恰好演繹了這個由客體到映像的過程,中國戲曲于是在薩特眼中呈現出了“戲劇性戲劇”的面貌,成為他支持自己戲劇觀的有力論據。
結 語
在薩特看來,中國戲曲是通過暗示性的姿勢既創造人物本質、也創造人物活動和生存環境的“情境劇”;是通過暗示減少特殊性,從而在最大程度上凝聚觀眾的“普遍性”戲劇;也是通過暗示造成觀眾與戲劇處于疏離與沉浸之間的“戲劇性戲劇”。原本已在審視和質疑法國戲劇狀況的薩特,在中國戲曲演出這面鏡子中看到了自己理想戲劇的樣子。
薩特通過“暗示”等動詞繼續思考著柏拉圖《理想國》留下的永恒問題:藝術、現實與真理的關系究竟如何?柏拉圖認為,戲劇是一切藝術中最具摹仿性的,因而也最易以假亂真蒙蔽人。盡管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為戲劇正名,指出戲劇的摹仿不是對現實畢肖的復制,歷史(現實)要變成詩(戲劇),須經情節的組織和編排,但是戲劇還是逐步墮入了瑣碎的日常經驗,有人將死刑犯當眾處死以展現耶穌受難,有人將生豬肉搬上舞臺。如果摹仿可分為理想化的摹仿和如實的摹仿,那么暗示其實與這兩種摹仿都不同,它是藝術、現實與真理的一種新關聯模式:一方面,能指被一定程度地凸顯出來,給符號表意的達成制造障礙;另一方面,最終的所指也不是某一實在物或某一理想化的模型,而是在觀眾心中喚起普遍概念。20世紀的戲劇人和理論家提出的“暗示”概念是對表意(所指)與風格(材質、能指)之間關系的權衡和思考。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中國戲曲的出現順應了西方戲劇內部正在醞釀的求新求變的渴望,為現代西方的戲劇理想提供了實例。
① 馬拉美認為戲劇應是舞蹈,因為舞蹈能將需要大段文字表達的東西暗示出來(Stéphane Mallarmé,,tome II,Paris:Gallimard,2003,p.171);雅里主張在《愚比王》()中使用標語牌,認為“標語牌的暗示性優于布景”(Alfred Jarry,,tome I,Paris:Gallimard,1972,p.1043);讓·莫雷阿斯認為龔古爾可被稱為象征主義者是因為其作品的“暗示性”(Jean Moréas,“Le Symbolisme”,https://berlol.net/chrono/chr1886a.htm);巴特認為舞臺應是“簡單、樸素、暗示性的,給觀眾想象的權力”(Roland Barthes,,Paris:Seuil,2002,p.119);阿皮亞稱物質現實不重要,暗示是舞臺藝術自由伸展的唯一基礎(Marie?Claude Hubert,,Malakoff:Armand Colin,2016,p.231);格洛托夫斯基將自己對演員表演的建議總結為“對暗示的特殊運用,旨在一種觀念造型(ideoplas?tic)的實現”(Jerzy Grotowski,,New York:Routledge,2002,p.38)。
②[71] Marie?Claude Hubert,,p.27,p.54.
③ 參見米利麗耶·戴特麗:《法國人對中國戲劇的認識》,孟華譯,《國外文學》1991年第2期;唐曉白:《二十世紀西方戲劇對中國戲曲的選擇策略》,《戲劇藝術》1999年第4期;Min Tian,,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8,pp.1-2。
④ Michel Contat,“Chronologie”,Jean?Paul Sartre,,Paris:Gallimard,2005,pp.XLVI-LVIII.薩特有關戲劇的演講、論文和訪談集《一種情境劇》()于1973首版,1992年再版。在兩個版本中,薩特觀看中國藝術代表團演出的年份均被誤寫為1956年(“note 15”,,Paris:Gallimard,1973,p.151;“note 15”,,Paris:Gallimard,1992,p.164)。
⑤ 1955年5月31日至7月3日,中國藝術代表團參加第二屆巴黎國際戲劇節活動,相關情況參見周麗娟編著:《中國戲曲藝術對外交流概覽(1949—2012)》,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178頁。關于首場演出的情況,參見張正貴、陸蕾采寫:《杜近芳口述實錄》,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6—98頁。據1955年6月3日《世界報》()的文章《京劇要來巴黎了……山坡與長城》(L’Opéra de Pékin doit passerà Paris...Rampe et grande muraille),這是中國劇團首次在法國劇場進行正式戲曲演出,但據林一、馬萱主編的《中國戲曲的跨文化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中國戲曲劇團走向歐美大約始于19世紀下半葉,1860年曾有中國戲曲劇團到巴黎為拿破侖三世演出。僅就20世紀而言,中國戲曲在法國劇場的首次正式演出是在1955年第二屆巴黎國際戲劇節上,程硯秋1932年赴歐考察期間并不曾在劇場演出(參見《程硯秋赴歐考察戲曲音樂報告書》,世界編譯館北平分館1933年版),而梅蘭芳1934年出訪法國也只與法國戲劇人有過探討和交流,并未演出(Cf.Charles Dullin,’,Paris:Gallimard,1969,pp.195-196)。
⑥ 西蒙娜·德·波伏瓦:《長征:中國紀行》,胡小躍譯,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264頁。
⑦⑧⑨???????????????[51][52][54][56][61][62][64][66][67][68][69] Jean?Paul Sartre,,Paris:Gallimard,1973,pp.86-87,p.310,p.132,p.227,p.81,p.118,p.86,p.86,p.131,pp.118-119,p.87,p.87,p.68,p.375,p.892,p.105,p.27,p.85,p.62,p.20,p.68,pp.61-62,p.118,p.105,p.113,p.105,p.28,p.113,p.29.
⑩ 參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編纂的在線詞典“évoquer”詞條,https://www.cnrtl.fr/definition/évoquer。
? https://www.cnrtl.fr/definition/suggérer.
?? 《梅耶荷德談話錄》,童道明編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77頁,第280頁。
? Charles Dullin,’,p.195.
? Jean Genet,,Paris:Gallimard,2002,p.815.
?? Simone de Beauvoir,’,Paris:Gallimard,1960,p.54,pp.202-203.
?“L’Opéra de PékinàSarah?Bernhardt”,,le 7 juin,1955.
? Paul Claudel,“Théatre”,’,http://fr.m.wikisource.org/wiki/Connaissance_de_l’Est/Théatre.
? 《杜近芳口述實錄》,第97頁。
? 在國內學界,該書的一個常見譯名為“演員的悖論”,本文選擇譯為“演員新解”的依據如下:在18世紀的詞典,如1762年的《法蘭西學院詞典》(’)中,paradoxe的含義是“針對常識提出的觀點,與常識相悖的觀點”(https://artflsrv03.uchicago.edu/philologic4/publicdicos/navigate/9/4798/?byte=2238994)。而通觀全書可知,狄德羅是要針對表演學上的陳舊觀念提出一種新主張,此處無“悖論”之意,故選擇“新解”一詞以突出“與普通觀點不同”之意。
? Jean?Paul Sartre,’,Paris:Nagel,1970,p.3.
? 克里斯汀·達伊格爾:《導讀薩特》,傅俊寧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5頁。
? Jean?Paul Sartre,,IX,Paris:Gallimard,1972,p.99.
?[53] Jean?Paul Sartre,’,Paris:Gallimard,p.64,p.113.
?[55] Roland Barthes,,Paris:Seuil,2015,p.20,pp.36-37.
? 根據《一種情境劇》的索引,布萊希特名字出現的次數遠多于其他人名。Cf.Jean?Paul Sartre,,p.376.
? Jan Knopf,,Stuttgart:J.B.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1980,S.392.
??[57][63] Bertolt Brecht,,Paris:Gallimard,2000,p.808,pp.808,809,p.803,pp.368,369,264.
? Patrice Pavis,,Malakoff:Armand Colin,2002,p.153.
? Bertolt Brecht,,p.808.在該文基礎上,布萊希特于次年寫成著名的《中國戲劇表演藝術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
? Patrice Pavis,,Villeneuve?d’Ascq: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2007,pp.64-65.
? Jean?Paul Sartre,,IV,pp.355-356.
?[60][70] Michel Contat,“Préface”,Jean?Paul Sartre,,pp.XI-XLIV,pp.XI-XLIV,pp.XI-XLIV.
[58] 尤金尼奧·巴爾巴、馮偉、張若男、王月:《戲劇人類學家眼中的中國戲曲——尤金尼奧·巴爾巴訪談錄》,《戲劇》2021年第4期。
[59] 艾利卡·費舍爾-李希特:《行為表演美學——關于演出的理論》,余匡復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0頁。
[65] Jean?Paul Sartre,,p.144.費舍爾-李希特也指出,即使在非符號學的接受過程中,也會不可避免地伴隨符號學的接受方式,雖然是“很有限度”的(《行為表演美學——關于演出的理論》,第18頁)。
[72] 自然主義戲劇代表人物安德烈·安托萬(AndréAntoine)的做法。
[73] Universalis電子百科全書“imitation”詞條,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imitation?esthet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