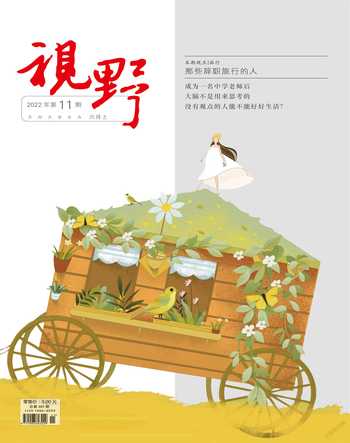古人是不是天一黑就睡覺?
張嵚

古時候沒有電,古人是不是天一黑就睡覺?
答:明朝嘉靖年間,造訪中國廣州的葡萄牙學者克路士,記錄了一幕奇特的“夜生活”場景:在“碰巧一個有月亮的夜”,他和幾個伙伴在河邊閑談,卻忽見一艘游艇駛來,游艇上的幾位廣州本地青年,正歡快地彈奏著各種樂器。同樣精通樂器的克路士見狀手癢,也加入到這群文藝青年的行列里,大家在歡快樂曲中,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以克路士本人的話說:“我是第一個有記錄的鑒賞中國音樂的歐洲人。”
這番經(jīng)歷,也被克路士寫進了他的《中國志》里,然后叫多人歐洲人看得眼熱——在同時代的西歐,人口幾萬人的城市,就已算是大型城市,日常商業(yè)活動比起中國來,自然冷清許多,更有嚴格的宵禁制度,“天一黑就睡覺”更是大多數(shù)人的常態(tài)。但在同時代的中國城市里,平民們卻已有了如此豐富的夜生活。
其實,對于中國古代大多數(shù)的老百姓來說,“夜生活”從來都是個遙遠的詞。就以農(nóng)村來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直是主要生活方式。從周朝開始,歷朝歷代的城市里,也執(zhí)行著嚴格的宵禁制度。只要夜幕降臨,城市里大街小巷就要封閉,別說出來過夜生活,就是隨便散個步,都有可能被辦罪。《三國志》里就把“夜行不休”當作大罪。東漢權(quán)閹蹇碩的叔父,只因晚上出了趟門,就被還是小官的曹操“即殺之”。
而到了唐朝初年,中國古代城市的宵禁制度,也一度嚴格到了極致。長安城里“鼓聲絕,則禁人行。曉鼓聲動,即聽行”。如果有人擅自上街,最輕的刑罰也是“笞二十”。諸如長安、洛陽這樣的“唐代巨型城市”,各市、坊、宮門、城門都有專人負責,幾乎層層設(shè)防。倘若有人擅自在夜晚開門,那就將“處徒刑二年”。《太平廣記》記載,盛唐天寶年間,有長安百姓宵禁后沒來得及歸家,為逃過懲罰,他只好躲在橋下對付了一宿。
如果那位記錄了“明代廣州文藝生活”的克路士先生,穿越到了宵禁嚴格的唐朝都城長安,那“夜里露天玩音樂”的后果,簡直閉著眼可以想。
不過,另外還要說明的是,別看宵禁森嚴,但古代統(tǒng)治階級的夜生活,從來熱鬧無比:比如達官貴人圈子里的夜晚飲宴,歷代都十分熱鬧。唐朝的宮廷內(nèi)宴,往往從下朝開始,到清晨才結(jié)束。明朝中期時,官員們就飲宴成風,為了方便官員們飲宴后歸家,明孝宗還特意命人在京城點燈,派侍衛(wèi)護送官員。清代中期時,由于官場腐敗,更是“無日不宴”,除了吃還要聽曲,一場宴會要幾天幾夜。對于古代“有錢人”來說,“天黑就睡覺”是不可能的。
但在那樣的年代里,普通老百姓的夜生活,一輩子里也難得幾次。比如唐代城市的宵禁,只是在上元節(jié)那天解禁。所以每年的這一晚,就是城市里最熱鬧的夜晚。這一天在唐朝也被稱為“放夜”,更是元宵節(jié)“開門燃燈”的好日子。長安城里“十萬人家火燭光”“羅綺滿街塵土香”,家家出來撒歡了玩。
隨著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這種森嚴的制度,在中晚唐時就遭到了沖擊,許多城市還有了夜市。到了宋朝年間,城市里的“市”“坊”被徹底打破,“夜生活”終于走向平民化:北宋都城汴京的酒肆瓦舍,幾乎是徹夜火爆。瓦舍里的“說唱”“雜耍”“雜劇”“相撲”等演出,每晚都惹得觀者如潮。特別是穿著很清涼的女子相撲比賽,把宋仁宗都招來與民同樂,氣得司馬光一頓大罵。另外還有大小夜市與酒樓,都是整夜熱鬧。“夜深燈火上樊樓”的詠嘆里,是多少宋朝人的夜生活記憶。
但這么熱鬧的“宋代夜生活”,卻也只局限在汴京、臨安等超大城市。明清時期的一大特點,就是夜生活范圍更大。從作為政治中心的南京、北京,到經(jīng)濟繁華的蘇州、杭州、廣州等地,乃至看上去比較“偏僻”的薊鎮(zhèn)、宣府等邊地,都有標志性的都市夜生活。尤其是經(jīng)濟相對落后的薊鎮(zhèn)、宣府等地,夜生活方面也“對標”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像薊鎮(zhèn)出現(xiàn)了“賽西湖”等娛樂場所,要熱鬧,就得像“一線城市”一樣。
而明代“都市夜生活”的方式,也比宋代更多元。像明清年間江浙等省的一些小城鎮(zhèn),都有“聚飲”的習慣。南京夜生活的焦點地區(qū),當屬秦淮河,每年端午時,市民們駕船在秦淮河上齊集,船上掛上燈火,號稱“燈船”。蘇州虎丘最熱鬧的時段,當屬每年八月半,從士大夫到平民,這天都會齊集虎丘。人們在夜里席地而坐,然后在登高望遠時呼號,還有鼓樂齊鳴。蘇州的山塘街夜市,云集店鋪上萬,唐伯虎就感慨“畫師應(yīng)道畫難工”——就算最高明的畫師,也難畫出山塘街的盛況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時火爆一時的“瓦舍”,明清年間卻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里的茶樓書場。拜當時發(fā)達的通俗文學所賜,以《三國》《水滸》《楊家將》等古典名著為藍本的評書,也在明清年間火爆一時,茶樓書場成了新的表演場所。
比如杭州城,據(jù)明代典籍記載,嘉靖年間時書場只有一兩所,很快就增加到五十多所。清代時杭州茶坊八十多所,“每茶坊皆有說書人”。許多說書場聽眾“常不下數(shù)百人”,表演時間通常是在晚上。明清的通俗文學與評書,就是這樣“互相刺激增長”。
對比夜生活比較豐富的城市,農(nóng)村的夜生活自然比較貧乏,不過隨著古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農(nóng)民們也有了享受夜生活的機會。即使是記錄了明末大亂的《豫變紀略》里也承認,明代承平時期,每到年尾時,普通的老農(nóng)也會穿上好衣服,去城里游樂赴宴,樂呵一整晚。《便民圖纂》記載,浙江農(nóng)村每年還有青苗會,勞累了一年的農(nóng)民在這天飲宴歌舞做樂。但要論明清年間農(nóng)民們最為期待的夜生活,卻還是賽社廟會。
在作為古代農(nóng)村祭祀節(jié)慶大日子的賽社廟會里,最讓農(nóng)民們期待的,就是文藝表演。明清年間的賽社廟會,節(jié)目已非常豐富,有雜技、百戲等項目,夜晚更有重頭戲——社戲。當時農(nóng)村的社戲,往往能吸引四里八鄉(xiāng)的上萬觀眾。《陶庵夢憶》記載,有一次山陰一個戲班唱了三天三夜社戲,上萬觀眾喊好,把地方官都嚇來了——誤以為是海寇偷襲。
而在每年這難得的夜生活里,也有許多鄉(xiāng)民只看戲還不過癮,還要登臺過癮。《陶庵夢憶》里的民間社戲,許多跑龍?zhí)椎亩际钱數(shù)剜l(xiāng)民。臺上臺下還常“互動”。清代戲曲家顧彩記載,一次有位樵夫跑來聽社戲,正趕上臺上演“秦檜害岳飛”,樵夫邊看邊氣,竟直接沖到臺上,把演秦檜的演員一頓暴打。吃瓜群眾們給他解釋說“這是假秦檜”,樵夫卻回答說:“我知道這是假的,要是真的,我就一斧子劈了他。”
雖然這讓人哭笑不得的一幕,顯然是荒唐了,但古代百姓的愛憎、辛勞,確確實實,濃縮其中。
(茅月從容摘自微信公眾號“朝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