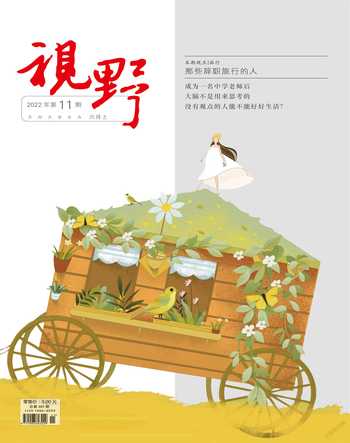快時代,慢讀書

文雯
最近,和一位00后小朋友談起讀書,他說在網上看到一個觀點,認為每個人都只能理解他已經理解的東西,既然如此,那讀書還有什么意義呢?
法國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早就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事實上,每個讀者都只能讀到已然存在于他內心的東西。”的確,所謂會心一笑,所謂共鳴與感動,其實都是在讀一本書的時候,穿越作者提供的文字,我們與自己的靈魂相遇了,我們看見了在日常生活中無暇照顧的那部分自我。
小朋友之所以感到困惑,在于他還沒有讀到普魯斯特緊接著補充的那段話,是這樣說的:“書籍只不過是一種光學儀器,作者將其提供給讀者,以便于他發現如果沒有這本書的幫助他就發現不了的東西。”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則在《哲學的慰藉》中進一步詮釋了這種感覺:“最好的書能清楚地闡明你長久以來,一直心有所感,卻從來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的那些東西。”
讀書的必要性之一,正在于此。閱讀是一個契機,讓我們從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有機會去凝神靜思,用心領悟,在那一刻豁然明朗,“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如果說書籍是一道風景,讀者只能辨認出其中熟悉的風景,不代表那些新鮮的、陌生的風景就沒有價值。閱讀是一扇窗一道門,帶領我們通往未知的疆域,拓展我們心靈的視野與想象的邊界,而這正是閱讀之所以令人著迷的另一大因素。
人類的好奇心與生俱來,讀書是滿足好奇心門檻最低的一件事。就像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小詩所寫:“何物帶咱去遠方/一只船不如一本書/就是千里馬也趕不上/一首歡快奔騰的詩/這種路最窮的人也能走/不會受通行稅的阻梗/這種車運載人的靈魂/它是多么節省”
“我知道讀書是必要的,但就是很難讀下去。”00后小朋友很誠實地拋出了自己的想法。在這個看視頻都恨不得要快進、倍速的時代,讀一本書確實太慢了。讀書的益處,也不能像游戲一樣給人及時的獎賞,它只是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們的氣質與思維。其實,每一個年代都自有它的快與慢。生而為人,置身世上,我們需要一份能與自身惰性相抗衡的自覺與堅韌。讀書,是升華智慧,是探索新知,也是自我修煉。
人生不過一場經歷,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都是人生的必需。在疫情肆虐的當下,行萬里路或成奢望,閑坐讀書亦是另一種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