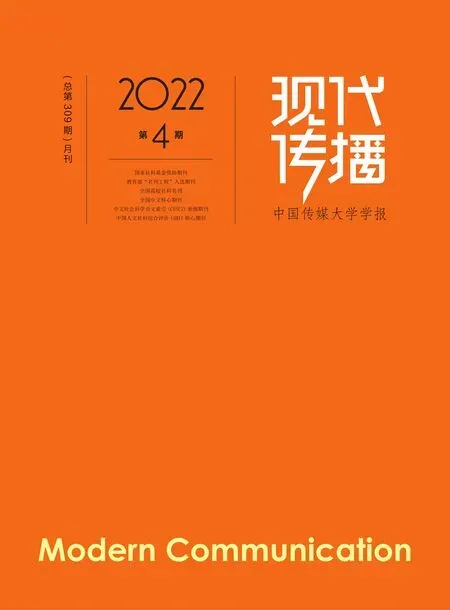未來已來:開放科學與定性研究
——對30位中國傳播學者的深度訪談*
徐敬宏 張如坤
一、引言
開放科學作為一種開放、創新、分享、協作的科學實踐,近五年來在人文社科領域受到廣泛關注,以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為代表的學科較早地對開放科學進行了研究和實踐。2020年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簡稱ICA)第70屆年會以“開放傳播”(Open Communication)為主題,將全球傳播學者的目光引向了開放科學,在傳播學領域掀起了開放科學的研究熱潮。
目前,全球傳播學對于開放科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量研究上,在定性研究上存在理論和實踐空白。由于在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問題上,我國傳播學沒有成熟的國外經驗可循,因此本研究擬與我國了解開放科學,并且具有豐富定性研究經驗的傳播學者展開深度訪談,就定性研究實施開放科學的重要性、可行性和必要性展開探討。
本研究的意義在于,從實踐層面看,開放傳播學的最終目標在于提升傳播學研究的科學水平、增進合作信任、促進知識創新,通過對我國定性傳播學者的深度訪談,探討并總結傳播學的定性研究進行開放科學的重要性、可行性和必要性,可以未雨綢繆,為未來我國傳播學推進開放科學、與國際接軌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一手經驗;從學理層面看,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定量研究如何進行開放科學上,對于定性研究的探討存在大量理論空白,本研究聚焦傳播學的定性研究,嘗試在學理上解釋并回應開放傳播學給定性研究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二、文獻綜述
(一)開放科學:內涵與研究進路
開放科學沒有統一的定義,目前學界廣為接受的定義來自歐盟“在地平線計劃中促進開放科學實踐”項目,其認為開放科學是一種科學實踐方式,“研究數據、實驗室筆記和研究過程等都應該免費獲得。通過互相合作,研究者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重新使用、再分配和復制”。①
從研究對象上看,開放科學有三大研究進路:(1)開放存取(Open Access),即公開獲取和免費下載已發表的研究,其目的是促進科研成果廣泛傳播,主要涉及出版過程;(2)開放數據(Open Data),即公開研究數據,如調查問卷和訪談記錄等,以便核查數據的真實性和供其他學者進行重復利用;(3)開放方法(Open Methodology),即公開研究方法和過程材料,如數據分析的代碼和文本分析的編碼表等,以便核查研究過程的嚴謹性。
三大研究進路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開放存取關注研究成果的最終出版或發表,類似于“黑盒測試”,研究者不必關注研究本身是如何進行的、是否符合科學規范,只需關注科研成果的傳播過程和效果;開放數據和開放方法深入到研究內部,從數據收集、數據處理到結果呈現,披露更多的研究細節和過程,類似于“白盒測試”,它允許外部研究人員回溯研究設計和邏輯推理,檢驗研究本身是否符合科學規范。開放存取的起源較早,相關的研究和實踐成果頗豐,近十年來,隨著開放科學的興起,學界研究的重心慢慢從開放存取轉向開放數據和開放方法,希望通過開放科學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應對學術的“復制危機”,進而搭建信任的橋梁。為了便于下文研究的展開,本文所指的開放科學也側重開放數據和開放方法。
開放科學是一個飽受爭議的話題,目前學界有支持和反對兩派觀點。支持者認為,開放科學不僅有助于提升科學研究的透明性、增強結果的可靠性,使數據收集和分析更加嚴謹,增進研究人員之間的信任,而且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現有的數據,減少數據的重復收集,把研究經費花在刀刃上,降低論文發表數量的同時提高論文的質量。反對者認為,開放科學會增加數據管理成本,帶來額外的法律和道德問題②,非但不能根除造假問題,反而會滋生“數據墳墓”“數據垃圾”和“數據寄生蟲”現象,加劇研究人員之間的不信任③。
(二)開放傳播學:動因及國內外進展
開放傳播學(Open Communication Science),顧名思義,即在傳播學領域進行開放科學實踐。有學者指出,不少發表在傳播學期刊和書籍中的研究未能清楚詳盡地記錄研究過程,這不僅影響了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展研究,阻礙了我們對于傳播過程的整體把握,甚至還限制了讀者們將傳播理論付諸實踐。④上述的研究模糊性對傳播學的發展具有消極影響,但影響更為惡劣的是傳播學內部深層的“暗箱操作”。2020年,《傳播學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刊登了《傳播學領域的開放科學議程》(An Agenda for Open Science in Communication)一文,該文由來自全球24家研究機構的37名傳播學者聯合署名。文中指出,在過去10年間,社會科學領域的許多權威發現并不可靠,傳播學同樣也存在嚴重問題,例如可疑操縱多(結論在前假設在后、P值操縱等)、出版偏見大(偏好陽性結果、忽視陰性結果或零結果)、可重復性低、統計效率低(平均效應估計值r偏小)、人為誤差大等。為了增強研究發現的可重復性、可復制性和普遍性,學者們急切呼吁在傳播學領域實施開放科學。⑤
目前,國外傳播學在開放科學上已經進行了初步探索,相關研究和實踐主要集中在定量研究上,強調數據的公開共享。除上述《傳播學刊》以外,《媒介心理學》(JournalofMediaPsychology)、《傳播研究報告》(CommunicationResearchReports)和《計算傳播研究》(ComputationalCommunicationResearch)等期刊也已經支持作者對定量研究進行預注冊、依據開放程度頒發開放科學徽章、接入第三方數據平臺進行數據共享。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簡稱OUP)為支持開放科學進程,將“提供學術論文的研究數據”納入其教育和學術使命,OUP旗下的學術期刊一律遵守TOP(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 Guidelines)準則。作者在投稿時必須接受OUP的數據可獲得性政策,從開放程度遞增的四個級別中選擇自己的開放級別,并在文末備注數據可獲得性聲明。此外,OUP還鼓勵作者通過公開的數據平臺(例如https://osf.io/)進行數據存檔以便數據分享和下載,并且將引用、使用公開數據納入參考文獻引用規范。
相比之下,我國對開放科學的研究起步較晚。2013年,我國人文社科領域開始出現關于開放科學的討論。近五年來,開放科學的研究數量飛速增長,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信息資源管理學科,如圖書、情報、檔案、出版等。2020年年底,我國出現了第一篇專門介紹開放科學與傳播學的中文文章。⑥
(三)開放傳播學與定性研究:實踐與理論空白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傳播學實證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二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從研究邏輯來看,定性研究屬于探索性研究,通過“后見之明”(postdiction)產生假設,這與定量研究通過預測(prediction)提出和檢驗假設的邏輯恰恰相反。⑦從數據收集特點來看,定性研究的數據收集具有內在的主體間性,其途徑包括深度訪談、焦點小組、觀察、視覺法、生活史和傳記,數據形式多為視頻、錄音帶、訪談指南、田野筆記和文字轉錄稿等。從數據分析方式來看,定性數據分析的方法有內容分析(定性)、案例研究、敘事、扎根理論、民族志、現象學等,在分析過程中會產生各種數據,如編碼員信度、編碼表、過程描述性文檔、代碼選擇和類目構建信息等,這些數據可以讓外部研究者了解作者是如何得出結論的。
一方面,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差異決定了二者的開放科學實踐不是步調一致的。從國內外開放科學現狀來看,定性研究明顯滯后于定量研究。但是,近年來,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也慢慢進入學者的視野。雖然目前高影響因子的期刊還很少要求定性研究像定量研究一樣嚴格遵循數據共享政策,但是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幾年,定性研究也一定會遇到有關數據共享的問題。目前,來自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已經探索出一些提升定性研究信效度的方案,例如驗證性的描述策略、評估編碼員間信度的量化策略、按比例降低損耗、報告檢查清單。⑧
另一方面,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差異也決定了二者在開放科學的適用條件和范圍上存在差異,不能簡單地將定量研究中的那套規則照搬到定性研究。目前,學者們對于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存在較大的觀點分歧。例如,在開放科學的重要環節之一——預注冊問題上,有學者指出,定性研究通常不檢驗假設,它的研究設計是靈活和主觀的,因而定性研究沒有必要像定量研究一樣進行預注冊;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定性研究進行預注冊可以靈活地跟蹤研究、檢查研究的主觀性,將預注冊與可驗證性審計(the confirmability audit)結合起來還可以提高定性研究的可信度,進而消除傳播偏見,激勵定性研究的學者持續報告自己的研究進展。⑨
到目前為止,傳播學領域專注于定性研究與開放科學的討論較少,有很多具體的問題亟待回答。例如在認識論層面,傳播學的定性研究進行開放科學的價值何在?在方法論層面,定性研究進行開放科學是否可行?在實踐層面,如何推進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進程?會面臨哪些潛在的道德和法律問題?帶著這些問題,本文就“開放科學與傳播學定性研究”這一話題,邀請國內傳播學者進行深度訪談。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及抽樣
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方法。深度訪談具有兩大特征,第一個特征是訪談問題是事先部分準備的,第二個特征是“要深入事實內部”。⑩由于目前國內傳播學領域的開放科學實踐剛剛起步,學者們對開放科學的了解不多,因此本研究決定采用滾雪球的抽樣方式,先隨機選擇一些對開放科學有所研究的資深學者并對其實施訪問,再請他們介紹另外一些了解開放科學的學者,根據所獲得的線索選擇此后的訪談對象。
(二)訪談對象
為了盡可能達到預期的訪談目標,本研究將上述抽樣框中的訪談對象進一步限定為:至少在傳播學領域的中英文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過一篇運用定性研究方法或混合研究方法的論文(或者專著的一章),且獲得了與傳播學相關的博士學位或長期在傳播學領域開展研究的學者。這些學者不僅具有豐富的定性研究經驗,而且也是未來定性研究進行開放科學實踐的重要參與者和直接受益者。經過篩選,最終的樣本包含30名訪談對象,訪談對象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訪談對象的性別、研究方向和身份

(續表)
(三)訪談方式及過程
受疫情影響,本研究于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10月31日,通過電話、微信和E-mail發送的方式,對30名傳播學者進行線上訪談,在獲得訪談對象的知情同意后,對訪談過程進行錄音或文字記錄。研究者首先向訪談對象詢問其基本信息(性別、最高學歷、工作單位、身份)和學術背景(論文發表經歷、研究興趣、擅長的定性研究方法),然后向符合篩選條件的訪談對象簡單介紹開放科學的概念和它在傳播學領域的進展,之后圍繞開放科學與傳播學定性研究這一主線進行訪談。訪談者根據訪談時的實際情況靈活地調整提問的方式和問題的順序,并根據訪談對象的研究背景展開個性化追問。
(四)數據分析方法
本研究借助“訊飛聽見”平臺將錄音資料逐字轉為文本,并由兩位作者進行核對和訂正,以保證機器轉錄的正確性。然后,將所有文本材料導入定性分析軟件NVivo進行編碼,編碼遵循主題分析的六步法,即熟悉材料、初步編碼、尋找主題、檢查主題、定義和命名主題、匯報成果。編碼由兩位作者共同完成,二者在協商的過程中達成一致意見,第一輪編碼采用開放式編碼來推導與研究目標相關的主題,隨后幾輪編碼進一步分析了主題的契合性和冗余度,直到得出明確的定義。
四、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重要性:開放定性研究的價值何在?
大部分訪談對象認為,在傳播學定性研究中進行開放科學是有價值的,這種價值主要體現在提升定性研究的透明性、給外部研究者啟發和靈感、為定性研究方法教學提供案例、豐富歷史研究和比較研究四個方面。
首先,訪談對象指出,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可以提升定性研究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使定性研究朝著更加規范的方向發展,增進傳播學者之間的信任。一位研究跨文化傳播的副教授指出,“定性研究常常被詬病于太過主觀隨意……中國的定性研究和思辨的界限往往是不清晰的,特別是數據分析過程不夠透明,例如文本是如何編碼的、主題是如何抽取的”。開放科學所倡導的公開、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對不規范的定性研究具有威懾作用,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會倒逼傳播學者小心翼翼地進行定性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呈現,使之更加科學嚴謹。
其次,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能幫助傳播學者從他人的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中汲取靈感,有助于集思廣益,“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開展研究。多位學者在訪談中指出,傳播學研究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學術對話和交流,學者們通過開放科學更清楚地看到前人研究了什么、是如何進行研究的,不僅可以從中獲取經驗,也可以發現以往研究的空白,進而使得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和科學。例如,一位研究計算傳播的副教授說:“雖然說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帶來的好處不會像量化那么大,但是對于年輕學者開闊視野,還是有好處的,不是說你看到了別人分享的定性數據,你立刻就能得出具體研究結論了,而是豐富你的想法。”
再次,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為開展研究方法教學提供了寶貴的案例。“中文傳播學文章中的定性研究方法和步驟是比較模糊的”,一位研究性別與傳播的博士生說,“如果有了開放數據和開放方法,我們可以更加細致地觀察別人是怎么從數據中提煉研究問題或者思想觀點的、是如何分析數據和呈現研究發現的,就好像以前我們是拍照,現在我們可以錄像,記錄整個研究的過程”。相比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教學案例偏少,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可以為傳播學教學提供豐富的二手資料,把優秀期刊上的論文案例引入課堂教學,系統地再現數據分析和觀點提煉的細節,開放科學所提供的完整的指導原則也使得定性研究有章可循。
最后,訪談對象認為定性研究的開放科學具有一定的歷史研究和比較研究價值。一位研究媒介史與傳播理論的教授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開放數據會慢慢過時,但是這對比較研究很有價值,它能使我們透過數據觀察媒介在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的演化……我覺得使用這些數據做研究的學者并不會給人留下壞印象,任何研究的價值都具有時間局限性,只要二手研究是嚴謹的和合乎道德的,它就具有學術價值”。
(二)可行性:開放定性研究是否可行?
雖然訪談對象對定性研究進行開放科學的意義給予了肯定,但是對于定性研究的驗證和定性數據的二次使用是否切實可行莫衷一是。悲觀者認為,在定性研究中實施開放科學面臨以下困難:數據的驗證、研究結論的復制、數據的重復利用。樂觀者則認為,不應拿著定量研究的標準苛求定性研究,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方法的改進,定性研究現階段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一些學者對驗證定性數據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開放科學不能根除定性數據造假的問題,定性數據通常是非數字形態的文圖聲像,數據體量大,且在數據收集過程中研究者自身的參與程度高,一些主觀因素較難控制。一位研究媒介技術與社會發展的講師認為,定性研究是真的還是假的,不是開放科學的問題,而是研究倫理和規范的問題,“如果你編碼的時候,就是偷懶的,或者是做了一些手腳,沒說的話你也編出來,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不對的……假設研究者是一門心思就造假的話,比如編造一些訪談,轉錄文字材料是看不出來的”。
還有一些學者對復制定性研究的結論是否有意義存疑。他們認為,定性研究的真實性無法依據研究是否可以被復制來衡量。例如,一位研究科技傳播的副教授質疑:“定性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如果公開數據的目的是核驗研究發現,那么不僅是文字轉錄稿,原始的錄音也需要提供,轉錄的過程也會導致解釋上的錯誤……如果把定性研究當成定量研究來評價,那就會毀了定性研究。”
有學者認為,即便復制定性研究有意義,現階段也缺乏具體可行的指導。一位研究媒介倫理的副教授指出,缺乏明確的規則會導致對定性數據的誤讀,“定性研究在本質上是主觀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相同的數據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只有限定好數據范圍,聚焦某個小切口的研究問題,才存在得出相同規律的可能性。在沒有一套規則的情況下,定性數據可以被自由地解釋,這樣一來就會出現問題,甚至導致扭曲和誤解”。
在定性數據的重復使用上,訪談對象指出,情境和“時新性”是具體實踐中的兩大障礙。一位研究傳播理論的副教授十分強調情境的重要性,她指出:“定性研究者往往選擇最能反映情境的方法……脫離情境,如何評價民族志和歷史敘事等定性研究?歷史檔案中的敘事是主要的還是次要的?在沒有書面記錄的情況下,和野外的陌生人進行的一段簡短對話如何闡釋?”此外,信息是瞬息萬變的,開放科學難以滿足傳播學學術研究的“時新性”要求,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以往研究中的二手數據可能缺乏解釋力。例如,一位研究方向為新媒體的博士生說:“由于數字化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傳媒業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定性數據被收集和公開共享時,它們可能已經過時了,再次利用這些數據是很困難的……如果一個媒體組織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怎么再去使用從那里收集的數據?”
樂觀者不否認定性研究的主觀性、迭代性和反身性給開放科學帶來了挑戰,但他們主張定性研究的這些特性可以轉化為開放科學的機遇,不能拿著定量研究的“尺子”衡量定性研究,在二次使用傳播學的定性數據時,具體選擇何種研究方法需要依據研究問題而定,因此在此基礎上得到的研究發現可能處在更高的通用層次,而不是原始的和重復的。一位智能傳播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表示,由于定性研究無法像定量研究一樣產出準確的結果,所以在開放科學的價值上,定性研究的好處往往被低估了,“一些人認為定性研究只適合表達意見或描述現象,所以他們更贊成定量研究,以為可以更客觀。事實上,定性研究進行開放科學的價值很大,這里面的潛力有待挖掘……近年來計算機技術的進步對收集、存儲和處理定性數據的幫助很大,定性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斷豐富,越來越客觀”。不少訪談者對二次使用定性數據充滿期待,例如一位專注理論研究的副教授說:“從本質上來說,我不認為在傳播研究中二次使用定性數據有天大的困難。實際上,反復分析這些定性數據反而能給我們帶來新的觀點和啟發。我們可以提出不同的研究問題,采用不同的方式編碼。所以,從某種程度上看,我們實際上從之前的研究或分析過的定性數據中得到更多的產出,這恰恰得益于定性研究的主觀性、迭代性和反身性。”
(三)必要性:開放定性研究如何推廣?
訪談對象對目前我國開放科學在定性研究方面的進展表示遺憾,他們指出,我國學者很少使用二手定性數據做研究,但實際上,二手定性數據也蘊藏著巨大的價值,只是現階段沒有得到充分挖掘,主要原因是參與度不夠,還未搭建出系統的架構。當談及是否有必要把開放科學作為傳播學定性研究的一種學術規范時,訪談對象的觀點呈現強制和自愿兩派。
一派觀點認為,有必要采取義務性或強制性舉措推進開放科學,特別是對于驗證研究結論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所必要的數據,作者僅僅匯報研究結果是不夠的,因為數據處理和分析過程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例如,一位研究健康傳播的副教授認為:“每位傳播學者都有義務采用一種強有力的、規范的研究方法,并遵循一套能夠確保數據報告公開透明的行為準則……任何形式的定性數據,只要得到許可,并且是研究人員可以合法獲取的數據,都應該公開共享。”
支持上述觀點的學者給出了兩大理由。第一,開放是科學研究的本質。這種特性不僅是為了克服偏見,也是為了提升科學自身的水準,只有當數據公開時,我們才能判斷數據是否有效、是否可靠,結論是否合理。數據應該是共享的,無論是定性的還是定量的,用“隱私保護”等作為借口來隱藏數據,理由是不充分的。特別是受到國家或者地方的社科基金資助的項目,更有義務向社會公開共享,這其中也包括大量未以論文形式公開發表的數據。例如,一位研究健康傳播的講師表示,因為這些數據“還沒有以報告、論文的形式發表”,所以外部研究人員不必束縛于他人的觀點,更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想象力,從多種角度開展探索研究,這樣文章的質量可以更高。除了鼓勵其他研究者表達他們的觀點外,這類數據還可以讓讀者獲得更充分的信息,更具有批判性,并且能夠在評估文章后自己作出意見判斷。
第二,開放科學的實現離不開每一個研究者的參與。在推進開放科學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是“木桶效應”,需要強制性的規范補足短板。例如,如果將提供數據作為提交同行評審或出版發表的可選項而不是必選項,那么就可能出現“濫竽充數”的現象,拉低傳播學整體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政治傳播的講師所述,要想讓開放科學成為一種文化,尤其是在定性研究中推進開放科學,“這絕對不是一個學者、一個部門所能做到的……我們需要一個更高水平的機構,如中華傳播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或者某種高校聯盟等來強制執行”,需要制定明確的規范機制,以確保開放科學的原則是大家相互同意和共同遵守的,這其中包括作者、期刊、高校和科研機構等。
另一派觀點認為,雖然開放科學對定性研究有益,但是數據開放共享不應該成為硬性規定,研究者可以自愿選擇是否公開研究數據以及公開哪些研究數據,特別是當定性數據本身包含敏感信息的時候。一位研究媒體政策與法規的講師認為,“與其說這是一個實際問題,不如說是一個教育問題……所有的研究人員在分享數據之前都應該考慮可能存在的倫理和法律問題”。
支持自愿原則的學者羅列了公開定性研究的三大問題。第一,身份識別問題。相比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研究問題本身帶有社會爭議性或敏感性,數據細節更為深入,夾雜更多有關個體身份特征的信息。因而,是否公開分享定性數據應該由研究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視情況而定,共享數據應該是自愿的,同時必須遵循基本的保密原則,保護隱私不受侵犯。一位深耕媒介社會學研究的教授指出,研究者只有在“不暴露采訪對象相關身份信息的情況下”才能公開定性數據的編碼,因為這些信息可能會使得其他人推斷出采訪對象的身份,甚至他們所在的群體的身份。一位研究新媒體傳播的博士生指出,有些數據本身就不適合分享,“個性化的內容、社會和政治敏感問題等,例如同性戀研究、政治迫害”。
第二,法律授權問題,主要涉及研究人員的知識產權和被采訪者的知情同意。一些學者認為,要求作者分享原始數據是不合理的,特別是“未以論文形式發表”的數據,這是對作者的勞動成果和知識產權的不尊重,會削弱研究者收集數據的積極性。一位研究視覺文化傳播的講師認為:“研究者可能在收集數據的若干時間后再次使用這些數據,而且作者有權保留這些數據僅用于自己的研究。”此外,訪談對象還指出,開放科學涉及對被訪者或觀察對象的更多的披露,他們出于信息保護的擔憂可能不會同意公開。
第三,數據安全問題,例如數據泄露和數據盜竊。一些學者對使用公開的定性數據從事不道德或非法行為表示擔憂。一位研究媒介使用與隱私保護的教授指出,目前,整個社會面臨著身份盜竊的問題,由于學術數據是由研究人員經過精心設計和收集整理的,因此數據更有條理、更系統,質量也更高,所以一旦面向社會開放,可能會吸引不法分子的注意。在他看來,存在安全問題隱患的數據分享應該“受到限制”,或者“至少應該等待較長的時間后再分享”,以確保定性數據的公開不會招致不良后果。
五、結論
本研究通過對30位從事傳播學定性研究的中國學者進行深度訪談,考察了在定性研究中進行開放科學實踐的重要性、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發現,訪談對象對開放科學總體持支持的態度,認為開放科學有助于提升傳播學定性研究的透明性和公開性,能給予外部研究者啟發和靈感,在為定性方法教學提供范本的同時,為歷史研究和比較研究開創了新的可能。同時,研究還發現,定性研究的獨特性使得其在開放科學的過程中存在數據驗證、復制和重復利用的困難,需要與定量研究區別對待,根據具體的研究問題和情境,恰當處理在數據共享環節上可能出現的身份識別、法律授權和數據安全問題。開放科學的實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項系統工程,離不開個人和社會的廣泛支持和參與。
此外,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采用滾雪球的抽樣方式選擇訪談對象,在樣本的代表性上具有一定的缺陷,后續研究可以采用全國性的更具代表性的樣本,來廣泛考察我國傳播學者對開放科學的認知和態度;第二,目前我國的開放傳播學還處于萌芽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本研究中訪談對象的觀點是對我國定性研究進行開放科學實踐的一種期待和想象,隨著開放科學實踐的深入發展,后續研究可以運用各種量化方法,印證本次訪談的觀點和結論。
注釋:
① Ivo Grigorov:OpenScienceDefinition,Foster,https://www.fosteropenscience.eu/learning/what-is-open-science/,2016.
② Abele-Brehm A.E.,Gollwitzer M.,Steinberg,U.AttitudesTowardOpenScienceandPublicDataSharingaSurveyAmongMembersoftheGermanPsychologicalSociety.Social Psychology,vol.50,no.4,2019.pp.252-260.
③ Cheah P.Y.,Tangseefa D.,Somsaman,A.PerceivedBenefits,Harms,andViewsAboutHowtoShareDataResponsibly:AQualitativeStudyofExperienceswithandAttitudesTowardDataSharingAmongResearchStaffandCommunityRepresentativesinThailand.Journal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Human Research Ethics,vol.10,no.3,2015.pp.278-289.
④ Lewis N.A.OpenCommunicationScience:APrimeronWhyandSomeRecommendationsforHow.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vol.14,no.2,2019.pp.71-82.
⑤ Dienlin T.,Johannes N.,Bowman N.D.,et al.AnAgendaforOpenSciencein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71,no.1,2021.pp.1-26.
⑥ 徐敬宏、張如坤:《邁向開放科學的傳播學:機遇、挑戰與未來》,《編輯之友》,2020年第12期,第76-84頁。
⑦ Nosek B.A.,Ebersole C.R.,Dehaven,A.C.ThePreregistrationRevolu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115,no.11,2018.pp.2600-2606.
⑧ Tsai A.C.,Kohrt B.A.,Matthews L.T.PromisesandPitfallsofDataSharinginQualitativeResearch.Soc Sci Med,vol.169,2016.pp.191-198.
⑨ Haven T.L.,Van Grootel,L.PreregisteringQualitativeResearch.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Policies and Quality Assurance,vol.26,no.3,2019.pp.229-244.
⑩ 楊善華、孫飛宇:《作為意義探究的深度訪談》,《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第53-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