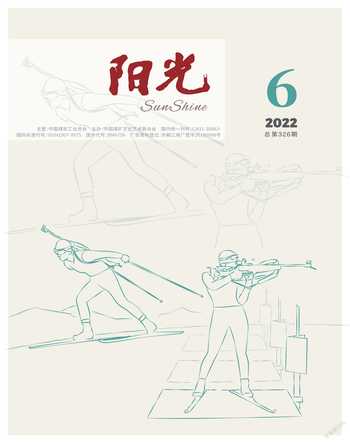獨秀山
還想跟從前一樣,一個人或約上一群人登上獨秀山的峰頂,不為別的,只為攀登。
我對獨秀山的好感最初源于山的名字。僅僅一個“獨”字,就能讓我心生無限的遐想。
獨秀山無所依附地聳立于大地之上,高傲地突兀于丘陵之中。獨立于群山,但又不遠離群山,這樣的山具有山的氣魄。后來我登上獨秀山,對于山之“秀”有了更深的了解,但也有些失望:和我看過的黃山、天柱山、泰山等聲名遠揚的山相比,獨秀山真是小巫見大巫。
據康熙《安慶府志》、民初《懷寧縣志》記述,獨秀山“西望如卓筆,北望如覆釜,為縣眾山之祖,無所依附,故稱獨秀”。又曰獨秀山“佇立峰頂,極目遠望,數百里潛桐懷大地,歷歷在目:遠眺東南,群山起伏如騰龍,江河奔流如走蛟;遙望西北,天柱聳崎刺蒼穹,丘陵崗地涌壯景;俯瞰腳下,井田畈田園風光綿繡,觀音洞水庫碧波蕩漾,風光四時變幻,美不勝收”。這番溢美之詞,讓我總感覺有些言過其實。我不知道這樣的記載算不算“敝帚自珍”?或者是一方文人為自個兒地盤上的山水貼金?姑且拋開家鄉的情結不說,對于美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許,他人眼中的獨秀山,就是一座巍峨秀美的山。
肉眼凡胎的我,登上獨秀山西望。第一眼看到的是黃墩鎮。黃墩鎮就在山腳下,站在高處,盡收眼底。那是一座沿著公路而建的小鎮,從地理位置上說,黃墩鎮是懷寧縣的中心。這里交通極為便利,在人口外流嚴重的當下,小鎮的商業氛圍依舊呈現出一派繁華,這是諸多內地小鎮所不具備的。站在獨秀山的山頂,我所能感受到的是這座山濃濃的煙火氣息,好像它就是陪同我長大的最親近的小伙伴,和我如影隨形。
待我對近現代的中國歷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我終于明白,獨秀山的名氣其實并不亞于眾多的名山,這當然與一位神州大地婦孺皆知的男人不無關聯,這個男人就是懷寧人陳獨秀。陳獨秀因山而得名,獨秀山因陳獨秀而出名。如果沒有陳獨秀,獨秀山就是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山。
陳獨秀,一八七九年出生于安徽省安慶市,名慶同,字仲甫。“慶”字是陳氏家族的輩分,“慶同”就是同慶的意思。“仲甫”是陳獨秀的字,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故稱“仲”。“甫”是對男子的美稱。早年,陳仲甫與友人登上家鄉的獨秀山,可能是登高望遠后感觸頗多,也可能是他切身感受到故鄉的山氣度不凡,他自號“獨秀山民”,后來連他的筆名也悄悄地改為了“獨秀”。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該刊就是后來聲名大噪的《新青年》。《新青年》的創刊,猶如黑暗長夜中閃出一堆耀眼的篝火,更像一聲地動山搖的春雷,驚醒了哀鴻遍野、死氣沉沉的中國大地。陳獨秀是想借此證明自己出類拔萃、非同凡響嗎?當然不是!他在行使自己作為炎黃子孫的使命擔當。《新青年》的創辦標志著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始。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始終沖鋒陷陣在最前沿。陳獨秀第一次在著名政論家章士釗辦的《甲寅》雜志上用筆名“獨秀”發表了一篇題為《愛國心與自覺心》的文章,此文的震撼力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過,“獨秀”這個筆名也因此遭到很多人的誤解和非議。有人據此認為陳獨秀自命不凡、自詡為“一枝獨秀”。就連他的同鄉好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看到這個筆名時也曾當面直言不諱地質問他:仲甫兄,你也太不謙虛了吧,這完全是目中無人呀。你以為這世上只有你才是奇才,“一枝獨秀”?陳獨秀聽后,趕忙解釋說家鄉懷寧縣有一座山叫獨秀山,小時候經常在那兒玩兒,因為非常喜歡那座山,便用了山的名字作為他的名字,只不過想表明他是獨秀山下的一介草民而已,實在沒有別的意思。
當年登上獨秀山的仲甫先生向山的四周遠眺的時候,又看到了些什么呢?除了窮山惡水便是滿目瘡痍。也許,在他看來,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處處山水都應該像他置身其中的獨秀山那樣綺麗多姿才對。為了達成這個心愿,他的肩頭自然沉甸甸的。
幾年前,在安慶近郊的獨秀園中漫步,我忽然心生疑惑,對于家鄉魂牽夢繞的陳獨秀,他的靈骨從四川江津遷回后,為何不安葬于獨秀山?若如此,山與人也便合二為一了。獨秀山中有獨秀,山獨秀,人更秀。豈不更好?
現今的獨秀山,被打造成了一個孩子們放飛童年的公園,山中有不少好玩兒的游樂項目。孩子是祖國的未來,為了孩子著想,這個出發點是錯不了的。只是我對于這場突然的改變,一時還難以接受。
深秋的一日,我獨自一人再次登上獨秀山頂,環顧四野,遠處的山川河流、村莊屋舍都在靜謐中呈現出一派國泰民安的景象。與陳獨秀生活的時代相比,中華大地已經發生了巨變,仲甫先生等先輩們為之奮斗的理想已成為現實。他們的在天之靈一定會為此感到欣慰的。年輕的仲甫先生可能曾經聽到過獨秀山的心跳,而此時身在獨秀山中的我也聽到了獨秀山的心跳。愿日月同輝,山河秀美!
范方啟: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曾在《江河文學》《四川文學》《人民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發表散文、小說;有作品被《散文選刊》選載;出版書籍三本,其中散文集《生命是一次美麗燃燒》被教育部推薦為中小學圖書館核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