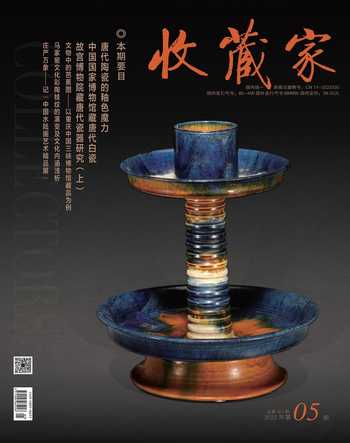長沙窯彩瓷裝飾剪影
郭三娟



長沙窯址位于今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銅官鎮至石渚湖一帶的湘江東岸,安史之亂以后逐漸發展,晚唐時期達到鼎盛,五代逐漸衰落。長沙窯瓷器素以彩飾著稱,據統計長沙窯施彩器物多達41%。①從長沙窯彩瓷的裝飾特征來講,在釉色方面,目前發現最大宗的產品為青釉,此外還見有白釉、綠釉、黑釉、銅紅釉等多種釉色;在技法方面,見有彩料彩釉繪畫、模印貼花、印花、劃花等各類工藝。豐富的釉色與多樣的技法,塑造了長沙窯瓷器裝飾富于變化、張力較強的藝術特點。
在唐代以青、白為主要瓷器釉色的大背景之下,長沙窯另辟蹊徑,開拓出以民間喜聞樂見的紋飾為主要裝飾題材的彩瓷體系,具有明確創作意義的文字題材是其很有自身特色的一類產品。長沙窯以褐色彩料或彩釉進行文字書寫的器類,多為青釉,見有執壺、罐、碗、盞、盒、枕等多種器類,題材有詩文、民間習俗、處世哲理、廣告題記等,涉獵內容廣泛,字體多樣,始開大規模以文字點綴瓷器之先河,在折射其銷售思路之靈活的同時,也反映了民間藝術的繁榮。
如青釉褐彩“客來莫直入”詩文壺(圖1),其短流的下方以褐彩書“客來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門三五下,自有出來人”,內容講述主客關系,強調了到別人家拜訪時應遵循先敲門而后人的禮節。在書寫上字里行間流露出任意揮運之氣,瀟灑自如。長沙窯此類勸善、強調禮節規范的詩文內容比較多見,類似的還有“仁義禮智信”(圖2)、“來時為作客,去后不身陳。無物將為信,留語贈主人”、“凡人莫偷盜,行坐飽酒食。不用說東西,汝亦自絳直”、“衣裳不知潔,人前滿面羞。行時無風采,坐在下行頭”等等,從不同角度勸人向善向美,強調日常社交的禮儀規范、德行修養,是唐代民間教化的真實載體,反映了傳統社會人際交往的普遍原則。青釉褐彩“寒食元無火”詩文壺(圖3),在短流的下方以褐彩書詩文一首,內容為“寒食元無火,青松自有煙。鳥啼新上柳,人拜古墳前”,筆法飄逸,藏頭舒足,強調意蘊,書寫內容反映了唐代寒食、清明節掃墓的習俗。長沙窯將題寫傳統節日習俗作為其裝飾內容的一種,除了民間情感的表達之外,也是一種極富營銷性的商業行為,借民間對傳統節日的重視程度激發其對節日衍生品的購買欲。
在廣告題記方面,長沙窯的品牌宣揚更為強烈,如青釉褐彩“陳家美春酒”題記壺(圖4),以褐綠彩書“陳家美春酒”5字,文字從右至左書排列于短流之下,按照2-1-2的字數模式縱向排列,這也是長沙窯書寫5字銘文類型短流執壺的普遍裝飾手法。題記內容為酒家品牌宣傳之用,點明了此壺的功用為酒具,作分酒、注酒之用,酒的廠家是陳家,品種是春酒。青釉褐彩“絕上”執壺(圖5),則采用一種更直白簡短的書寫方式裝飾于短流之下,以宣揚其產品質量和檔次。
長沙窯彩瓷上也見有大量的繪畫類圖案,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包括花卉、果實、草葉、樹木等植物紋,鳥、鹿、羊、獅、魚、蟲、摩羯、龍等動物紋,童子、仕女、老者、高士、胡人等人物紋以及茅廬、佛塔、山巒、云紋、水波、阿拉伯文字②、聯珠以及寫意圖形等其他紋飾。繪畫風格有精細有粗放,有具象有寫意,裝飾色彩多變。
湖南省博物館藏青釉褐彩臥獅紋執壺(圖6)和飛鳳紋執壺(圖7)是長沙窯精細繪畫的代表,兩者均采用白描手法以褐彩描繪臥伏的雄獅和奮翼的鳳凰,線條細膩流暢,筆觸生動,飛鳳紋執壺在鳳紋旁還書有“飛鳳”二字。以彩繪于瓷上,以瓷作新的繪畫載體,也體現了畫師嫻熟的繪畫技法。長沙窯還存在一種以褐彩與綠彩相互結合刻畫紋飾的手法,兩種色彩或相間使用,或配合使用,一粗一細進行輪廓描繪和細節展現,畫風通常比較粗獷。以湖南省博物館藏青釉褐綠彩鳳紋執壺(圖8)為例,其以褐彩勾勒鳳鳥大致輪廓,包括眼睛、羽翼、尾巴、雙足等主要部位,以綠彩在輪廓外圍進行渲染,刻畫出一幅惟妙惟肖的飛鳳圖,形成與白描飛鳳迥然不同的裝飾風格。青釉褐綠彩蓮花紋執壺(圖9),亦以褐彩、綠彩進行繪畫組合,以綠彩繪蓮枝大致輪廓,以褐彩繪花瓣蓮葉的筋葉脈絡,寥寥數筆,蓮花形象赫然于瓷上,別有韻味。
寫意類圖案裝飾,是長沙窯彩瓷中相對有特色的一類,常見白釉綠彩、白釉紅綠彩、青釉褐彩等種類,這些裝飾多為釉上彩,即在底釉之上施一種或多種彩釉,入窯一次性燒成。隨意而靈動的線條裝飾,不拘泥于形式,與底釉相互呼應,頗有美感。青釉褐彩裝飾以青釉為底,再施褐釉,褐釉自然流淌于青釉之上,呈現出不規則的、自由而奔放的寫意紋飾,以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青釉褐彩執壺(圖10)最為典型,青、褐兩種色彩對比極大,也形成了一定的視覺反差。白釉綠彩裝飾以乳濁白釉為底,再繪以綠釉(圖11),因釉料的厚薄、燒成氛圍等因素,也會有紅綠彩的呈色(圖12),飄逸的綠彩或紅綠彩與沉穩樸素的白色底釉相映成趣,頗有藝術色彩。
除單純地以彩繪于器表之上,長沙窯還見有一種模印貼花與彩釉相結合的裝飾手法。模印貼花是先以瓷泥或其他材質制好裝飾所需紋樣的陰文模具,然后利用模具用上好瓷泥印出花紋薄片,取出后粘貼于制好的瓷坯之上,一般貼在執壺、罐、缽等器物較為醒目的腹部或肩部,施青釉后在貼片部位,往往還會涂一層褐斑。模印貼花是西亞地區陶器和玻璃器常見的裝飾手法,中原地區鞏義窯唐三彩模印貼花的產生可能與此相關,又對長沙窯貼花裝飾產生了重要影響。長沙窯的貼花裝飾題材,涉及對鳥、菩提樹、椰棗、坐獅、走獅、胡旋舞及相關奏樂等多個方面,具有濃郁的西亞文化色彩。1973年衡陽市水井出土的青釉褐斑模印貼花胡人樂舞壺(圖13)便是其中代表,其所貼塑一胡人扭動身軀,婆娑起舞,另一人側身奏樂,貼片處另施加褐斑,與貼塑紋飾相映襯,形成較強的畫面感。長沙窯瓷器上的胡人樂舞裝飾中,常見起舞于圓毯或方毯上的胡人舞者,其縱橫騰踏,左右旋轉,舞者兩側往往還有一吹笛或拍板的奏樂者,幾組裝飾形成一個小型樂舞隊,舞者踩著拍板節拍旋舞,極具觀賞性。
長沙窯吸收多元的文化因素進行彩瓷裝飾,打開了更廣闊的銷售市場,通過揚州、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口,外銷到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及北非等地區,在9世紀掀起了中國瓷器外銷的第一股浪潮,其龐大的外銷規模,也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聯珠紋在長沙窯彩瓷上的運用比較廣泛,以其組成的幾何形、動植物圖案在薩珊波斯、粟特金銀器、玻璃器及織物中屢見不鮮,為西亞、中亞地區的主要裝飾紋樣。隨著西亞、中亞地區金銀器、玻璃器等器物大量輸入中土,聯珠紋也逐漸為中原所吸收。長沙窯瓷器大量借鑒這一裝飾紋樣,并加以創造性發揮,多以褐、綠兩彩點綴為聯珠紋,相間使用,組成各式圖案,紋樣精美者以湖南省博物館藏聯珠紋執壺(圖14)和揚州博物館藏聯珠紋蓮花云雙系罐(圖15)為代表,兩件器物均采用褐彩、綠彩聯珠紋分別組合為山巒紋、蓮花云紋,滿飾于器身,構圖飽滿,色彩對比較強。1980年揚州市東風磚廠肖家山工地唐墓出土的青釉綠彩阿拉伯文扁壺(圖16),壺身肩部、下腹部兩側各置對稱扁橫系,為背水穿帶用。通體施青綠釉,腹部一面繪綠彩長腳卷云紋,一面綠彩書阿拉伯文“真主最偉大”(漢譯),具有濃郁的伊斯蘭風格。在瓷器上用阿拉伯文書寫經文是伊斯蘭陶器的一個顯著特點,既有裝飾效果又有宗教內涵。中晚唐時期,伊斯蘭教在中國已經有了較為廣泛的傳播,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有眾多的阿拉伯人活動。長沙窯窯工學習阿拉伯文裝飾器物,也反映了其為滿足域外消費者需求所做的努力。
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發現一艘唐代寶歷二年(826)“黑石號”沉船,打撈上來的商品包括成套的銅、鐵和鉛器,以及玻璃器、漆器、香料和67000多件陶瓷器等,代表了中國瓷器外銷的第一個高峰。“黑石號”出水長沙窯陶瓷多達56500件,以青釉彩繪碗為大宗產品。這類碗有大、中、小三種,大者口徑達20厘米,中者口徑為15厘米左右,小者口徑在6.4厘米左右,小碗往往在口緣內外飾四塊對稱褐斑,此類裝飾的碗常作為外銷產品。碗內紋飾利用褐綠彩相間描繪,所繪題材包括各種花卉(圖17)、飛鳥(圖18)、云氣(圖19)、摩羯、帆船、西亞人物、文字等。“黑石號”出水瓷器中繪有大量的云氣紋圖案,與中國傳統云氣紋在構圖上不大相同,同類紋飾也有人認為是阿拉伯文,不易識讀,或為唐代畫師摹寫時產生了誤讀,使得文字失去了可讀性,這種操作上的失誤反而使得原本表達宗教含義的阿拉伯文成為長沙窯瓷器上的裝飾新樣。
長沙窯彩瓷既保留了中國本土內斂含蓄的裝飾特點,也兼容了奔放熱烈的異域風格,它像文化傳遞的信使,收納聯結了多元的中西文化風格,也傳遞出文明互鑒下的燦爛色彩,留下了輝煌絢麗的大唐雄風。
注釋:
①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長沙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6,第106頁。
②李建毛《長沙窯瓷上繪畫的起源》,載李建毛主編《長沙窯繪畫》,湖南美術出版社,2018,第16頁。74F75F46-7DDC-4D00-AB14-D6C94A0FFE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