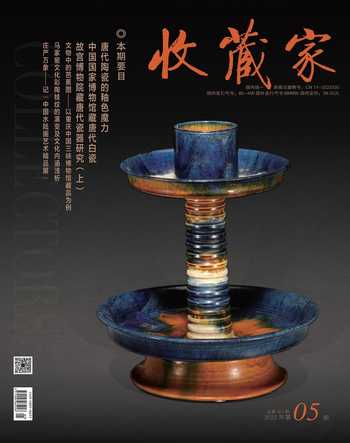馬家窯文化彩陶蛙紋的演變及文化內涵淺析
王嘉雯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以絢爛多姿的彩陶最具代表,其紋飾種類繁多,主要包括幾何紋飾和動物紋飾兩大類。其中,動物紋飾頗受歡迎,不僅因為圖案形象取材于現實,貼近人們的生活,更是反映了遠古先民豐富的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和文化觀念。特別是彩陶紋飾中的蛙紋,造型多樣,文化蘊意深厚。
一、蛙紋的產生
蛙紋是彩陶上一種常見的紋飾,早期的蛙紋飾較為寫實,像兒童的簡筆畫,比較稚拙,它的形象來源于自然界的動物——蛙。蛙是一種兩棲動物,常出現在有水的地方,它的叫聲響亮,彈跳出眾,是水中的“精靈”。如此靈動的生物為何會被繪制于陶器上?這大概與先民們的生產生活有關。遠古先民喜逐水而居,食蝦捕魚,河水中豐富的水產資源是他們主要的物質來源之一。日常的生產生活使他們與魚、蛙等水生動物長期接觸,因而對這些動物的形象印象深刻。當制作彩陶時,先民們自然而然地便把頭腦中已有的圖案形象作為了裝飾紋樣繪制于陶器上。
另一種說法是蛙紋的產生源于蛙的叫聲與陶器的剮蹭聲相似①。蛙可以發出“哇”的聲音,劃蹭陶器會發出類似“嘎哇”的聲響,由于聲音的響動引起了古人的關注,借助相似的聲響先民們可能便把蛙和陶器不假思索地聯系在一起,使蛙成為陶器上不可或缺的圖案紋飾。而且,在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蟲鳴蛙唱,熱鬧的氛圍能夠帶給人們希望,因此,蛙的形象寄托了先民們祈求物質豐裕、吉祥順遂的美好愿望。
二、蛙紋的演變過程
目前,蛙紋最早發現于仰韶文化彩陶器上,在陜西臨潼姜寨聚落遺址、陜西西鄉縣何家灣遺址、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中均出土了帶有蛙紋的陶器。仰韶文化半坡期與廟底溝期蛙紋形態稍顯不同,半坡期繪畫更加寫實、樸素、自然,蛙背紋理呈不規則點狀,圓點大小不一、形態各異,蛙體四肢張開,略顯動勢(圖1)。而廟底溝期蛙紋繪制雖仍為寫實風格,但開始講究規則,蛙背紋理較有序,背點形態規矩統一,蛙體動勢所剩無幾②。
馬家窯文化時期,在陶器內壁和外壁上均發現有蛙紋裝飾,其表現形式多樣。早期的馬家窯類型蛙紋,繪制于器外壁者較多,形態在寫實的基礎上有所簡化,逐漸趨向于抽象化③。也有學者認為馬家窯類型時期蛙紋仍為寫實的表現手法所繪④。在筆者看來,每個文化類型時期紋飾的特點都是在繼承之前紋飾特征風格的基礎上,加上當時人們新的認知和審美傾向發展而來的,具有與之前紋飾不同的特征風格和時代風貌。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彩陶蛙紋在繼承了仰韶文化彩陶蛙紋特征的基礎上得到發展,不僅紋樣更加簡單,而且出現了變形蛙紋和蝌蚪紋。
變體蛙紋壺(圖2),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屬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約前3000~前2700),高27.5、口徑13、腹徑26.5、底徑10.8厘米,此壺以濃重的黑彩生動地描繪了蛙肥碩的形象。蛙凸顯的雙眼,圓滾滾的身體,給人以圓潤笨拙之感。簡單的黑色線條在陶器本色的襯托下,勾勒出蛙夸張肥大的樣子,增添了畫面的質樸感和趣味性,表現了這一時期原始先民的生活情趣和藝術表現力。
漩渦蛙紋內彩盆(圖3、圖4),現藏于蘭州市博物館,屬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高12.5、口徑25、底徑9.5厘米,蛙紋黑彩繪于盆底內壁中央,圖案省略了蛙的頭部,只表現出軀體和四肢,蛙體以黑色菱形方塊表示,四肢伸展,呈跳躍姿態,頗具動感。雖然只用寥寥數筆繪制而成,但仍具有質樸的寫實主義風格,蛙的形態活潑生動,紋飾造型富有創造性。
連身變體蛙紋內彩盆(圖5),現藏于蘭州市博物館,屬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高10.7、口徑27.4、底徑10厘米,盆內壁以三條黑線作圓表示軀體,上下兩條圓形黑線外側繪有多條弧線表示肢體,對此圖案指代的具體事物說法眾多,如:連身變體蛙、蜥蜴、浪花、千足蟲等。紋飾圖案雖繪制簡單,但其表現形式帶有神秘色彩,可能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蛙紋與之前蛙紋相比有了明顯的不同,紋飾既體現了蛙的特點又表現出人的特征,可謂是蛙人合體,充滿了濃郁神秘的宗教色彩。正是由于其紋飾獨具風格的形態,學者們對其命名爭論不已。有些學者認為此紋飾蛙的特征鮮明,是在馬家窯類型蛙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還應稱其為“蛙紋”;也有學者認為此紋飾帶有人的屬性,應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如還將其稱為“蛙紋”不符合紋飾的形象特征,因此特定為“神人紋”;還有學者考慮到此紋飾蛙人兼具的特征風貌,采取折中的辦法,將其定名為“神人式的蛙紋”或“蛙人紋”⑤。筆者認為,此紋飾是蛙的特殊演變形式,與仰韶文化的人面魚紋⑥(圖6)有異曲同工之效,選擇將其稱為“變體蛙紋”“人形蛙紋”或“蛙人紋”可能更為貼切。
半山類型時期還出現了蛙紋作為人像輔助性紋飾的現象,如青海樂都柳灣出土的裸體浮雕彩陶壺(圖7),壺上裸體人像胸部豐滿,下方塑造了夸張的男性生殖器,兩腿外側黑彩繪有蛙紋,壺的背部也繪了蛙的形象(圖8),這樣的藝術表現手法表明陶壺的組合紋飾具有特別的涵義。有學者認為人蛙組合源于社會性質的轉變,是男性生殖崇拜的反映⑦;也有學者認為當時為母系氏族社會,女性占主導地位,屬女性崇拜,與蛙搭配,應跟生殖崇拜相關,表達了當時人們對人口繁盛、子嗣綿延的向往與祈盼⑧。筆者認同該時期為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轉變的過渡時期,男性社會地位逐漸提高,女性地位逐漸降低或趨于男女地位平等階段。裸體浮雕彩陶壺上刻畫得人像為男女同體,從側面印證了當時男女的社會地位及各自的重要性。男、女生殖器官的突出表現輔以表示多子的蛙紋,反映了原始先民具有生殖崇拜的意識和思想。還有一種說法為裸體人像被視作兩性人,與遠古時期的薩滿教有關,代表了溝通天地人神的巫師形象,而蛙紋的繪制體現了巫師作法時可能需要借助青蛙附體⑨。
馬家窯文化晚期的馬廠類型蛙紋除繼承了半山類型蛙紋的特點之外,還發展出了一種蛙紋的特殊簡化形式——“肢爪紋”,以此突顯了蛙腿在遠古人類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蛙彈跳有力的四肢,是古人無法企及的,它所代表的非凡能力,帶給人們無限的遐想。94F0A381-21DF-4785-BBDB-0F33F1B792B4
變體神人紋罐(圖9、圖10),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屬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約前2300~前2000),高44、口徑13、腹徑19.8、底徑11厘米,罐頸腹之間突出的組合紋飾為對稱繪制的肢爪紋和圓圈紋,每組肢爪紋由三排組成,每排紋飾形制相同,長短逐排增加,似乎有向外延展的趨勢,代表了遠古人類期盼擁有的無窮力量。
菱格條帶神人紋壺(圖11),現藏于秦安縣博物館,屬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高25.4、口徑11.7、腹徑24、底徑10厘米,中心圖案用簡單的線條勾勒出人蛙形象,周圍的黑色雙層鏤空格帶體現了古人的巧思,具有特殊的寓意,可能象征蛙的卵帶,人形下方的圓圈代表了女性生殖器官。上述紋飾特征表明,彩陶的裝飾圖案是對原始時期生殖崇拜的反映。⑩
神人紋壺(圖12),現藏于蘭州市博物館,屬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高30.5、口徑9.5、腹徑30.5、底徑11厘米,圖案以對稱方式繪制了人蛙形象和圓圈網格紋。神秘的人蛙造型省略了下肢,以頭身為中心,上肢呈“W”形姿勢,與半山類型蛙紋形貌相似,但又有所簡化,體現了時代發展所帶來的人類認知方式上的轉變和抽象思維能力的提高。
由此可見,蛙紋的發展經歷了仰韶時期的“具體化”階段,紋飾生動、質樸;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的“簡化”階段,同時還出現了變體蛙紋形態;半山、馬廠類型的“擬人化”階段,此時紋飾具有人、蛙雙重特點,應與原始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圖13)。馬廠類型蛙紋與半山類型相較,更為簡化,出現了局部特征的紋飾圖案,如:肢爪紋、“半身”紋等,抽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圖14)。
三、蛙紋的文化內涵
蛙紋是我國傳統的動物紋飾之一,在彩陶裝飾紋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文化內涵深厚,意蘊深廣,反映了遠古先民原始的宗教信仰、豐富的精神世界以及具有時代思想的藝術表達方式。
(一)生殖崇拜
繁衍,是生命延續的途徑和方式,人類通過一代代的繁衍發展至今。原始時期,人類生產條件差,生活環境惡劣,致使嬰兒存活率低下,兒童夭折情況屢有發生。為了祈求子孫繁盛,瓜瓞綿綿,先民于是把目光放在擁有超凡生殖能力的動植物上,如:葫蘆、魚、蛙等,由此,蛙成為了遠古人類頂禮膜拜的對象。
從考古發現來看,蛙紋裝飾也與女性形象相搭配。上文提到的裸體浮雕彩陶壺上塑造了帶有明顯胸部特征和生殖器官的人像,并輔繪蛙紋,二者的巧妙結合應是先民的有意為之,反映了他們對生育繁衍的重視以及當時原始生殖崇拜觀念的盛行。
(二)圖騰崇拜
圖騰崇拜是一種古老的精神信仰,遠古時期,許多氏族部落都有屬于自己的圖騰文化,且多以動物形象作為圖騰,有的部落以蛇為圖騰,有的則以鳥為圖騰,還有以蛙為圖騰的。為何先民會選擇蛙作為圖騰呢?目前說法不一,常見的有三種解釋:其一,女媧說。女媧的“媧”與“蛙”同音,兩者可能存在某種特殊的關系。在某些學者看來媧即是蛙11,女媧由蛙發展而來,其所在部落以蛙為圖騰,奉蛙為先祖。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類型蛙紋的擬人化發展趨勢,印證了蛙已出現了人格化的特征,此時,蛙的形象指代的可能就是女媧。因此,根據上述說法所言,女媧族以蛙為圖騰便不足為奇了。
其二,蛙龍說。從自然界的蛙到仰韶、馬家窯文化的蛙紋,體現了事物具象到抽象的過程。從蛙紋到肢爪紋再到蛇形盤曲的蛙爪紋,可以探尋到龍的演變12。此種說法認為,蛙的部分特征是龍形象的重要構成元素,作為龍的原始雛形,蛙也是遠古人類信奉的對象,成為氏族部落的圖騰,代表了當時人們追求的信仰和精神。
其三,天黿說。“黽”是蛙的一種古老稱呼,黿是一種兩棲動物,也是古人崇拜敬畏之物,屬黽類。天黿為龜與蛙的復合體,是當時人們崇拜的神物,以它為圖騰,表達了先民期望部族勢力發展壯大,人丁興旺繁盛的美好愿望。有學者認為,龜蛙的這種復合形式是黃帝氏族的圖騰,之后發展成為華夏民族的族徽。13
(三)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形式,其對象涉及了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風雨雷電、石木水火、鳥獸蟲魚等,這些自然事物及自然現象對遠古人類的生產生活、思維認知、審美表達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古人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對時間的概念以太陽和月亮的走勢為準,因先民對日月交替現象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于是便產生了對日月的崇拜。在我國古代,蛙與月亮關系密切。《后漢書·天文志上》劉昭注引張衡《靈憲》中有“嫦娥遂托身于月,是為蟾蜍。”在河南洛陽西漢壁畫墓中和南陽東漢畫像石上,都刻畫了蟾蜍在月宮的場景;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帛畫上,一邊作日,一邊為月,日中有鳥,月中有蟾蜍,與典籍文獻《淮南子·精神訓》中“日中有俊鳥,而月中有蟾蜍”14相互印證,說明蛙確與月亮有關,可被視作月的“代言人”。
生活中,常見到蛙鳴雨至的自然現象,古典詩詞中多有描繪。如:北宋歐陽修《雨中獨酌二首·其二》中有“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有“雨積蛙鳴亂”;南宋陸游《露生》中有“蛙聲經雨狀”等詩句。蛙成為了雨的使者,通過其叫聲提醒人們雨的到來。此項“特殊功能”,也給蛙帶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被人們認為其具有預示未來的超常能力,從而便產生了崇拜、敬畏的心理。
(四)靈魂崇拜
自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開始就有“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遺址中發現隨葬有死者生前用過的物品。在古代先民眼里萬物皆有靈,人雖死,其靈魂還在,靈魂的觀念由來已久。
彩陶紋飾中的蛙紋作為一種圖案化的象征符號,表現了原始先民對生命的贊頌和對靈魂的崇敬。15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類型的“擬人化”蛙紋,突出了人與蛙的特點,有學者認為這種紋飾體現了原始宗教信仰中借助蛙作法的巫師形象,也可能反映了看不見、摸不著、無肉體、非人非蛙、非物質世界存在的靈魂模樣。不管是哪種解釋,都是人類內心活動的展示,表達了先民們希望通過與神靈溝通,得到神靈的指示,以保一世平安、萬世順遂。94F0A381-21DF-4785-BBDB-0F33F1B792B4
原始人類憑借自己對事物的認知,加上抽象化地再創造,把現實生活與虛幻的靈魂世界用繪畫的方式加以呈現,是古人精神信仰與審美藝術方面的巧妙結合,別具一格的彩陶紋飾內涵豐富,值得后人用心體會。
四、結語
馬家窯文化彩陶紋飾是原始藝術表現形式之一,其絢麗的色彩、悠遠的意境增添了畫面的審美趣味和文化涵義。彩陶紋飾的創造在現實與虛幻、具體與抽象、人類與神靈間轉換,體現了先民對事物的感知、對生活的思考,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其豐富的精神世界締造了遠古文化藝術的氣質與風采,延續千年,影響深遠。
蛙紋作為中國古代傳統的裝飾紋樣,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特別是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文化時期,紋飾特征鮮明,形象多樣,圖案逐漸簡化趨于抽象化,是遠古時期時代精神和文化風貌的具體呈現。這種含蓄的藝術表現手法是古代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他們通過認知、啟發、思考、藝術加工以及再創造,賦予了蛙紋新的內涵和價值,同時,也充實了古人的精神生活,并使原始崇拜、精神信仰和宗教文化與繪畫藝術相結合,構成了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民族文化,承載了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力量。原始彩陶藝術中的蛙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是人類共有的寶貴財富。
注釋:
①曹南、王俊杰《甘肅彩陶蛙紋的生態學解釋》,《絲綢之路》2020年第4期。
②朱盡暉《仰韶蛙紋藝術圖像考文化》,《西北美術》2005年第2期。
③王春法《國色初光——甘肅彩陶藝術》,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第260頁。
④⑤⑦段小強《馬家窯文化彩陶蛙形紋飾新解》,《蘭州學刊》2009年第9期。
⑥人面魚紋發現于陜西西安半坡遺址的陶盆上,稱陶盆為“人面魚紋彩陶盆”。盆內壁繪有人魚合體的圖案,具有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
⑧⑨中國國家博物館《文物里的古代中國·遠古至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第84~85頁。
⑩王春法《國色初光——甘肅彩陶藝術》,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第307頁。
11莊會秀《半山馬廠彩陶蛙人紋藝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12王志安、鄧宏海《世界視野中的馬家窯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第117~118頁。
13祁慶富《彩陶蛙紋之謎》,《中國民族博覽》1997年第2期。
14趙宗藝《淮南子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324頁。
15楊畬《彩陶蛙紋與靈魂崇拜》,《雪蓮》2010年第6期。94F0A381-21DF-4785-BBDB-0F33F1B792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