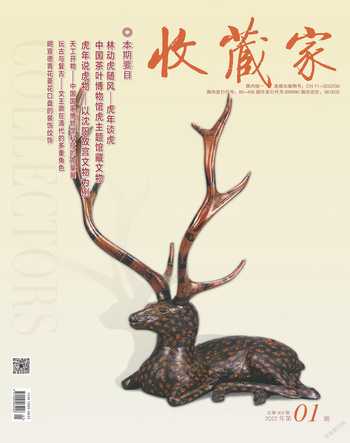商周十供中亞尊的審美意義探析
胡廣澤




清代乾隆皇帝賜給孔府10件商周古青銅器作為祭祀時所用的禮器,這10件古器物習稱“周十供”或“十供”①,后世通稱為“商周十供”。在商周十供之中,木鼎和亞尊是被認為尊貴的。在人類藝術史上,中國的先人們創造了絢爛多彩的青銅時代,如今考古和收藏等工作的開展讓我們能夠欣賞到足夠多的古代青銅藝術珍品,作為物品,古代青銅器帶給我們的是歷史與科學方面的參考,但在文明的長河中,一件備受尊重的器物也能傳遞給我們更多物品之外的信息。這些信息包含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等所帶來的審美觀念通過一些被特殊對待過的器物能夠展現出來。商周十供中樸實無華卻盎然燦爛的亞尊,正是能夠體現儒家文化視角下對于“美”的獨特追求與闡釋。
一、對亞尊的考析
1.是“亞尊”還是“亞弓觚”
根據亞尊的真實器物形制可以看到,它和古青銅尊形不太類似,和古青銅觚更類似一些。雖然后來文物部門工作人員將其定名為了“獸面紋觚”,但是“獸面紋觚”的名字不具備專指性,因為其他的有獸面紋的觚也可以叫這個名字。包括亞尊在內的商周十供被乾隆皇帝賜予給孔府,一并賜予的還有精制的圖冊和檀幾②。圖冊后來下落不明,但《曲阜縣志》是根據圖冊所記載的,亞尊在其中的在冊名字就是“周亞尊”。又因它銘文為“亞弓”,山東文物考古研究院又有“亞弓觚”的叫法?。為什么皇家會將形狀為觚的高規格器物命名為“尊”呢?而現今只是簡單的把它稱為“獸面紋觚”是不是也會不合適呢?這些都值得考證。現代根據對青銅器形的斷代了解,可以確定“亞尊”是商代的晚期的器物,而不是乾隆時期認為的“周器”。
“尊”的命名,由狹義之尊和廣義之尊的區別④。正如《殷周禮樂器考略》中所云:
自宋以來,名稱之混淆者莫尊也。有觶焉,有觚焉,有壺焉,有罍焉,大概以大小定之。余所見古器銘辭,無專著尊名一類。則尊乃共名而非專名。《匋齋吉金錄》所圖之杉禁,有卣二、尊二、盉一、觚一、斝一、爵一、角一、觶三,其尊二乃一觚一觶。為之改定,則與《特牲饋食禮》之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之數合,而缺一爵耳。尊之為觶、觚、壺、罍形者,歸為觶、觚、壺、罍。專名之尊,則以犧象諸尊當之。
據此可知,“亞尊”應為“亞弓觚”,但它為什么會存在名稱的錯位呢?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2.“亞”字的內涵
“亞”字是亞尊上的銘文。“亞”字圖形符號在先秦時期,具有著特別的文化含義,作為一種裝飾性質的圖案形式,反映著中國古人的普遍審美觀③。在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如亞尊中的“亞”字樣形體便是“亞”字輪廓的雙鉤線,有表示“祭祀之地”“宮殿建筑”的形意?。亞形所表示的廟室與族氏之間有著內在的密切關系。在商朝,祭祀和占卜可以參與甚至干預政事,可以說商代是一個神權和政權有機結合的政治形式。因此,“亞”字很可能就代表著是祭祀和上層政治的地位,而亞尊很可能就是在祭祀和政治(比如禮制)活動的用物。從而,亞尊也被祭祀、政治活動所賦予了一些精神、意識以及文化方面的信息,這是它精神及審美價值的重要基礎和體現。
《金石索》中對亞尊的說明有:
銘作亞,形又為弓,古者射必有飲,而亞則有廟室之義,意此為射宮飲器歟?《金石索》是依據《曲阜縣志》和乾隆商周十供圖冊的記載而收錄,也可以說明清代時,也有通過“亞”字來猜測亞尊的級別是不低的。李零認為,在商代“族氏銘文”中,凡帶“亞”的族氏大抵都表示該國與商王間的一種宗法關系?。商周時期,王室等貴族統治者做事繁縟復雜、規制頗多,亞尊的“亞”字銘文之下還有一個“弓”字。所以,清代之時認為此器物的本意是飲酒時演習射禮的用物。因此,通過銘文我們可以猜測乾隆皇帝把這樣的一件東西賜予代表著中國正統儒家文化的孔府時,就是對亞尊“亞弓”銘文所代表的文化信仰的推崇,也正是對孔子所倡導的恢復周禮等理念的贊同。
亞尊是一件觚,觚的存世雖然少,但觚確實是在金文之自有其字的。《金石索》也有“亞尊‘茲器狀如觚’與《宣和博古圖》等類書所記載類似”的看法。因此清人是明白亞尊其實是觚的,卻因為它的“亞弓”銘文,猜測它可能是祭祀和政治禮制中的用物,而將其改稱為“尊”。畢竟,在青銅器中,尊和觚是功能相近(盛酒)的器物,只不過是尊比較大一些。清代時,人們也有諧音避諱思想,觚與尊的音所代表的效果也截然不一樣的,而且亞尊和其他的十供是皇家送給學術道統代表孔府祭祀所用,因此才選定“亞尊”的名字。這只是一種猜測。
二、亞尊的造型藝術
皇家需要通過尊崇孔子的學術正統來獲得天下士民的認可與支持,選定的賜予孔府的祭祀禮器需要在政治、文化、禮制等多方面能夠足堪大任,亞尊的選定,與它的造型藝術所代表的更多的精神意義有關。
1.造型和紋飾
亞尊是觚的造型,喇叭敞口,兩段有紋飾處被腰部隔開,腰部有兩個十字的透孔。亞尊的敞口是光滑無棱無紋飾的,和著名的天觚不同。天觚敞口有4道三棱形棱脊,器物造型雖然更復雜,紋飾也更多,卻也變得更為“華麗”,與圣人之德不符。而亞尊卻能給人一種“雖古拙無華,莊正而典雅”的藝術美感。亞尊的紋飾分為上下兩段,均為典型的獸面紋。獸面紋舊稱饕餮紋。饕餮之名本于《呂氏春秋·先識覽》:“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宋代人將青銅器上表現獸的頭部,或以獸的頭部為主的紋飾都稱饕餮紋⑨。
商周青銅器的獸面紋飾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自然神的崇拜,散發著神秘與肅穆的氣氛。商代的紋飾淵源可以追溯到荒古的時代,吸收遠古時代各種新石器文化,經過長期融合、選擇而形成。青銅器紋飾是殷商先民“尊神”意識的體現,周代則發展為“敬天法祖”,形成宗教、政權、族權三位一體的表征。商周統治者用青銅器紋飾的“猙獰恐怖”來表達王權的“神秘威嚴”,以表達其對政治權力、地位與財富的不可挑戰性。抽象化的獸面紋飾中寄托的是一種威嚴、意志、榮貴、幻想和希望。張光直同樣認為“青銅便是政治和權力”,但他認為獸面紋不是為了威嚇,而是為了與神溝通。亞尊的造型外觀上樸實不張揚、不過于繁縟,符合儒家中重德法天、溫厚內斂、文質彬彬的審美追求;上下兩處的獸面紋,也蘊含著王權、信仰、理想、文化、正統、威嚴的集合,適用于清代時皇權謀求文化道統支持的場景。
2.觚的“十”字孔
亞尊的底部和敞口連接處,有兩個穿透的十字孔洞。這樣的十字孔洞在現存的觚當中,于商周之際比較普遍。這個十字孔的用途如何,也存在爭議。觀點一:是十字孔是有功能意義,是用來懸掛或者持取的,沒有裝飾意義;觀點二:十字孔是工藝需要,制作的時候底部起范懸空的需要,但是無法解釋為什么有的觚沒有十字孔;觀點三:十字口有功能意義,但也也具有精神意義,但是功能意義和精神意義到底如何進行確切解釋,現在還是在探討階段。觚為飲酒器,類似于現在餐桌上的酒壺,是和爵搭配使用的,而且觚、爵、觶、斝等飲酒器也多配對成雙。中國北方冬天飲酒常常是把酒倒進酒壺溫一下再喝,當然古酒與今酒應有所不同也要考慮進去。東漢末年,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傳為千古佳話,想必古代的酒煮一下應該更好喝,故猜測觚是不是用來煮酒的。因為此觚的底部是中空的,兩個十字孔有利于底部的如木炭等物燃燒通氣。觚所能容納的酒量,其實也不多,差不多是爵的數倍左右。
《說文·角部》:
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
這也是對觚的十字孔的功能的一種猜測。但青銅器器型中的斝是專用煮酒的,有的觚也沒有十字孔,說明煮酒也不是觚的功能范疇。故而觚的十字孔很可能是具有裝飾意義或者是其他精神意義。據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早在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中就出現了十字紋,常與寬帶紋同時出現,其后在馬家窯文化、良渚文化、辛店文化等都能看到這種神秘的十字紋。考古學家也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許多巖畫遺跡,也能看到熟悉的十字形太陽和其他樣式的太陽。也出現過十字太陽高懸于人類與動物之上,多次出現一人手中持有十字,站在太陽下,類似巫師作法圖。殷商時期,“帝日”“賓日”“拜日”的禮儀非常盛行,在金文和甲骨文中也有類似于人舉十字孔形太陽的表現,證明太陽崇拜是商代宗教和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器物圈足上有“十字孔”應是其精神的表現。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大多是一脈相承或是在縱向的相承中融合其他文化而發展。比如中國文明中,對魚的崇拜,也能夠慢慢上溯到新時期時代等。所以同樣的,對于十字紋類的太陽崇拜和祭祀表達能夠傳遞到殷周時期在邏輯上是講的通的。而且,十字孔很明顯是有選擇的出現在青銅器中的。可以肯定的是,商人重祭重卜的一些行為會逐漸演變為周代禮制禮儀的部分,十字紋可以看作是祭祀文化和君權神授的精神文明體現,也代表文明的傳承和先秦時代充滿著神秘色彩的審美需要,也就是某些裝飾的符號意義,充滿著敬畏、威嚴、崇拜等精神性的復雜心理。
三、亞尊的審美功能
清代到如今,社會環境、政治制度、文化信仰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周亞尊”到“獸面紋觚(亞弓觚)”,也從“古器盎然”變為如今“泯然眾人”。這種以亞尊為物化代表的審美變化背后是多方面的審美追求所交織而成的。清時可見的存世流傳的觚也有不少,比亞尊工藝精湛、造型優美、紋飾復雜者也有,但是皇權的需要、正統儒家代表著天下學問道統的禮制教化需要,讓亞尊成為“周十供”中與木鼎相比肩的佼佼者。雖然后世查知木鼎、亞尊屬于殷商時期的物品,乾隆皇帝錯認為其是周代器物,但是商代物品出現在周代的政、教活動中也不足為奇。“禮”成為后世選定孔家祭祀選用物品的審美出發點,禮代表秩序和傳承的文化理念,比如立嫡不立長、立長不立賢、立德不立威,正是這種審美觀念的體現,當然也可以延伸到對亞尊的審美認知上來。
本質為觚的亞尊在乾隆時期被推崇為“尊”,極盡恩榮,也是源于它的上面所承載聯系的文化意義以及其他的符合裝飾意義。中華文化是獨立發源、一脈相承發展、融合多方演變而來,亞尊或許能夠成為上古至先秦時代的文化發展、審美推崇的一個見證和體現。根據現代考古學家對所知青銅文物的統計分析,認為觚這種器物到西周中期已屬軍見。文化有一定的獨立性和滯后性,但是如果僅僅是一種飲酒器,這種用具怎么會慢慢消失了呢,除非有好的功能替代品。比如鏡,古代生活需要鏡,現代生活也需要鏡,這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繼承性。所以,大膽猜測下,觚的精神活動功能遠遠大于社會生活功能。商人重巫重卜,巫卜的大量活動產生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延及周代,或許商代巫教也成為周禮(教制)的一部,代表著先民內心復雜的敬天尊神以及對文明的認識,在延續上一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繼承了代代流傳的裝飾崇拜。像獸面紋、十字孔(紋)就可以找到大量新石器時期的遺跡遺物遺存。原始時代人們主要對于黑暗的恐懼,而崇拜太陽力量(如可以帶來光明,使夜晚開始聚集的野獸逃散);商代人在繼承這種文化傳統后,加上自身中晚期遇到洪水、寒冷氣候而愈發懼怕自然的力量,認為是天神發怒而惡化生存環境,更加推崇太陽和巫卜,以達到和神交流,獲得政權的權威以及生存的希望。這些復雜的因素交織在一起促進了文明的進展,也促進了殷商時期巫教和禮教的發展,上層建筑會影響文化的發展,所以青銅器,尤其是禮器(祭祀、政治所用)在造型、裝飾、功能的審美也受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四、結語
中華文明能夠一脈相承并綿延不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一統的王朝會和文化階層合作,形成在文化道統、秩序人心、權力合法性上的穩固,從而確保大多數人的生活保障和穩定。商周時期的王權和巫教祭祀的合作,西漢董仲舒提及的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理論,乾隆皇帝對儒家學說、孔府祭祀的重視等等均體現出這種君、天、學的合作關系。這種關系也體現在審美造物上,為藝術史中的藝術實踐提供了豐富的可能,也是一種美的含義在特定歷史環境和文明進程中的體現。亞尊,如今在博物館中是一件普通的青銅文物,可它能夠體現中華文化的一脈相承以及多種文明審美的交織。亞尊的紋飾等裝飾元素源于新石器時代留下的文明傳統,產生它的那個時代有用它來參與復雜的祭祀巫教等精神活動的極大可能。清代時用亞尊來對表達對學問道統的禮遇推崇,而今文化環境的改變影響了人們的審美眼光,人們不再對亞尊摻雜進神秘的巫教情結、對上天的敬畏、對國家意識形態的禮敬等復雜的情感和心理活動,故而亞尊褪去了“伯仲木鼎,朱紫燦爛,古器盤然”的美,成了獸面紋觚或亞弓觚。但是亞尊的造型、紋飾、結構等客觀的實體,能夠證明中華民族的審美文明的發展,亞尊的藝術史意義也在于此。
注釋:
①孔維亮《“商周十供”命運的歷史變遷》,《文物天地》2020年第6期。
②孔維亮《“商周十供”相關問題的考證》,《文物天地》2020年第7期。
③徐倩倩《亞弓觚(商)》,《齊魯學刊》2019年第6期。
④徐中舒《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商務印書館,2015,第208頁。
⑤王亞楠《“亞”紋樣圖案與中式傳統審美的關系》,吉林藝術學院,2012。
⑥王夢迎《商周時期“亞”族氏銘文研究》,天津師范大學,2018。
⑦朱鳳翰《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復合氏名》,《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
⑧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齊魯書社,2009
⑨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⑩王志忠《商周青銅器餐餐紋研究》,河北大學,2021
(責任編輯: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