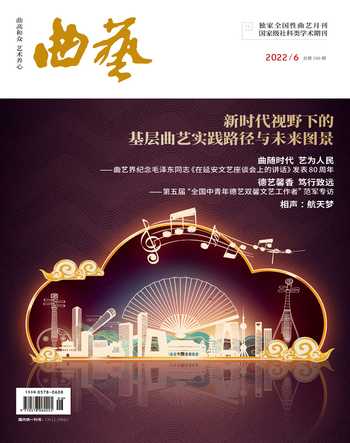光風霽月云海樂 歲月不居天酬勤
李成麗
就語言的交流表述而言,方言土語最具地方特色,它是一個地方民俗文化的生動名片,尤其身居他鄉同為異鄉客的時候,離鄉的游子聽到彼此的鄉音,更是可以瞬間拉近彼此的距離,并激發出各自的汪汪淚目。在這表面的狀態之下,實際上,它可能還是一個區域民族性格和當地歷史文化的沉淀,可能還是藝術傳承的基因和密碼。但同時,方言土語因彼此地域性的巨大差異,造成了在他鄉異域溝通的極大困難,也正因此,國內普通話快速的普及,國際上英語等標準化語言得以盛行。當然在這盛行的背后,是每天每個時刻都有區域性語言消失的現象發生。今天,我們在享受標準化語言帶來便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各自所屬的方言地域性標簽迅速消退,更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同一性大方位區間的所謂“本地人”。一言以蔽之,千姿百態的語言類型不復存在,由語言承載的千姿百態的各種民俗形式也不復存在,所以也才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提法和大面積推廣,有了“口頭藝術傳承”的學科。對于藝術創作而言,我們追求的是區別于同類別或異類別之后無可取代的“獨特性”,即個體特性或特質,尤其是在多媒體、自媒體、立體形象展示平臺迅速發展與普及的今天,藝術作品所體現的“獨特性”就更顯重要。在這種概念引導的前提下,我以為,一部作品如果能夠在不影響更大范圍受眾接受的同時,能夠在展現自我作品“獨特性”的條件下,通過作品充分反映出時代前行的足跡,充分展示出所屬藝術類別的語言韻味之美,充分折射出人性之光芒,引發受眾進行反思反省,并能夠在劇場引發演員與觀眾的互動與共振,產生“同頻”效應,那么,這部作品將會是海量作品中的佼佼者。同樣,以這樣的概念判定,我認為:《合浪浪許家》就是這樣一部優秀的方言話劇作品。我們從如下3個方面分析。
法國文豪雨果在論述戲劇的地方色彩和時代氣息時說:“地方色彩不該在戲劇的表面,而該在作品的內部,甚至作品的中心,它生動而均勻、自然而然由內而形之外,可以說是流布到戲劇的各部分,正像樹液從根部一直輸送到樹葉的尖端一樣。戲劇應彌漫著時代氣息,像彌漫著空氣一樣,使人只要一進去或者一出來就感到時代和氣氛都變了”(《克倫威爾·序》)。《合浪浪許家》通過反映修車師傅許有福的生活變遷,以及通過他所折射出的他的家庭的悲喜故事,集中展示了改革開放40年來,身處于城市平民階層的普通小人物的生活情態,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變化,完全吻合并體現了“小切口、大情懷”的創作思路,展示了時代發展、人民幸福的宏大主題。特定時代的“道具”——自行車,仿佛沉淀已久的民俗一樣,既襯托起了許有福的身份和性格,也交待清了故事的年代背景,更串聯起了這個“合浪浪”(太原古城胡同)的戲劇敘述鏈條。
正因為作者將主人公定位在我們所熟悉的,兩手沾滿油漬,十字街頭低頭忙碌,正在補胎或擰螺絲、換零件的修車工人身份上,所以我們(也是觀眾)瞬間有了個人的參與感和親歷感,有了心理上的共鳴,有了聯想性的親切——這個人物是我們身邊的人物,這位許有福師傅,他像不像你我的父親或叔父?抑或像你我的祖父輩?在自行車作為家庭生活中唯一交通工具的時代,靠著這個當時社會上最為普通的手藝,維持著兩兒一女的基本生活和求學上進。他的妻子因病早故,他又當爹爹又當媽媽拉扯著孩子,甚至不敢再娶妻;他是底層市民,靠辛苦賺錢,靠節儉積累,攢下的毛票收藏在褲子的腰帶里,但卻能夠在大兒子赴南方創業遇到困難時,接濟幾十萬元……。一號角色這份職業的設計,既說明了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階層角色,又將過去時代標志性手工業修理的職業給予了亮相,雖然這一職業目前已有所衰微,但卻是20世紀人們腦海中的清晰記憶;還有許家養的小鸚鵡,也將那個時代流行于市民中的寵物——一種準風俗的情景給予了展示。總體上看,舞臺上的這些人物和生活,就是對我們所生活的那個年代的回望,舞臺上設計的每一個小人物、每一個小動作,或者一句話、一個眼神兒,都會勾起了我們生命中曾經出現的那個人、那些事、那段情、那個老房子、那片老建筑、那篇曲藝段子、那個戲曲聲腔、那一聲沿街叫賣……看完全劇,人們會感嘆,一個修自行車的工人,通過自己的勤勞和節儉,也能在這個時代找到自己的生活發展道路,也能過上了好日子,那么,現實中的我們,有幸處于國泰民安中的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去奮斗和拼搏,有什么理由不去爭當新時代向前發展的正效因子。而亦悲亦喜、亦笑亦哭的表演以及沉淀于其中的生活的滄桑感,不也正是本劇的藝術魅力所在嗎?
《合浪浪許家》是一部由太原蓮花落串場的作品,在這部作品的現場演出中,太原方言的語言表達形式強化了本地觀眾和熟悉太原方言觀眾的認同感和參與度,通過方言的使用,也使得作品準確傳遞出了區域性傳統文化的意蘊之美,迅速鞏固了自我的受眾群體,同時把太原古城的風俗和一些地標建筑,用方言的形式,向現場的觀眾羅列和展示。這也讓我想起古代羅馬戲劇理論家賀拉斯所說:“我勸告已經懂得寫什么的作家到生活中,到風俗的習慣中去尋找模型,從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語言吧”。(《詩藝》)在本劇中,主要演員對舞臺上活生生的太原方言的駕馭,使我們在現場強烈地感受到:這個方言劇,是演員由內心生發出的對“母語”的自然流露,而非一般意義上演員加工出來的臺詞,這種感覺或許就是迅捷消除與觀眾距離感的根由,也使我思考起這樣一個問題:柴京云導演運用曲藝的手段,使演員與觀眾的距離迅速拉近,避免了一般話劇形式的鋪陳,也使得這部曲藝方言劇,天然地使當地觀眾產生了對本劇的親近感。
當然,在一片贊揚聲當中,也有個別專家提出了:本劇主人公的太原方言表達,是否會影響該劇向更大范圍、更高層級的推廣?我個人認為,對于太原方言而言,它是一種有著強烈個體特色的地方性語言,是“晉方言”覆蓋區的龍頭語言形式,但同時它的發音和表述,除了一些個別特定稱謂或者專有名詞外,一般性的交流是沒有障礙的——再確切地說,由柴京海飾演的《合浪浪許家》的主人公許有福,他所運用的太原話,其實是在基本符合漢語拼音基礎上的太原話,所以本劇在保持自我特色的同時進行更大范圍推廣也是完全可行的。如果為了所謂的推廣而舍棄了方言的使用,那么,這部劇的特色將不再鮮明,因方言表述在劇中產生的特殊效果也將不復存在,隨之現場演出效果也將大打折扣,也就是說,可能會失去人們所期待的那種語言的味道,那種民俗的沉淀,甚至是那種鄉愁的懷舊和思緒,最終可能失去一種文化的色彩。

坦率而言,通過一部作品,要留住一種方言,或許是大話,但通過一部生動的作品,讓人們加深對方言的記憶卻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通過《合浪浪許家》,人們感受到了“晉語”,感受到了太原方言,感受到了忻州市五臺縣的土語。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說太原方言或其他地方性語言的人,將越來越稀少,那么,用方言創作的作品將更能凸顯其價值。假以時日,若10年之后,當我們再回頭觀望時,《合浪浪許家》,是不是會成為歷史的獨特回憶呢?
喜劇是極難導演的藝術形式,從某種程度上看,讓觀眾笑比讓觀眾哭更艱難。而在這其中,喜劇導演掌握戲劇節奏的能力——業界行話說所謂“掌握火候”的能力——考驗著導演的素質,事實上也幾乎考驗著導演畢生的藝術積累。本劇的總導演是柴京云,他與兄弟柴京海是曲藝界公認的黃金搭檔,但在本劇中,兄弟倆則一為導演一為主演。宏觀地說,柴京云執導的《合浪浪許家》,確實體現了他對“獨一性”特色分寸感的把握,體現了他對戲劇節奏的掌控能力。事實上在大家聽說他要執導大型喜劇時,特別是要執導以太原話為主的大型喜劇時,人們是為他捏著一把汗的。雖說我們對他的藝術創作能力并不抱懷疑,但從柴京云過去的創作經歷看,他編導的大同數來寶《工錢》《隔輩親》《望子成龍》等,都是小型曲藝作品,而且是以大同話為主的小型曲藝作品——《合浪浪許家》作為一部大型喜劇而且是以太原話表演的大型喜劇,當然對他的宏觀把握能力給予了考驗。令人驚喜的是,我們看到,柴京云導演不僅順利地通過了考驗,甚至在許多方面更出色地超越了小型節目的局限,顯示了他作為導演的天賦。同時我們也想到,相對于多年從事大同數來寶創作與表演的經歷,或者簡單的抖包袱聊段子就可以逗笑觀眾的經歷,本劇中,“二柴兄弟”的默契配合可能也是柴京云作為導演成功的秘密武器——主演配合導演,可能克服了不少語言轉換和二三度創作的困難。可以這樣說,《合浪浪許家》,喚醒了“二柴”全部的人生積累,為觀眾表達了一種飽含深意的微笑,更多時候甚至是笑意散去,再引發心頭的淡淡哀傷——這種情境,更需要編導為人物命運設置自我的鏡像對照。而這,或許就是導演與演員們對本體藝術“獨一性”特色分寸感把握能力的體現,能做到這一點很難,尤其是對于駕馭這樣一部挑戰自我專業領域的作品,一定是他們人生積淀和藝術積淀后的厚積薄發。說到這里,我們也希望,積累與沉淀了幾十年的“柴氏兄弟”文藝品牌,能夠在山西文藝創作振興的大潮中樹起一座標桿——一個人才就是一項事業,兩個人才就是一個品牌。有可能,兄弟二人親密合作幾十年創造喜劇的品牌,也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和容易。如何使“柴氏兄弟”文藝品牌在省城立足、擴大、弘揚,使這兩位喜劇的奇才發揮更大作用,使山西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蘊有更精彩的表現,既應當是柴氏兄弟的現實思考,也應當成為文化管理者的責任所在。
令人驚喜的還有,柴京云、柴京海的愛徒王名樂創作才能的嶄露頭角,二十幾歲的毛頭小伙駕馭了如此跨度的題材,而且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我們設想,假以時日,依照目前的進步速度,誰都無法預料這位年輕編劇兼演員的未來前途。我們當然希望、盼望,在這片古老的黃土地上,王名樂能夠像前輩老師一樣,扛起山西曲藝乃至山西話劇振興的大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還需要充分肯定的是,除柴京海的精彩表演以外,其他演員的表演也令人贊賞。說五臺方言的老王和說山東方言的小伙,以及主人公許有福的女兒、兒媳等角色,均表演不慍不火,輕松自然,以自己的本分和本色,為本劇的喜劇色彩增色不少,圓滿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任務。總之,這個表演班底的珠聯璧合,為本劇立下了三度創作的成功基礎,每一個人物表演的鮮活,都能夠給觀眾留下較深的印象,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總之,在2021年疫情肆虐的時候,在山西舞臺看到這樣一部劇目,堪稱幸事、奇事。衷心希望這個創作團隊、這個演出班底,在以后的日子,再接再厲推出更加厚實、在藝術舞臺上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新作!
(作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廳藝委會委員,山西省藝術研究院戲劇曲藝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