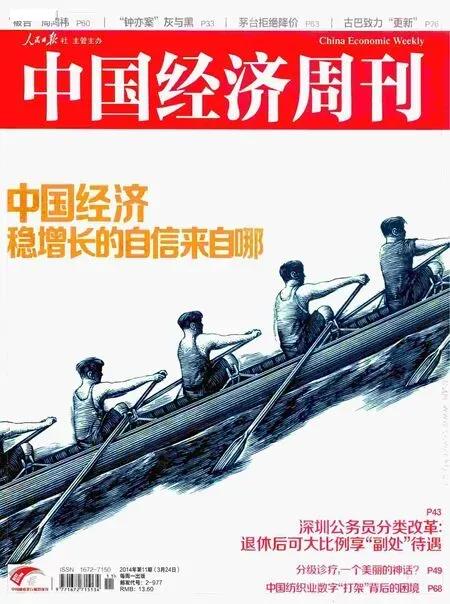中國貨幣政策可以更有效
鈕文新
5月2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重要講話指出,當前正處于決定全年經濟走勢的關鍵節點,必須搶抓時間窗口,努力推動經濟重回正常軌道。
兩天前的5月23日,央行兩次召開會議,一次是會同中國銀保監會召集24家主要金融機構,分析當下中國的貨幣信貸形勢,并要求“各主要金融機構要切實承擔主體責任,調動行內各方面力量,高效對接有效信貸需求,強化政策傳導”;另一次是當日召開的央行內部會議,提出“與金融機構共同擔負起金融支持穩住宏觀經濟大盤的重任”。可見,中國金融管理當局已經有了更強的緊迫感,尤其是央行要“主動作為”的提法更顯有力而及時。

但是,央行的“主動作為”需要找準“抓手”。這個“抓手”不該僅僅是一些臨時措施,比如加大再貸款力度或短期資金支持,而更該是“救急”與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并重,抓住經濟急需巨大金融支撐的契機,圖謀長遠,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構成可持續、更有效的支撐。
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疫情影響可能是短期的,但短期的影響未必短期內可以恢復。畢竟,企業在疫情期間投入的金錢和資源只能讓企業活下來,而并不產生經濟收益,這些投入還要依靠未來的生產效益予以“逐步填補”,所以它不是短期的事情,需要金融持續支持。二是除了疫情,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壓力更可能是長期的,這就要求中國金融長期、持續、大規模地著力于國內大循環建設,所以就算疫情過去了,金融對經濟的支撐力度也不能說撤就撤,而必須要與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相匹配。
金融支撐往往伴隨著杠桿率向上的壓力。所以,如何既能有力地支撐經濟,又不至于導致債務杠桿過高的系統性風險?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對中國金融智慧的大考。
金融人都知道,銀行手里有個“神秘的粥鍋”,它可以把存款變成貸款、把貸款再變成存款,并通過這樣的循環創造M2。經濟學家經常使用一個常識性的公式“M2=基礎貨幣×貨幣乘數”來說明問題。這個公式告訴我們:M2起源于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然后銀行用基礎貨幣向企業發放貸款,企業用這些貸款去支付,同時將貸款轉換為其他企業的在銀行的存款,其他銀行再用這些存款去從事貸款。從銀行業整體看,這就是存款變貸款、貸款又變存款的循環過程。
銀行這樣的“存貸款循環”最終將基礎貨幣放大很多倍,這個倍數就是貨幣乘數。因此所謂銀行手里的?“神秘的粥鍋”,實際就是銀行通過放大基礎貨幣倍數——提高貨幣乘數去增加M2供給的過程。
問題是:促使M2增長,是否可以在央行限制基礎貨幣供給的情況下,長期、單純依托向“神秘的粥鍋”里不斷“兌水”去實現?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認為:必須如此。因為經濟需要多少貨幣只有市場知道、政府不知道,所以貨幣發行需要市場說了算(即商業金融機構通過信用創造去實現),而不是政府說了算。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還認為,如果讓政府說了算,政府會為了政績而大量發行國債,透支貨幣,從而引發惡性通脹。
真是這樣?事實證明:金融危機往往都是“神秘的粥鍋”得不到有效控制的結果。現代貨幣理論的創始人蘭德爾·雷認為:為提高流通中貨幣(M2)而任由“神秘的粥鍋”不斷擴張,這不僅是債務杠桿不斷提高的源頭,同時也是2008年美國乃至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所以現代貨幣理論主張:政府要收回貨幣發行權,如果任由商業金融機構創造貨幣,實際上等于國家貨幣主權的旁落,是錯誤的做法。
注意:現代貨幣理論指的主權貨幣是基礎貨幣,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貨幣,是“神秘的粥鍋”里的“米”,而貨幣乘數則是“神秘的粥鍋”里的“水”。
在中國,經濟學家向松祚也在《新資本論》一書中論證:通貨膨脹往往源于商業信用擴張——貨幣乘數不斷上升推動M2增長,而非基礎貨幣發行的結果。按常識:我們憑什么不相信政府,認為政府會因政績需求、無度擴大財政赤字而逼迫貨幣超發?反而應當信任商業金融機構,認為它們不會出于投機需求而無度擴張信用?其實,將貨幣發行權讓渡給商業金融機構,這恰恰是金融資本主義典型特征。
如果偏離貨幣國家主權,而把貨幣發行權讓渡給商業金融機構,經濟能持續健康發展嗎?事實證明:近年來,中國M2增長恰恰是“不增加基礎貨幣,而靠貨幣乘數不斷推漲”的過程。這是不是過去金融發展過程中“跑偏”之處?
讓我們回歸常識吧!?GDP增長必然要有與之匹配的M2增長,而M2增長也應當要有與之匹配的基礎貨幣增長,這是常識。通俗一點講:要讓“神秘的粥鍋”里的粥又多又好,能夠讓更多更高大的成人吃了解餓,我們就必須同時往粥鍋里加米加水,而絕不能只加水、不加米。
為說明問題,大家要關注三條常識性的邏輯線。
第一條邏輯線:在貨幣學中,貨幣乘數又叫“貨幣流轉速度”,它指的是“從貨幣到商品再到貨幣”的交易流轉速度。所以應該看到:貨幣乘數越高,也就是貨幣流轉速度越高;貨幣流轉速度越高,其相對的貨幣流轉的“時間周期”越短;貨幣流轉的“時間周期”越短,意味著各種借貸構成的金融商品的期限越短。這就是所謂的金融短期化。進一步明確地說:不給基礎貨幣而靠貨幣乘數推高M2的方式導致金融短期化,其真實金融含義應當是:銀行只有且必須通過不斷降低信貸期限,加速信貸周轉,以滿足國家經濟增長對貨幣貸款數量增長的要求。
這種金融方式或可適于美國等國家以服務為主的經濟結構,因為無論是商業還是金融,“從貨幣到商品(金融商品)再到貨幣”的速度很快,但它是否適于制造業、實體經濟為本的中國?我們知道,生產過程是“從貨幣到原材料、再到生產加工、再到商品銷售、再到貨幣”的過程,這個過程遠遠長于簡單的“從貨幣到商品再到貨幣”的過程。所以,美國2008年以前的貨幣金融方式并不適于中國,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走向金融長期化方向,而不能走向金融短期化方向。
第二條邏輯線:銀行存款期限越短、銀行信貸期限就越短,銀行和企業都會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存貸款期限、投融資期限錯配”,這其中暗藏著流動性風險,而流動性風險實際是金融風險的核心;為降低流動性風險,銀行和企業都必須“超量借入短期資金”,以致全社會債務總額遠遠超過?“有效債務需求”。也就是說:全社會債務總量巨大,但真正使用到商品生產和實業服務的數量很少。那些債務差額在干什么?在金融圈里空轉。為什么要空轉?因為所有企業和金融機構都必須依靠這些短期債務維系流動性安全。為什么金融空轉尾大不掉?道理可能就在于此。
進一步的邏輯就是:債務期限錯配越嚴重,短期借貸需求規模就越大,當期限錯配達到一定的邊際,很可能導致全社會短期債務需求大增,全社會債務杠桿率過高,系統性金融風險(流動性風險)累積。尤其是在現有的體制下,長期貸款容易傾斜到國家項目、國有企業(因為風險小、責任小、易識別),而民營企業發展則缺乏足夠的支持,以致國家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民間投資不斷弱化。
第三條邏輯線:金融短期化使得中國金融表面看貨幣很多、流動性很大,但真正能夠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可被當作資本使用的長期資金嚴重短缺。所以,站在必須依賴長期資金的實體經濟、制造業的角度,金融短期化可以說是“貨幣政策的名松實緊”。長此以往,中國經濟增長或受到壓制。
此外,我們還應當看到:將貨幣發行權授予商業金融機構,這是金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貨幣發行權是金融的核心權力,誰拿到這個權力,誰就獲得“鑄幣稅”收入。而金融資本恰恰是因為擁有這個權力,在財富再分配中占據了優勢地位,所以金融才會“脫實向虛”,不為創造財富服務,而為財富分配服務。
目前看來,繼續沿著“不給基礎貨幣而只靠貨幣乘數提高去刺激M2增長”的路,已經走不下去了。因為,債務杠桿和流動性風險已經強力約束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不是嗎?近年來,中國頻頻需要財政發力去托住經濟增速,這時候央行就會說:容忍宏觀杠桿率上升。但當經濟剛剛好轉,央行立即回歸降杠桿之路,而降杠桿的結果又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此周而復始,是不是該多問幾個為什么?
那中國的金融問題到底出在哪兒?第一,中國經濟體量越發龐大,必然要求金融擁有“更大的粥鍋和更多的粥”;第二,要做好這鍋粥,必須同時加米又加水,而絕不能只加水、不加米;第三,貨幣發行權必須收歸國家,這樣才能有效地迫使金融回歸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道路,中國才有實現共同富裕的金融基礎。
為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應當是:長期的資本金融為主,短期的貨幣金融為輔;支撐創新的股權資本為主,支撐傳統產業的債務資本為輔。

為此,結合當下穩經濟對金融提出的要求,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盡快實施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達成目標。其核心在于:請央行為人民幣“換錨”,通過大量收購政府債券(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券),向市場注入長期基礎貨幣,并引導商業銀行釋放更多長期貸款,大量置換短期的、為維系流動性安全而超量投放的短期借貸。按照“神秘的粥鍋”理論,實際就是“加米降水”,提高粥的品質;按照貨幣理論,實際是在保持M2適度增長的前提下,增加基礎貨幣,降低貨幣乘數。
第一,釋放長期基礎貨幣是構建長期金融的基礎,而金融長期化必然節省大量的、為維系流動性安全的短期借貸資金,從而大幅降低全社會的債務杠桿率,大大提高中國國家金融安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第二,金融長期化不僅是疫情影響長期性的客觀要求,同時也是實體經濟、制造業為本——中國經濟特征的客觀要求,還是中國破解地方政府債務——這個“灰犀牛”風險的客觀要求,更是中央政府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和能動性、保持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的客觀要求。
第三,回歸本源地看,居民凈儲蓄(存款—貸款)是銀行信貸的根本源泉。而從近年來的情況看,隨著居民信貸消費、投資的不斷增長,銀行中的居民凈儲蓄規模相對于中國經濟總量、銀行業資產總量都在不斷縮減,這當然也會導致銀行可貸資源不足,尤其是長期存款資源嚴重短缺。這個缺口必須予以補足,否則銀行信貸增長能力就會受到限制,甚至出現負增長壓力,怎么辦?除中央銀行提供更多長期基礎貨幣以外,別無他途。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