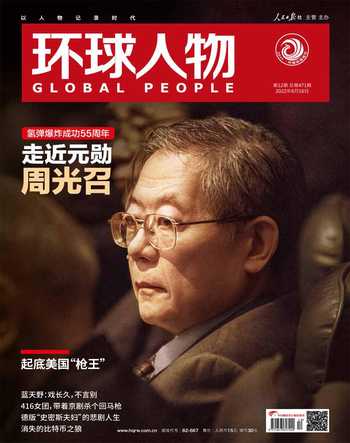為中共四大踏上“協調之旅”
尹潔

維經斯基(1893年—1953年)
在熱播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有這樣一個細節:1920年,一名外國人在上海與陳獨秀見面時,想按照西方習慣擁抱對方,陳獨秀卻做了一個抱拳的動作,說:“按中國的習俗來。”這名外國人馬上說:“那我們就握個手吧。”陳獨秀微微一笑說:“這個可以。”
這名外國人,就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第一位代表——維經斯基。
上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為幫助中國革命,先后派多位代表來華,維經斯基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1920年4月到1927年5月,他先后6次來華,7年間累計在中國度過了4年時光。除了第一次“播種之旅”,值得大書特書的還有1924年底到1925年初的“協調之旅”。
著名國際共運活動家馬克·卡扎寧曾這樣描述維經斯基:“他個頭不大,臉上棱角分明,有一雙明亮的、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他說話很簡潔,有時還不太連貫,但意思表達永遠是干凈利落……”
維經斯基于1893年出生在俄國,20歲時移居美國,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開始從事政治活動。十月革命勝利后,他回到祖國,加入俄共(布),后來進入共產國際,負責遠東事務。
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偕妻子庫茲涅佐娃,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來到中國,目的是了解五四運動后中國的情況,以及能否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一行人達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學俄語外教的介紹下,見到了李大釗。維經斯基當時取的中文名字叫吳廷康,他對李大釗說:“共產國際知道中國發生過幾百萬人罷工、罷課、罷市的革命運動,所以派我到中國來看看。”
李大釗十分高興,第二天就把他們請到了北大圖書館,就建黨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最后寫了親筆信,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見陳獨秀。
“當時蘇俄政權剛剛建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好,所以維經斯基初次來華時是非常受歡迎的。”中共四大紀念館研究館員孫露依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包惠僧曾經回憶,維經斯基中等身材,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上海“與陳獨秀一見如故”。陳獨秀還專門邀請各界知識分子,多次舉行座談會,請維經斯基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及革命后的巨大社會變化。
1920年8月,維經斯基從上海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寫了一封信,說:“我們對最近工作的展望是,希望在這個月內把各種革命學生團體組織起來,建立一個總的社會主義青年團。”
在維經斯基的協助和推動下,陳獨秀等人的建黨計劃也加快了速度: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等進步書刊的社會影響力迅速擴大;勞動補習學校、外國語學社等進步教育機構也有了顯著發展,維經斯基和夫人庫茲涅佐娃、楊明齋還在外國語學社里教俄語。
同年11月中下旬,在陳獨秀的建議下,維經斯基又在上海會見了孫中山,雙方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座談。
為了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成果,維經斯基于1921年春回國,因此未能參加中共一大。但他首次來華期間的各項工作,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維經斯基用他豐富的革命經驗,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幫助。”孫露依說。許多建黨親歷者稱維經斯基是協助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貢獻的人”。那段時期,他成為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一座橋梁。

上、下圖:進步刊物《勞動界》《共產黨》封面。
1923年,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的建議,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后者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隨后,國共合作持續推進,雙方關系似乎步入了一段“蜜月期”。但實際上,國民黨右派一直在制造摩擦。1924年6月,鄧澤如、張繼等人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彈劾共產黨案》,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確于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不宜黨中有黨”。此后,兩黨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當時,在國共合作的一些問題上,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共產國際因此再次派遣維經斯基來華協調工作,讓一拖再拖的中共四大順利召開。”孫露依說。
1924年底,維經斯基抵達上海,與陳獨秀、彭述之組建了中共四大提案起草委員會,確定了大會的中心議題。12月19日,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寫了一封信,通報了中共四大的籌備情況。他在信中寫道:“在一周時間內,我們這里舉行了中央全會……代表大會的中心議題是黨滲透到城市工人群眾中去的問題,也就是從在小組中做宣傳工作過渡到在工廠中做鼓動工作的問題,向工人們說明現在中國政治斗爭的基本因素。”
此外,維經斯基還在信中匯報了上海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在上海一地,黨已在紡織工人、機械工人和煙草工人中間成立了地下工人組織,并且都設有由工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自今年7月以來,我們建立了8所工人學校,這些學校是我們進行合法宣傳的中心。”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虹口的石庫門弄堂里召開。由于要提防外國巡捕和國內軍閥的破壞,位于二樓的會場被布置成英文補習班的樣子,還擺放了課桌椅和黑板。為了讓這個“英文補習班”更加令人信服,每一名代表面前的桌上都放了一本英文書,而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維經斯基,也自然而然地當起了“外教”。
在這次大會上,維經斯基帶來了他起草的兩份文件——《對于農民運動之決議案》和《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并由中共代表瞿秋白譯成中文。在決議案中,維經斯基強調了中國農民革命的重要性:“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并且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取得勝利。”
中共四大總結了國共合作以來的經驗教訓。對于陳獨秀與鮑羅廷之間的分歧,經過維經斯基的調解,決定由中共中央和鮑羅廷組成預算委員會,確定共產黨的經費數額,同時中共在工作中接受鮑羅廷的指導。
1925年2月,回到莫斯科的維經斯基給中共中央和鮑羅廷寫了一封信,強調共識的來之不易。1926年6月,維經斯基最后一次來華,在廣州進行了一個月的實地考察,分析了國民黨右派反復制造分裂的原因、后果以及共產黨應該采取的對策。

1924年12月,維經斯基致信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通報了中共四大的籌備情況。(此為信件印刷版,原件存于俄羅斯檔案館)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共產國際認為維經斯基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錯誤,將他調離了中國。對于大革命的失敗,維經斯基也做了反思,并主動攬責:“對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1927年6月,他啟程回國,結束了自己在中國的工作。
維經斯基之所以能在上海取得顯著的工作成效,與他的性格有很大關系。14歲時,家境貧寒的他曾在俄國一家印刷廠里當了3年排字工人,之后又到另一個地方當了3年會計。這兩份工作讓維經斯基養成了處事沉穩、行事嚴謹的作風。以至于他來到中國后,被大家誤以為是學經濟統計出身的,因為在座談中,他對蘇俄國民經濟發展的相關數據記得很清楚,可以隨口引用。
此外,維經斯基的閱歷也很豐富,懂得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因為窮困,他在青年時代前往美國謀生,一邊做工一邊學習,5年時間里不僅開闊了眼界,練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語,也參與了很多政治活動,這些都為他日后在中國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第一次與陳獨秀見面時,這個高鼻梁、藍眼睛的外國人態度謙和、平易近人,說話做事細致周到,給陳獨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時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欺凌,因此革命者普遍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共產國際代表如果不了解、不注意這一點,很容易給中國同志留下“高高在上”“傲慢”的印象。
相比后來的馬林等人,維經斯基更加懂得求同存異的道理。他與陳獨秀并非沒有分歧,比如在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吸納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上,維經斯基認為是可以的,陳獨秀則堅決反對。
由于不太了解中國的復雜情況,維經斯基從個人經驗出發,認為所有宣傳過社會主義、從事過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社會團體,都可稱為“革命小組”,并試圖借助陳獨秀、李大釗的威望將這些團體統一起來,組建成共產黨。陳獨秀則認為,建黨應有嚴格的標準和條件,必須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為首要前提。
雖然觀點有所不同,二人卻沒有發生沖突,更沒有影響工作上的配合。維經斯基最終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終止了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合作。這種態度和作風贏得了不少人的好感。羅章龍回憶說:“維經斯基這個人工作很細致。他來了之后,除了開座談會,介紹蘇俄情況,了解中國情況之外,還找人個別談話。通過個別談話,可以了解座談會上不易得到的情況。”

1921年,維經斯基(右二)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參加會議。

紀念館里復原的中共四大會場。
張國燾的評價是:“他(維經斯基)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黃種人與白種人,使人覺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時對于中國情形還不熟悉,也不妄談中國的實際政治問題。他這種謙虛的態度表現在他很推崇陳獨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觸的中國革命人物,總是說他們都是學有專長的……也許這就是他能與陳獨秀先生等相處無間的最大原因。”
在寫給共產國際的信中,維經斯基不僅肯定了陳獨秀的建黨籌備工作,還稱贊他是“一位享有聲望的中國革命者”。陳獨秀也通過維經斯基認識到共產國際的重要性,曾對張國燾說:“如果能與共產國際建立關系,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還是共產主義運動實際經驗上,都可以獲得莫大的幫助。”“如果共產國際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
遺憾的是,共產國際后來派的代表大多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中國共產黨人,也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傷害。
回國后的維經斯基脫離了共產國際的政治事務,擔任了全俄農業合作社園藝中心副主席,后來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終年60歲。
維經斯基(1893年—1953年)原名格里格里·納烏莫維奇·札爾欣,出生于俄國,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后負責共產國際遠東事務。先后6次來華,參與建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1925年出席中共四大,大革命失敗后回國,195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