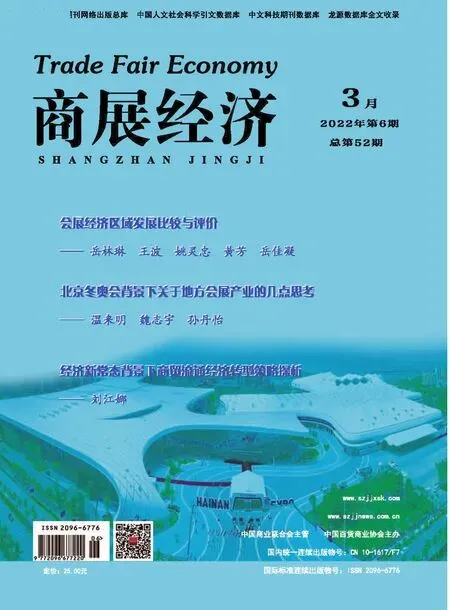疫情對各國GDP的沖擊路徑分析及經濟刺激政策效用評估
趙晨曦
(鄭州大學商學院 河南鄭州 450001)
新冠疫情既不同于外生的突發性自然災害,也不同于內生的突發公共事件。它起源于外生的新冠病毒,其發展演變取決于全球抗疫舉措,屬于外生伴隨內生、兩者互相作用的災難。影響更具全球性,持續時間長,而且伴隨極大的不確定性。新冠疫情不僅威脅全球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也對全球宏觀經濟、不同產業和微觀企業產生了重大沖擊(王永貴,2020)。2008年金融危機全球蔓延引起世界經濟衰退,而2020年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沖擊仍在持續蔓延,短期受到負面影響是必然的(宋清輝,2020),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按下“暫停鍵”,許多企業停產或半停產、停工或半停工,供給端和需求端同時快速下降。其中,旅游業和消費首當其沖遭遇一股強寒流(梁艷芬,2020)。另外,全球貿易活動受貿易保護主義影響增長疲軟,伴隨疫情全球擴散帶來的禁航禁運對全球貿易增長更是雪上加霜(田素華,2020),國際大宗商品需求、汽車及電子元器件供應,以及東亞“三角貿易”供應鏈也受到嚴重沖擊(王若蘭,2020),加大了全球經濟的下行壓力。世界貨幣組織將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調整為-3%,受新冠疫情全球擴散影響,2020年2月26日美國道瓊斯指數下跌1031點,下跌幅度達3.56%(田素華,2020)。新冠疫情已成為全球性問題、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危機事件,需各國協同治理、聯防聯控。為此,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不斷推出超常的經濟應對政策,對各國的疫情防控成效、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世界經濟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
1 國際主要經濟體GDP疫情沖擊路徑分析
此次新冠疫情下,全球性經濟衰退直接沖擊實體經濟的基礎,即居民和企業,造成經濟衰退。此次全球性GDP下降、經濟衰退,是由于疫情導致各國國內供給側出現斷裂,導致GDP下滑,繼而引發需求側沖擊,造成各國經濟危機。同時由于新冠疫情全球擴散,導致各國供給側沖擊沿著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傳導,引發全球供給側與需求側連鎖反應,帶來全球性GDP快速下滑。
1.1 國際機構對主要經濟體GDP增長率的預測
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預測,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將萎縮近1%;高盛、標普等機構均已經明確表示目前全國經濟已陷入衰退。其中,惠譽認為,如果封鎖時間再延長,那么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增速會陸續下降2個百分點;標普在報告中指出,實體經濟沖擊成為影響深遠的放大器,使得金融環境趨緊,在此情形下,經濟衰退或將演化為金融壓力。
1.2 新冠疫情危機下全球行業分化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行業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產生明顯的行業分化。新冠疫情首先使得需求大幅度下降,封城、社會隔離等措施使居民消費大幅下滑,企業對上游產品及原材料的需求大幅下降。供給受到極大沖擊,社會隔離等措施致使勞動力短缺,各行各業生產停滯,各國供應鏈中斷。對服務業、產業鏈較為全球化的行業、進出口貿易相關行業,都帶來較大負面沖擊。此外,金融市場狀況惡化,市場流動性指標呈現金融危機時的走勢;盡管央行向市場提供大量流動性,但金融機構間的流動性供給意愿并未上升;大規模美元回流使得新興市場貨幣面臨貶值壓力;資產價格大幅下跌。餐飲、住宿、娛樂、旅游、傳統教育、零售、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受影響最大;醫療、互聯網行業、資本密集度較高的行業受影響較小。
1.3 國際主要經濟體三大產業GDP貢獻率及一級行業比重結構
中國三大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從高到低依次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新冠疫情擴散正值服務行業旺季的第一季度,壓制第三產業推動GDP增長能力,GDP衰退下降。中國餐飲娛樂、交通運輸、批發零售業占16%。新冠疫情期間實行的隔離防控措施,對GDP最大的沖擊來自需求側,中國國內需求短期急劇下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下降23.58%,固定資產投資下降25.02%,國內企業大面積停工停產,供應側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此外,國內需求端與國際需求端的雙重萎縮,造成國內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13.5%,出口下降13%。
2019年美國餐飲娛樂、交通運輸、批發零售業占比18%,制造業占比較低,嚴重依賴國外供應鏈,中國停工停產對美國制造業造成的損失較大;美國的金融業、保險業、房地產業占比21%,比重較大,而且美國居民平均儲蓄率較低。服務業占80%以上,而服務業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再加上美國金融市場持續動蕩,所以說新冠疫情扼住了美國經濟增長的“命脈”。
德國制造業占25%,批發零售、餐飲住宿和運輸業占16%,疫情期間德國沒有停工停產,而且德國有來自國外的大宗訂單,航天航空業與機械制造業的大訂單緩解了疫情帶來的沖擊。德國金融業僅占4%,而且一直奉行審慎的金融發展政策,金融渠道不會對德國有較大影響,因而德國主要受全球需求端與產業鏈影響,造成制造業下滑,進而沖擊國內GDP。
對于英國和日本,服務業增加值占比最大,制造業占比其次,農林牧漁增加值占比較小。新冠疫情期間,各國嚴格封城防控措施,旅游業消費急劇下降,嚴重沖擊GDP;工業與制造業占比較高,對GDP增長的沖擊較為嚴重。農林漁牧業增加值占比較低,而且疫情對農業影響較小,因此,不會對GDP增長帶來較大沖擊。
對于中國和德國,新冠疫情主要通過制造業沖擊GDP,美國主要通過金融業影響GDP,日本主要通過旅游業、制造業和金融業影響GDP,英國主要通過服務業、制造業沖擊GDP。這5個國家的餐飲娛樂、住宿旅游、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的占比都在16%~18%。因此新冠疫情通過傳統服務業渠道對各國的影響差不多,但如果疫情持續時間比較長,中國與德國的制造業沖擊也會傳導給金融業。
2 國際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刺激政策
為應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沖擊,國際主要經濟體結合國情出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美國與德國對企業進行直接現金補貼,減少供給側沖擊,對家庭采用直升機撒錢模式,減少需求側沖擊,對醫療和其他行業直接給予財政資金,緩解金融側沖擊,加強新冠疫情防治與控制;法國對企業直接現金補貼,對家庭與醫療等方面采取直升機撒錢模式;意大利對企業提供貸款擔保,對家庭和醫療采取直接現金補貼;印度、尼泊爾、泰國、日本、韓國、荷蘭等國家均采用直升機撒錢模式。
2.1 相同點
面對新冠疫情沖擊,各國有著基本的共識:一方面,經濟刺激需幫助企業和民眾渡過生產和消費危機,消費端大規模減稅,加大救濟金規模,延長貸款,直接發放工資補貼;生產端對小型企業發放貸款,同時防止大型企業債務出現連鎖反應,避免國家利益受到沖擊。另一方面,需兼顧短期效果與中長期效益,為經濟中長期發展注入動力。
2.2 不同點
其一,企業支持資金金額規模相差甚遠。與歐美國家的大量企業紓困資金相比,中國政府公布面向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紓困資金相差甚遠;其二,就業補貼政策方式大相徑庭。美國、英國、德國等地區都出臺了就業補助政策,而中國則沒有,僅僅依靠失業保險的力量,同時要求企業在停工期間給員工支付至少一個月的正常工資,“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其三,對于企業救助模式也有所不同。歐美國家在疫情期間對小微企業采用直接現金補貼模式,經濟救助規模超出GDP的10%,同時采取措施支持各國主要大型企業,法國政府實行國家擔保,美國的國家貸救助,德國政府注入資金入股。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對小微企業幾乎沒有補貼;其四,刺激消費不同。歐美多國采取對消費者直接發放現金補貼刺激消費,而中國則采取向消費者發放消費券,但也是僅在部分大城市;其五,貨幣政策力度不同。美聯儲兩次累計降息150個BP至零利率,推出無限量量化寬松政策,英國兩次降息,中國央行連續降息等,都沒有美國極端。
3 國際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刺激政策效用評估
疫情下各國進行大力度救助經濟,經濟刺激政策切實執行和落實,有助于緩解經濟因新冠疫情受到的沖擊,也有助于穩定民眾恐慌情緒。PMI作為國際上通用的監測宏觀經濟走勢的先行性指數之一,該指數具有較強的預測、預警作用。因此本文基于國際主要經濟體2020年1—5月綜合PMI指數數據,評估國際主要經濟體在疫情期間采取的經濟救助政策效果,分析全球經濟形勢是否有所好轉。

表1 2020年1-5月國際主要經濟體綜合PMI指數
國際主要經濟體從2020年1月開始,PMI不同程度下滑。國內1—2月的PMI產出指數快速下滑,2—3月,財政和貨幣政策雙管齊下,進行經濟救助,隨著復工復產,經濟開始回暖,PMI產出指數快速上升;而歐美國家因疫情趨勢1—3月下滑幅度不大,3—4月疫情在歐美國家爆發致使歐美等國家的PMI值快速下滑,隨著5月所有成員國不同程度“解封”,其經濟下滑程度趨于溫和;美國服務業活動出現有史以來最嚴重收縮,打出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組合拳”,有效緩解了流動性危機,同時隨著封鎖措施逐步取消,下降幅度放緩,但美國國內局勢動蕩,經濟需要長時間才能回到之前的巔峰;英國、澳大利亞經濟前景改善,有助于提振某些行業的活動;日本制造業受到的損害可能會繼續惡化,放松緊急狀態的措施,服務業經濟開始逐步復蘇。新冠疫情快速沖擊各國經濟、社會、人民生活,國家經濟快速衰退。為應對新冠疫情的惡劣影響,全球進入戒備狀態,紛紛制定經濟救助計劃,從企業到家庭再到醫療衛生救助體系,經濟開始向好的態勢發展。
4 結語
10多年前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出口拉動,所以彼時的刺激計劃以刺激投資和出口為主;如今消費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占比達60%、服務業占比達53%,消費已經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同時中小民營企業和服務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
因而救助與刺激計劃,應以中小微民營企業、出口和傳統制造業為主,經濟刺激方向以消費、服務業、新經濟為重點,讓企業渡過危機,保持供應鏈與產業鏈完整。兼顧消費補貼、中小微企業救助、新產業扶持、智慧城市建設等全方位救助與刺激,積極復工復產,保持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穩定,平抑物價,保障需求不發生大幅下降。此外,財政政策應以受短期沖擊大而長期刺激無效的部門為主,對消費、服務業、新經濟扶持并刺激,培育長期增長動力;貨幣政策執行逆周期調控的本位工作,果斷大幅降準、降息,緩解流動性危機,解決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等的融資難問題,降低實際利率,刺激民間投資與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