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yè)績(jī)型股權(quán)激勵(lì)與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的披露
李丹鳳 首都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大學(xué)
引言
審計(jì)報(bào)告是財(cái)務(wù)報(bào)告預(yù)期使用者了解被審計(jì)單位,做出正確經(jīng)濟(jì)決策的重要途徑。為打破審計(jì)“黑箱”,增加審計(jì)工作的透明度(Reid 等,2019),我國(guó)財(cái)政部于2016年出臺(tái)了新審計(jì)準(zhǔn)則。新審計(jì)準(zhǔn)則要求審計(jì)師在審計(jì)報(bào)告中披露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而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審計(jì)報(bào)告的異質(zhì)性信息含量,使得報(bào)表使用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企業(yè)。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也認(rèn)為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能夠提高審計(jì)報(bào)告的溝通價(jià)值,對(duì)市場(chǎng)反應(yīng)、分析師預(yù)測(cè)準(zhǔn)確性、會(huì)計(jì)穩(wěn)健性等產(chǎn)生重要影響(王翠琳等,2021;薛剛等,2020;洪金明,2020)。但也有部分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guó)上市公司的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開始出現(xiàn)同質(zhì)化傾向(李奇鳳等,2021)。最直觀的表現(xiàn)在于,在2017年,有66.72%的上市公司將收入確認(rèn)披露為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而到了2020年,這一比例增加至80.78%,這說(shuō)明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異質(zhì)性信息含量可能在逐年降低。因此,為促進(jìn)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持續(xù)提供增量信息,防止新審計(jì)報(bào)告最終成為模板化語(yǔ)言,探究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影響因素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然而現(xiàn)有文獻(xiàn)主要以審計(jì)師特征(陳麗紅等,2021;徐暢等,2021)為切入點(diǎn)探究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影響因素,鮮有文獻(xiàn)從被審計(jì)單位活動(dòng)特征的角度出發(fā)進(jìn)行分析。
本文將探究業(yè)績(jī)型股權(quán)激勵(lì)計(jì)劃的實(shí)行對(duì)審計(jì)師披露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的潛在影響,首先,基于新審計(jì)報(bào)告準(zhǔn)則的大背景和被審計(jì)單位在業(yè)績(jī)考核期的情況特殊性,本文首次發(fā)現(xiàn)業(yè)績(jī)型股權(quán)激勵(lì)的實(shí)施會(huì)使審計(jì)師披露更充分的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豐富了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影響因素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其次,本文從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這一獨(dú)特視角檢驗(yàn)了企業(yè)股權(quán)激勵(lì)的實(shí)施對(duì)審計(jì)師行為的影響,豐富了股權(quán)激勵(lì)經(jīng)濟(jì)后果方面的研究;最后,通過(guò)研究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影響因素,有助于為監(jiān)管者提供監(jiān)督新視角。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shè)
我國(guó)上市公司的股權(quán)激勵(lì)制度多為業(yè)績(jī)考核型。被激勵(lì)對(duì)象只有完成規(guī)定的業(yè)績(jī)條件,才能解鎖相應(yīng)的行權(quán)工具。而目前絕大多數(shù)上市公司對(duì)被激勵(lì)對(duì)象行使權(quán)的授予都采取“一刀切”和“零遞延”模式(謝德仁,2019)。也就是說(shuō),只要管理層在解鎖年度沒有完成規(guī)定業(yè)績(jī),該年度對(duì)應(yīng)的激勵(lì)工具將全部作廢,不得按比例也不得遞延至以后年度解鎖。而股權(quán)激勵(lì)收益往往較為重大,這無(wú)疑會(huì)造成管理層在考核期內(nèi)不同于平常的決策行為。已有研究表明,股權(quán)激勵(lì)計(jì)劃的實(shí)施會(huì)導(dǎo)致管理層通過(guò)頻繁并購(gòu)(潘星宇等,2021)、向政府尋租(閆華紅等,2021)、激進(jìn)避稅(王一舒等,2020)、投資高風(fēng)險(xiǎn)項(xiàng)目(卜君等,2020)等方式調(diào)控業(yè)績(jī),以上行為均會(huì)使公司狀況趨向復(fù)雜,增加審計(jì)師進(jìn)行審計(jì)工作的難度。并且管理層為完成業(yè)績(jī)考核還會(huì)采用應(yīng)計(jì)盈余管理(劉寶華等,2016)、真實(shí)盈余管理(唐國(guó)瓊等,2018)、損益分類操縱(謝德仁等,2019)等手段,直接造成會(huì)計(jì)信息的扭曲,如此更會(huì)增加外部審計(jì)師發(fā)表不恰當(dāng)審計(jì)意見的概率。
風(fēng)險(xiǎn)感知在人類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Slovic,1987)。伴隨股權(quán)激勵(lì)業(yè)績(jī)考核而產(chǎn)生的管理層會(huì)計(jì)信息扭曲動(dòng)機(jī)以及復(fù)雜公司狀況會(huì)導(dǎo)致審計(jì)師感知到的審計(jì)風(fēng)險(xiǎn)增加。對(duì)此審計(jì)師可能會(huì)選擇增加審計(jì)投入、更謹(jǐn)慎地出具審計(jì)意見(洪金明等,2021)或提高審計(jì)收費(fèi)(王曉亮等,2019)等策略。而新審計(jì)準(zhǔn)則的實(shí)施特別是對(duì)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的披露為審計(jì)師的風(fēng)險(xiǎn)應(yīng)對(duì)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當(dāng)財(cái)務(wù)造假案發(fā)生時(shí),決定審計(jì)師是否受到處罰的根本依據(jù)并不在于其所發(fā)表審計(jì)意見的對(duì)錯(cuò),而在于審計(jì)師是否做到了在當(dāng)時(shí)狀況下對(duì)財(cái)務(wù)報(bào)表盡職盡責(zé)的合理保證。作為公開披露的特殊“工作底稿”,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允許審計(jì)師在審計(jì)報(bào)告中進(jìn)行差異化的表述。也就是說(shuō),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可以記錄審計(jì)師根據(jù)企業(yè)特有風(fēng)險(xiǎn)事項(xiàng)所實(shí)施的針對(duì)性審計(jì)程序,為審計(jì)師的努力工作提供有力證據(jù)。而根據(jù)心理學(xué)有罪控制理論,如果在事件發(fā)生之前,行動(dòng)者已經(jīng)執(zhí)行了必要的措施進(jìn)行防范,則社會(huì)群眾不會(huì)因?yàn)樽罱K產(chǎn)生的負(fù)面結(jié)果而去追究行動(dòng)者的責(zé)任(Alicke等,2008)。因此對(duì)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的充分披露能夠?yàn)閷徲?jì)師實(shí)現(xiàn)一定程度的“免責(zé)”功能,有利于降低審計(jì)師可能面臨的訴訟或處罰風(fēng)險(xiǎn)(黃亮華等,2021),即可以認(rèn)為,在被審計(jì)單位實(shí)行股權(quán)激勵(lì)的業(yè)績(jī)考核年度,由于其特殊的公司狀況和復(fù)雜的業(yè)務(wù)環(huán)境,使得審計(jì)師感知到更高的審計(jì)風(fēng)險(xiǎn),從而會(huì)對(duì)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進(jìn)行更加詳盡的披露,并作為自我“辯護(hù)”的一種聲明。此外,現(xiàn)有研究發(fā)現(xiàn)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還存在公司治理作用,能夠顯著減少企業(yè)的盈余管理等行為(喻采平等,2021),提高審計(jì)后的會(huì)計(jì)信息質(zhì)量(吳溪等,2019;楊開元等,2020)。在連續(xù)審計(jì)的背景下,充分披露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也有利于降低以后年度的審計(jì)風(fēng)險(xiǎn)。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shè)H1:
假設(shè)H1:在被審計(jì)單位實(shí)行股權(quán)激勵(lì)的業(yè)績(jī)考核期內(nèi),審計(jì)師披露的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更充分。
二、研究設(shè)計(jì)
(一)樣本選擇及數(shù)據(jù)來(lái)源
本文以2017年-2020年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并剔除金融公司ST樣本以及數(shù)據(jù)缺失樣本。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duì)各連續(xù)變量進(jìn)行了1%的縮尾處理。本文的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數(shù)據(jù)通過(guò)閱讀上市公司審計(jì)報(bào)告手工搜集和整理獲得,其余所需樣本公司的各項(xiàng)財(cái)務(wù)數(shù)據(jù)以及股權(quán)激勵(lì)方案表均來(lái)自CSMAR數(shù)據(jù)庫(kù)。
(二)變量定義
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充分性:一般而言,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項(xiàng)數(shù)以及文本字?jǐn)?shù)越多,審計(jì)師對(duì)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的描述以及應(yīng)對(duì)程序也就越詳細(xì),同時(shí)在文本中加入數(shù)字化信息能夠傳遞精確的定量信息,能夠提高外部使用者對(duì)審計(jì)事項(xiàng)段“關(guān)鍵”信息的感知水平。本文借鑒陳麗紅(2021)、王艷艷(2018)等的方法,從三個(gè)維度衡量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充分性:(1)披露數(shù)量(KAM_Num):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數(shù)量。(2)披露篇幅(KAM_Words):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描述段和審計(jì)應(yīng)對(duì)段的總文本字?jǐn)?shù)取自然對(duì)數(shù)。(3)披露精確度(KAM_Times):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中的金額提及次數(shù)以及比例提及次數(shù)之和取自然對(duì)數(shù)。
股權(quán)激勵(lì)(EI):如果企業(yè)實(shí)施了業(yè)績(jī)型股權(quán)激勵(lì)且當(dāng)年處于業(yè)績(jī)考核期時(shí),該變量取1,其余情況該變量均取0。
控制變量:本文選取若干控制變量進(jìn)入模型,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Size)、總資產(chǎn)凈利率(Roa)、資產(chǎn)負(fù)債率(Lev)、營(yíng)業(yè)收入增長(zhǎng)率(Growth)、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Soe)、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Sha)、獨(dú)立董事比例(Ind)、董事會(huì)規(guī)模(Boa)、審計(jì)費(fèi)用(Fee)。與此同時(shí),本文還控制了年度、行業(yè)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
(三)模型建立
根據(jù)假設(shè)H1,本文構(gòu)建模型(1)、模型(2)、模型(3)以檢驗(yàn)業(yè)績(jī)型股權(quán)激勵(lì)實(shí)施與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充分性的關(guān)系,具體模型為:

其中,i代表企業(yè);t代表年份;Ctrl代表影響審計(jì)師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充分性的一組控制變量。本文預(yù)計(jì)α、β以及γ均顯著為正。
三、實(shí)證結(jié)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tǒng)計(jì)
表1展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結(jié)果。為了便于解釋,本文描述了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總字?jǐn)?shù)(KAM_NWords)以及金額比例提及次數(shù)(KAM_NTimes)。可見,無(wú)論是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個(gè)數(shù)(KAM_Num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別為1、6和2.038)、披露文本字?jǐn)?shù)(KAM_NWords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別為246、7372和1207.192)還是金額比例提及次數(shù)(KAM_NTimes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別為0、52和4.559),不同公司之間均存在較大差異。而股權(quán)激勵(lì)(EI)的均值表明股權(quán)激勵(lì)業(yè)績(jī)考核期樣本占到了總樣本的24.3%,股權(quán)激勵(lì)已愈發(fā)常態(tài)化。其余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與現(xiàn)有文獻(xiàn)大體一致,不存在異常狀況,在此不再累述。

表1 主要描述性統(tǒng)計(jì)量
(二)回歸結(jié)果分析
為了驗(yàn)證業(yè)績(jī)型股權(quán)激勵(lì)計(jì)劃的實(shí)施對(duì)審計(jì)師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影響,對(duì)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別進(jìn)行回歸。回歸結(jié)果如表2列(1)—(3)所示。結(jié)果表明,在考慮相關(guān)控制變量后,股權(quán)激勵(lì)(EI)與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個(gè)數(shù)(KAM_Num
)的回歸系數(shù)為0.042,在1%水平上顯著;股權(quán)激勵(lì)(EI
)與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篇幅(KAM_Words
)的回歸系數(shù)為0.061,在1%水平上顯著;股權(quán)激勵(lì)(EI
)與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精確度(KAM_Words
)的回歸系數(shù)為0.023,在10%水平上顯著。說(shuō)明在股權(quán)激勵(lì)的業(yè)績(jī)考核年度,審計(jì)師披露了更充分的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初步驗(yàn)證假設(shè)H1。
表2 多元回歸結(jié)果
(三)穩(wěn)健性檢驗(yàn)
本文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包括,通過(guò)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對(duì)樣本進(jìn)行1:1的最近鄰匹配,對(duì)匹配后的樣本重新進(jìn)行回歸;將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滯后一期重新進(jìn)行回歸以緩解此內(nèi)生性問(wèn)題;控制審計(jì)師性別(Gender
)以及學(xué)歷(Phd
)重新進(jìn)行回歸等,檢驗(yàn)結(jié)果均與前文敘述一致。結(jié)語(yǔ)
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為我國(guó)上市公司股權(quán)激勵(lì)制度設(shè)計(jì)的不合理提供了審計(jì)師層面的證據(jù),上市公司還應(yīng)繼續(xù)健全內(nèi)部治理機(jī)制以更有效地發(fā)揮股權(quán)激勵(lì)的制度優(yōu)勢(shì)。從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還可以看出,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披露的確是審計(jì)師傳遞信號(hào)的一種途徑,外部使用者不應(yīng)僅僅關(guān)注審計(jì)意見,還應(yīng)關(guān)注關(guān)鍵審計(jì)事項(xiàng)的披露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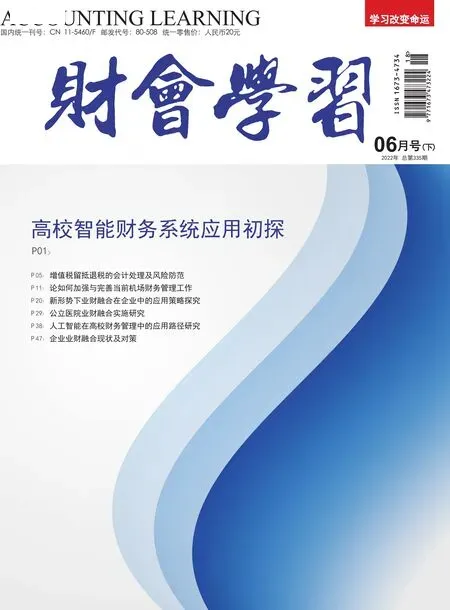 財(cái)會(huì)學(xué)習(xí)2022年18期
財(cái)會(huì)學(xué)習(xí)2022年18期
- 財(cái)會(huì)學(xué)習(xí)的其它文章
- 電力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實(shí)施策略分析
- 新形勢(shì)下小區(qū)物業(yè)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策略分析
- 新時(shí)期如何強(qiáng)化會(huì)計(jì)財(cái)務(wù)管理中的內(nèi)部控制工作
- 提升財(cái)務(wù)管理能力 促進(jìn)智慧停車發(fā)展—以國(guó)有停車經(jīng)營(yíng)企業(yè)為例
- 預(yù)算一體化系統(tǒng)在教學(xué)改革中應(yīng)用研究—以職業(yè)院校會(huì)計(jì)專業(yè)教學(xué)為例
- 構(gòu)建和完善財(cái)政投資評(píng)審制度的踐行與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