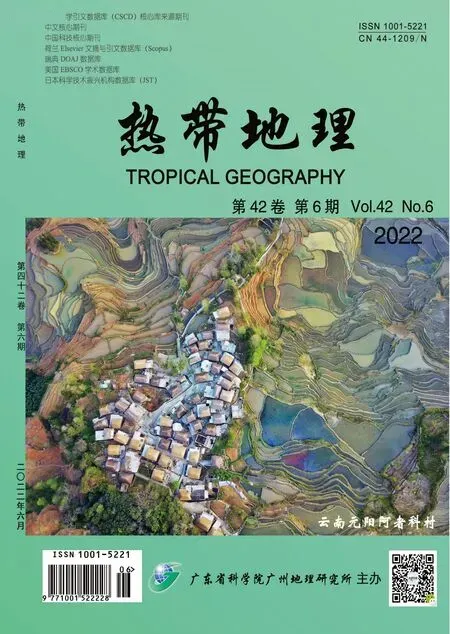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空間演化及其影響因素
張 杰,盛科榮,王傳陽
(山東理工大學經濟學院,山東 淄博 255012)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金融業不斷發展壯大,近40年內成長起來如工商銀行、平安保險、國泰君安等一大批本土大型金融業企業集團。中國人民銀行網站①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93266/index.html。發布的公告顯示,截至2019年末,中國金融業企業總資產達318.69萬億元,超過當年中國GDP的3倍。與此同時,這些金融業企業的空間組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分支機構布局快速擴張,國家層面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逐步形成了覆蓋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等領域,種類齊全、競爭充分的金融機構體系(易綱,2019)。在大型金融業企業跨多區位空間組織發展的帶動下,中國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得到快速發展,城市可以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通過規模借用、知識流動、經驗交流、相互協作來提高城市的經濟績效(盛科榮等,2021),城市的空間結構正在由中心地模式下的等級空間聯系向網絡模式下的多維空間聯系轉變(王士君等,2019)。基于金融業企業網絡視角的城市網絡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經濟地理學者關注的熱點。
近年來,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2個維度。一是聚焦于單一行業企業網絡視角的研究,如馬學廣(2017)、鄒小華(2019)等基于銀行分支機構網絡視角研究了中國城市網絡的關聯結構及演變特征,指出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之間的聯系構成了中國城市網絡的主干,城市節點度和網絡密度以胡煥庸線為界的地區差異特征顯著增強;Pan等(2016)利用風險投資公司數據構建城市間投資網絡研究了中國金融中心的地理格局,發現北京、深圳和上海在中國風險投資中處于領先地位;劉丙章等(2020)指出市場機會、區位效應和金融集聚是近20年來影響在華外資銀行空間網絡的主導因素;季菲菲等(2014)解析了長三角地區金融機構網絡的擴張機理,發現政策導向、擇優鏈接和路徑依賴對于金融網絡的空間擴張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詹璇等(2016)揭示了銀行網點分布與公共交通網絡的耦合關系具有一定的空間不平穩性和空間異質性特征。另一些學者注意到了國內金融網絡擴張與世界城市網絡的聯系特征,如Rossi 等(2005)通過對巴西31家國內外大型銀行組成的全球分支機構網絡的研究發現,圣保羅在全球金融網絡聯系中處于主導地位的同時,其他中等規模城市的國內外聯系也得到了加強;薛德升等(2018)基于中資商業銀行的世界城市網絡研究同樣發現,中國大陸城市與境外世界城市的聯系顯著增強,呈現出向頂級金融中心以及北美、西歐和亞太3個核心地區集中的趨勢,并逐漸向全球范圍延伸。
二是聚焦于多行業企業網絡視角的研究,如尹俊(2011)、Derudder(2013)、趙金麗(2019)等基于銀行、保險、證券等細分行業中大型金融機構總部—分支區位數據研究了國家層面上城市網絡的鏈接關系及時空過程,指出金融聯系視角下城市的網絡連接度與城市的重要性密切相關,城市在網絡中的相對連接率隨著城市重要性的下降而遞減,且銀行業與保險業之間以高層級金融聯系為主,證券業之間多為低層級金融聯系;Pan 等(2017)從APS 企業(如證券公司、律師事務所及會計事務所)在上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IPO)過程中提供服務聯系的視角研究了中國城市網絡的權力地位與層級特征,發現北京、深圳和上海在中國城市網絡中處于戰略主導地位,三者間緊密的合作與競爭關系構成了國家的控制中心和金融中心;Coe 等(2014)將金融引入全球生產網絡的研究中,萃取出全球金融網絡的概念,探討了全球金融網絡與全球生產網絡的互動關系,指出高階商業服務、世界城市和離岸行政區是全球金融網絡的3個核心要素;Brown等(2002)基于中美洲地區的研究發現,部分處在世界城市網絡核心區塊之外的城市,同樣可以通過與紐約、邁阿密等“世界城市”以及“區域性門戶城市”建立服務聯系流,從而連接到世界城市網絡中;Bassens 等(2010)通過對伊斯蘭國家金融機構的全球分支網絡研究發現,其主要金融聯系存在于伊斯蘭國家重要城市之間,以及這些城市與紐約、倫敦等少數頂級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之間。也有學者從區域尺度對金融網絡展開研究,如溫鋒華等(2017)分析了京津冀地區城市金融服務功能集聚與網絡聯系特征,朱惠斌等(2015)揭示了珠三角地區金融網絡的多中心和層級性特征,龍飛揚等(2019)探究了江蘇省金融聯系網絡的時空演化規律及其影響因素。上述研究加深了對金融網絡發展規律的認識,但總體上,現有文獻更多是基于單一行業視角或提取高層級聯系的多行業視角,對金融網絡生長發育作用機理的解析力度稍顯不足,基于金融全行業視角城市網絡的構建以及城市網絡發育機理的探討亟待加強。
鑒于此,本文借鑒世界城市網絡的分析方法,利用中國金融業企業總部—分支機構數據,探討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演化規律及其作用機理。以期豐富和加深對中國城市網絡結構特征的理解,補充和完善金融地理學的相關研究,為城市網絡理論體系的構建與發展提供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城市間金融網絡的構建
采用Taylor 等(2004)提出的鏈鎖網絡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界定城市間鏈接關系,即如果企業s在城市i和城市j同時設立分支機構,則認為城市i和城市j之間存在經濟聯系。金融業企業樣本共計839家,包括193家銀行(含6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12家股份制銀行、134家城市商業銀行和41家外資法人銀行)、236家保險公司、133家證券公司、128 家基金公司和149 家期貨公司。其中,銀行和保險公司名單來源于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②http://www.cbirc.gov.cn/,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期貨公司名單來源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③http://www.csrc.gov.cn/。金融業企業分支機構的數據主要根據“啟信寶”網站④https://www.qixin.com/提供的關系圖譜整理,共計155 917家,并結合各個公司的年報數據進行了校準,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城市樣本為中國大陸285個地級行政區,不包括30 個自治州、8 個地區、3 個盟以及三沙市等8個缺乏完整屬性數據的城市。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由285 個城市和839 家金融業企業組成的2-mode 服務價值矩陣V。矩陣V中的值vis為企業s在城市i的服務值,參照Taylor等(2004)的做法,將服務值劃分為5個等級,每個等級機構依據其重要性進行區間賦分。其中,總部為4,省級分支為3,市級分支為2,營業部為1,無分支機構為0。
鏈鎖網絡模型的關鍵在于其映射功能,通過企業作為中介,可以將2-mode的城市-企業關系矩陣(285城市×839企業)轉化為1-mode的城市-城市關系矩陣(285城市×285城市)。由此得到城市i和城市j之間的網絡連通度(Taylor et al.,2004):

式中:vis和vjs分別代表企業s在城市i和城市j的服務值。基于金融業企業和其分支機構的成立時間,可以建立多個年份的城市關系矩陣,選取2001 和2019年2個時間斷面構建城市間金融網絡,用以揭示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空間格局和演化特征。
1.2 金融網絡空間結構的分析方法
1.2.1 連通度 城市i的總連通度計算公式為(Taylor et al.,2004):

式中:CDCi-j表示城市i和城市j之間的網絡連通度,因為城市i最多有n-1 個這樣的連接,對城市i與其他所有城市之間的聯系值進行加總,可以得到城市i的總連通度。
1.2.2k-核k-核是建立在點度數基礎上的凝聚子群分析方法:如果一個子圖是k-核凝聚子群,則該子圖中每個節點(城市)都至少與該子圖中的其他k個節點(城市)保持聯系。本文k-核凝聚子群分析建立在2019年的二值對稱矩陣的基礎上,為此以網絡平均密度作為截斷值對285×285無向多值矩陣進行二值化處理。k-核作為凝聚子群的一種分析方法,其優勢在于可以根據不同的k值得出不同的k-核凝聚子群,便于揭示節點(城市)間鏈接強度的分層結構特征(盛科榮等,2019)。
1.2.3 核心—邊緣方法 核心—邊緣結構分析可以根據節點聯系的緊密程度將網絡劃分為聯系緊密的核心區塊與聯系稀疏的邊緣區塊。采用Borgatti 等(1999)提出的離散模型識別城市網絡的核心—邊緣結構,離散模型同樣建立在二值矩陣的基礎上。離散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尋找一個二值的模式矩陣,使得二值的觀測矩陣和模式矩陣的相關系數達到最大。估計觀測矩陣與模式矩陣相關性的方法為:

式中:aij表示在觀測矩陣中城市i和城市j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如果存在關系,則aij= 1,否則aij= 0;δij表示模式矩陣中城市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如果存在關系,則δij= 1,否則δij= 0;ci(cj)表示城市i(j)被分配到的區塊(核心或邊緣)。當觀測到的網絡結構與理想的模式矩陣的相關系數達到最大時,即當ρ值給出最高的z分值時,可以識別出城市的網絡地位,從而將網絡結構劃分為核心區塊和邊緣區塊兩部分。
核心度的計算基于連續型的核心—邊緣結構模型(Borgatti et al.,1999),模式矩陣定義為:

式中:c代表每一個節點核心度的非負向量。核心度的范圍是0~1,核心度越大,意味著城市在網絡中擁有的權力越大。
1.3 金融網絡影響因素的計量方法
采用非參數檢驗方法中的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回歸分析方法定量識別城市間金融網絡的影響因素。與傳統的OLS方法相比,QAP回歸分析方法無需滿足自變量之間相互獨立的前提條件,能較好地處理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其結果也更加有效和穩健,因而更加適用于以“關系型數據”為基礎的假設檢驗(高鵬等,2019)。具體分析步驟為:首先,對被解釋變量矩陣和解釋變量矩陣對應的長向量元素進行常規的多元回歸分析,得到實際參數估計值和判定系數R2;其次,同時隨機置換解釋變量矩陣的各行與各列,重新進行估計,保留所有的估計系數和判定系數R2;最后,多次重復上述置換步驟,計算隨機置換次數中大于或等于第一步計算得到的實際參數估計值的比例,從而估計統計量的標準誤,完成顯著性檢驗(邵漢華等,2018;馮穎等,2020)。
2 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空間格局
2.1 金融網絡的中心性體系呈現空間指向和路徑依賴的特征
從圖1可以看出,網絡連通度較高的城市大多數是區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傳統意義上的權力中心,具有顯著的空間指向性,如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天津,長三角城市群的上海、蘇州、杭州,珠三角城市群的廣州、佛山、深圳,成渝城市群的成都、重慶,遼中南城市群的大連、沈陽,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漢、長沙,山東半島城市群的青島、濟南以及海峽西岸城市群的廈門、福州。這種權力格局的演化呈現路徑依賴的特征,即2001年網絡連通度較高的城市在2019 年也具有較高的網絡連通度:2001-2019年,僅有佛山1個城市退出了網絡連通度排名前10 位,而深圳進入了網絡連通度排名前10 位(表1)。西部地區城市(除了昆明、烏魯木齊等個別城市以外)的網絡連通度明顯偏低,說明這些城市在金融網絡權力中處于邊緣位置。進一步構建首位度、10 城市指數、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3 個指標測度城市網絡權力的集中度,這3 個指標分別由2001 年的0.026 5、0.194 0、0.007 8 演化為2019 年的0.024 4、0.166 1、0.006 6,反映了中國金融網絡呈明顯集中但緩慢下降的中心勢趨向。

圖1 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空間格局(網絡連通度>100 000)Fig.1 The linkage patterns of urban financial network in China(city-dyad connectivity above 100,000)

表1 金融網絡的層級分化Table 1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of financial network
2.2 金融網絡的鏈接關系呈現縱深關聯和層級分化的特征
隨著金融業企業設立越來越多的分支機構,金融網絡的關聯性得到提高:2001-2019 年,網絡密度由6 360.39 增加到14 600.65;原有的40 470個城市對之間的鏈接關系得到強化,聯系值總量由257 405 079 增加到590 888 553。與此同時,城市間金融網絡的可達性也在不斷提升,網絡平均路徑長度、 緊湊度(compactness) 和離散度(breadth)分別由2001 年的2.000、0.502、0.498 變化為2019年的1.947、0.527、0.473。k-核分析結果表明(表2),金融網絡存在5種分區:6-核子群由北京、上海、深圳等11個城市構成,5-核子群由18個城市構成——包括6-核的11個城市以及大連、寧波等7 個網絡連通度相對較低的城市,3-核子群由24個城市構成——包括5-核的18個城市以及長沙、昆明等6 個網絡連通度更低的城市,以此類推,2-核子群共有30個城市,1-核子群共有34個城市。可以看出,k-核子群呈現“金字塔”式的分布特征,度數較低的k-核子群逐層遞減式地構成度數較高的k-核子群,這意味著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鏈接強度存在明顯的層級分化,并且這種特征將隨著金融業企業分支機構的設立持續呈現。

表2 k-核的分析結果Table 2 Results of k-cores analysis
2.3 金融網絡的核心—邊緣結構呈現逐漸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
從2001-2019 年,核心地位的城市數量由17個擴張到25個(表3)。核心地位城市的演化呈現2個顯著特征:一是核心城市增長同樣也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那些長期處于核心地位的城市傾向于一直保持著核心地位:2001年核心地位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重慶、廣州等17 個城市,2019 年的核心城市中增加了南京、昆明、青島等8個城市,這意味著金融業的發展強化了現有中心的地位,并開始向外逐步擴張。二是核心地位的城市也呈現等級次序的分化,北京和上海的核心度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北京是全國的政治決策中心,吸引了包括四大國有銀行在內的142家金融業企業的集聚,上海是交通銀行、太平洋保險、國泰君安等182家金融業企業總部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北京和上海承擔著全國性金融服務樞紐城市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核心區塊的城市數量是增加的,但城市的核心度大多是降低的,這可能意味著城市網絡權力的分布轉向功能性的多中心格局。

表3 金融網絡的核心—邊緣結構Table 3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of financial network
3 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影響因素
3.1 變量選取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2019年金融網絡關系矩陣,具體包括多值無向金融網絡關系矩陣和二值無向金融網絡關系矩陣2種類型,其中二值無向金融網絡關系矩陣通過對多值無向金融網絡關系矩陣采用金融網絡平均密度為截斷值進行二值化處理獲得,用以檢驗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在基于鏈鎖網絡模型構建的金融網絡中,城市網絡關系起源于金融業企業總部和分支機構之間的經濟聯系,因此金融機構不同地理位置的區位選擇行為構成理解金融網絡關聯格局的微觀基礎。Porteous(1995)的信息腹地理論(the information hinterland theory)提供了一個理解金融機構區位選擇的綜合分析框架。根據該理論,信息流的可達性是影響金融機構區位選擇以及金融中心發育過程的關鍵因素。這種可達性可能受先天的地理區位優勢影響,但同樣也會被后天形成的城市屬性聯系所改變,如市場潛力、政治資源、知識資本、經濟開放、交通聯系、地理區位等。一方面,金融機構往往持有大量利率敏感型資產,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行業條件、公司情況等都會影響公司的預期現金流和投資者的必要收益率,從而影響金融機構的利潤,這要求金融機構接近規章信息的發源地。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的收入來源有投資銀行業務、經紀業務、保險業務等,金融機構必須和發行公司、投資者之間保持密切的聯系,這要求金融機構接近規模較大的市場信息來源地。因此,規章信息、市場信息的空間差異以及影響信息流傳遞的因素從根本上塑造著金融網絡的關聯格局。
從這個思路出發,選取7種解釋變量:1)市場潛力(value),以城市中所擁有的所有A 股上市公司的總市值(包括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對數計量,用以檢驗一個有著較大市場潛力的城市是否會像新經濟地理理論所指出的更容易集聚金融服務活動,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⑤https://www.wind.com.cn。;2)政治資源(capital),采用城市行政級別虛擬變量來計量,用以檢驗城市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規章信息的可及性)對金融網絡關聯格局的影響,其中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均賦值為1,其他城市賦值為0;3)知識資本(knowledge),采用全市專利授權數(件)計量,用以測度城市的創新能力對金融網絡關聯格局的影響,數據來自2019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司,2020);4)經濟開放度(open),采用城市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對數計量,用以檢驗國際資本流動中的經濟地理位置對城市金融網絡關聯格局的影響,數據來自201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5)空間距離(distance),以每一對城市之間的歐式距離(km)計量,用以表征地方空間中的物理距離,根據ArcGIS軟件計算得到;6)東部地區虛擬變量(east),將東部地區的城市編碼為1,其他地區的城市編碼為0,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11個省(市);7)網絡時間滯后項(lag2001),采用2001年的金融網絡關系矩陣刻畫,用以俘獲前期金融網絡關系格局對當期金融網絡關系格局的影響。
QAP回歸分析建立在關系矩陣的基礎上,城市層面的屬性指標需要轉換為城市間屬性關系矩陣。其中,政治資源、東部地區虛擬變量按照最小值方法直接轉化為二值關系矩陣:如果城市i或城市j的編碼為0,則屬性關系矩陣的i行j列的值為0,否則編碼為1;市場潛力、知識資本、經濟開放度和空間距離首先以平均值為截斷值進行二值化處理(高于平均值的數值重新編碼為1,低于平均值的編碼為0),然后按照上述方法轉換為屬性關系鄰接矩陣。
3.2 結果分析
表4顯示了QAP回歸方程的分析結果,提供了市場潛力、政治資源、知識資本、經濟開放度等因素影響金融網絡格局的直接證據。總體上,回歸分析取得了較好的擬合效果,基本結論有:

表4 QAP回歸分析結果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QAP regressions
市場潛力(value)、政治資源(capital)、知識資本(knowledge)和經濟開放度(open)的系數均為正值且顯著,說明金融網絡更多地建立在市場潛力較大、政治資源豐富、知識資本密集和經濟開放度較高的城市之間。金融業企業提供的財富管理、風險投資等業務大多是非標準化并且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產品,因此對金融業企業而言,靠近更大的經濟腹地并與客戶保持良好的溝通十分重要(Head et al.,2004)。這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新經濟地理學早期的研究成果,反映出“流動空間”背景下市場潛力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政治資源豐富的權力中心是各種類型“規章信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監督管理等)的發源地,對于金融機構總部的區位選擇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這與Pan 等(2017)的研究結果一致,他們發現中國城市在金融網絡中的等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城市在政治等級體系中所處的地位。
知識資本(knowledge)所表征的創新能力是吸引金融機構集聚的重要因素,創新能力越高的城市,產業化發展對直接融資的需求越活躍。近些年來,為創新型企業提供長期的融資支持與上市輔導成為中信證券等大型券商的重要盈利來源,以風險投資公司、證券公司為核心的金融中介已經成為區域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商直接投資在金融網絡的發育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城市承擔著外資進入中國的門戶功能,這同時也會吸引大量金融業企業的集聚。這一結論呼應了Porteous(1995)的研究,他發現國際資本在塑造澳大利亞和加拿大2個擁有全球最高外資規模的發達經濟體的金融中心過程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
空間距離(distance)的系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空間距離是金融網絡生長發育的限制因素,即金融業企業分支機構的設立受到地理距離的影響,這意味在“流動空間”背景下“距離專制”仍然是城市網絡關系生長發育的制約因素。Zhao 等(2017)的研究也表明,地理位置鄰近的城市之間傾向于建立更為密切的鏈接關系,組織間的合作概率受到潛在伙伴地理位置鄰近性的強烈影響。
東部地區虛擬變量(east)的系數為正值且顯著,表明具有更優越地理區位的城市之間傾向于產生更多的鏈接關系。這一結果與城市接收信息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區位條件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如早期的河流航運港口,后來的鐵路、公路樞紐以及今天的航空、衛星通訊(Laulajainen,2003)。大量的經驗也表明,便捷的交通條件是金融服務業空間集聚的重要因素。
網絡時間滯后項(lag2001)的系數為正值且顯著,說明長期存在較多鏈接關系的城市之間傾向于進一步提高鏈接關系的強度,而曾經缺乏經濟聯系的城市之間也將繼續維持較少的鏈接關系。對于金融業企業而言,方便獲取有價值的信息流(valuable information flow)是企業區位選擇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選址初期,一旦企業在特定城市布局,在信息流共享、風險資本集聚、投資成本降低等因素的作用下,循環累積的因果關系就開始發揮作用,吸引更多的金融業企業集聚,這個過程不僅使得曾經具有較高網絡連通度的城市獲得了更高的權力或威望,還進一步強化了城市之間已經建立的鏈接關系。
4 討論
結合金融網絡鏈接關系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嘗試提出一個金融網絡發育機理綜合分析框架,用以解析金融網絡空間增長的影響因素和動力過程(圖2)。

圖2 金融網絡發育機理分析框架Fig.2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financial network growth
在本文分析框架中,金融管制放松下的金融企業區位選擇行為是理解城市網絡空間結構的邏輯起點。由于非標準信息、信息不對稱等在金融市場中大量存在,而未預期的利好信息將抬高金融機構的利潤,因此在市場規模、政治權力、區位條件、創新能力等維度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城市吸引了大量金融企業集聚。這種微觀層面上的金融企業區位選擇行為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以擇優鏈接、地理鄰近、空間集聚等為主要特征的城市鏈接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城市間的網絡關系取決于城市所有權優勢和城市區位優勢之間的匹配。這些動力過程推動著金融網絡自組織系統的有序演化,形成了日益復雜的城市網絡空間結構,如權力等級、網絡腹地、功能分工、凝聚子群、核心—邊緣等。城市網絡的發展又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信息溢出等途徑提高市場運行效率,這將進一步推動金融企業網絡的發展,從而形成金融企業網絡和城市網絡的互動過程。但城市網絡的發展也將放大城市之間(特別是總部城市和分支機構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這對網絡化發展環境下的城市治理體系和政策設計提出新的要求。
根據本文分析框架,金融網絡的發育存在3種動力機制。1)擇優鏈接機制。這個過程可以理解為金融業企業區位選擇對信息流依賴性的可觀測結果:市場潛力較大、政治資源豐富、知識資本密集、經濟開放度較高的城市擁有更好的信息和政策優勢,能夠吸引更多高素質的勞動力和投資導向型的資本,從而使得城市擁有更大的經濟規模,并逐步將傳統城市體系中的信息流優勢轉化為網絡競爭優勢。2)地理鄰近效應。信息的流動性受到城市地理區位和網絡可達性的強烈約束,而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壓縮了城市間的時空距離并顯著降低了交易活動的成本,有助于構成日益復雜中國城市網絡體系。在各類資源要素流動性日益增強的背景下,時間距離鄰近性的效應在增強,具有更好網絡可達性的城市將呈現更高的競爭力。3)空間集聚效應。這個過程表現為金融業企業區位選擇過程中的集聚行為:一旦某種類型的金融機構選擇布局在特定城市,在信息流共享、風險資本集聚、投資成本降低等因素的作用下,將會吸引更多相同類型的金融活動集聚,即歷史上形成的城市網絡關系深刻影響未來城市網絡關系的發展。
本文分析結果有助于金融地理學中2個理論問題的探討:1)證實了信息腹地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基于金融業企業總部—分支機構聯系構建的城市網絡反映了金融業企業與高質量市場信息空間匹配的內在要求,研究發現政治資源對于城市間金融網絡關系的生長發育具有積極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Porteous(1995)、Thrift(2000)的結論,即信息腹地的規模與發展前景是吸引金融機構集聚的關鍵因素,金融市場的“隨機游走”特征使得金融機構傾向于聚集到具備一定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的高質量信息腹地,并由此發展為金融中心。2)證實了信息外部性理論在塑造金融中心時發揮的主導作用。由于市場上充斥著大量的非標準化信息,信息生產者和信息消費者搜集處理信息的成本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提高,非標準化信息的潛在效應和質量會隨之降低,因此金融機構首先會將一些規模較大的決策、研究型部門設立在非標準化信息的密集地,在空間集聚效應的作用下,更多的金融機構匯聚于此,這種巨大的“信息外部性”使得金融機構在信息流的倍增中獲益,并由此進行更多的信息套利活動。
5 結論與建議
基于中國金融業企業總部—分支機構數據,利用鏈鎖網絡模型和二次指派程序,系統解析了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空間演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
1)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呈現顯著關聯、層級分化的核心—邊緣結構特征。近20年來金融網絡的關聯程度顯著增強,城市對之間的鏈接關系不斷強化,以北京、上海、深圳、重慶為代表的城市群主要城市構成了金融網絡的核心節點,使得金融網絡的中心性體系具有明顯的空間指向和路徑依賴特征;城市間鏈接關系向縱深化發展的同時也呈現層級分化的結構特征,并且這種特征會隨著金融業企業分支機構的設立持續存在;城市的網絡地位不斷分化,核心—邊緣結構分析揭示了一個高度結構化的核心聚類和分布廣泛的邊緣聚類共存的金融網絡體系。
2)關鍵資源、空間距離、區位條件和歷史基礎是影響金融網絡空間格局的關鍵因素。市場潛力、政治資源、知識資本和經濟開放度深刻影響著城市間鏈接強度,鏈接關系更傾向于發生在那些市場潛力較大、政治資源豐富、知識資本密集和經濟開放度較高的城市之間;空間距離對金融網絡的約束作用較為明顯,金融活動的集聚性特征使得金融業企業分支機構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距離的影響;以東部地區虛擬變量表征的地理鄰近性對城市網絡關系強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長期存在較多鏈接關系的城市之間傾向于進一步提高鏈接關系的強度,而曾經缺乏經濟聯系的城市之間也將繼續維持著較少的鏈接關系。
據此,對未來中國城市化政策提出2點建議:
1)高度重視網絡環境下的城市間發展差距,支持城市在金融網絡中選擇差異化的發展路徑。金融網絡的鏈接關系具有明顯的層級結構特征,關聯結構的縱深發展傾向于擴大而不是縮小城市之間的經濟差距,這意味著擁有著資源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城市將具有更高的網絡資源利用和支配能力,而市場規模較小、政治地位較低、知識資本薄弱的城市將進一步被邊緣化。未來應順應城市網絡權力分化的發展趨勢,支持北京、上海、深圳建設全國性的金融服務樞紐城市,支持成都、南京、青島、大連建設區域性的金融中心城市,促進其他城市選擇適合自身的功能定位,建立起功能完善的金融網絡體系,實現金融企業網絡和城市網絡的良性互動。
2)盡快完善城市網絡層面的治理體系,充分發揮金融網絡對城市經濟增長的供給引導功能。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發展使得城市之間的聯系突破了傳統地方空間中以地理鄰近性界定的腹地范圍,未來要在完善區域城市群層面治理體系的同時,順應鏈接關系擇優選擇的規律,在更大空間尺度上支持資源互補、相互依賴的城市通過城市委員會、專題項目共建等多種形式開展合作,提升網絡中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網絡的發展過程中,城市的稟賦優勢決定了城市的網絡地位,反過來城市的網絡地位也會改善城市的經濟績效,因此應積極促進金融中心城市建設和實體經濟發展的有效結合,使得金融網絡的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城市的資金需求,更好地促進城市的創新發展。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采用多個行業的金融業企業網絡數據(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基金業和期貨業),全面系統地揭示了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時空格局;利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假設檢驗方法,定量識別和測度了金融網絡的影響因素,探索性地提出了一個理解金融網絡生長發育機理和過程的概念框架。當然,本文也存在不足之處。如限于計量方法與篇幅,未能定量解析內生網絡結構效應對于金融網絡鏈接關系的影響,各個行業視角下金融網絡空間結構的對比分析也稍顯不足。未來應綜合考慮城市屬性變量和內生結構效應變量對于城市間鏈接強度和關系廣度的影響,開展分層次、多時序的城市網絡結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