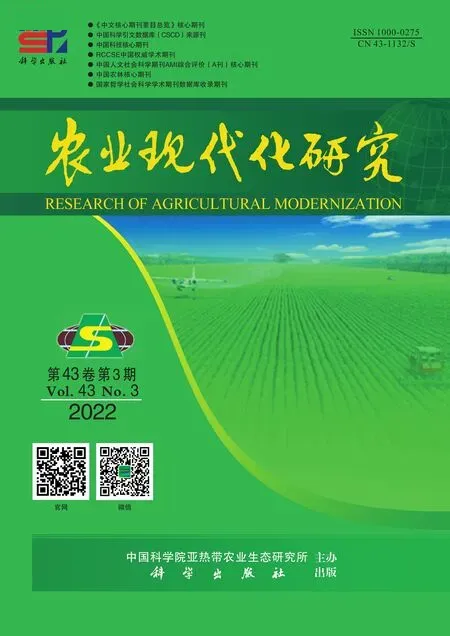亞熱帶丘陵區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特征與水體面源 污染關系研究
彭健 ,李希 ,李裕元 ,王浩 ,孟岑,曾睿,王棟
(1. 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亞熱帶農業生態過程重點實驗室,湖南 長沙 410125;2.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3. 湖南艾布魯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長沙 410000)
隨著點源污染不斷得到有效控制,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已成為我國農村環境的最突出問題[1]。面源污染量大面廣,污染源分散度高,對水體污染持續性較強[2],容易導致底棲動物功能、豐富度和群落結構的改變,因此,水體健康和底棲動物的相關研究備受國內外學者關注[3],探討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特征與水體面源污染的關系對于池塘水體面源污染的預防與修復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目前我國農村地區以污染物遷移方向為主線、以小流域或集水區為單元開展綜合生態治理是治理面源污染的重要方向[4-5]。池塘是我國南方地區十分常見的小型水體[6-7],作為小流域水文循環的重要節點,對于調蓄地表經流、抗旱和農業面源污染物消納轉化均具有重要作用[8]。同時,池塘水體水質的變化也會引起包含底棲動物在內的水生生態系統特征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池塘的生態功能。
底棲動物作為池塘等濕地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重要參與者,是池塘濕地生態功能健康的重要標志之一[9],在水生生態系統中扮演消費者角色,一方面以細菌、有機碎屑顆粒和底棲藻類為食,促進水體有機物降解,另一方面可為魚類提供天然餌料,加速池塘生態系統營養物質的遷移轉化[10]。由于底棲動物對環境變化反應敏感,當水體受到污染時,其群落結構及多樣性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可對濕地系統水質變化起到指示作用[11],因此也受到水環境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目前針對河流水系[12]、湖泊[13]、水庫[14]等大型水體底棲動物的研究常見報道,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密切相關的小型水體中底棲動物的研究則相對集中于人工濕地[15],人工濕地與天然池塘之間的底棲動物群落特征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進一步研究天然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特征可以反映一個地區池塘水體面源污染狀況,建立具有一定指示作用的生物指標體系。為此,本研究于2020 年7 月(夏季)和12月(冬季)對亞熱帶丘陵區金井小流域15 口典型池塘底棲動物物種、豐度、生物量和水體污染情況進行了現場采樣調查,通過分析兩季池塘水體污染情況和相關底棲動物的群落特征,探討了底棲動物群落特征隨季節和水體污染程度變化的關系,研究結果可為池塘水體面源污染的治理修復提供參考依據和數據支撐。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與采樣位點設置
研究區位于湖南省長沙縣金井鎮,地理坐標范圍28°30′~28°39′ N、113°18′~113°29′ E(圖1),區內平均海拔98.3 m,為典型丘陵地貌,屬于典型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多年平均氣溫17.1 ℃,全年無霜期274 d,日照時數1 663 h,熱量充足,多年平均降水量1 394.6 mm,主要集中于4—7 月份。當地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有農田(36.47%)、茶園(3.40%)、林地(49.01%)等[16]。利用研究區高分辨率影像(2016年12 月,0.5 m 分辨率),采用ArcGIS 軟件完成研究區內森林、農田、居民區、池塘、水庫和道路等土地利用要素的目視解譯與矢量圖層輸出,按影像解譯結果,該小流域池塘數量有2 012 個,密度高達19 個/km2。課題組定期監測其中142 個池塘的水質變化,通過實地調查,獲取池塘周邊景觀類型、池塘經營管理(是否養魚)和池塘周邊污染物輸入來源、綜合水質情況等基本信息,從142 個池塘中挑選15 個水質狀況、污染物來源、分布區域和經營模式等有顯著差異的典型池塘(平均水深約3 m)進行底棲動物群落調查與采樣分析,采樣點分布見圖1。
1.2 池塘底棲動物調查
分別于2020 年7 月(夏季)和12 月(冬季)開展兩次底棲動物的調查采樣分析,其中底棲動物調查采用1/16 m2彼得森采泥器,每口池塘采用五點取樣法采集底泥樣,泥樣當即用60 目尼龍網篩清洗后倒入采樣瓶,瓶中加入10%甲醛密封保存后帶回實驗室,再用60 目尼龍網篩在自來水下沖洗,將甲醛洗凈后將網篩內的剩余物倒入解剖盤中,用鑷子將底棲動物樣本逐一撿出,放入盛有80%乙醇溶液的離心管中,隨后在光學顯微鏡下逐個進行物種鑒定和分類計數,并用濾紙將底棲動物表面水分吸干后在萬分之一天平上稱重,最終匯總記錄結果并換算成單位面積的個體數量即豐度(ind/m2)和鮮重質量即生物量(g/m2)[17]。
1.3 水樣采集與測定
在進行底棲動物調查的同時采集水樣并帶回室內進行相關水質指標的分析,部分水體理化指標現場實時測定。用哈希便攜式水質分析儀(型號:HQ40d)測定水溫(T)、酸堿度(pH)和溶解氧(DO),用雷磁DDB-303A 便攜式電導率儀測定電導率(EC)。
水質指標測定方法按照《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第4 版)進行。氨氮(NH4+-N)、硝態氮 (NO3--N)和溶解態有機碳(DOC)的測定方法為將水樣抽濾過0.45 μm 膜后,取濾液直接上流動注射儀(AA3,德國SEAL 公司)和TOC 分析儀(島津Vwp,日本)測定;總氮(TN)采用堿性過硫酸鉀消解后用流動注射儀(AA3,德國SEAL 公司)測定;總磷(TP)采用過硫酸鉀消解后,用鉬酸銨分光光度法測定[18]。
1.4 數據處理與計算
底棲動物群落特征指數采用優勢度指數(Y)確定池塘底棲動物的優勢物種;采用單位面積底棲動物的數量(豐度,ind/m2)和生物量(g/m2)來評價底棲動物的數量特征;采用Shannon-Weiner 多樣性指數(H ′)、Margalef 豐富度指數(D)、Pielou均勻度指數(J)分析底棲動物的多樣性特征。各主要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Y 為優勢度指數,當Y >0.02 時,確定該物種為優勢種;Ai為相對豐度,即種i 的個體數量占總物種個體數量的比例;Fi為物種i 出現的頻率;S為總的物種數目。
水質健康評價參照有關監測技術規范對相關水質參數進行限定,本研究中pH 的限定范圍取6.50~8.50,處于此區間內為合格;DO 限定值取5 mg/L,高于5 mg/L 為合格;NH4+-N、NO3--N、TN、TP 和DOC 的限定值分別取1.00 mg/L、1.00 mg/L、1.00 mg/L、0.20 mg/L 和6.00 mg/L。評價方法依據農用水源環境質量監測技術規范[19],采用單項污染指數和負荷比對監測參數進行單項評價,再通過綜合污染指數對水體環境質量進行整體評價。單項污染指數計算公式為:

式中:Pi為水環境中污染物i 的污染指數;Ci為水環境中污染物i 的實測值;C0為水環境中污染物的限量標準值。根據該計算方法,為了便于累積計算比較,需對Pi數據進行標準化計算:當Pi≤1 時表示水環境未受污染,指標合格,標準化值Ni=Pi;當Pi>1 時,表示水環境受到污染,指標不合格,標準化值Ni= 1.0+5×lgPi,由此,在單項污染指數評價的基礎上,采用兼顧單項污染指數最大值和平均值的綜合污染指數Pj進行評價,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Nmaxi為標準化的最大單項污染指數,Navei為標準化的平均單項污染指數。依據水體環境綜合污染指數,可將池塘水質狀況分為5 個等級(表1),對所研究池塘水質的污染程度進行評價。

表1 水體綜合污染指數分級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of waters
1.5 數據分析
運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來檢驗不同類型池塘環境因子、底棲動物群落特征差異的顯著性,采用Duncan’s 多重比較檢驗組間差異。采用皮爾遜相關分析來檢驗底棲動物種類數、不同類群密度和生物量與主要環境因子的相關性,如果P <0.05,則認為有顯著相關關系,并對底棲動物與環境因子間進行主成分分析(PCA)。以上所有分析在SPSS 21.0 軟件中完成。使用CANOCO 5 進行冗余分析(RDA)。
2 結果與分析
2.1 池塘水體污染程度與分類
對15 個調查池塘兩個觀測季節綜合污染指數的計算結果表明,水體污染均達到輕污染程度以上(Pj>1,圖2),研究區池塘水體主要污染物平均值為3.03,超出警戒水平。總體上,池塘冬季水體污染程度明顯高于夏季,4、6 和13~15 號池塘冬季污染程度有所降低,區域內夏季高溫多雨,冬季低溫少雨,降雨可能是導致兩季污染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13~15 號池塘可能由于周邊地理環境屬于林地而影響了地表徑流,導致夏季污染程度反而高于冬季,而4 號和6 號池塘周邊為居民地,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根據實際調查結果,結合水體污染指數分級,可將15 個池塘劃分為3 類,即輕度污染(綜合污染指數1~2 級):夏季7~12 號塘,冬季7 號塘和13 號塘;中度污染(綜合污染指數3 級):夏季1~3 號池塘,冬季11、14 和15 號塘;重度污染(綜合污染指數>3 級):夏季4~6 號塘和13~15 號塘,冬季1~6、8、9、10 和12 號塘。

圖2 水環境綜合污染指數Fig. 2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of water environment
根據池塘分類結果,參照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 3838—2002),金井河小流域池塘水體總磷測定結果一般可達到地表水Ⅱ類~Ⅲ類之間,兩季平均總磷含量僅為0.09 mg/L,而總氮一般為Ⅴ類或劣Ⅴ類,夏季總氮平均含量為3.98 mg/L,地表水Ⅳ類超標率達到73.3%,冬季總氮和氨氮平均含量甚至高達6.21 mg/L 和4.59 mg/L,總氮和氨氮地表水Ⅴ類超標率分別為100%和86%以上(表2),表明 總氮和氨氮是金井河流域池塘水體污染的主要指標。

表2 不同污染程度池塘氮磷指標Table 2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dexes of pond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degrees
2.2 底棲動物群落特征
對底棲動物種類的調查結果顯示,2 個季節共采集底棲動物22 種,包括節肢動物、環節動物和軟體動物三大類群,節肢動物種類14 種,占群落總種數64%,軟體動物和環節動物種數均為4 種,群落結構相對較為簡單(表3)。兩季物種數略有差異,其中夏季略多為16 種,冬季略少為14 種。總體而言,研究區池塘中主要以節肢動物和環節動物為主,軟體動物數目和種類均較少,耐污性較強的霍甫水絲蚓、黃色羽搖蚊和中國長足搖蚊在研究區域池塘中占據絕對優勢。
底棲動物豐度調查結果顯示,夏季和冬季污染程度較低的輕污染池塘均具有較高的底棲動物豐度,平均分別為930 ind/m2和1 808 ind/m2(圖3), 隨污染程度的升高底棲動物豐度呈顯著下降的趨勢(P<0.05),重污染池塘豐度平均僅為251 ind/m2(夏季)和352 ind/m2(冬季)。總體而言,冬季平均豐度(913 ind/m2)顯著高于夏季(544 ind/m2)。底棲動物生物量的變化(圖3)與豐度表現為相同的趨勢,冬季平均生物量(6.67 g/m2)總體上顯著高于夏季(1.48 g/m2,P <0.05),且隨污染程度增加底棲動物生物量呈顯著增加趨勢(P <0.05),但冬季中污染和重污染之間生物量差異不顯著(P >0.05)。

表3 不同池塘冬夏兩季底棲動物物種及優勢度(Y)Table 3 Species and dominance (Y) of zoobenthos in different ponds in winter and summer

圖3 池塘不同污染程度下底棲動物豐度和生物量Fig. 3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zoobentho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levels in ponds

圖4 池塘不同污染程度下底棲動物的相對豐度Fig. 4 Relative abundance of zoobentho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levels in ponds
從池塘不同物種底棲動物相對豐度的變化來看(圖4),其受季節影響較大,冬季黃色羽搖蚊和幽蚊相對豐度明顯要低于夏季,而霍甫水絲蚓冬季的相對豐度則顯著增加(P<0.01),庫蠓、蘇氏尾鰓蚓和克拉伯水絲蚓 的相對豐度在冬季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底棲動物相對豐度受污染程度的影響也較大,總體來看,黃色羽搖蚊在中度污染池塘中相對豐度最大,水體污染程度升高會導致其相對豐度的下降。同樣,霍甫水絲蚓在總體污染程度較低的夏季,其相對豐度與污染程度成正比,而在總體污染程度較高的冬季,其相對豐度則與污染程度成反比。蘇氏尾鰓蚓則在冬季重污染程度池塘中相對豐度顯著增加(P<0.01)。
池塘底棲動物多樣性指數的分析結果表明,總體上冬季各項指數均顯著高于夏季(P<0.05,表4),而多樣性指數隨水質變化的趨勢基本一致:Shannon- Weiner 多樣性指數(H′)和Margalef 豐富度指數(D)均隨著池塘水體污染程度的升高呈降低趨勢,而Pielou 均勻度指數(J)變化趨勢不明顯,且三種多樣性指數中除了冬季的物種豐富度指數隨水質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顯著水平以外(P<0.05),其余指標的差異均不顯著(P>0.05)。

表4 不同污染程度池塘底棲動物多樣性指數Table 4 Diversity index of zoobentho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levels in ponds
2.3 底棲動物物種分布與環境因子的相關性分析
對池塘水環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PCA)結果表明,9 個環境因子的累計解釋方差占總方差的75.94%,其中第一(F1)、第二(F2)和第三主成分 (F3)的貢獻率分別為36.19%、21.95%和17.81% (表5),表明9 種環境因子均對底棲動物的組成和分布有較為重要的影響。F1 主要為TN、NH4+-N、TP 的組合,且與三者均呈正荷載;F2 主要為T、pH、DO、NO3--N 組合,與T、DO 呈正荷載,與pH、NO3
--N 呈負荷載;F3 主要為EC 和DOC,均呈正荷載。

表5 環境因子總方差解釋表Table 5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通過前選法和蒙特卡羅檢驗排除貢獻小的因子,進一步對6 種優勢底棲物種(Y>0.02,且出現頻度超過一次的)霍甫水絲蚓、蘇氏尾鰓蚓、黃色羽搖蚊、中國長足搖蚊、幽蚊、庫蠓的生物量與環境因子間進行RDA 分析,結果發現,總解釋變量達到41.39%,其中軸1 和軸2 的解釋率較高,特征值分別為0.150 和0.132,分別解釋了14.99%和13.15%的物種數據方差變異以及34.68%和30.43%的物種與環境關系變異(表6),表明水體環境對底棲動物的豐度、生物量以及優勢度有重要影響。從RDA 排序圖中可知:第一排序軸與N 相關環境因子呈顯著正相關,與DO、T 呈顯著負相關。黃色羽搖蚊與T 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蘇氏尾鰓蚓和霍甫水絲蚓這兩種耐污能力強的物種則與TN、NH4+-N 呈顯著正相關。第一排序軸上顯示最大正值的主要有霍甫水絲蚓、蘇氏尾鰓蚓、中國長足搖蚊和幽蚊等,表明這些物種能夠耐受較高程度污染(圖5)。
3 討論
3.1 典型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特征及其季節變化
本研究發現金井小流域池塘兩季底棲動物物種組成相對簡單,物種多樣性總體上較低,冬季豐度與生物量顯著高于夏季。區內調查已知的底棲動物僅有22 種,物種數目和多樣性均遠低于我國相關區域河流、湖泊等大型水體的調查結果,如韋建福等[20]在廣西南溪河研究發現的大型底棲動物有208種,王丑明等[21]在洞庭湖的研究共鑒定出大型底棲動物58 種,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池塘屬于相對破碎化的微小型生境,相互間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而且池塘與周邊大型水體之間的物種遷移途徑和信息交流機會相對較少[22]。本研究中發現的軟體動物也相對較少,僅有中華圓田螺、銅銹環棱螺、膀胱螺、凸旋螺和小土蝸5 種,且出現頻次較低,均不是優勢種,這與大型湖泊內底棲動物的物種構成有顯著區別,如鄒亮華等[23]對鄱陽湖的研究結果表明,河蜆、銅銹環棱螺和大沼螺在各湖區均占據顯著優勢地位。研究區軟體動物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可能還與池塘水體NH4+-N 濃度總體偏高(0.3~9.0 mg/L,表2)有密切關系,據Ilarri 等[24]的研究,NH4+-N 對底棲動物尤其是軟體動物會產生較高的生物毒性,會導致軟體動物的豐度和生物量下降。

表6 底棲動物群落與環境因子冗余分析(RDA)結果Table 6 Results of redundancy analysis (RDA) of zoobenthos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圖5 底棲動物群落與環境因子冗余分析Fig. 5 Redundancy analysis (RDA) of zoobenthos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金井河流域池塘水體冬季的污染程度總體上明顯高于夏季。研究區屬于典型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雨,冬季低溫少雨,降雨對稀釋區域內池塘水體的污染物濃度有重要作用。申雅莉等[25]對金井河小流域調查發現,該區域池塘TN、TP 濃度呈明顯的季節性變化趨勢,其中雨季較低而旱季較高,這與本研究的觀測結果基本一致,13~15 號池塘冬季綜合污染指數低于夏季,可能是因為這三個池塘周邊環境為林地,與農田相比,林地能夠更好地控制徑流養分流失,緩解地下水污染,有利于農業面源污染的控制[26]。相應地,研究區冬季底棲動物豐度和密度均顯著高于夏季(圖3),其中分布最為廣泛的霍甫水絲蚓和蘇氏尾鰓蚓等耐污種的豐度及生物量均與水體富營養化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圖5),對反映池塘水體的富營養化程度具有明顯的指示作用,其豐度及生物量越大,則水體的富營養化程度就越高,這與國內相關區域的研究結果較一致,如超富營養化水體中霍甫水絲蚓豐度最高可達到10 524 ind/m2[27],而在中、低富營養化水體中僅為27 ind/m2[28],這些均表明面源污染導致的池塘水體富營養化變化對底棲動物物種及生物量的影響程度甚至要高于溫度(季節)變化的影響。水溫主要直接影響搖蚊類、寡毛類水生昆蟲的生長、繁殖和羽化進程[29],導致其在夏季更為活躍,冬季則以幼蟲形態棲息于底泥之中,因此該類底棲動物在冬季的豐度相對較高,這可能主要決定于該類物種生活史與生活習性的本性。但是郭寧寧等[30]對亞熱帶丘陵區淺水人工濕地(水深20 cm 左右)的研究表明,夏、秋季濕地底棲動物的多樣性指數、豐富度指數和均勻度指數。總體上均高于春、冬季,與本文結果不盡一致,表明水深可能也是影響底棲動物多樣性的重要因素,具體影響機理尚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3.2 農業面源污染對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特征的影響
隨污染程度升高,底棲動物豐度呈顯著下降趨勢(P <0.05),多樣性指數和豐富度指數均隨著池塘水體污染程度的升高呈降低趨勢但并未達到統計顯著水平(P >0.05),主要面源污染指標TN、NH4
+-N 可能是影響研究區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特征的最主要因素。李麗娟等[31]對太子河大型底棲動物的研究發現,氮磷等無機污染物進入河流后會導致底棲動物攝食功能群以收集者功能群和濾食者功能群為主,表明底棲動物多樣性受水體污染影響且與污染程度呈負相關。
對池塘底棲動物豐度、生物量、多樣性指數和底棲動物物種分布與池塘水質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均顯示,非季節性分布的霍甫水絲蚓和蘇氏尾鰓蚓這兩種耐污能力較強的物種的豐度和生物量與TN、NH4
+-N 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表明水體總氮與氨氮濃度是影響本區域對底棲動物物種多樣性和群落構成的主導因子,霍甫水絲蚓和蘇氏尾鰓蚓對反映池塘水體的富營養化程度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對于不同的底棲動物,對環境因素變化的響應特征也不盡相同,如郭寧寧等[30]研究發現,水體溶氧(DO)是影響腹足綱底棲動物(如螺類)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寡毛綱(如霍甫水絲蚓)和昆蟲綱(如搖蚊幼蟲)與水體TN、COD 的關系更為密切。
本研究也發現,底棲動物生物量冬季較夏季高,但在水體污染程度由中到高變化時池塘底棲動物生物量的增加則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當水質指標超過耐污種的正響應閾值時,部分耐污種達到了耐受極限而開始減少,如程佩瑄等[32]研究發現,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對水質指示的指標閾值也有相應的變化,不同底棲動物均有其適宜的水質范圍,超出該范圍,其存活能力就會顯著降低。富營養化水體雖然能為底棲動物提供更為豐富的食物來源,但過高的富營養化程度也會導致底泥中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的變化,本研究中主要體現為物種多樣性的顯著降低,同時PCA 分析中發現底棲動物豐度和生物量與pH 呈負荷載,這與蘆康樂[33]對黃河三角洲蘆葦濕地的調查結果較為一致,水體的pH 是影響底棲動物分布的一個重要環境因子,不同的底棲動物,其適宜的pH 不同,因而分布也不同。
3.3 底棲動物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意義
本次調查的池塘主要分布于土地利用方式為農田和茶園的區域,化肥的施用和降雨可造成農業面源污染,導致池塘水體營養鹽濃度總體偏高。區域內池塘底棲動物物種多樣性較低且優勢種均為耐污種,表明了池塘水環境較差的污染現狀,為防止池塘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應加強該區域水體環境的保護和污染治理工作。
底棲動物群落特征與水體污染密切關聯,其作為水生生態系統食物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營養鹽的流動循環和污染物的去除有重要作用[34]。實際調查過程中也發現,污染程度相對較高的池塘水生植物相對較少,因此底棲動物的棲息環境也相對較差。靳聰聰等[35]發現沉水植物的構建可以有效控制農業地區水體中農藥等污染物的濃度,降低其生態風險,有利于恢復底棲動物的多樣性。底棲動物通過移動、攝食和筑穴等生物擾動作用改變沉積物的物理和化學性質,從而影響水生態系統中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田勝艷等[36]研究發現,生物擾動可以促進沉積物顆粒的遷移混合、釋放沉積物中有機物質、改變沉積環境并提高沉積物中有機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從而提高水體有機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因此通過底棲動物添加來強化污染池塘濕地等水體底泥污染的方法也不失為一條有效途徑,一些試驗已經證明了該技術的可行性,如陳桐等[37]在野外進行的圍隔試驗發現,投加螺和蚌的密度為150 g/m2時對水體TN 的去除率可達72.6%,朱明璇等[38]利用水生動植物聯合技術凈化水庫水試驗的研究也表明,水生動植物聯合能取得最佳的水質凈化效果。因此,構建包含底棲動物的復合人工濕地生態系統可能是提升人工濕地污染物消納容量的有效途徑,其作用機理尚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4 結論
對亞熱帶丘陵區典型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的研究表明,該區域池塘中底棲動物多樣性相對較低,共采集到底棲動物22 種,其中以節肢動物居多,耐污性較強的黃色羽搖蚊、霍甫水絲蚓和中華長足搖蚊為主要優勢種。
池塘底棲動物豐度、生物量與水體富營養化程度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同時也受季節變化的顯著影響,其中冬季底棲動物豐度和生物量顯著高于夏季。
不同底棲動物對水環境因子表現出不同的響應特征,黃色羽搖蚊生物量與溫度呈顯著正相關,而霍甫水絲蚓和蘇氏尾鰓蚓生物量則與水體總氮、氨氮呈顯著正相關,霍甫水絲蚓和蘇氏尾鰓蚓的豐度和生物量對于反映該區域池塘水體面源污染狀況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