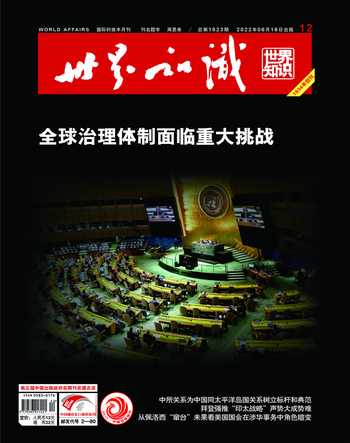構建基于包容性全球化的全球治理體制
盛斌
全球治理是伴隨著全球化與全球性問題而產生的。全球化是全球治理的前提,如果沒有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數據信息的流動,以及沒有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與關聯,也就不會有全球治理。全球性問題是全球治理的對象,諸如貿易投資、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等重大問題必須依靠全球集體行動與共同規則加以應對與解決。
回顧歷史,自187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全球化已歷經了150多年的時間。隨著技術進步大幅度降低交通與通訊等交易成本,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開放與自由的經濟政策,以跨境貿易、資本流動和移民為標志的全球化得到極大推進。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至2008年期間,以中間品貿易、服務外包和垂直直接投資(FDI)為特征的全球價值鏈模式使全球化進入國際化生產的“超級”時代。
全球化面臨嚴重挑戰
然而,全球化的進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從上世紀初到現在共遭受了三次重大沖擊:第一次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45年),第二次是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至新世紀之初,第三次是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當前,全球化仍處于艱難時刻,對全球治理體制與秩序構成了嚴峻挑戰。
從2008年后至今的第三次全球化沖擊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慢全球化”。2008~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從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爆發,蔓延至實體經濟并使其遭受重創,在全球造成“貿易大崩潰”。世界經濟隨之陷入中長期“結構性低迷”——發達國家經濟難以實現“平庸增長”,諸多國家患上“日本病”,而其財政政策空間極其有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十分乏力;金磚國家除中國外呈現出“金磚不金”,一些國家患上“拉美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貧富差距拉大,貨幣危機頻發。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促使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談判停滯不前,多邊主義弱化,“超級全球化”的高光時刻風光不再。
第二階段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公投“脫歐”后的“逆全球化”思潮與行動泛濫。美英等國右翼民粹主義突起,強調本國優先和身份認同,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和移民;發達國家低收入勞工階層以及部分中產階級成為反全球化的主要支持力量,形成與精英階層、高技能勞動力、大型跨國公司等群體的社會分裂和對峙。在這種背景下,多邊主義受到進一步侵蝕,WTO爭端解決機制陷入癱瘓。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重新談判簽署的《美墨加協定》的區域性貿易保護色彩與排他性規則加重。更為嚴重的是,特朗普政府揮舞關稅大棒,發起對中國、歐盟等國家的貿易戰。

由于供應鏈中斷,2022年2月11日,大量的集裝箱積壓在美國新澤西州南科爾尼港口。
第三階段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去全球化”的加速。疫情蔓延與加劇大幅提高了貿易與離岸成本,嚴重降低了貨物、FDI與人員的流動性,全球供應鏈體系遭受破壞,全球價值鏈貿易的重要性顯著降低。同時,“病毒保護主義”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新變種,供應鏈安全成為各國關注的主要目標,尤其是與疫情防護與治療有關的物資與設備生產的供應鏈安全。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紛紛出臺出口管制措施和強化國內供應鏈等政策,跨國公司也相繼做出商業戰略調整,主要表現為本土化(供應鏈回流)、多元化(供應鏈轉移)和近岸化(供應鏈縮短)。全球化回縮的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
第四階段是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引發的“全球化分裂”陰霾。首先,愈演愈烈的地緣政治沖突導致全球結構的分裂格局。以美歐為主體的北約在烏克蘭問題上與俄羅斯對峙;美國糾集英日澳印等國在“印太”地區打造“亞洲北約”,試圖利用臺灣、南海等問題制衡中國。其次,地緣經濟強化了區域內向化趨勢與區域間競合關系。以歐盟(EU)、北美的《美墨加協定》(USMCA)、亞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代表的三大區域價值鏈板塊業已形成,美歐之間通過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加快標準與規則協調,美國拋出“印太”框架企圖對沖中國的“一帶一路”。第三,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分歧在規則競爭領域凸顯。美國極力鼓吹與渲染“價值觀貿易”(強調人權、勞工標準、知識產權、環境、國有企業占比等)、“安全貿易”(政治、意識形態、網絡安全等)與“供應鏈貿易”(減少對中國的過度依賴),試圖搶占貿易新規則與標準的制高點。此外,美國還在全球數字標準與規則領域大做文章,在國內監管(例如隱私、安全、消費者保護、源代碼、算法或加密保護)、跨境數據流動(數據本地化、跨境數字產品征稅)、數字技術標準(互聯網、5G)等方面聯合盟友加快制訂全球規則。
全球化前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中美兩國在全球化問題上分野迥異。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處心積慮打造基于價值觀—安全—供應鏈三位一體的再全球化,其關鍵是突出美國自身的領導力,極力排斥中國。而中國則積極倡導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包容性發展理念的新全球化進程。中國倡導的全球化強調人的全球化,是對資本的全球化的傳統模式的超越。它不同于以往以市場為導向、基于價值理性的單一模式的全球化,而是以發展為導向、基于工具理性、強調包容與多元、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新型全球化。
如何實現新型全球化
首先,必須解決不平等問題。全球化在提高總體效率與福利的同時具有收入分配效應,會形成贏家與輸家,對特定群體——例如進口競爭部門、低技能勞動力、弱勢群體等形成沖擊,雖然其沖擊影響與其帶來的技術進步相比不大,但卻十分容易在政治上得到操縱與渲染。理論與經驗都表明,貿易保護不能根治不平等問題,真正有效的是調整國內政策與改革,包括教育、就業、稅收、再分配與社會安全網絡等。因此,鞏固民族國家的國內治理體系,特別是關注包容、共享與普惠發展是實現新型全球化的基礎與前提。
其次,必須實現廣泛的發展目標。全球化、市場化、自由化只是手段途徑,發展才是終極目標。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要實現效率、公平與風險管理之間的有效平衡,保障促進發展的政策空間和規制主權,探索提出基于發展利益的全球治理規則。
第三,必須維護開放型多邊體制。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孤立主義、霸凌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泛政治化和軍事化聯盟都將破壞多邊體制與和平秩序,以鄰為壑、脫鉤排斥、制裁禁運最終將導致一個沒有贏家的世界。相反,大國應起到引領與表率作用,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貨幣性、技術性與制度性公共產品。中國在此已大有所為,仍大有可為,成為全球新的需求吸收者、全球新的資本提供者、全球價值鏈或供應鏈的核心供給者、新發展治理的倡導者,成為新型全球化的“穩定器”和全球治理的“推進器”。D6005CD9-C747-4538-B9F9-D4182D94BB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