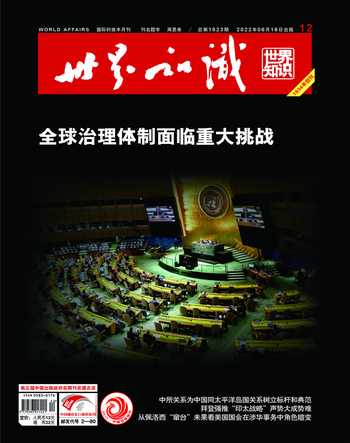從佩洛西“竄臺”未果看美國國會在涉華事務中角色嬗變
刁大明

2022年5月17日,美國副總統兼國會參議長哈里斯(左)與國會眾議長佩洛西(右)共同出席國會為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安排的演講會。
4月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因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取消了次日即將開啟的亞太行程,其中包括擬議4月10日對我國臺灣省的“竄訪”。雖然此“突發”情形暫時擱置了美國聯邦政壇第三號人物向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發起挑釁的惡劣行為,但近年來美國國會日趨主動、活躍地向美對華政策調整施加影響的態勢卻無法令人忽視。這種“活躍”不僅表現為第115屆國會周期啟動以來罕見通過的多項負面涉華法案,也體現在某些國會議員頻繁竄訪臺灣上。
就在佩洛西取消行程一周之后,一個包括國會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在內的兩院兩黨議員代表團就抵達了臺北。5月下旬美總統拜登訪問韓國、日本期間,多位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公開致函白宮,要求在拜登的亞洲行程中“增加臺灣”。這些已經完成的實際舉動與佩洛西沒能實現的行程加在一起,再次說明隨著近年中美關系的劇烈變化,國會在對華政策上的角色正悄然發生著嬗變。
長期以來,中美關系的關注者和研究者一般認為,基于兩國建交以來的歷史經驗,美國國會在這一關系中扮演的角色多為“麻煩制造者”與“負面背景音”。早在1979年1月1日兩國正式建交之時,當時的第96屆美國國會不愿充當卡特白宮的配角,在兩院分別以超過三分之二即足以推翻總統否決的票數,通過了所謂《與臺灣關系法》。這一至今仍貽害無窮的立法行為背后,是華盛頓傳統精英對“圈外人”卡特的不滿,是美國國內兩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美國國內親臺反華勢力游說的結果,也是當時主導美國會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民主黨人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因黨內總統提名爭奪等積怨而對卡特發起的一次政治反擊。
卡特之后的幾任美國總統不約而同地認識到把好對華政策“方向盤”的重要性,不管被擠到“后排座椅”上的國會議員們如何叫囂、滋事,也一定要維護自己在外交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克林頓執政初期,即便對國會議員們將所謂“人權”問題與授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決定相掛鉤的要求有所附和,但仍努力避免將之“立法化”。當然,國會對總統獨攬對華政策“方向盤”的做法也有過“反抗”,比較突出的一次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佩洛西等民主黨人曾極力推動對華濫施制裁,被老布什總統兩次行使否決權,最后以塞入當時的財年授權法案才得以勉強通過。
白宮與國會在對華政策上相對固定的互動模式,塑造了美國國會轉而借助某些特有制度權力和規則安排來施加影響的傾向。最典型的做法是,由某些國會議員提出兩院甚至一院通過即可生效成法、無須提交總統簽署的決議案。這種繞開白宮的行事方式可以在某些特定時段內或某些特定議題上給中美關系制造不和諧音,起到毒化兩國合作氛圍甚至阻斷具體合作事項的作用,當然也算是某些國會議員向長期資助他們的某些特殊利益群體的一種變相“交差”。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隨著聯邦財政立法與債務上限等問題成為國會山的政治斗爭焦點,美國國會某些人轉而又將涉華條款以“修正案”形式塞入新財年的撥款、預算或授權法案,比如2011年被塞入撥款法案的禁止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以任何形式同中方進行交流的“沃爾夫條款”,2012年被塞入授權法案的推動對臺軍售F-16 C/D的相關修正案,等等。這些“明火執仗”插手涉華事務做法的背后邏輯是,為了防止因聯邦債務突破上限而發生所謂的“政府關門”危機,不具備“單向否決權”的總統根本不可能因某些涉華內容而全盤拒絕任何一項財政類立法。于是,國會利用自己手里的“錢袋子”,成功獲得了動搖總統手中“方向盤”的機會。

2021年12月7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梅內德斯(左)在一次聽證會上。2022年4月,此人率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代表團訪臺。
粗看從1979年中美建交到第115屆國會之間的38年,白宮和國會的關系似乎就像一輛汽車上駕駛員和后座喧嘩乘客之間的關系,但這并不足以概括美國聯邦憲政框架內圍繞重大外交政策問題的府會關系全貌。一般來說,美國國會的立法權能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發揮三類重大作用:一是通過立法分配國家戰略資源的“結構型”或“分配型決策”,二是設定長期努力方向的“戰略型決策”,三是應對突發事件做出快速反應的“應激型決策”。自中美建交以來直至特朗普上臺,白宮其實一直在已經設定好的結構型、戰略型決策的道路上行事,至多容許國會在必要時提供為數有限的應激型參與。換言之,掌握著“方向盤”的白宮還不需要國會來直接下場為某種政策方向的改變和調整來重新“架橋鋪路”,因而也就呈現出我們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看到的白宮始終主導方向的狀況。
然而,這并非是一成不變的。2017年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在處理對華關系時大量采取了至今仍影響極壞的錯誤甚至極端行為,刺激了國會在對華政策制定和調整過程中的角色提升。從2018年3月所謂“與臺灣交往法案”到2020年7月所謂“香港自治法案”,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簽署了近十項專門針對臺灣、涉疆、涉港、涉藏等問題的所謂“立法”。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白宮對華推進“大國戰略競爭”的整體氛圍下,第115、116屆美國國會兩院內的涉華提案數量雖然猛增,但最后實際通過的立法數量卻并沒有發生同等比例的“井噴”。換言之,這兩屆國會的涉華立法只是在“內容”上的突破,是在消極性、嚴重性、破壞性意義上的變本加厲。2017至2020年間經由特朗普簽署生效的“五毒俱全”立法中的大多數曾在前幾屆國會中被反復提出,卻都“泥牛入海”,直到特朗普這個“政治素人”高喊著“美國優先”口號坐進白宮橢圓辦公室。
究其原因,初步的解釋應該是,特朗普放任、縱容甚至暗推了國會的反華遏華立法。為了對中國實現“極限施壓”效果,特朗普自認為需要更多反華遏華的立法工具。于是,當他看到國會可以在這方面充實“政策工具箱”時,便選擇松開原本應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方向盤”,接過國會遞過的一件件瞄準中國的“武器”。盡管特朗普自認為他仍牢牢掌握著何時、何地、因何而扣動扳機的最終決定權,但這些來自國會的立法工具最終占據了白宮“工具箱”的絕大部分空間,逐漸開始影響對華政策的基本方向,甚至形成了綁架總統外交政策、左右涉華輿論風向的能力。更嚴重的是,當這位加速美國政治和戰略巨變的總統離開白宮之后,其所放任通過的那些立法繼續有效、無法回調,成為懸在中美關系之上的一把把“利劍”。
如果說特朗普所需要的在本質上還是國會的“應激型決策”的話,那么誓言為美國和世界“重建更好未來”(B3W)的拜登則是邀請國會出來進行結構型和戰略型決策的立法。對拜登及其政府而言,既然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對華戰略的新定位,明確中國是“競爭者”與“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而且這個定位在美國兩黨政治精英群體當中已形成了某種共識,那么他所要采取的下一步就是要通過資源再次分配、結構調整以及重新設定新的長期戰略規劃,來配合重新確定的對華定位,推動新的對華戰略。在這種情況下,拜登作為總統需要把國會直接請到美國戰略決策和演進的前排席位上來,替他鋪就新的道路。過去一年多以來,拜登及其政府實際上也是這么做的,美國對華定位及相關政策的“立法化”進程也是這樣被繼續推動的。現如今,白宮這個新訴求最直接地表現為其對國會所謂“競爭法案”的長期且迫切期待,該法案已于今年3月在國會最終成為對華競爭的“總劇本”。
決策和施策影響力得到提升的“快感”反過來也刺激到美國國會中的某些人,特別是那些長期以炒作涉華議題、推動對華強硬為業的某些議員們。他們在討論涉華問題時變得更加躁動,極力通過制造議題和事端“刷存在感”“提影響力”,與臺灣方面的勾連也更加肆無忌憚。佩洛西“竄臺”行程因其染新冠病毒擱淺,但卻并未完全取消,仍在“計劃”當中,成了中美關系頭上又一把“懸劍”。白宮對國會的需要也構成某種“政治交易”,對國會某些人樂此不疲的涉華冒險行為有時樂見其成,直到實在過火時才出面勸阻,或通過本黨議員加以牽制,以免白宮為防止中美正面沖突、激烈對抗等“災難性后果”而有意設立的“護欄”被徹底踢破。
如今,國會應白宮之“邀”站到前臺,為對華長期戰略競爭設定相關立法,這是中美建交以來從未有過的危險狀況。如果說1995年李登輝在美國國會親臺議員安排下竄訪美國所展現出的國會“重要性”激發了當時我國國內的美國國會研究,現如今美國府會的新互動有理由引發我們的再聚焦。今年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大概率將喪失對國會的控制權,由共和黨主導的新一屆國會或將徹底失去約束和制衡,給中美關系帶來更多、更大的破壞,這更加凸顯了我們關注、研究進而影響美國國會政治的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