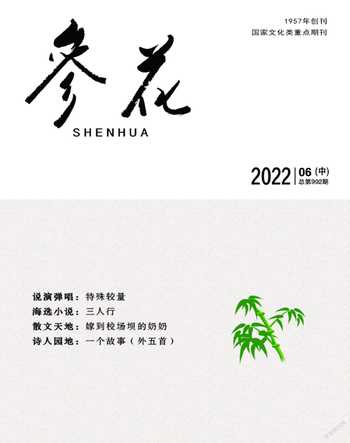沙背甸
春時的沙背甸,是“萬條垂下綠絲絳”的蔥蘢,是“竹外桃花三兩枝”的清秀,是一壟一壟金黃的起伏,是“小橋流水人家”的愜意。
一夜暖風拂過,沙背甸的油菜花便一地兒一地兒地鋪開,花開繁茂,燦爛金黃,媚亮了坡坡溝溝。沙背甸地勢特殊,群山環、碧水中,油菜花隨坡勢爬上山頭,又沿洼地潛入谷底,這一壟一壟的黃,層次起伏,像流動的金色河流,若翻翻滾滾的波濤,曠遠深層。
在黃燦燦的金色掩映中,若隱若現著沙背甸人的新居,屋前舍后,總有三三兩兩的花朵點綴。好雨知時節地跟著暖風兒的腳丫,啪嗒嗒地叩擊地面,深入泥層,喚醒那些沉睡了整個冬的萬物。漸次盛開的梨花、桃花不擇地勢,或屋前,或溪畔,或橋旁,有一枝獨秀的清寂,也簇簇擁擁著熱鬧,開得肆無忌憚,開得旁若無人。在花紅柳綠中,星羅著碧亮碧亮的魚塘,魚塘倒映著藍天白云,倒映著滿岸蔥蘢的綠意,岸上楊柳依依,偶爾在微風中擺動下腰身,偶爾低眉柔眼垂向塘面,風再一招搖,或有花兒輕悄悄落在塘面,忽聞“撲騰”一聲輕響,有魚兒越過水面,又迅速潛入水底,一圈一圈的波紋漾開去。“春江水暖鴨先知”,有些塘面嘎嘎地輕漾著歡唱的鴨群聲。
那些在草場趕了羊群,趕了牛群的,吆喝幾聲,咩咩咩……哞哞哞……牲畜們列隊,在一片青翠里,扯了脖子向著藍天,唱喝著回應,聲音在青翠翠的草場悠悠揚揚。
沙背甸,是雙牌縣的一個村莊,由十個自然村落組成。沙背甸滿地流動的金黃,總能預示一年的好兆頭,花兒涂著陽光的色彩,整個原野欣欣向榮。祿壽村的人總是把稻子一收割,就開始張羅著油菜的下種,其他幾個村落也跟著間或地種些油菜,許是喜歡那滿地金黃的好兆頭,許是喜歡廚間飄出菜籽油炒菜的香醇,許是喜歡那好收成帶來的好經濟。
當柔亮了一季的金色漸次隱去,飽吸了雨水和陽光的菜籽,日漸飽滿。收割了菜籽,便有了對香噴噴的菜籽油的期待。擇一個好日子,菜籽油的香味便開始回蕩在與古舊渡口相映襯的村莊上。沙背甸的菜籽油,因瀧泊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環境,竟格外地來得香酣,常被十里八鄉的居民和遠來的游客們惦記。也有村人喜歡香芋,便也栽種些香芋,于是嶺腳便成了香芋的基地,有些村莊則會把藥材種在坡坡嶺嶺。
沿著花海抵達的沙背甸渡口,總令我念念不忘。許是那佇立渡口眺望了上千年的老碑,許是那守望渡口與老碑兩兩相依的古樟,許是那些浮著舊時光韻味的老屋,許是那久久回響著歲月聲響的小巷。
古樟安靜地立在渡口,慈眉善目,如此安詳。古樟老了,身上每一處經絡、每一寸肌膚都密密麻麻,繡滿了歲月的斑痕。它在花紅柳綠、風和日麗里走過了一千二百多個春夏秋冬,也在電閃雷鳴中一次次滌蕩自己的骨骼。青苔和藤蔓頑皮地爬上它的衣角,覆過它的腰身,攀上它的臂膀,慢慢地,青苔和藤蔓們習慣了這種攀爬,開始以樹為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它們把自己爬成一件樹袍,不知不覺地裹上樟樹,這樹袍生動得讓整棵樟樹鮮活明艷起來,宛若躍躍欲飛的青龍。它盤旋在那里,依然守望著渡口,眺望著遠方。
村人告訴我,這古樟見證過他們爺爺的爺爺輩的成長,卻仍然“身強體壯”,他們深信,這古樟佑護了沙背甸連年的風調雨順,沙背甸的后生們長得彪悍,沙背甸人的日子也過得日漸富足……
據村里的老人說,古樟守護的這個渡口修建于道光年間,瀧河上游的各種珍貴木材在放排漢子們的吆喝聲里,在他們響亮亮吼出的山歌里,沿水路下行,當地人叫這些放排人“排牯佬”。排牯佬常隨木排捎帶些山里的野珍。沙背甸是他們補給的好場所。沙背甸村人黃能波老師,手心撫上岸邊古碑,告訴我說,這塊碑上面的文字記載了道光年間百姓修繕碼頭的情況,從列在上面捐資的商鋪名可以看出,當年沙背甸村該是商鋪林立并且繁華熱鬧的,上面眾多的捐資名單讓我們感受到當年先人們熱衷公益、造福鄉里的淳樸民風。他又指了指古樟,告訴我這岸邊曾經全都是這樣的古樟。這個因水流回旋而沖積出來的平地,被百姓們沿岸栽種香樟,曾經林木成蔭,樹蔭下排排的石墩子慵懶地臥在陰涼里。歇涼的人們在這里談笑風生,孩童們在這里嬉戲打鬧……
古樟前淌過的瀟水河,閃著微微的綠光,在陽光下泛起粼粼的波光,這一季的雨水,讓它豐腴飽滿,它把岸邊的石階藏在身底,留給河岸少有的幾階石板,這些石板匍匐在歲月的滄桑里,脊背不知道渡了多少鏗鏘或蹣跚的腳步。
若想從碼頭去到街道,必得踩著石板,拾級而上。抬頭,牌頭在歲月里早已滄桑,只剩得一扇殘破的門樓,在不遠處與古樟為伴,牌頭上長滿了綠色的植物,一種叫破骨風的草藥在牌頭上茂盛生長著,仿若牌頭長了一大撮頭發。我看過去的時候,它們在風里搖擺了下身子。牌頭上“汪洋共仰”四個大字早不見蹤跡,想是被經年累月的風雨抹擦掉了痕跡。世間很多東西都是這樣,悄然隱去,又以另樣的形式鮮活于人們的腦海。
拾級而上過牌頭,入古巷,看到青石板路和騰翹而出的老屋檐角,看到街道兩側林立著棟棟木板房與土磚房民居,每棟房屋前面都有木制的舊時鋪面。這些古民居都是明清年代的建筑,雖布滿滄桑,但大部分保存完好。林立的古商鋪靜默著,無論風雨,無論烈日,它們頑強、倔強地立在歲月的河流里。大多數的商鋪屋門大開,屋子里擺放著老舊的物什,這些物什基本是木質家具和難得一見的舊時的農耕器具,斑駁彌漫在歲月的眼里。走走這條古時繁華的街道,看看殘存在石板路兩邊的商鋪,不禁感嘆起先人古樸的民風和老商鋪當年的繁華。街道估計每日都有人打掃,干凈透亮、一塵不染。屋舍四周,卻是野草的歡場,它們拔節生長、舒腰展背。
這林林立立的舊商鋪讓我們瞬間穿越時光,似乎看得到它當年的繁華,遙遙地,聽得挾在風里的吆喝聲,似乎看到排牯佬們邁著大步,提著物什,一路走著,一路晃動著他們健壯黝黑的膀子,他們與鋪面里的生意人打著招呼,談笑風生,也或者討價還價,彼此陶醉在各自的生意經里……我似乎看到了當年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閉上眼睛,嗅著陽光的味道,想尋得那些故去事物的痕跡。我想尋得樹蔭下的談笑風生,尋得商家們討價還價的日常瑣碎,尋得槳拍河面,嘩嘩聲中漢子們放排的吆喝聲……
“女崽,進來坐坐!”耳畔有招呼聲,睜眼望去,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立在一家院門口,這家老舊的木頭房子的里外潔凈得一塵不染,屋檐的竹竿上晾著些粗布衣衫。院落里的景色穿透門楣,跌入眼底。抬腿跨入院落,里面別有洞天,屋子后有很大的一片園子,種著各類蔬果,辣椒樹上已掛滿或青或紅的果實,南瓜的藤蔓在地面撲騰開去,絲瓜朵朵燦燦的花攀在墻頭……再過去的別院里還有些雞鴨,角落里置放著一捆捆的柴火。再往旁邊些,是一個壓水井。
沙背甸人的日子這么美好,阿婆卻一直不肯搬離渡口。問其原因,阿婆看向陽光下的大樹,幾只蟬在那扯了肚皮嚷嚷“知了,知了”,阿婆咧嘴一笑道,“這兒多好,我在這,它們會常回來的。”
也許,阿婆是在守護渡口,守護古樟,守護舊去的時光,也許還有更多。
作者簡介:張靈芝,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