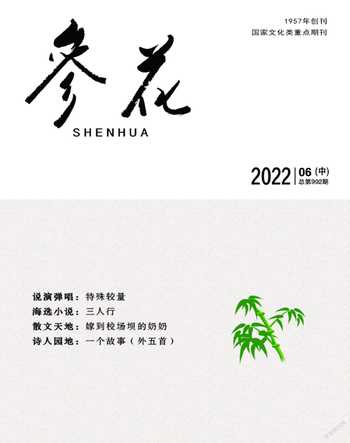古鎮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掘與傳承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世界文明的進一步發展,人們關于傳統文化又有了不同的認知。隨著20世紀80年代“文化尋根”思潮的掀起,新生一代的文人學者對五四時期關于傳統文化的態度逐漸有了明顯轉變,不再是一味批判,弘揚和繼承成了新的態勢,當然,這一文化發展的趨勢是正確的,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當今時代文化發展的主題。本文圍繞王劍冰散文《祖巷》中優秀的古鎮傳統文化展開,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精神氣脈與文化意蘊以及古鎮文化的未來走向等幾個方面淺述。
一、王劍冰散文中的文化意識
在文本展開之前,筆者認為要先從作者王劍冰談起。他作為新一代的散文大家,集創作、研究、編刊于一身,他帶著自己獨特的文化意識,行走于祖國的山水間,又懷著萬千感慨從中而來,用自己敏感的思想和恰到好處的力度去感受理解歷史,又以精彩巧妙的文學創作藝術將自己對文化的感悟絲絲注入筆墨文章。他擅長寫山水古跡,似乎大自然的每一處經過他眼都有著獨特的魅力。為何他的散文能夠被文壇盛贊?通常情況下,散文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在藝術表現和思想引領上擁有著天生的缺陷,所以變革時期的文學一般都是由小說引領,因為小說對思想傳播具有明顯的張力。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在五四時期享譽文壇的文學大家魯迅先生的作品中,也不乏令人稱頌的散文著作。而作為后起之秀的王劍冰更是為散文的書寫開辟了新的高峰,他寫山水古跡,歌頌自然風光并非只是單純慨嘆,而是用他獨特的審美感受對他所寫的山水古跡的歷史、文化進行探尋、追思。他的文章飽含對故土的思戀、對歷史的追問和思考、對自然山水的滿目傾心以及蘊藏在字里行間的真摯情感和文化意識。說到這里,便能夠理解為何王劍冰的散文倍受文壇推崇,“不只是他的散文作品中融入了詩藝和小說藝術”,最重要的是他對文化意識的敏感度。
當然,王劍冰在旅途中“漂泊與回歸”的同時,又為那些引人注目的山水古跡寫下篇章,筆者認為他這樣做的初心大概是想引起讀者對傳統文化的“追問和反思”。然而這一做法還是遭到了質疑,唐小林在其文章《不可思議的王劍冰現象》中,對王劍冰的散文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王劍冰的散文之所以能夠在文壇倍受推崇,不過是受賈平凹、侯修圃及余繼聰等一些作家的過高吹捧,通過套路得此榮譽。他在文章中提到,王劍冰的散文充滿著淺薄和呆滯,想象貧乏、比喻俗套,思維陳舊,邏輯不通。而當今時代呈現一種“王劍冰現象”,即藝術觀念的陳腐,寫作模式的固化和無病呻吟的矯情。他認為這是一種弊病,不可否認他的這種觀點是有先進性的,但是就王劍冰的散文成就來說,他的這種批判過于片面和嚴重了。王劍冰寫家鄉,寫歷史,寫山水不僅僅是單一表面的泛泛之談,更不是為了某種利益而作的商業軟文,“他以風格獨特的散文,構筑起一個既清新明麗,又蘊藉雋永的藝術世界,豐富了中國當代散文文壇”。像《絕版的周莊》《遠遠的少女》《遼遠蒼茫的渤海灣》《干涸的鴻溝,歷史的裂痕》《祖巷》等作品,靜下心來去品讀他的作品,會發現作者在文章中所要彰顯的內涵是深刻的、多元的,同時,他也在嘗試用現代文學的審美眼光、文學意識去欣賞和解讀歷史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他想為文學和歷史文化開拓一個新的連接點,而這個連接點恰是王劍冰投置在文章中的文化意識。
二、珠璣巷中的“家”的概念
觸及“家”這個字眼,每個人的心都會為之一顫,那是一種深深藏在中華兒女心底的鄉愁符號,是一種不會枯竭的精神動力。關于“家”的定義,最早出現在甲骨文中,它的本義是住所,后來引申為安家落戶、定居,還可以指自己居住的房子。從具體上說,能夠遮風擋雨的是家,但從抽象上說,由親親關系維系著的才叫家,但不可否認的是,親親關系才是家概念中最重要的部分。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當然這只是家的最小的文化呈現形式,而從大的層面講,由家人、同村的鄰居以及同屬于中華民族的同胞們所組成的團體,依然可以親切地稱呼它為家,無論是大家還是小家,它們都有著共通的屬性。并且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它內在的屬性也從未改變,家的概念一直存在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同時,蘊藏在家文化中的民族傳統美德也一直被傳承著,這是一條系著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心的精神文化紐帶。20世紀初期的文學浪潮忽視了家文化的重要性,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文化尋根”思潮的興起,“家祠文化”又開始受到文人學者的重視,從“家”這個概念衍生出來的各種優秀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成了文人學者爭先推崇的對象。
王劍冰在其文章《祖巷》中就大方且具體地傳遞了“家”概念背后深刻的文化內涵。祖巷即為珠璣巷,作者在文章中首先交代了珠璣巷的來歷,經追溯,珠璣巷從唐代開始,眾多先輩曾在未知窮途中翻山越嶺來到這里,期間就有張九齡、蘇東坡、禪宗六祖惠能等人,他們在這遙遠的地方開辟了新的家園,或許他們最初的愿望只是為了安身立命,卻沒想到珠璣巷成了他們心頭永遠的牽絆。一千多年來,這里匯集了不計其數的人,超過一百七十個姓氏,而這則為流浪漂泊的茫然者提供了一份關于家的念想。王劍冰在文中說,珠璣巷的存在是一個廣泛的融合,姓氏的融合、情感的融合、力量的融合,乃至家庭的融合,而筆者還想補充一句,這種融合不正是潛藏在眾人心底的家的意識使然嗎?從前姓氏的集合為遠道而來的鄉親提供了認親的途徑,如今家祠的集合讓這一環節變得更加容易,歸鄉尋家的難度恰恰說明了那流淌在人們血液中剪不斷的家的念想,無論多么遙遠艱難也要奔赴家鄉。此外,珠璣巷的房屋建筑也大有名堂,擁擠的房屋構造,不是由于地域狹小,而是當地人給它賦予了更特殊的內涵,擁擠在一起的房屋就像是手拉手并肩站在一起的人,它們所代表的,不只是生活功能,更是團結功能。更值得一說的是,珠璣巷的鄉親們為了接待前來認祖歸宗的鄉親,每家每戶都留一個人出來接待,他們接待的不只是自家親人,而是所有來這里認親的人,且從不計較得失。珠璣巷人的種種做法,不管是姓氏和家祠的集合,特殊的房屋構造,還是每家每戶留守接待鄉親的人,這無一不是家概念的具體表現,而促使他們這么做的,也正是蘊藏在家概念背后的強烈的精神歸屬感。這種真誠的態度、無私奉獻的精神以及發人深省的凝聚力,直至今天,依然能帶給人們穿越時空的感動,而這份感動也恰恰是蘊藏在家文化中的魅力彰顯。
三、文化尋根與指引——以珠璣巷的精神氣脈和人文意蘊為出發點
再說祖巷的名字“珠璣巷”,乍一看會以為此名是由當地盛產珠璣而得來,其實不然,因為這里既不產珠璣,也不是販賣珠璣的地方,那為何要叫珠璣巷呢?作者王劍冰從歷史中尋到了兩種說法,一說唐中期敬宗巷人張昌,七世同堂,和睦共居,聲名遠播,皇帝賜其一條珠璣絳環,同時,他又是張九齡后世裔孫,因張家人丁興旺,又孝義和睦,由此更改巷名;二說是南宋時,地處中原的開封祥符的許多官員及富商為避元人而大舉南遷至此,又因家鄉祥符有珠璣巷,為解相思之情,便更改地名。不只是巷名的來歷有種種說法,這里的三街四巷:(珠璣街、棋盤街、馬仔街;洙泗巷、黃茅巷、鐵爐巷和臘巷)每一個都能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找到其說法由來,但是關于哪種說法是正確的,在此刻已經顯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最重要的是這些歷史古跡背后所彰顯的文化魅力和人文意蘊,珠璣巷里的當地人和中原人的這種新型鄉親關系,具有穿越時空的恒久特質,這不僅是先輩們重視推崇的特質,更是當今時代所要學習和推崇的。
此外,珠璣巷所體現的精神氣脈更是值得一提。首先,要說到的是沒有圍擋的珠璣巷處處彰顯著包容,無論你從哪里來,看到這樣的村落格局,筆者認為你一定會放下猶豫和戒備,而能夠讓人們產生這種情感的,不就是最讓人們牽掛在心頭的“家”嗎?幾千年來,珠璣巷一直扮演著“家”這個角色,它就像一座中轉站,南來北往的人都在這里歇腳啟程,抑或是定居安享晚年。而且,遷居來這里的人不都是布衣白丁,亦有名聲大噪、富貴顯赫的人家,但是珠璣巷卻沒有想象中的豪宅大院、沒有私修的花園麗景,究其背后的原因,無外乎是來這里定居的人大多是和珠璣巷一般,是有故事、有經歷的,他們經歷世事的風浪,逐漸變得收束心性,如今只顯露溫柔善意于外界。其次,似是為了彰顯誠意,當地人在梅關地界立一“善”字,往來的人在看到的瞬間,整顆心都會變得柔軟。當然,不僅只有善被重視,在這里被廣泛傳達的還有“友善、和睦、禮貌、孝悌、節儉”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而這些美德則成就了珠璣巷千百年生生不息的燦爛。最后說到的就是深邃入心的珠璣精神,作者在文中提到了三位著名人物,其一是南宋度宗咸淳年間,胡氏兄妹遭奸佞迫害,胡妃被貶庶民,后逃匿漂泊于市,機緣之下遇到珠璣商人黃貯萬,二人回到珠璣巷結為夫妻。胡妃心性善良,當遇到天災時,胡妃告知鄉親撈取田螺抵抗饑餓,不幸的是,皇帝對胡妃的再次查找,使珠璣巷的百姓受到牽連,為了不株連鄉人,保全這處美好的存在,胡妃選擇投井自盡。鄉人們為了紀念她,便在井上為她修了七級佛塔,至今猶存。其二是南唐時期的何昶,他受后晉高祖石敬瑭賞識,做了侍御史。后又受周世宗重用,受命持節南下,宣撫南漢帝劉晟,被封南海參軍。路過珠璣巷,見這里風物醇美,便安家于此。后因珠璣一帶匪寇侵擾,他奉命出征時,遇到強烈的龍卷風,與夫人隨船傾覆江中。其三是羅貴,他被許多珠璣巷人和廣府人尊為“羅貴祖”,最初到珠璣巷來的羅彥環就是羅貴的六世祖。他曾帶領眾人砍竹結筏,順湞江南遷。這些名人事跡彰顯了珠璣巷人“異姓一家、同舟共濟、和諧共贏、開拓進取”的精神氣脈,不僅是先輩們有如此壯跡,近代許多珠璣巷后裔也依然傳承著珠璣精神,在不少領域產生深廣影響,他們在新中國的革命建設中,一次又一次展現著這種精神氣脈。由此可知,不論是優秀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好,還是深入人心的珠璣精神也好,它們都具有穿越時空的恒久特質,它們既能夠讓珠璣巷的精神氣脈和人文意蘊延續下去,又能夠為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增添風采。
四、結語
恰如作者王劍冰在文章中寫到的一樣,他推崇蘊藏在珠璣巷文化中的人文意蘊,精神氣脈,他認為,充滿文化的古跡不該被淹沒在歷史長河里,他在文章結尾寫道,“應該有更多的人來這里看看,領略它的精神氣脈,人文意蘊,這里有道德倫理學、社會心理學、姓氏文化學、民族融合學乃至中華交通史、民族遷移史、文明發展史的一個冊頁”,而擁有這種豐富歷史文化的古鎮,不是只有珠璣巷這一處,這些古鎮承載著的不僅僅是一代一代人的記憶,更為重要的是,蘊含在其背后的豐富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社會變革與經濟發展為主導的時代,在外來文化沖擊的時代,蘊藏在古鎮背后的傳統民族文化該如何更好地發揚傳承,這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課題,王劍冰用他的作品,再一次凸顯了文學對傳承一代文化的重要性。當然,對于“家”的概念、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弘揚已經不是首次提起,但筆者認為對主流文化的弘揚還須引起重視。筆者贊同王劍冰這種對文化的敏感度,這不僅是一個文人學者應當具備的文化素養,也是值得普通大眾效仿的行徑。
參考文獻:
[1]劉海燕.王劍冰的散文視界[J].中州大學學報,2016,33(01):44-47.
[2]婁曉凱.漂泊與回歸反思與追問——論王劍冰的散文世界[J].平頂山學院學報,2005(06):30-32.
[3]唐小林.不可思議的“王劍冰現象”[J].文學自由談,2021(06):10-20.
[4]婁曉凱.詩意的真誠——看王劍冰散文的美學特征[J].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5(03):94-96.
[5]陳歡.說不盡的“祠堂”——綜觀20世紀鄉土文學看取“祠堂”視角的整體變遷軌跡[J].涪陵師范學院學報,2005(04):37-41.
(作者簡介:馬容芳,女,本科,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責任編輯 于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