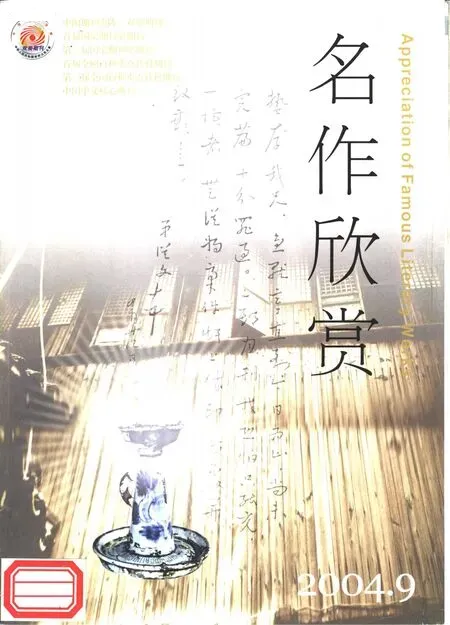信守“中國的”“理論的”“有用的” 三大關鍵
李桂奎
恩師黃霖先生,學識淵博,近六十年如一日,筆耕不輟,在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批評研究領域中均多有創獲。關于其學術之路,先生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從‘兩金開始,我選擇了行人稀少的那條路。”“就是常常走在陌生的、崎嶇的,甚至是有點風險的行人稀少的道路上。”(《中華讀書報》2021年05月26日)所謂“兩金”指的是搞小說批評不可繞過的金圣嘆和《金瓶梅》。一開始,先生致力于當時還一片模糊的小說批評史研究,并著手小說序跋等論著資料整理,后來拓展到評點、話體等多種批評形式,并將思想史、學術史、批評史融合起來,從而創構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在這條行人稀少的康莊大道上,先生堅持以文獻研究支撐文學文本研究,以文學文本研究支撐文學批評研究,以文學批評研究支撐文論體系建構,一以貫之信守“中國的”“理論的”“有用的”三個關鍵。
立足本土,堅守“中國的”學術立場
在一段較長歷史時期備受歐風美雨侵襲的學術氛圍中,黃霖先生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承傳復旦大學郭紹虞、朱東潤、劉大杰、趙景深等諸位先生奠定的“始終能堅持以中為本,洋為中用,做新學問,創新局面”等學術傳統,既不忽視外來理論方法,又堅守“中國的”這一學術正道。
先生早就重視西方文論的借鑒,卻不像有些人為求一時之新而生搬硬套,而是注意以西方文論為鏡,旨在借以鏡照中華民族文學批評理論的優勢和特點。在被稱為“方法論年”的1985年,先生于《社會科學研究》第1期發表《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芻議》一文,通過與西方相較,指出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家在探索、總結創造人物典型的經驗和規律時的優越性,突出這套“中國的”小說批評“堅持形神兼備、繪形傳神”“強調性格對比、相得益彰”之特質,并發掘了其從“實”到“虛”、從“真”到“假”的理論的獨特和優勝之處,指出葉晝所論述的“同而不同處有辨”,贊賞寫人的個性“一毫不差,半些不混”,比起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涉及“這一個”時將要早兩百年,金圣嘆所闡發的“性格”理論也要比黑格爾的性格說早一個半世紀,他所說的“任憑提起一個,都似舊時熟識”也比別林斯基的那句名言“每一個典型對于讀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早整整兩個世紀……從而由衷地表達了對老祖宗留下的文論思想的“自豪”。該文除了強調資料整理和文獻考證之外,還提出“注重民族傳統”“注意比較研究”“努力前后貫通”三條建議,這三條建議均隱含著一腔關于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中國的”情懷。其中,那段關于小說寫人問題的論述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將這些材料整理出來,加以總結,就可以立即改變人們對于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全局的看法,清楚地認識到我國古代關于人物形象的理論不是貧乏,而是絢麗多彩,獨具特色,不至于一談到人物形象的理論時,開口黑格爾,閉口別車杜,而不知有祖宗了。”此論“中國的”寫人問題時,先生正值壯年,真可謂氣盛言宜,立論剴切,至今讀來仍覺擲地有聲、理直氣壯。這是我多年堅持至今仍在從事的中國文學寫人研究及中國寫人學理論建構的出發點。
20世紀90年代,當許多人感到中國文論“失語”,并流露出驚慌失措甚至迷茫情緒時,先生卻通過扎實的個案分析,得出結論說:即使在波瀾壯闊的近代文學批評中,照樣是“傳統改造了西學”,而并非相反。1994年,發表于《文學評論》第3期的《中國近代文學批評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對中國近代文學批評中固有的“中國的”底蘊和力量進行過這樣一番精辟的分析和總結:“他們在引進西方文學觀念時,盡管從這里反對中國傳統出發,但最后又從那里與中國傳統結下不解之緣。而且,這個緣結得越和諧,其成績就越突出。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所以高出包括他自己以往的文化著作在內的一般譯介,就因為他將西方的觀點與中國的傳統融為一體,用傳統的‘意境說消化了叔本華的藝術論。”并由此得出結論說:“在近代文學思想變革的潮流中,再西化的文論家也很難擺脫傳統,這正像人站在地球上很難被人推出地球一樣。”即使“那些接受西方觀念的熱情較高、否定傳統的態度較為堅決、影響大而又具代表性的文學批評家”,如王國維、梁啟超以及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等,無論怎么鼓吹如何學習西方,到頭來骨子里還是“中國的”。由此可見,在眾人慨嘆傳統文論“失語”的前前后后,先生卻能鎮靜而清醒地看到,前輩先行者們流淌的依然是中國“傳統”血液,一路貫穿的依然是難以撼動的“中國的”力量。這份文論自覺、文化自信是先知先覺性的。
先生在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時,特別重視中國特有的文論形式,尤其對長期被人忽視,甚至否定的“評點”批評方式與“話體”文學批評,率先展開研究。眾所周知,《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史上的經典,研究它的論著也汗牛充棟。但有關它的評點,卻一時間很少有人予以全面的關注。先生導夫先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有意收羅《文心雕龍》的評點,經常趁開會出差之際,去國內外圖書館抄錄,日積月累,終于做成了《文心雕龍匯評》一書。同時,他下功夫著手搜羅與整理歷來未受人注意的小說話,積數十年之力,完成了一部洋洋十五卷的《歷代小說話》(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
先生一邊身體力行,一邊還組織學生在評點與話體批評兩條戰線上展開全面的工作。在評點方面,對從《詩經》《楚辭》《文選》《世說新語》到杜詩韓文等重要詩文別集與小說戲曲名著,一部一部地做匯評的整理和專門的研究;在話體之作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起就組織學生關注近現代報刊上各種文體的話體批評,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著作與《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叢刊》。在這兩大工程一并推進的過程中,先生組織了多次國內外學術會議,并出版了多輯《文學評點論稿》《民國舊體文論與文學研究》論文集,探討評點與話體這類“即目散評”式的文學批評的特點與價值。這正如先生所總結的,中國的評點、話體這類傳統批評方式,特別適合于文學批評,因為文學的基本屬性是以感性具體的藝術形象來表達作者的情思的。批評者從即目的、具體的感性形象入手,經過切身體悟,從而使評者與作品乃至作者的心靈相溝通與融合,這就為評者領悟作品的整體風貌與內在精神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這比之評者與作品站在“主客兩分”相對的位置上,脫離具體的形象去解剖,更為符合文學批評的規律,而且對讀者來說,讀來當更有一種親切感,更容易接受。這類批評,即目所悟,直抒己見,隨手作評,點到為止,盡管會給人以一種零散而雜亂的錯覺,但實際上,多數文學評點是形散而神完,外雜而內整,總是會有一個核心的見解或理論包容在里面,它們不但具有文獻價值,而且也具有理論價值。即使到了現代,看來似乎是一種被“新文學”所淘汰的“陳舊”的批評方式,實際上固有的傳統并未被割斷,人們在沿著中西融合、新舊共濟、古今通變的道路向前走的過程中,傳統的力量依然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回過頭看,先生所堅守的“中國的”立場,其實是傳承復旦批評史學派的必然。通常而言,出身通常會影響甚至決定研究立場和路數,從郭紹虞、朱東潤、劉大杰到王運熙、顧易生,一路走來,復旦大學搞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都是古代文學出身,而且也都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力軍,其特點或長處就是都比較重視基礎文獻工作。每談到這一點,先生又仿佛是一個“出身”決定論者和身體力行者。總之,作為一個搞古代文學出身的學者,先生深深地體驗到,以“中國的”為研究立場,是他自然也是自覺的選擇。
依史立說,注重“理論的”創新建構
文學批評離不開理論支撐,否則便容易流于信口雌黃。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中,黃霖先生一直重視“理論的”建設與建構。他既從事偏于縱向的“史”之研究,參與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的撰寫,然后又編寫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中的“近代卷”,并負責編選了《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中國近代文論選》;又能依托于雄厚的“史述”積累,致力于偏重橫向的體系建構,與王運熙先生一起主編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三卷本,有力地推動了復旦文學批評史研究向“史論結合”轉變。先生憑著富有啟發性、應用性的“理論的”創新,開辟出批評史、思想史、學術史等多元結合的廣闊園地,令人刮目相看。
在研究路數上,先生向來主張學術研究應該縱橫結合,具體到文學批評理論研究中更應該“史”“論”兼顧。根據先生的回憶,其理論意識的養成主要還是得力于章培恒老師的教導。先生讀大學二年級時,章先生給他的一篇關于《離騷》的發言提綱寫過一段批語,在高度肯定他“寫得很好”的同時,熱切地希望他“在古代文學和文學理論兩方面都做更深入的學習,進一步充實自己”。這一勸勉烙印在他的內心深處。在先生看來,重視“理論的”,道理很簡單:搞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怎么能不關注理論呢?言行一致,早在20世紀80年代,先生所撰寫的《古小說論概觀》即分出縱觀篇和橫觀篇,既對小說理論批評做了縱向的史的描述,又對小說理論批評做了橫向概論,雙管齊下,兩條腿走路。在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小說批評”部分及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的過程中,先生不滿足于一般性的時間梳理和材料的堆積羅列,而選取在中國文學批評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金圣嘆及其《水滸傳》評批作為突破口,在搞清金圣嘆生活的經歷、矛盾的思想、文學的創作與文論思想的基礎上,確立了這樣一個承前啟后的史論坐標。然后,前列羅燁、吳承恩、謝肇淛、李贄、葉晝、馮夢龍等人的小說理論,后續毛宗崗、張道深、曹雪芹、脂硯齋、閑齋老人、梁啟超、吳沃堯、徐念慈、王國維、王鐘麒、黃人、林紓、管達如、呂思勉等人的小說理論,在較為完整、系統地梳理了中國小說理論批評演變過程的基礎上,對中國小說理論的特點和脈絡進行了系統化的總結。
作為一門學科,“中國文學批評史”實際上包含著“史”與“論”兩個方面,除了歷時的史的梳理,也包括對于文學批評的種種理論問題的研究,小至某一觀點、某一范疇,大至整個中國文學批評的特點、體系等研究,并不是因中有個“史”字,就將其誤解為只是編寫有關文學批評歷程的史著。甚至可以說,史中有論,論中有史,更應該是常態。從學術史上看,關于文學批評的論著論文占了很大分量,既有綜論中國文學批評的,如傅庚生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通論》、賴力行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董乃斌編著的《文學史學原理研究》等;也有像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之類論范疇的,陳衍的《鐘嶸〈詩品〉平議》之類論一本書的,朱東潤的《司空圖詩論綜述》之類論批評家個人的。
在“論”這一方面,先生也孜孜矻矻、扎扎實實地做了不少工作。1995年,先生推出《意象系統論》(《學術月刊》第7期)一文,指出:“藝術創作是一個心物交互作用的過程,其最后的表現形態在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中往往被稱為‘意象‘意境‘興象‘境外之象以及‘興趣‘神韻‘境界等等。這些概念名目各異,內涵混沌,但精神相通,且貫穿中國文論的始終,形成了一個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論系統,且名之曰‘意象系統。”同年,《賦比興論》(《復旦學報》第6期)一文通過對傳統賦、比、興三者新的闡發,認為它們不僅是三種最基本的文學思維,而且是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心物交互”作用的三種不同方式;不僅是詩法,而且也是小說戲曲作法;不僅應用于“抒情”“敘事”“寫景”以及“狀物”,而且也應用于“寫人”(“描人”),打開了人們的視野。筆者的《“賦比興”寫人功能之抉發及其理論價值》(《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頗得益于該文的滋養和啟發。
先生關于傳統文學理論著作的理論研究,自然是“理論的”。2009年,《〈文心雕龍〉:中國第一部寫作心理學論著》(《河北學刊》第1期)一文指出:“《文心雕龍》的書名,清楚地表明了全書的性質與主旨。‘文心,即‘為文之用心,就是寫作時的整個心理活動。‘文心雕龍的本意是將寫作的心理活動用精美的文辭予以細密地論述。”先生由此得出結論說,《文心雕龍》是一部以寫作心理學為核心的文章學。另外,他還進行了如下具體的分析:“《原道》等五篇論‘文之樞紐,揭示了指導寫作心理活動的總的原則。以下二十篇,通過對不同文體寫作特點與歷史的考察,進一步具體論證了以上原則的正確性。下篇從《風骨》至《總術》篇,是在上篇確立的原則下,將各種文體打通后,正面論述了一系列臨文寫作時心理活動的特點、規則、方法與問題。后面《時序》至《知音》五篇,補充論述了一些與臨文寫作心理活動密切相關的幾個重要問題,使得全書的結構更加完整、系統。”顯然,先生對《文心雕龍》的性質、特點和體系性所進行的新的闡釋與綜括,是富有理論高度的。
除了傳統詩文評以及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先生還熱衷于戲曲批評研究,尤其是關于《西廂記》的評點,同樣也是既重視文獻考輯,也重視理論闡發的示范與樣板。2002年,《復旦學報》第2期發表的《論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一文指出,葉晝的可貴之處就是與批《水滸傳》一樣,非常重視引入畫論中的傳神論,強調作品能夠寫出“畫亦不到此”(第十出眉批)的人物的神與態、性與情。因此,他常常使用“入神”“窮神”“傳神至此”等批語。在他看來,就寫人文學而言,用“態”來評論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特征,還是一個比較恰當的范疇。葉晝在借鑒前人的《西廂記》人物論的基礎上,又喜歡用“有態”“有態致”來品評人物,特別是對于鶯鶯,一再用“嬌態”“嬌甚”“嬌態如畫,妙妙”來揭示這個千金小姐的嬌美與矜持。這種獨到的發現,啟發我們進一步研究介于“形神”之間的“態”這一范疇的思路。
先生理論建構的重頭戲是“原人論”的提出與逐漸完善。基于廣泛涉獵的文學批評資源,對于傳統文學理論的一些范疇探討的基礎,從20世紀末始,先生開始著力于中國文學理論批評體系的建構,其標志性成果是他主筆的《原人論》(2000)。這部著作本著“從世界性中抓住特殊點”“從歷時性中找出統一點”“從多元性中找出融合點”等理念撰寫,從“心化”“生命化”“實用化”等層面展開,初步建構起一套中國特色的“原人”文藝理論體系。先生經常強調學術研究既要講公理,但也必須有個性,即“有我”;除了不隨人后,還要有獨到的眼光,有“不從眾”的識見,這種治學精神也充分體現在他對“原人論”的建構上。先生曾回憶說:“面對當時學界正在激烈地爭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有沒有體系的問題……我終于從唐代佛教理論中找到了‘原人兩字,借用它作為我們的‘綱,用它來概括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體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可見,“原人論”這一理論的提出是長期積累、厚積薄發的結果。先生深感拈出“原人”二字來概括中國文論是頗得其神韻的。當然,即便如此,先生也并沒有停下探索的腳步。近年來,他在主編的“馬工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原人論”進行了新的思考,從而把文學的本原(本質或根本)概括為四點:“文自人”“文似人”“文寫人”“文為人”。在先生看來,中國古代認知文學的最核心的特質、基因與傳統是“文學原人論”,即認為:“文學源于人,以人為本。這個本,既是‘本源的本,也是‘根本的本。這個‘人,是指作為人類的人、社會群體的人,不是指個體的人(論述個體創作時除外)。”這里所謂的“文”,即“文學”,指的是學科或藝術門類意義上的較為泛化的概念。當然,除了自己身體力行地注重理論建構,先生還注意指導學生投入理論建構。我近些年投身“中國寫人學”理論建構,便得益于先生長期誨人不倦的指教。
長期以來,研究方法上的文人相輕現象時有出現:有的搞理論的看不起搞文獻整理的,也有的注重文獻整理與考據的看不上搞理論研究的。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研究上可謂是統籌兼顧。他始終認為,文獻與文論二者并不矛盾,可以互相依從,故而在具體研究中,先生善于用“實”的文獻來證明理論,又用貌似“虛”的理論來負載文獻資料。先生的理論創新基于長期的“史”的系統梳理與研究,因而不僅言必有據,而且有思想高度。
面向當代,致力于“有用的”學術研究
在中國文論史上,北宋王安石在《上人書》中提出的“有補于世”“以適用為本”等觀念,既成為強調為文助益、補益國家、社會的一道古訓,也符合服務于國計民生的今理,影響深遠。文論研究也應持此古訓。黃霖先生的文學批評史研究,從批評史論、學術史論,到評點研究,再到話體文論研究;從資料編寫,到教材編寫,理論與推廣互動,堅持面向“社會之需要、時代之精神、文化之變革”,堅持“以創新為目標,以有用為旨歸”;堅持為學致用,始終把“有用的”作為自己的重要研究目標。
在先生心目中,“有用的”是復旦大學老一輩學者的治學靈魂。先生曾經坦言,他在學術研究上所追求的用世精神,是深受朱東潤、章培恒等老師影響的結果。先生一向不希望將傳統的一些文化瑰寶只當作古董來欣賞,而是希望老祖宗的優秀的文學作品與文論精神能在現代社會生生不息。這不僅表現在他寫過諸如直接呼吁“文論研究應追求有用于世”之類的文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常將這種治學精神貫徹在他的論著中,使這些論著躍動著可觸摸的時代脈搏。
有道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國際政治如此,國際文化、國際文論亦然。先生嘗言:他不忍心看到許多人用西方的理論來消解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故而責無旁貸地肩負起發揚光大中國傳統的文論思想,建構源于傳統的偉大文學體系,讓老祖宗的一些優秀的精神重放光芒的神圣使命。
在《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總前言總結過去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先生面對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系列現實問題提出了九大關系,闡發了自己關于文學研究的價值追求問題的認識,提倡學術研究要有人文關懷的精神,要關心現實,關懷現代人的生存,關心老百姓的問題;而認為“象牙塔里做學問”雖能滿足一己之興趣,但是若放棄對當代現實文化的人文思考,難免容易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基礎。就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研究來說,若放棄重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熱情和努力,自身也就容易喪失精神支柱。因此,先生明確指出,研究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現在要討論的不是要不要追求“有用于世”的問題,而是應該關注如何“有用于世”的問題。正確的態度和理念應該是:“確認傳統的文論還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不僅僅在書齋中要研究它,承續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實踐中復興它,光大它。”
按照先生的說法,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有用于世”,就是把傳統的某些理論應用于現代的合理思想加以豐富和完善,重新建構。通過付諸實踐,以運用或化入到當代的文學批評或自主性的文論建設中。在先生眼里,近百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也的確是始終追求能有用于世的。傳統文論中有些東西,如“意境”說,從鐘嶸的“滋味”說,中經王昌齡的“意境”說、司空圖的“味外之味”說、嚴羽的“興趣”說、王士禛的“神韻”說,再到王國維的“意境”說,雖然經歷了千變萬化,但其基本內涵血脈相承,至今猶存。輪到當今,我們應該繼續通過激活、闡發、重構,為之續命。為此,他在2002年發表于《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的《從消解走向重構——世紀之初古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進行了系統探討和總結。當然,先生也看到了古代文論研究看似“很難為世所用”這一現實困惑,但仍要知難而上。
通常而言,所謂“有用的”這個“用”,首先就是人們常說的,剔除其糟粕,承傳其精華,以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一段歷史時期里,在所謂“古今”相結合的道路上,不論是“以今釋古”,還是“析古入今”,其基本立足點都是以今化古,而所謂“今”,實為“西”,即以西方的一套來消解和吞并傳統。面對這種困境,先生在《從消解走向重構——世紀之初古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出了“立足在中國,以我化人”的努力方向和期望。除了大方向的指引、總體目標的指示,以及可行性論證,先生還提出了具體可行的實施方案,即分四步走:“面對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史的研究不能放松”“加強橫向的中國特色的體系的研究和構建”“要立志于發展傳統的文論”“再從經院的研究跨到實際的運用”。先生所倡導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體系重建,視野是面向世界的、全球化的,立場卻是“中國的”,是立足于中華民族特色的,歸根結底是“為世所用”“有補于世”的。
在先生看來,古代與現代之間,畢竟血脈相連,基因是息息相通的。從學理上講,中國文學批評能“古為今用”的基礎就是歷史的發展遵循著“通變”的規律,在“變”的同時,也有相“通”之處、統一之點。事實上,現代的不少文論話語,比如“比興”“知音”“氣勢”“氣象”“意象”“意境”“形神”“敘事”“結構”“性格”“陽剛”“陰柔”“意在言外”“情景交融”等,是從古代借鑒而來,將舊的范疇賦予了新意,活躍在當今文壇。而反過來看,建構當代的文論,只有植根于傳統文論土壤,才能真正生根、發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
當然,先生所追求的這種“有用的”治學理念和為學精神,更是被貫徹到他作為首席專家的“馬工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部全國統編教材的編寫中。該教材打破了近一個世紀以來習慣以作家作品來排序的格局,第一次以中國傳統的范疇、觀點、論題來論史,不只是改變了一種固有的寫作形式,而是在于企求更能彰顯中國文論的主要話語與優秀精神,便于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習與了解我國傳統文論中的精粹,在以后欣賞、批評中外古今文學作品與構建現代的文論體系時,更清醒地堅持“中國的”立場,并鍛造出以中化西的學養,潛移默化地形成對中華本土文論的自豪感。
多年來,黃霖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堅守“中國的”“理論的”“有用的”三大關鍵。在郭紹虞、朱東潤、劉大杰等先生開辟的陣地上,伴隨著王運熙、顧易生等先生開疆拓土,并脫穎而出與第三代團隊的同仁們一起,在復旦大學中國批評史學科建設的道路上,一路前行,走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