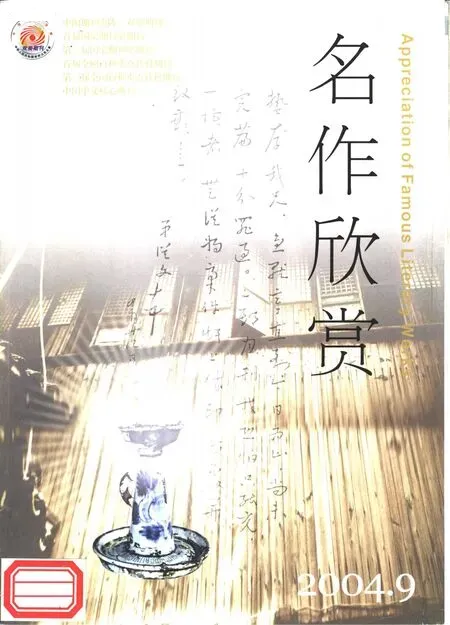路遙的漢中之旅
程文
關鍵詞:路遙 王蓬 報告文學 《漢中盆地行》
物質年代的精神堅守
1988年,沸騰的80年代即將走到了盡頭,文學神圣年代的純真夢想,也終將讓位于下一個時代的商業大潮。來自南方經濟特區金錢財富的招引和誘惑,越來越多地席卷了中國文壇上那些曾經傾心膜拜繆斯的詩人和作家。造富的空氣、社會的轉型,讓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不得不做出改變,否則將難以容身。
面對洶涌而至的市場經濟浪潮,身為著名作家,路遙的內心是悲哀而無奈的。他曾經自嘲式地對身邊的同事、青年作家航宇說道:“我也是人,又不是跟錢有仇。咱不能光坐著看人家賺錢,也要想一些賺錢的辦法,要不恐怕就是這個城市里最貧窮的一個窮光蛋了。”
路遙的朋友、作家海波在《人生路遙》中談到這時期路遙被經濟所困,寫道:
一次在1988年前后,他打電話叫我過去,說有要緊事要商量。去了后才知道他不是給我介紹好書,而是想和我一塊兒做生意。他說,他有一朋友是飛行員,能從廣東、福建那邊往西安捎牛仔褲,要我出面在西安登記一店鋪,和他合伙做這生意。并說:“進貨的本錢和運輸全不要你管,你只管去賣;有風險我們承擔,有利潤咱們均分。”但當時的我卻斷然不能接受,反問他說:“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人了嗎?”他無奈地看著我,好半天不說話,只是深深地嘆氣。
另外一次好像在1990年,他對我說:“實在窮得沒辦法了,能不能找個掙錢的事做,寫報告文學也行。”當時我正給西影短片部籌劃一部電視劇,出資方是漢中市西鄉縣政府,這個縣的副縣長呂陽平和我關系很好,我就把這事告訴了呂。呂陽平一聽很爽快地答應了,說他們縣有一名高中生在全國奧林匹克物理競賽中獲得第一名,如果路遙能寫寫這個人,對他們縣的教育事業肯定有促進作用,同時我們還談好了報酬。……誰知路遙又后悔了,他堅決表示不寫了,要我寫。人家是沖著路遙的名氣來的,我寫了未必能交差,只得向呂陽平說了實情,這事才不了了之。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路遙當時非常需要錢,但他更愛面子,真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這年夏天,路遙接到延大好友、陜西洛川縣委宣傳部長王雙全的信,便給王雙全復信致意。2021年,筆者來到洛川采訪王雙全,得見此信,全文如下:
雙泉兄:
我外出才返回,見您信及照片。
西安很熱,也想出去躲躲,家屬孩子一塊走也不方便,只好硬著頭皮待在西安。
您個人的工作問題,可多和申老師(延安大學校長申沛昌)商量,他的意見會是成熟的。
先寫這幾句。
問全家好!
路遙1/7/88
同年,陜西作協《延河》雜志資深編輯徐岳自籌資金,創辦了一份《中外紀實文學》刊物,但因運營不善,面臨虧損危機。于是,徐岳想借文友路遙的大名,為刊物打開一條生路。徐岳把這想法告訴路遙,請他去一趟漢中采訪,寫作報告文學,路遙爽快應允。后來,徐岳又邀請了西安電影制片廠的著名編劇莫伸,年底12月間三人結伴南下漢中,開始了采訪之旅。
冬天的漢中,依然是一派嶺南春色,風光明麗,生機盎然,這對于從小在黃土窯洞里長大的路遙,自然是無比新鮮,也倍添好感。路遙一行來到漢中以后,按照文友李長錄的安排,入住漢中制藥廠專家樓。當天下午,漢中制藥廠廠長唐東生主持召開座談會,歡迎路遙發言。后來,徐岳在回憶文章《在龍年最后的日子里》中回顧這段往事,寫道:
我永遠不會忘記路遙同志,就是抓住這個機遇,給《中外紀實文學》貼了廣告。他的那些即席講話,很得體,使企業人聽罷,覺得這個刊物很親切。我想,這是那些胡吹冒撂者,根本不可能達到的效果。
當晚,路遙跟徐岳、莫伸定了工作制度:一不打擾文友,二不驚動官方,三是結束采訪后,開展幾項活動,就返回西安。
但到了第五天,王蓬等文友來訪,漢中主管文教的行署副專員崔興亭也特地來看路遙。于是,路遙應他們的要求,搬到了漢中行署招待所。就在這里,路遙采訪了新上任的漢中行署專員趙世居。
王蓬曾經目睹路遙與漢中領導干部的交流,在《苦難與輝煌》中寫道:
路遙1988年冬來漢中,與漢中書記專員有過幾次座談。我發現他一點都不拘謹,從容自若,提問得體,不時插句幽默風趣的笑話,輕易地便使氣氛自始至終保持一種輕松和愉悅。
采訪之余,路遙還出席了漢中地區組織的文學活動,為文學青年做報告。徐岳回憶此事,寫道:
漢中市的文學青年和愛好者大約千余人集中在劇院里,請我們去做報告。會議由當地的文學民間領袖王蓬主持。我的話很簡單,除了講《中外紀實文學》的創辦宗旨外,特意說明路遙和莫伸,是我們編輯部請來的客人,請他們兩位做報告。這自然也是一種借路遙之名巧妙的廣告,當然也符合實際情況。路遙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主要內容是青年文學愛好者要破除對文學和作家的神秘感,搞文學和搞其他工作是一樣的。其次講了要做好本身工作,做人與做文并重。他絲毫沒有炫耀自己已取得的成功和榮耀。
除過漢中制藥廠、漢中城固雪茄卷煙廠,路遙還應邀采訪了鄉鎮企業石馬黃板紙廠,徐岳在文章中記錄了這樁有趣的軼事:
漢中之行是十分開心的。一天晚上,有一個女青年找到我,說她是石馬黃板紙廠的廠長派來的,操一口漢中腔抱怨說:“你們只去國營大廠,也不把我們鄉鎮企業看看。”我趕忙找到路遙,征求他的意見,因為石馬鄉離市區較遠,路遙一聽,眉眼里充滿了柔和的笑意,嘴勁很大地說:“去!誰叫我看他的廠都去!”我又說:“她還帶了一點土特產,收不收?”他依然嘴勁很大地說:“要!給甚要甚!”說完,我們大家都笑了。
不僅如此,徐岳還饒有興味地講到了他跟路遙在一起無拘無束地放談趣事:
我有時站在二樓,看著路遙,就覺得他的形體是“圓”的,我也深知他的性格是“方”的,有棱有角,使人覺得很難說話。但是,在這里,我卻感覺不出他的棱和角,晚上多是海闊天空的閑聊,諸如男人如何沖破妻子的“經濟封鎖”,使男人活得真像男人,而不是“難人”,其幽默常使人忍俊不禁。當然也談創作,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個細節,是他寫《平凡的世界》這部巨著時,繁重而緊張的抄稿勞動,竟然使他的五指死死地撮合在一起,竟然沒了捉筆的空隙。然而他創造了一個法子,將一團紙塞入手心,在撮合的五指間撐出個縫隙,再將筆插入縫隙內,繼續抄寫。說到這些時,他總要操著濃重的、富有表現力的陜北話,先重重地吹口哨般地“銳——”一聲,再十分嚴肅地說“可艱苦啦!”
順暢的采訪活動、愉快的交流活動,使日夜操勞寫作的路遙獲得了短暫的精神放松。此外,王蓬熱情陪伴路遙,游覽漢中的多處名勝古跡。2022年,王蓬接受筆者的微信采訪,談到這段往事,寫道:
這次他們三人的漢中之行是以寫報告文學為主。我沒有參與此事,但參與了他們來漢中的一些活動,比如陪游西漢三遺址、拜將壇等,還有勉縣的武侯祠、墓。
這次他們幾位一起來,對我來講都是文友,無親疏遠近之分,活動都是集體,只記得當時他們住地委(即行署)招待所。有天晚上送他們回去的路上,路遙對我說:你先在漢中干著,有機會還是要進省作協,當專業作家,名正言順。我嘴里雖贊同,但內心深處卻認同“文人宜散不宜聚”的古訓。再者,父母全家都在漢中,去西安談何容易!之后,陳忠實任省作協主席時,也邀我去西安,我都婉拒,直到退休漢中。
路遙具有與生俱來的政治組織才能,凡是朋友們中有才有德者,他總是竭力相幫,并著意提拔。對文友王蓬如此,對好友王雙全也是如此,王雙全在回憶文章《我與路遙的相處時光》中談到一件往事,寫道:
1990年秋的一個下午,我利用到西安出差的機會,又到省作協,在作家樓三樓他的家里閑諞。他又給我談起單位的工作,他說自己雖為主持工作的常務副主席,可是工作太忙,顧不上管理方面的事。特別是機關事務工作,缺少一個管后勤的人手,問我來不來,想讓我幫他管理后勤總務工作。現在回想起來,感到同學之情多么的深,多么的重,路遙在非常忙碌的工作中,卻總是惦記著我,隨時愿意伸出友誼之手幫助我,這的確是我們交往中最難能可貴的一點。
關心路遙的王蓬,在漢中陪伴路遙期間,總是想方設法給路遙創造一點精神上的快樂,他在《苦難與輝煌》中寫道:
路遙過分看重已經取得的榮譽,愛惜自己的羽毛,平常與任何女同志來往都很莊重,幾乎不去任何社交場合,甚至有種殉難的苦行僧味兒。
1988年冬,他與莫伸、徐岳來漢中,都穿得單薄,我找幾件毛衣讓他們加上。莫伸、徐岳穿了,路遙臉都凍青了,就是不穿。事后,我突然想起,路遙不止一次說過他最喜歡冬天,不怕冷,但冷畢竟于身體不相宜啊!
我于是晚上讓他們進舞廳,想著活動活動身上也暖和一些。但去了舞廳,路遙也不跳,一支接一支地吸煙,然后坐在那兒靜靜地聽音樂。
路遙同行的文友莫伸,在回憶文章《永遠無悔的犧牲》中追憶了1988年冬天路遙的漢中之行,也對路遙表達了同情和惋惜,寫道:
有一天晚上,我們閑聊天。路遙敞開心扉,告訴了我許多他人生道路上的波折與經歷,甚至生活中諸多的順心與不順心。我很吃驚,路遙是個謹言慎行的人,這在我與他的交往中還是頭一回。更重要的是,就在這天晚上,我知道了他在生活中絕非幸運者。他的人生煩惱比一般人只怕要更多些!
還是那次漢中之行,我和路遙曾應邀到一家單位吃飯。陪同我們的有漢中地區某局一位領導干部。這位干部年近六十,馬上面臨退休。吃飯時,他突然問路遙:“老路,咱倆誰大?”
而那一年,路遙才39歲!
緊接著一次宴飯,是在漢中黃板紙廠。開車去接我們的司機是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他的孩子與路遙的孩子年齡相差不大。孩子當時稱呼路遙:“爺爺。”
一般人與路遙相處,總感覺他比實際年齡要大,這固然與路遙氣質上的深沉有關,但也多少反映出路遙勞累過度所造成的惡果。那天,我看著路遙兩鬢上已泛出的斑斑白絲,感觸萬千。由于朋友們的熱情安排,路遙的漢中之行十分愉悅。漢中之行圓滿結束后,路遙回到西安的家里,開始專力寫作。徐岳回憶路遙投入寫作的情景,寫道:
回到西安后,已近春節。路遙先在家里給我寫稿子,春節過后,他像個小學生,背著一包鼓鼓囊囊的書,佝僂著肥厚的背,去了西影,林達(路遙妻子)說:“他給你到西影大酒店寫稿子去了。”
聽了這話,我的心向下沉了一下。后來見到路遙,便說:“啊呀,你寫個這文章,還費這么大的事!”
“我要對得起‘路遙兩個字!”
他說話時一臉逼人的冷氣。
唉,這一臉冷氣,把他自己逼得太可憐了。
同是作家,王蓬談到這件事,也被路遙認真虔誠的創作精神感動,寫道:
其時《人生》已為他贏得了大名聲,《平凡的世界》大稿已交了編輯部。此時對他來說,寫個小稿稿,“殺雞焉用牛刀?”然而他用了。他就是這么嘔心瀝血!
莫伸更是對路遙這種忘我獻身的創作態度表達了由衷的敬意,他寫道:
路遙對創作有許多精到的理解。比如他說:“創作是自己對自己進行的戰爭!其殘酷根本不亞于真實的打仗!”
再比如他說:“要當作家,就必須學會對自己下狠心!輕輕松松就能當上作家,那作家這個職業也就一錢不值!”
于是,1989年徐岳主編的《中外紀實文學》雜志上赫然增添了路遙的一篇大作《漢中論》,刊發時,徐岳加了一段“編者按”:
這是作者不遠千里采訪漢中之后,又不顧年關將至,戮力而成的一篇認真之作。原題為《漢中盆地行》,《漢中論》三字屬編者所改。因為我們久有希望,想開設一個欄目,以散文的手法從宏觀上放筆于某個地區或某個行業的發展問題。如是文章,文人們可以寫,一個地區、一個行業的官員們亦可以寫。只要對政府、對行業的經濟工作以及讀者能有某些啟示、參考價值的,我們都將在顯著位置,隆重推出。下期本欄目大作將出自誰人之手?請讀者拭目以待。
同年10月,王蓬主編的報告文學集《秦巴大潮》出版,王蓬將路遙這篇《漢中盆地行》收入該書,為路遙爭得了一筆可觀的稿費。王蓬回憶此事,寫道:
那時,我也協助漢中市文化局編了本報告文學《秦巴大潮》。聯系我在魯院、北大時的同學聶震寧幫助出版,他當時在廣西漓江出版社任編輯室主任。我把路遙為徐岳寫的《漢中論》改名為《漢中盆地行》,放在《秦巴大潮》卷首以壯行色。憑此,我向文化局為路遙討要了500元稿酬,當時已相當可觀。路遙拿過裝錢的信封很高興,拉著我的手使勁握了幾下,意思夠朋友。
漢中之行,給路遙帶來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收獲,使路遙對有著悠久歷史、美麗富饒的漢中盆地心生偏愛,一生中前后來過五六次之多。三年以后,路遙溘然長逝。同年,徐岳在哀悼路遙的文章里,表達了對文友的懷念之情:
路遙遠離我們而去之后,他的家人說:“路遙還欠你們編輯部一千塊錢呢!”我說:“他早還了。”他的漢中盆地之行,難道不值一千元嗎?
90年代:最后的輝煌
當時代的巨輪碾壓過20世紀最后一個十年的門檻時,喧囂歡騰的市場經濟狂潮呼嘯而至,裹挾著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致富夢想,一起匯聚成20世紀末中國社會復雜多面、生機勃勃、機遇與風險并存、輝煌與獰惡交織的生態。地處古都西安的陜西作協,在現代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愈發顯得境遇尷尬。路遙的文友、作家李天芳在回憶文章《財富》中寫到了以路遙為代表的作家們的生存困境:
不管作家們如何鐘情于改革,如何歡呼它、頌揚它,但當它的腳步日漸逼近真正到來之際,靈魂工程師首先感到的還是它對自己的挑戰。報紙上見天見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費醫療制度改革等等,一樣一件都在說明社會主義大鍋飯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這一切對所有人則一律平等,它不因為你是作家,你曾為它講過一大籮筐的好話,你就可以少給一個銅板。作為剛剛步入中年的路遙,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誰都更加敏銳地意識到生存的挑戰和未來的負擔……他一下從沙發上坐起,不安地說:“不行,咱們得賺點錢……”
不是他有意裝窮,有意隱瞞經濟情報,實在是收入有限,支出無窮。錢需要一把一把地花,文章卻得一個個字地寫。他仿佛有一個永遠填不滿的坑。遠在陜北山村的兩個家,四個生身父母和養父母,還有眾多的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幫扶和贍養。遠親近鄰,七姑八舅,哪個鄉下人遇到難處,能不向他伸手?在城里他還有他的小家,他又極不善精打細算,計劃經濟。
“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他不止一次調侃著這句流行語。關于如何賺錢以適應社會的變化,他腦子里的設想像小說構思一樣,一串一串的。時而是開家大餐廳,時而是搞個運輸隊,時而又想在黃土高原辦個牧場……務虛少說也務了兩三年,但無論他還是我,還是我們大院的其他人,總不見有誰邁出去一步。
1991年3月路遙榮膺茅盾文學獎的輝光剛散去,至高無上的文學殊榮只給作家帶來五千元的獎金,這對切實改善他的生活環境沒有多大助益。同年冬天,路遙應約寫作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次年春天完稿。這部用六萬多文字譜寫出的英雄交響曲,傾注了路遙的激情、思考和心血,成為路遙的作品里當之無愧的絕響。同時,這部絕筆之作也給路遙帶來了優渥的稿酬。即便這樣,路遙的經濟狀況依然是入不敷出,他似乎永遠拼盡全力拉拽著一輛負重的大車,一聲不響地低頭向前艱難爬坡,只是到了生命力量接近耗盡的時候,他才悲愴而無助地倒在了路上。
1992年3月,王蓬應廣西《漓江》雜志主編聶震寧之約,向路遙這位陜西文壇巨子約稿。然而,此時的路遙已是身心疲憊、意趣索然,他給王蓬的信中訴說了自己的境況:
王蓬兄:
您好!
先后兩信都收讀,因許多無法啟齒的原因耽誤了復信,請能原諒。
我是一個較為內向的人,有時很難在口頭或行為表述自己內心激越的情緒。但和您、莫伸這樣一些人待在一塊感到自在,因為我們真的超越了一些局限。
三本書出得都不錯,我因身體不太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閱讀完,我一定會用文字說說您,只是在時間上盡量寬容我。就目前而言,您是陜西最有沖勁的作家,您諸事備齊,只待東風,成功是肯定的。有人已成強弩之末,您正箭在弦上。干吧!
為聶震寧寫稿一事,現在有這么個情況;我手頭編了一本文論性質的集子,名曰《作家的勞動》,約十五六萬字,包括以前的一些文學言論(七八萬字)和有關《平凡的世界》的一篇大型隨筆(六萬多字)。
本來,此書可以不出,因陜人社擬出我五卷文集。這些東西也將會包括進去,但我覺得這些東西淹沒在小說中有點兒痛心,因此單集了一本,一則我看重這些文字,二則也想多拿幾千元稿酬,就我目前及今后一段時間來看,因身體差,寫作拿點錢很不容易了,現在,想請你出面同聶震寧聯系一下,看能不能在漓江出這本賠錢的書。因為我目前遇到難以言傳的苦衷(經濟上),也許您以后會恍然大悟。
莫伸不久前來過,我們又談起上您那里去逛一圈,但他目前走不開,又只能等到下一次了。
西安目前很“亂”,窮人富人都在談論如何賺錢,想必漢中也一樣,這一回,應該是有智慧的人賺點錢了,有機會咱們還可以好好論證一下,先寫這些。
祝好
路遙
1992年3月27日
信中,路遙談到的三本書,指的是王蓬1991年10月、11月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長篇小說《水葬》、傳記文學《流浪者的足跡》和漓江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中篇小說集《黑牡丹和她的丈夫》。此前1989年10月,王蓬的中短篇小說集《隱密》也是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路遙的摯友、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編輯李金玉擔任了王蓬這三部作品的責任編輯。對此,李金玉在回憶文章《平凡的世界輝煌的人生》中談到了路遙對陜西文友們的幫助,寫道:
《平凡的世界》出版后,我又給陜西的作者出了一些書,有的書稿是路遙推薦的,有的不是。
但不管是不是他推薦的,他都說這些人寫東西不容易,讓我盡量想辦法出版。在我的印象里,他都是說這些人的好話,沒有說過任何一個人的壞話。我知道他是真誠地想幫他們。有的書最終沒能出版,是因為我人微言輕,能力有限,不能說服我的領導,與路遙無關。路遙去世后,我聽到有人說的一些閑話,心里很為路遙難過:這就是他視為朋友并曾經幫助過的人嗎?
路遙總是惦念文學道路上像他一樣艱難跋涉的奮進者,并且盡自己所能幫助別人,王蓬就是其中之一。這是許多與路遙有過真心交往的朋友,不管是功成名就還是籍籍無名,不管是官運亨通還是被人遺忘,不管是城市精英還是鄉村作者,他們對路遙的為人和心地的切身感受,正如作家劉路在回憶文章《坦誠的朋友》中談到路遙,動情地贊揚道:
1984年5月的一天,路遙應邀來陜西師大做報告,當他談到《人生》的創作經過時,他對學生們說,在《人生》的創作過程中,我得到了你們劉路老師的極為寶貴的支持,他把自己很多非常好的素材借給了我,可以說,高加林的形象,是我和他共同創造的。我借他的這筆債,怕永遠也還不了啦!
當時我坐在臺下,真是感動極了!望著學生們向我投來的目光,我連忙站起來說,不用還了,不用還了!
這就是路遙,一個坦誠的朋友,一個坦誠的作家。對別人給他的哪怕一點幫助,他都永遠記著!
劉路的說法,從作家海波那里得到了復證。2020年,筆者在延安采訪海波,他談到路遙,由衷地贊嘆道:“路遙的心地,有時候善良得讓人無法想象。”
海波是路遙的同鄉同學,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得到了路遙的無私幫助和大力提攜,他通過堅持不懈地練筆,終得走出陜北農村,進入城市從事創作。三十年間,海波先后調入延安、西寧、西安、北京等地工作,并勤奮筆耕、創作不輟,最終成為延安地區有影響力的“山花”派作家。
1992年5月,路遙生命里程中的最后一個夏天,疾病纏身的路遙寫給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導演何志銘一封便箋,希望由他拍攝一部宣傳陜北某家企業的紀錄片。2020年,筆者來到榆林采訪何志銘,得見此信,全文如下:
志銘:
好!
世曄(作家航宇)有點事,想請您幫助解決,希望能用智慧的方式給予協助,予取妥善處理好。具體事由他面述。
路遙
92.5.1
2021年,何志銘接受筆者微信采訪,談到這次失敗的拍攝計劃,寫道:
那個字條,是路遙弄到一萬元拍專題費用,讓張世曄(航宇)找我,讓給他先開發票。他攬下個活,可能是陜北一個采石油礦隊,早忘了。專題片投入一萬,他拿五千元寫稿,給我五千元制作費,我在西影短片部任主任有點權力。但此事后來投資方改變想法而泡湯了。那時流行支持企業家!這事沒下文,過去這事太多了!
于是,路遙只能抱守著“著名作家、青年導師、陜北文學巨樹、陜西作協副主席”等一系列耀眼的光環,默默承受著不為人知的經濟上和精神上的雙重熬煎。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路遙的負擔,加速了病魔對路遙身體的摧殘。加之生活中、家庭中諸多難以言說的糾葛和矛盾,這一切催使路遙過早地面臨著死神的叩門。終于,這年8月,路遙抱病北上延安,為自己即將出版的《路遙文集》籌措出書經費,豈料,他卻不幸在延安一病不起。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宿命。1983年路遙將要赴北京領獎,他北上銅川找四弟王天樂借款。1991年路遙榮獲茅盾文學獎,他找在延安的王天樂籌錢。1992年路遙為了出版文集,再次去延安找延大校長申沛昌籌措資金。金錢、財富、享樂、浮華、舒適的生活、闊綽的消費,路遙從來沒有徹底領受過;家庭的溫暖、親人的簇擁、天倫的樂趣,路遙更是在沒日沒夜的寫作勞動中被人為地隔絕。他曾經悲憤地說過這樣的話:“我這一輩子,沒吃沒喝,還打了半輩子的光棍漢!”
就這樣,病入膏肓的路遙陷入無人理解的孤獨與悲哀之中。從1992年8月8日路遙病倒,到9月5日路遙從延安人民醫院轉院到西安西京醫院,此后他的病勢陡轉直下。在難熬的102個日日夜夜里,在醫護人員的救治下,路遙與病魔做著最后的抗爭。最終,多少治療,多少祝愿,多少人力和物力,都擋不住死神到來的腳步。
1992年11月14日,病危中的路遙還記掛著自己所欠的債務,航宇在《路遙的時間》一書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到了下午,天就黑了,幾乎說了一天話的路遙突然問我,你知道我還欠人家多少錢?有的我一時想不起來了。你看我這么長時間住在醫院,也還不了。但還不了也不能忘,不要讓人家覺得我病了,就沒那么一回事了,而且連一句話也沒有。等我出院后,第一任務就是還債。
路遙又同我核對了一下他欠別人的債務。
然而路遙最終沒能償清債務,三天之后,路遙走了,永遠地走了。
路遙逝世以后,第二年,路遙的兩位陜北老鄉:導演何志銘和作家航宇,得到延安大學校長申沛昌提供的資金支持,合作拍攝了紀錄片《路遙》,并遵照陜北傳統風俗,趕在1993年11月17日路遙周年忌日于西安雍村飯店舉行了首映。該片保留了路遙生前珍貴的影像資料,流傳至今。
1993年王蓬來到西安,住進陜西作協,遇見了航宇。當他得知航宇正在制作《路遙》錄像帶時,立即慷慨解囊,資助航宇一千元錢,買下五十盤復制的《路遙》錄像帶,帶回漢中代為銷售,為宣傳路遙盡到了朋友情誼。后來,王蓬多次撰文緬懷路遙,寄托對故友的懷念和哀思,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永志不忘。”
路遙的文友、作家曉雷至今保存著路遙臨終前兩個月手寫的兩張條據,他在回憶文章《破碎的借條》中細述往事,無限感慨地寫道:
其實,這是形勢使然。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作家這個行當已經面臨了嚴重的挑戰。按照往常的寫作慣性和套路從事純文學創作,發表文章與出版書籍已變得日漸艱難,菲薄的稿費與暴漲的物價形成的剪刀差讓大部分作家入不敷出,生計維艱,情緒低落,生存的困窘和創作的危機,已打亂了計劃經濟條件下作家的工作生活常態,連一向特立獨行、率性而為的路遙也不得不去適應風云變幻,而在原本出自激情與靈感的創造性工作中委屈自己,為稿酬而被迫屈尊就駕,去寫并非情動于中而行乎其外的熟悉題材。
看著兩張條據,我不由得去想此時路遙急于領稿費的用途,后來發現其他材料,終于弄明白,這原是為妻子赴京調動工作、安排女兒上學等等急用,臨時領取稿費;稿費不夠,又不得不再次借款。生活的嗖嗖冷風是在怎樣地吹拂著一盞曾經光焰四射又行將熄滅的生命之燈。
路遙離去以后,文學創作如同其他行業一樣,在經濟市場的不斷沖擊與調整,淘汰與選擇,分離與重組,解構與整合,漸漸步入適者生存的嶄新軌道,名家與名作也會成為名牌商品,一旦成名,身價百倍。以路遙的實力,他不難躍入這種行列與位置,但是上帝沒有給他安排這種機會,他帶著種種遺憾與缺失離去。
結語
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體制邁向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轉折階段,與此相應,中國文學界的作家們也在時代大潮來臨時各自做出自己的選擇。或與時俱進,或故步自封,或銷聲匿跡,或光彩不再,歷史檢驗著新時代每一個作家的良知和責任心。作為新時期陜西文壇的代表作家,路遙一方面被現實生活所迫,陸續寫作和發表了一些有償報告文學;另一方面,路遙頑強地捍衛著嚴肅文學的精神堡壘,謹守心靈中對文學的神圣信仰。因此,即便是疾病纏身、家事日繁、俗世多累,路遙并未停止對文學事業的不懈追求,他后期的作品里,依然葆有著純正的品格、深沉的感情和博大的氣勢,閃耀著睿哲的光芒和滄桑的余輝,只是從前期激情如火的吶喊,逐漸轉向寬容眾生的博愛,面對廣大讀者,路遙從不孤單,他是為文學頂峰而存在的。與此同時,路遙也在陜西作協任職期間,以自己的智慧和真誠,竭盡所能幫扶了一批身處窮困逆境里的作家,他們中如王蓬、海波,都已成為陜西文壇的驕子。
時光荏苒,歲月如潮,路遙離開人世已三十個春秋。時間能夠無情地淘汰和帶走一切物質的東西,唯獨不能更替和降格的是人類孜孜不倦、永恒追求、改變自身命運、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誠如20世紀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論述人類社會發展所說的那樣:“生存就是改變,改變就是成熟,成熟就是不斷創造自己。”如果說當今的中國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精神文明的變革,而這些都是20世紀末期路遙所處的時代所未曾經歷過的,正因如此,每當我們屢屢回眸20世紀80年代路遙和以他為代表的陜西優秀作家的奮斗征程時,總會被他們執著而強悍、沉實而剛毅的品格,以及獻身文學創作、敢于攀登高峰的無畏精神所震撼。尤為可貴的是,他們在努力改變命運的同時,又將自己的命運與改善祖國、人民的命運緊密融合在一起,從而達到了中國當代文學中前所未有的精神峰巔。這是路遙留給當今中國社會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