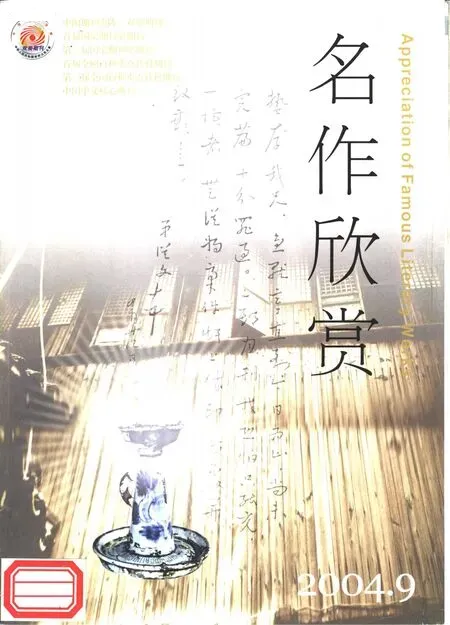創造我們自己時代的“現代”
王晴飛 周明全
王晴飛,生于1980年,江蘇泗洪人。南京大學理學學士、文學博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現任職于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文學論文集《望桐集》等。
“此人之肉,彼人之毒”
周明全(以下簡稱周):這幾年,你從社科院到刊物,最后又落腳大學,短短幾年,在三個城市,從事了三個不同的職業。這幾年的情況是,很多大學老師到刊物工作,如《當代作家評論》的韓春燕、《小說評論》的王春林、《揚子江文學評論》的何同彬、《南方文壇》副主編曾攀等,我自己在刊物,也覺得在刊物蠻自由的,你為何從刊物去大學?
王晴飛(以下簡稱王):這個怎么說呢,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吧。此人之肉,彼人之毒。對于我來說,人生最理想的職業是大學教師,但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會有各自的際遇,也會有各自的困難。世界并不是為某個人設定,最理想的未必總是可以立刻實現,而且有的時候經歷了各種情況,也不知道自己“最理想”的是什么,所以我們只能在具體的情境下主動或被動地做出選擇。每個人的我之為“我”,也往往不是自己最初期待的結果,而是在不斷地選擇與被選擇中逐漸成為的那個“我”。從刊物到大學,于我個人,是夙愿以償,了解我的朋友多數也都是拍手稱快,拍案而起,認為我終于從短途車坐上了長途車。對于這些理解我的朋友,我是心懷感激的。
如果撇除外界的因素,我是懶得變動且執行力很弱的人,有時候身處并非自己理想的境遇,也沒有足夠的動力做出大的改變,因為實在怕麻煩。而且我也覺得人生似乎并沒有“最好的”,有次好的就已經很不錯,所謂的“好”,往往只是在我們既有的選擇中讓自己覺得更適宜也更適意的。所以有時我也會感激人生中那些不可控因素,甚至是一些不大的挫折(挫折要有,但不要太大,不然gameover,就沒得玩了)。如果人生一路順遂,本科畢業讀碩士,碩士畢業讀博士,博士畢業去一所大學教書,一直到六十歲退休,那我可能不會遇到很多風景。有時候恰恰是一些當時看來“不順”的際遇,賦予人一些預料之外的東西,讓人生變得有意思一些。
周:多在一些崗位上體驗一下,對從事文學研究也是好事。工作環境的變化,對你的研究也帶來一些新的挑戰吧?
王:首先環境確實是有了變化,而我也確實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我之前的大學經驗,是學生眼中看到的大學,而學生眼中的大學和教師眼中的大學,其實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表達對大學向往的時候,會有長期任教于大學的朋友潑冷水,給我對大學的浪漫想象降溫。
不過說到對研究的挑戰,我倒也并沒有覺得很大。大學教師真正需要做的是兩件事,一是教書,一是研究。在大學教書,于我確實是一個新經驗,不過我也很樂于去學習怎樣教書,而且我總有一種不知道哪里來的自信,似乎我天然就適合教書。人在做有價值的事時,總是會有更大的熱情。我覺得有價值的事情,就是可以參與并看到事物的生長,做研究會看到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在慢慢生長,教書則看到學生的慢慢生長,這都是很讓人快樂的事。人生有什么比做快樂的事同時還順便解決了謀生問題更好的呢?
周:工作環境的變化,也可能帶來研究方向的轉變,畢竟要適應大學的考核方式。你到大學后,研究方向上做了哪些調整和規劃?
王:工作環境的變化,確實對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過在具體的研究上,影響倒并不大。大學的考核方式確實會更細碎一些,但是說到大體,其實與科研機構并沒有本質區別,大家的標準其實都是那幾個,課題啊、論文啊。而且考核方式主要體現在成果的形式或刊發的載體,而不在內容,我研究的內容和興趣不太會因此而變化。當然,也可能是我本來就疏于規劃,并沒有非常明確的方向。這確實是我需要克服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以后(過了四十歲以后,確實會感到,留給我們的有效工作時間其實已經不多了)。目前而言,我會較多留意當下比較有創造性的作品,也會關注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學之間的關系,想多了解一些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中國人的情感與想象模式。
大學給個人研究或知識結構帶來的變化,會體現在講課上。比如,為了把問題給學生講清楚,會對以前泛泛閱讀的作品或問題仔細研讀,在這個過程中會發現以前忽略的問題。當然我講課時間尚短,這樣的時候有,尚不太多。
作為一個中年人,我并不預期會有完美的環境,我也認為無論環境怎樣,人活在其中,都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人和環境是可以適當互動的。理想的情況當然是盡量讓自己的興趣、個性與環境之間保持一個良性的平衡。但如果外界標準實在讓自己不舒服,那就舍棄一部分標準吧,只要自己的選擇和內心自洽,就可以獲得愉快與寧靜。我也不太相信沒有個人興趣、熱情的學術會是好的學術。人們經常說,“學好不容易,學壞一出溜”,但是“出溜”真舒服啊,我當然不是說人應該“出溜”下去,混跡于“心理舒適區”,但是面對和自己個性或興趣過分犯沖的標準,偶爾“出溜”一下也是可以諒解的吧?我們不必時時刻刻都對“標準”保持忠誠。
周:心態好,把一些事情看淡點,人就更輕松自由了。去年年底和陳思和老師談批評家的出道問題,陳老師認為,現在我們看到的(如客座研究員制度、“今日批評家”等)幾乎都是面上出道的幾個發力點。當時他建議我“要從更加廣泛的學術傳承背景上去討論,從價值取向的變化中找出這一代批評家在學術與批評之間游走的狀況,學院體制對他們的批評事業的干擾,以及在媒體批評與學院批評之間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我覺得陳老師的建議非常好,你之前在社科院工作,后來又到刊物,在不同性質的單位工作過,現在在大學里工作,你覺得學院體制對文學批評有哪些干擾?
王:對于這些方面,我的感受其實有些遲鈍,這可能跟我總覺得自己不在學院中(我確實時常會隱隱覺得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有一個“學院”,但有時候又覺得似乎并不存在這樣的地方),也不專心致力于做文學批評有關,我也覺得人應該跟某一種被便宜性命名的整體保持適當的距離,所以很少思考批評家群體該如何或者會如何的問題,偶有思考,也是會想作為個體的“我”在既定的環境或者說體制里怎樣盡量做得好一些。所以我所說的只能對我個人有效。
至于學院體制對文學批評的干擾,我想這里想表達的或許是指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外部的,文學批評這項工作在大學學術體制里的重要性會低于文學史研究,不會得到充分的重視,甚至文學批評文章不被計入考核成果,這雖然只是外部問題,但是成為一種學術風氣或潛在的對學術價值的判斷,可能會引導青年人學術方向的選擇。一是內部的,就是現行的學院體制對于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的理解,會有一個相對的延后,所以有時候會顯得停留在比較陳舊的知識體系和觀念里。
不過就我個人而言,說起來可能沒什么意思——很多事從個人角度說都會沒什么意思,也沒什么道理——那就是學院體制對我沒什么干擾。我愿意把學院的作用理解為更專業的,更沉潛的,不輕易被輕淺的風氣裹挾的一種氣質或者說方法,而并不一定意味著更堅硬、更封閉、更保守的。在這種方法之下,文學批評會在文學文本與文學理論、文學現象與社會現實、個人趣味與文學原則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和有益的張力,使兩端互相激發、創造。
對“學院”這樣的理解,或許會被認為過于理想化,但是個人就是可以這樣理解,因為只要你自己相信這一點,也往這方向努力就好了。至少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它是可以實現的。而給學院賦予某種狹義的內涵——正如我們所見,可以是完全相反的內涵,且各有道理——并從而支持或反對它,是容易的,但我更愿意想的問題是怎樣使“學院”于我們自身對于文學的理解有益。
周:你這些年閱讀量很大,但文章并不是很多,你是有意放緩自己的寫作速度還是有其他考慮?
王:說來慚愧,閱讀量大恐未必屬實,寫得少確是無可抵賴。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絕無有意放緩速度或其他考慮,甚至我也很羨慕那些手快的朋友。傾盡全力都不敢說做得夠好,哪里還敢保存實力?
寫得少,有兩個原因。一是懶散,所以經常是“半年不開張,開張管半年”,尤其是寫完一篇比較用心的長文之后,會沉浸在勞作后那種充實的喜悅中,可以躺下來看幾個月的閑書而不至于產生負罪感。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很少去規劃自己,興趣上喜新厭舊,所以很多覺得好玩的題目,在研讀一段時間之后,就會放在一邊,而被新的題目吸引。當然“新”和“舊”是相對的,因為“舊”話題被擱置后,過兩年或許又會被撿起來,成為“新”話題,繼續做起來。所以有時候跟朋友聊天說到我的某篇論文,我可以毫不心虛地說:這篇文章,從動念到完成,花了x年時間。(x可以是2,也可以是3或5)。因為確實從動念后有三五年就沒有再看過。這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習慣,因為重新撿起來的時候,要把冷灶燒熱,關于這個題目就需要一個新的“預熱”時間。當然,從正面來說,有時暫時擱置也是因為覺得準備不足,就不強行去寫,而是先放一放,等著它慢慢長大。而一個題目一旦動了念,即便平時不去專門搜集材料,在看其他書或閑覽的時候,與之相關的內容,也還是會自動從紙面浮現出來。所以有時候一篇文章一直覺得沒有把握去寫,但是某一天看到某一本書,或是某一條材料,忽然就覺得可以動手了。當然,顧隨教人寫作,說到“巧遲不如拙速”,這句話我也常記在心,提醒自己,有的時候不必過于求全,不妨稍微寫得快一些。
周:你認為,這十年來,在學術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變化?
王:突破肯定談不上,我目前不太去想一些特別整體性的問題,即便涉及整體性的問題,也多是從局部入手,小題大做——我總覺得自己對局部的了解還不夠。當然這也是我需要克服的問題,因為實際上總體和局部的了解應該是相互作用的,我們不太可能先窮盡所有的局部再去了解整體(實際上也不存在一個既有的整體),也不可能先充分了解了整體,再去研究局部,只能是大概有一個整體的輪廓,以這個輪廓去大致確定局部的定位,同時在對局部的研究中調整對整體的認知,這個過程是無盡的。所以我想我也應該慢慢試著去研究更“整體”一些的問題。我平時的閱讀和研究不是很有明確的整體目標,多是隨著興趣讀相關的書,解決自己對世界認知的一些困惑,屬于日拱一卒型。所以我這十年所做的工作,談不上突破,只能是說為將來的突破做準備——假如將來會有突破的話。
如果說這十年有什么變化或者說進步,我想是慢慢懂得如何閱讀、理解以及評論文學作品了。2015年我們聊過一次,那次我說到我更多地研究的是死人,而很少研究活人。所謂研究死人,其實是文學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活人,指的是文學評論。二者雖然有相通之處,畢竟還是有所不同。2014年以后,由于外部的原因,加上隨波逐流(如果用褒義詞,也可以說是隨遇而安)的習性,我較多地關注活人,閱讀了比較多的當下作品,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更多地懂得了如何切近新鮮的文學作品。
“‘虛心涵泳,充分體味作品自身”
周:我看你近年的文章,對當代作家的關注較多,其實每位從事文學批評的從業者,都有自己偏重的作家。你比較喜歡的作家是哪些?或者說,你一直集中關注、跟蹤研究的作家是哪幾位?
王:對,近幾年我確實對當下作家的作品關注得多一些。不過也沒有特別集中關注或跟蹤研究的作家,我想我的閱讀還是以“我”為主,在日常閱讀中發現能夠吸引自己的有創造性和獨特性的作品,會停下來仔細研讀,而不太會刻意追蹤某一個或幾個作家,所以說不上哪些是特別偏重的作家,因為畢竟發生在當下,文學的演變如流水,充滿不確定性——當然,當下最大的魅力也正在于這種無法預測的不確定性——下一部能夠吸引到我們的作品是什么,其實無法預測,也充滿偶然性。我只能說近些年我認真評論過的作家如劉亮程、朱琺、石一楓等,都是很有意思也值得關注的。當然,沒有評論過的作家,并不代表我就覺得不好,因為評論也是和個人性情有關的,有的作品很好,你也知道很好,但是與你的性情不合,你覺得自己可能很難充分理解它;也可能其實有意評論,但是一時沒有想到合適的談論方式,或者覺得準備還不足,也會暫時擱置,但會一直關注。而且那些沒有被談論的作品,也并非不存在,它們隱藏在每一篇文章的背后,作為背景,制約著我們下筆的分寸。
周:近年,你寫過兩篇關于賈平凹的評論文章,對賈平凹的寫作多有批評。對賈平凹或他們這代作家的評價,往往有兩極化的現象,他們同輩或稍晚一代的批評家,對他們的寫作基本是持肯定的,而年輕一代的批評家,則對他們的寫作有諸多批評。你認為這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一代人有一代的人審美”有關,還是年輕一代的審美更加自覺化?
王:這個說起來也很有意思。看起來好像是我一直在批評賈平凹老師,但是實際上有很多偶然性。最初好像就是因為很偶然的因素,寫過一篇對賈平凹的寫作提出質疑的文章,后來就決定再也不寫了。之所以決定不寫,也不是覺得這樣寫不對,而是我覺得應該有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事要去做。但是這個世界是這樣的,質疑的文章有時候會比肯定的文章傳得遠(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于是大家知道你寫過批評某位大作家的文章,下次編輯想要這方面的稿子時就會想到你(畢竟你是熟手),而來約稿的編輯又往往是好朋友,不好意思推托(比如有一篇就是你逼我寫的),于是就又寫了一篇,這樣就會被一步步套牢,我給人留下的可以寫批評某一位大作家文章的印象就更深了。
這樣說,似乎有推脫責任的嫌疑,實際上既然答應了約稿,自然是文責自負,因為答應了就是覺得可以寫也應該寫。不過我不建議給“批評”或“表揚”賦予過多的倫理內涵,比如我們可以認為愛“表揚”的評論家是厚道的,也可以認為是拍馬屁的,我們可以認為好“批評”的評論家代表了良知,也可以認為是嘩眾取寵。這些兩極化的判斷都可能是對的,也都可能是不對的,凡是一件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說明我們的思維已經走在了錯誤的道路上,問題的根本一定不在這里。
文學應該批評(狹義的批評)還是表揚,我認為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甚至這樣的一種兩分法其實會模糊了文學批評的真正意義。文學批評不是要去夸一個作家,或是去罵一個作家,而是要進行一種有價值的創造。我們在閱讀之初,自然要盡量排除先見,“虛”心涵泳,充分體味作品自身,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做出論斷。應該是先信后疑,而不應只疑不信,或只信不疑。信才能得其大體,疑才不會在文本中迷失自己,被作家牽著鼻子走。如果預先懸置一個“夸”或“罵”的目標,帶著這樣的目標去閱讀作品,自我就不會真正打開,“我”與作品也沒有形成有效的互動,很容易只看到自己需要看到的東西,而不能對作品有整體的感知,“我”在閱讀過程中也不會有任何成長。“小心假設,大膽求證”,這樣的話從字面上來說當然沒問題,但事實上人在有了既定假設之后,求證時自然就不免向假設靠攏。當然,我現在決定,以后輕易不再寫批評賈老師的文章了。這次是認真的。
至于不同時代的人對賈平凹作品評論的兩極化,我以前倒沒有特別在意,如果有的話,我想這里可能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如你所說的,不同年代的人,在審美上有差異;二是我覺得作家的作品也在變化,老一輩的評論家可能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早期,所以評論新作時總不免帶有早期的閱讀體驗和審美判斷,而年輕的評論家可能更多看到他的新作。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原因也可能在于文學之外。現在的評論很多時候是人情或任務。所謂人情,指的是大家都有交情,寫評論常常會成為捧場或支持。我們現在流行“小伙伴”,老一輩自然也會有他們的“老伙伴”。所謂任務,指的是寫作未必是自己內心真實情感和態度的流露,而只是為了多一篇文章,用于評職稱或完成考核。論文只是謀飯的工具——我從來不反對寫文章可以謀飯,但不應該僅僅是謀飯。這樣的評論,其實是可以量產的,因為大家好歹都是讀過博士、碩士的人,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知識,最擅長的就是花式夸人,可以說幾乎沒有夸不了的人。只要給個角度,把腹中的知識堆積上去,就會是一篇論文。尤其是賈平凹老師特別體貼,他的每部長篇小說都有一篇非常用心的后記,在后記中,他會手把手推心置腹地教你如何正確閱讀、理解、闡釋他的小說。評論家只要按圖索驥,照章發揮即可。
所以我們的時代會有一個現象,就是作家會非常希望自己被評論,我也見過很多作家抱怨評論家不夠關心他(不關心的表現就是不給他寫評論),但如果評論是一種含有情感和態度的創造性工作,那我想作家面對評論的態度也會嚴正慎重得多,不會像現在這樣輕松乃至輕佻地要求自己“被看”,因為你真不知道這群評論家會說出什么話來——但是現在,他會預設,評論就是捧場。而且誰夸我我就覺得誰說得好、說得對,這本就是人性。
至于我們這代人是否比老一輩更審美自覺化,我也沒那么樂觀。從知識結構上,我們這代人,在專業知識方面,可能會更完備一些,因為趕上了好時代。但是也因此,我們的評論可能也會更單一,因為都被局限在相似的專業知識里,一方面是專業化程度加深,一方面是廣度上反而未必趕得上前輩。大家經常說的同質化其實就源于這一點。大家讀著同樣的書——也因此少讀專業以外的書,有著差不多的經歷(本科—碩士—博士—高校或研究機構),在對人心、人性的理解上其實反而可能不如我們的前輩。而且如前面已經說到的,老一輩有老一輩的“老伙伴”,我們也有我們的“小伙伴”,在人情方面大家也可以說是半斤八兩,年輕一代未必比老一輩更自覺。
周:之前聽你多次談起網絡文學,尤其是你談網絡文學與古典文學之間存在某些關聯,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幾乎沒關注過網絡文學,根據你的閱讀,你認為網絡文學今天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
王:我確實讀過不少網絡小說,一度甚至頗有沉溺,尤其是兩次手術后養病,因體力不足,注意力不能集中,更是看了很多網絡小說,既算是過了網癮,也算是一種休息吧。
根據我有限的閱讀,目前網絡文學的發展,尚屬于群雄并起的草莽時代,雖然也孕育了不少新的可能性,但還只能算是出現了陳勝、吳廣,而沒有劉邦、項羽——所以才會遍地“大神”。我想至少要產生類似于武俠小說中的金庸這樣的作者,作為類型文學的網絡小說才算是真正立住了。
而且我們對網絡文學的理解和想象也為現狀所限,仿佛網絡文學就只能是小說,而小說又只能是類型文學,甚至爽文。我想在網絡文學出現之初,它其實倒是反套路的,甚至可以說是先鋒的,當然也不乏類型文學(畢竟最早產生巨大影響力的網絡小說是《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但是并不像現在這樣在資本的驅使下,類型文學一枝獨大。現在的網絡文學看似繁榮,但只體現在作品和讀者數量上,從文學的品質和品類上看,是狹窄的。“網絡”是一種新的生產和傳播方式,這種新方式會影響“文學”呈現出來的樣貌,但并不必然排斥所謂的“傳統文學”,也不必然排斥小眾和嚴肅文學。但我也相信,隨著那些與“傳統文學”相比有真正異質感的可能性的發揚光大,“傳統作家”遷移到“網絡”,網絡文學的前景是闊大的,不會再簡單地只是加一些“網絡”元素的“傳統文學”的低配版。所以,可以說我對網絡文學的現狀評價不高,但對網絡文學的未來很看好。
至于網絡文學和古典的關系,當下也的確出現了一些古典文學修養很好同時也著力借鑒古典文學符號、情節和方法的網絡小說,但是從總體上來說,與其說是網絡文學和古典文學關系密切,毋寧說它是與傳統文化關系密切,而實際上類型文學、通俗文學都不免跟傳統文化藕斷絲連,因為中國人的情感與欲望結構,是植根于傳統文化之中的。而對于多數網絡作家,傳統文化也只是作為碎片化的標識點綴在作品中,以期喚起讀者熟悉的情感想象模式,他們并沒有能力從整體上去把握傳統。
周:你有一段時間很迷戀古典文學,集中研究過一段《聊齋志異》,當時還準備就此寫一系列文章。你是如何看待古典小說的?它們在今天還有哪些意義和價值?
王:確有此事,不過我還沒有想好如何去寫,所以看了兩遍,最后只寫了一篇關于汪曾祺改寫“聊齋”的文章。這也出于一種考慮,就是不必跨界太遠,雖是說“聊齋”,但也是在說汪曾祺,畢竟所學專業是現當代文學,把話題拉到專業內,比較有底氣些。
至于古典文學或者說古典文化著作,我確實一直很有興趣閱讀,這不是出于具體研究的需要,而純粹是覺得有意思,也是覺得作為中國文學研究者,應該多了解一些中國文化的來路。
說到這里,我會想到我們今天該如何看待或者說評價中國傳統文學。在“五四”時期,新文化派和守舊派在文化上是對立的,也各有道理。新派——比如胡適——會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倫理已經不能適合新的時代,那時候緊迫的是“現代”,是讓中國進入“現代國家”之列,是讓中國人先生存下來,所以他們會以“求同”思維看中國傳統,認為傳統文化乃至漢字不能與世界相通,不能合于“現代”的“普遍”,所以需要被淘汰。而守舊派——比如劉師培(其實還包括屬于新派的周作人,看出了文化斷裂的復雜性)——倒是“求異”思維,會認為恰恰是那些與“世界”不同的部分,才是中國文學的根本,才是中國文學足以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理由。
到了今天,中國也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現代”歷程,雖然挫折不斷,很多地方雖不能說是已經“足夠”現代,但是“現代”也的確深入人心,我們面對古典文學的態度和判斷,也的確應該與“五四”先哲有一些不同。這種不同不是對“五四”的背叛,而恰恰是繼承——每一個時代的人都要認識自己的時代使命,面對自己時代面臨的問題。當然,我們說的“現代”,固然是來自對西方的借鑒,但也并不存在一個現成的“現代”可以直接拾來,我們的“現代”只能是我們在我們的時代里,面對我們的問題和處境,結合我們的傳統,創造出來。日本藝術家岡本太郎有一本書,書名即是“傳統即創造”,傳統需要創造,現代更需要我們的創造。而古典文學在今天的意義,我想是可以使我們在“現代”的路上越走越遠時,以過去的“經典”來作為鏡鑒,參與“現代”的創造,當然,在“現代”之眼中,“古典”也會再次“創造”,洗濯出新的意義與價值。如果“古典”只是古人認識的那個古典,它對于我們現代人就沒有意義,我們今天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如“學衡派”、林紓,多有恕詞,甚至去發掘他們的價值,絕不是因為他們是正確的,而恰恰因為他們是失敗的,他們只有失敗了,才有被重新發掘的價值。
“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哪里”
周:2015年,我們對話時,你在談批評觀時說過:“我們只有了解胡適,了解周作人,甚至了解學衡派,才能更深入地了解魯迅。對于他們的研究,當然會給我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學觀,而這種文學觀有助于我在評論當下文學作品時分寸的把握。當然,文學觀過分穩定、單一是很危險的,我相信最好的狀況是在持續的閱讀、思考中不斷地微調自己的文學觀,使自己能夠更多地向新鮮、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寫作經驗敞開,而不至于過分抱殘守缺。”七年過去了,你的閱讀和思考更加深入了,批評觀也相對穩定了吧?這些年你的閱讀和思考、寫作,你所秉持的批評理念是什么?
王:我關于批評的看法,并沒有根本的變化,如果說有什么變化,就是我對于你上面所引的這段話理解得更深入了一些,有些在以前懸為理想的目標,現在覺得似乎可以比較踏實地觸摸到了。當然,看到朋友引用自己多年前的文章里的話,心中是有點惴惴不安的,因為如果現在覺得之前的說法很幼稚,會覺得羞愧,就像看到自己兒童時的照片;如果覺得之前的說法很好,就更羞愧,因為這說明這些年的學問沒什么長進。
周:在《“業余”的批評及牙與胃的功能》中,你談及:“在我們與文學世界之間,就隔著一個文學理論的鴻溝。這些文學理論與文學術語,成為我們閱讀、批評文學的視角。但正如狂奴欺主,工具也會反客為主,束縛文學閱讀者的眼光,就好像望遠鏡本是要人看得遙遠,顯微鏡是為了觀察得精細,只用望遠鏡和顯微鏡則不免管窺蠡測,只見一斑。文學理論和文學術語也會變成文藝黑話,限制我們看到第一手的文學世界。過度依賴文藝黑話的評論可以用一個函數公式來展現:f(x)=y。x是作品,f是文藝黑話,y則是評論文章。只要將作品源源不斷地放入文藝黑話的算法里,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文學評論產生出來。當然有時候f也不僅僅是文藝黑話,也可能是某一種特定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這樣的評論是可以批發,并且立等可取的。”這個觀點我非常贊同,過多地使用理論或理論缺失,可能都是問題。那你認為,文藝理論和文本解讀,它們應該如何平衡,才能更趨于合理或完美?
王:這句話開了點玩笑,甚至故意用了個函數公式,不過意思還是認真的。文學理論在今天我們對文學的理解中,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不懂文學理論就不可能懂現代文學,在你所引的這篇短文里,我還說:“直接與現實狹路相逢,赤手捉蛇,固然是一種本事,可是放著現成的橋不走,偏要去泅水,也不免迂執……”現代文學與現代理論之間是相互浸潤的關系,靠天然的直覺和體悟,不可能真正懂得現代文學——而實際上,處在現代的文學語境里,也不存在不被現代理論“污染”的直覺。
不過理論的使用,要有其適用性。理論有其深刻性,也有其抽象性,當它與具體的文學作品遭遇時,需要有一個相互的激發,而非可以即拆即用;我們日常用到的文學理論,多來自西方,這些理論是從西方文學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移植到中國,自然要有一些變形;具體到使用理論的個人,也會各有天性、才情的差異,有的人適合耍大刀,有的人適合用繡花針,也并不是只要理論好,就一定適合每個人。
最為重要的是,不論理論如何重要,最終和文學文本短兵相接的,是有理論素養的“我”,而不是理論自身。所謂文學理解、文學批評,都應該是“我”先真正懂得了“理論”,然后“我”去闡釋文學,而“我”與文學的交融搏斗,也不僅僅是對靜止的理論的使用,而是在創造理論新的內涵。理論也只有在不斷的文學評論實踐中,才能真正地完成。如果“我”確實懂得了理論,而又能真正在文本中悉心涵泳,那評論呈現出來的就會是一個完整圓融的樣貌,而不是所謂的“兩張皮”,就好像我們吃了各種食物,最后都變成力氣,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健康的人,而不是各種尚未消化完全的食物。
周:在《“業余”的批評及牙與胃的功能》中,你也談及:“在閱讀上要盡量做到‘牙好,胃也要好。牙好,可以嚼得動;胃好,可以吃得進。只有廣泛涉獵,才能造就健壯的體魄,養成健全的人格,兼有趣味的綜合與理智的分析。”在今天這種龐雜的知識生產下,要做到絕對意義上的廣,也很難。或者說,太廣似乎也會影響到專。今天,我們會看到很多批評家涉獵的領域很廣,但似乎似是而非的東西又很多。我知道你的閱讀是很廣的,在廣和專之間,你是如何平衡的?
王:如前面我們聊到的,一件事如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說明我們的思維已經走在了錯誤的道路上,比如廣博與專精的關系,強調哪一方面都可以,但也都有缺失。其實廣博和專精是在同一個方向上的。如你所說涉獵廣,很容易似是而非,似是而非不可能算得上真正的廣博;而致力于“專”可能視野狹窄,視野狹窄又如何能避免一葉障目而有真正的專精呢?專精一定是建立在一定的廣度之上的。沒有一定的整體感,我們對于部分,不可能做出真正精準的理解與評判。而沒有精深的研究,所謂廣博,其實不過是碎片化知識的拼湊,甚至是茶余飯后聽來的耳食之言,這樣的見識出租車司機會超越我們,百度更會超過所有人。
所以廣博與專精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做到也確實難,因為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所以我想可以設定有范圍的廣博,而且所謂廣博,起碼要達到“高等常識”的程度,而專精則也不宜限制太窄,可以適當放寬,這樣不至于坐井觀天。
當然,最重要的是多深度閱讀,有足夠多的深度研讀,專精與廣博才會平衡得更好。所謂“一力降十會”,就像練武功,如果力量達到了,很多本來使不出來的招式也使得出來了,很多本來需要費盡心思平衡的兩難問題也就不再是兩難了。之所以有很多兩難,只不過是因為我們讀書太少,力量太小。當然這也是理想境界,我們可能永遠都達不到類似于錢鍾書那樣的閱讀量,我本人也平衡得不好——不然就不會出現你前面問的為什么寫得太少的問題,但是我很向往讀書上的“大力者”的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周:近幾年,年輕批評家似乎都有一種“出圈”的沖動,除了專業外,廣泛參與到文化領域,甚至是偏娛樂的圈子中去。但你是少有的一直保持定力的年輕批評家。你是如何看待年輕一代部分批評家的“出圈”現象的?
王: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話題。我覺得這個話題得從幾個層面來看。
首先,批評家以個人身份參與到圈外領域,是個人自由,更無傷大雅,只要自己覺得好就好,甚至一個優秀、有趣的人出圈,會讓更多人看到有趣的人與事,倒是群己兩利的。在這個層面,我們要注意的反倒是出圈的效果怎么樣——我們要能夠把本“圈”內真正好的東西帶給更多人,到了別的“圈”,也要達到該“圈”的及格線。畢竟要出圈,其實是能同時跨過兩個圈的門檻,而不能因為我們有“批評家”的身份,就要求別人對我們“低標準、寬要求”,不能因為自己是“外行”,就真的“外行”。舉個例子吧,我想如果能像易中天那樣,讓更多的人喜歡文學與歷史,其實也是有功德的。
其次,作為一門學科,或者說一個行當,如果常有“出圈”的焦慮,以不能“出圈”、未能被更廣大的人群知道為憾,這是不成熟的。那很可能說明這個行當還不成其為一個行當,這門學科也還沒有成其為一門學科。因為我們不能想象一個研究相對論的人會遺憾懂得相對論的人太少,甚至恰恰相反,他們很可能有另一種心理,會以自己的研究被更少人懂得為榮。我們在看科學家的軼事時會發現這樣的自得:全世界懂得量子力學的人只有三個,而“我”是其中之一。一門學科有廣大影響,于社會有益,是一回事,這個行當的從業者以知道自己的人數多寡判斷優劣,是另一碼事。
最后要說的一點,就是不論有沒有出圈,我們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要出圈,先要在圈里。陳寅恪在談論學術時,曾提出“預流”之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陳垣〈敦煌劫余錄〉序》)我們可以移來說“在圈”與“出圈”。我想一個學者,首先要“預流”,然后才談得上超越潮流;同樣,如果要出圈,首先要在這個“圈”里,先要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工作做好,在此之上才能談得上“出圈”,把本來只為“圈內人”能領略的美好風景帶給更多人,如果從一開始就不曾在圈里,那還說什么出圈呢?那不叫“出圈”,那是沒入門。
周:若給批評家朋友或晚輩推薦幾本書,你會推薦哪幾本?
王:推薦書,就像開藥方,要針對對方的癥狀和需求,而且我很少覺得會有一本或幾本書讓人讀了會立刻就能掌握某種秘訣或法則,像武俠小說中的男主人公獲得奇遇,修煉了某種絕世武功(比如降龍十八掌或易筋經之類),一朝登天,走上人生巔峰,我們不論是要更多地理解這個世界,還是掌握一些閱讀、理解、闡釋文學的方法,都需要大量地讀書閱世,甚至在讀書較多以后,很多“爛書”也會從反面給我們以啟示。所以上次我們聊的時候,你提出這個問題,我其實是躲懶,偷換了概念,糊弄了過去。這次我想如果非要推薦的話,就推薦米蘭·昆德拉的《帷幕》和《小說的藝術》吧,倒不是說這兩本書就一定比其他談論文學的書更好,只是它們在我個人關于文學理論的閱讀中,是最早對我的文學理解產生很大沖擊的。
周:謝謝晴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