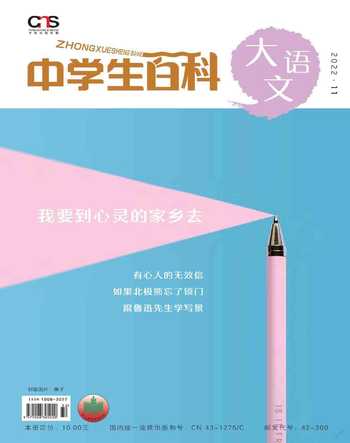哲學的意義在于追“問”
張建慶
“問”這個漢字,是“門”框里一個張開的“口”,這個結構形象生動地展示了身處困境之“門”的人竭力超越的姿態。當我們跨越這道“門”,從另一個世界來到此世界時,我們都“張開了嘴巴”——人一生下來,為什么首先不是睜開眼睛,而是緊閉眼睛,并且張開嘴巴放聲大哭?有人說“這是新生命為誕生而發出的嘹亮號角”,以此向世界宣告:“我來了!”
哲學家卻說,人是從虛無中被拋擲到此世界的。之所以初來乍到卻“放聲大哭”,乃是因為我們對當下之世界有深深的恐懼和不安,有無盡的困惑與驚訝。“我”不知道自己來到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不是充滿了風險?內心無名的恐懼和不安陣陣涌來,放聲大哭只是給自己壯膽而已。但是,在長久的啼哭而沒有發生什么危險之后,最初的恐懼和不安會慢慢褪去。“我”止住了哭喊,睜開了眼睛,豎起了耳朵,邁開了腳步,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困惑和更大的驚訝——這個世界“我”從來沒有來過,“我”完全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海,不知道它們意味著什么,“我”想要開口“問”,但又說不出。“我”張大驚奇的嘴巴只是想要問:這是什么地方?為什么我從來沒有見過?誰能告訴我?

柏拉圖說,哲學的起源就是驚愕,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瞥見了星星、太陽和蒼穹,而這一瞥,便使我們產生了去探求萬物的沖動,于是哲學就在我們的心中油然而生……除了驚奇之外,哲學沒有別的開端。亞里士多德說,古往今來人們開始哲理探索,都應起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他們先是驚異于種種迷惑的現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重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運行以及宇宙之創生,作成說明。正是這種驚訝、驚愕、驚奇、驚異,使我們從最初的蒙昧和混沌中慢慢地覺醒過來: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這一切的一切又是從哪里來的?
從泰勒斯的“仰望星空”到屈原的“天問”,從蘇軾的“把酒問青天”到牛頓的“蘋果何以落地”,從“嫦娥奔月”到“嫦娥探月”——探究這些問題,其實并無什么實用的、功利的目的,只不過是人發自內心的一種需要、慰藉罷了。
人,走出了黑暗的“洞穴”,推開分割此岸與彼岸的“門”,站在了新的太陽底下,他不能不問:“我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雅斯貝爾斯認為,哲學的本質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哲學(philosophia)——這個希臘詞是由“philo”(愛)和“sophia”(智慧)結合而成的,意思就是:愛好知識(本質)的人,同那種占有知識的人是不同的。這個詞的含義一直保留到今天:哲學的本質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所謂哲學,就是前進路上的過程,哲學提出問題要比解答問題來得重要,而且每一個回答又將引出新的問題。
所以,哲學不是“智慧”,而是“愛智慧”,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只有神才有智慧,人是沒有這個資格的,人至多只能像愛神一樣去“愛”智慧。
(作者系湖州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