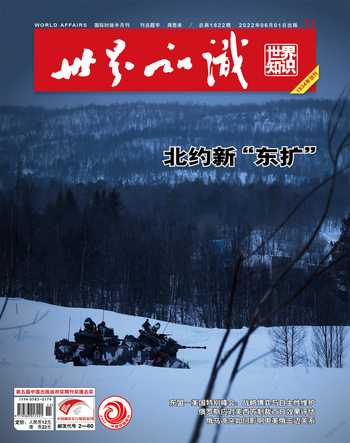韓國和北約“走近”:歷史和現實的纏繞
劉天聰
近來,韓國與北約頻繁互動,吸引了周邊國家的廣泛關注。韓國和北約頗有歷史淵源,此輪走近各取所需,背后真正的推手是美國打造多邊化、全球化同盟體系的長期謀劃與策動。“泛西方陣營”加緊抱團,國際政治安全形勢面臨新挑戰。
韓國與北約的“前世今生”有著緊密的政治聯系,雙方作為美國全球同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識形態和對外戰略接近,合作歷史悠久,存在“感情基礎”。
我們都知道,朝鮮半島南北分裂以及韓國的誕生,是冷戰初期美國在亞洲戰略收縮的產物。1947年,隨著冷戰全面開始,美蘇根據1945年雅爾塔協議合作托管朝鮮半島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美國杜魯門政府當時認為,歐洲才是美國的戰略重心,朝鮮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很小,重要性排序很低,加之戰后美國國內裁軍、削減軍費的政治壓力巨大,朝鮮內部形勢又異常復雜、美國難以大包大攬,1948年5月,美國決定主動“減負”,在半島南部組織單方面選舉,扶植李承晚上臺。
當時,美國在東亞收縮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騰出手來在歐洲扎根擴張、遏制蘇聯。1948年7月,美國與《布魯塞爾條約》成員國英、法、比、荷、盧及加拿大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建立跨大西洋的同盟條約組織。這輪會議延續了將近一年。1949年4月,以美國為首的12國外長在華盛頓簽署《北大西洋公約》,北約組織成立。與此同時,1949年上半年,美軍陸續從韓國全部撤出,隨后與韓方簽訂了美韓《相互防衛援助協定》《軍事顧問協定》。這輪此消彼長,標志著美國基本上完成了戰后初期在亞洲收縮力量和防線并將主要戰略部署錨定歐洲的政策調整。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政府認為戰爭是由蘇聯支持發動的,是“柏林危機的更大規模重演”,必須予以堅決回擊,“否則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于是迅速作出決定并大規模軍事介入。為了加強介入的合法性,美國操縱安理會連續通過第82、83、84號決議,授權組建“聯合國軍”,由美國統一指揮,參加朝鮮戰爭。從構成上看,“聯合國軍”基本是北約聯軍的翻版,除葡萄牙和冰島外,其他北約成員國全部派軍隊或后勤支援團參戰。按人數計算,北約成員國派兵數量占到了“聯合國軍”的97%。
1953年7月,朝鮮戰爭以“停戰”結束,但“聯合國軍司令部”并未解散,這個由13國組成、一直存在至今的“北約亞洲分部”成為美長期干涉朝鮮半島內政的工具。由于有韓美同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政治聯系,從1948年建國至上世紀60年代初第一批與韓國建交的國家里,北約成員國占了一多半。這些國家既是韓國“最早的朋友”,又在朝鮮戰爭中“以鮮血守衛過韓國”,在后來的半個多世紀里,被歷屆韓國政府視為核心“友邦”。
冷戰期間,韓國和北約作為美國同盟體系的東西兩翼,為美國贏得與蘇聯的競爭、建立全球霸權立下“汗馬功勞”,但直至21世紀初,雙方之間的橫向聯系并不多,更多是同時作為美國盟友、協調性地配合美國的外交安全布局,服務其地區與全球戰略。
2008年2月,保守勢力的代表李明博出任韓國總統。此后,在美國的撮合下,韓國開始與北約走近。2009年12月,韓國外交通商部次官補李容浚訪問北約總部,與北約副秘書長比索涅羅簽署雙邊情報安全諒解備忘錄。2010年3月,韓國與北約簽署協定,成為北約組織下設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第45個成員國。2012年9月,韓國與北約簽訂《個別伙伴合作計劃》(IPCP),為雙邊全面合作構建起基本框架。
2013年2月樸槿惠上臺,韓國保守派繼續執政,與北約的合作進一步加深。2013年4月,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訪韓,這是北約領導人首次到訪朝鮮半島。此訪期間,雙方就共同應對朝鮮半島核問題達成諸多共識,商定加強網絡安全合作,特別提到“韓國將參加北約合作網絡防御卓越中心(CCDCOE)主管的網絡防御訓練”。2016年10月,尹炳世赴布魯塞爾參加北約阿富汗問題部長級會議和北約理事會關于半島局勢的專門討論會。在韓國的推動下,同年12月,北約理事會首次就朝核問題召開特別會議,通過針對朝鮮的措辭嚴厲的聯合聲明。
2017年初樸槿惠遭彈劾下臺,文在寅在隨后的大選中獲勝,進步勢力重掌政權,但韓國與北約加強合作的方向并未發生變化。2017年11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訪韓,雙方就朝核、東北亞局勢及網絡安全、防擴散、反恐等問題進行交流,并根據形勢變化修訂了《個別伙伴合作計劃》。2021年11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議長元仁哲訪問北約總部,與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鮑爾等高官會晤,商定加強交流和合作。
2022年以來,北約與韓國頻繁互動,俄烏沖突爆發后雙方關系更是急劇升溫。4月7日,韓國外長鄭義溶受邀參加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外長會議,就烏克蘭問題和半島局勢闡述基本立場,并與相關國家外長會晤,商討加強北約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亞太四國的合作方案。同月11日至14日,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鮑爾訪韓。月底,韓國候任外長樸振透露當選總統尹錫悅已收到相關方邀請,正在考慮是否參加即將于6月底舉行的北約峰會。5月5日,韓國宣布加入CCDCOE,成為該機構的首個亞洲成員。
韓國與北約的快速走近沖擊地區安全,使近期本已日益惡化的半島、東北亞局勢雪上加霜,并在全球層面上進一步助長政治分裂、陣營對立的消極潮流。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此系韓國首次加入北約常設的、帶有情報交換和軍事安全技術合作性質的機制化平臺,意味著美國的東亞盟國與歐洲同盟體系邁出了相互融合、橫向一體化的關鍵一步,這個“從無到有、從零到一”政治意義重大,長期影響不可低估。
韓國和北約的走近雖然有韓歐雙方的相互需求,但更重要的是美國在背后的策動。在俄烏沖突不斷加劇、中美博弈日益激化的背景下,韓國與北約近期的熱絡,作為美國主導的“新冷戰”一環的色彩更加明顯。
美國試圖打通歐亞同盟體系、重建并拓展“泛西方陣營”的戰略謀劃是韓國與北約走近的最大動力。近年來美國軟硬兼施,不斷拉攏、要求其他國家加入其遏制中國的陣營,在供應鏈、高科技、意識形態等領域與中國謀脫鉤、搞對立,其糾集的對象不僅限于傳統的亞太國家,也包括北約成員國等域外國家,試圖打造全球性的泛西方遏華陣營,以“新冷戰”壓制中國的發展。俄烏沖突爆發后,為最大限度對俄施壓,美國強化、拓展同盟體系的動作進一步加快。如果說之前是為了對付中國,引歐洲盟友之力投放到亞太,那么這一輪就是為了對付俄羅斯,又將亞太力量歸并過去,強化在歐洲方向的部署。

2022年5月16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國會全體會議上發表就職以來的首次講話。
長期以來,韓國的戰略重心一直集中在半島、東北亞和亞太地區,對歐洲安全事務并不特別關心——這從今年以前韓國與北約的高層往來中談論的主要議題從未涉及過歐安問題便可窺見。而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韓國歷屆政府一向重視與俄羅斯的關系,建交以來經貿往來不斷加強,文在寅時期又著力深化雙方在全球事務和國防軍事方面的合作,2021年3月韓俄剛剛簽署了《國防合作協定》,韓國最新研制的運載火箭也大量使用俄技術和部件。在這樣的形勢下,韓國此次不惜損害韓俄關系加入對俄制裁,又在如此敏感的時期公然與北約攜手,背后的美國推力之大可想而知。
當然,韓國對北約也有自己的政治安全訴求,并不都是給美國“做嫁衣”。一是在朝鮮和半島核問題上爭取外部支持。朝鮮始終是韓國最重要的安全關切。在近年來半島核問題長期拖而不決、逐漸國際化的情況下,囊括三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德、意等多個重要國家的北約集團,立場態度對韓日趨重要,無論是在安理會層面對朝施壓,還是落實國際制裁,韓國都必須獲得北約和北約國家的支持。二是提高國際地位和話語權。隨著經濟與科技不斷發展、國力不斷提升、流行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大,韓國對更高國際地位的心理訴求大為上升。加之氣候變化、網絡安全、防擴散、反恐等全球問題也日益關系到韓國的實際利益,韓國近年正多管齊下,著力拓展域外關系,與北約走近是其中重要一環。三是平衡中國的影響。韓國對華經濟依賴度非常高,政治、安全也受到中國的巨大影響。近年在不斷夯實韓美同盟基礎上,韓國著力加強與東盟、印度、歐洲等域外力量之間的關系,作為平衡中國的杠桿。
歐洲也希望進一步深化與韓國的關系。當前主要訴求是建立對俄施壓統一戰線。韓國是俄第七大貿易伙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又是國際金融強國,拉韓加入對俄制裁無疑可進一步打擊俄經濟。2月28日,韓外交部宣布對俄停止出口戰略物資,并參與將俄踢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SWIFT)的行動。此外,歐洲還有借朝核問題逐步介入東亞事務,與韓國基于意識形態在全球事務上加強合作和政策協調的考量。
由于韓國和北約的主要假想敵仍有差別,加之俄朝關系具有一定特殊性,韓國并不愿直接為歐洲承擔集體防御的義務。可預見的未來,韓國直接加入北約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美國推動下,北約還將繼續向亞太擴張,與韓國深化關系。尹錫悅政府就職后,韓國進一步融入美國的全球同盟體系、與北約“相向而行”加強各方面合作,如密切高層往來、參加聯合軍演、加入相關經貿或科技合作機制等,將是大概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