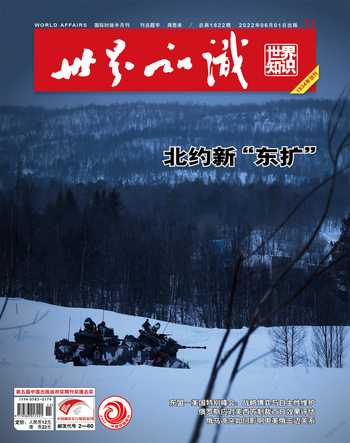新興市場崛起勢頭受挫

江瑞平
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快速崛起,作為世界百年大變局的最重要變化趨勢,近年來備受關注。而在遠慮與近憂雙雙重壓之下,這一崛起勢頭已經并仍將嚴重受挫,更需高度重視。
大勢:增長優勢逐漸喪失,崛起進程明顯趨緩 進入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整體快速崛起,主要表現為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所占比重和地位快速攀升。如按購買力平價測算,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在2000年為43.4%,2007年升至50.1%,首次超過發達國家占比,到2020年更升至57.6%,20年間攀升了14.3個百分點。而按名義匯率測算,這一占比在2000年為21%,到2020年攀升至40.5%,20年間攀升了19.5個百分點,幾乎翻了一番。推動這一占比攀升的直接原因,是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群體,長期保持了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相對于發達國家的顯著增長優勢。在這20年間,按名義匯率測算的全球經濟總量僅增長了1.5倍,發達國家更僅增長了0.9倍,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卻增長了3.8倍。這意味著在這20年間,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或增幅,要分別相當于全球平均和發達國家的2.5倍和4.2倍!
但從20年間的變化趨勢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相對于全球平均和發達國家的增長優勢,卻呈不斷縮小之勢,直至近年來幾乎完全喪失。如在2003~2012年10年間,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始終要比發達國家高出4個以上百分點,最多高出6.1個百分點,平均高出4.9個百分點。但在此之后,這一增長優勢開始逐步縮小,2013年跌破4個百分點,降至3.6個百分點;2014年又跌破3個百分點,降至2.7個百分點;2021年再跌破2個百分點,降至1.6個百分點;2022年預測更將跌破1個百分點,降至0.5個百分點!由此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所占比重的攀升步伐逐步放慢,崛起進程明顯趨緩。如按名義匯率測算,這一占比在2005~2010年五年間攀升10.7個百分點,由23.9%升至34.6%;2010~2015年五年間已降至4.9個百分點,由34.6%升至39.5%;2015~2020年五年間更降至只有1個百分點,由39.5%略升至40.5%,盡顯停滯之勢!
遠慮:治理赤字更難破解,轉型壓力更難化解 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整體快速崛起,首先得益于經濟全球化為其積極利用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市場,實現與國內人力資源優勢的高效組合,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機遇。而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卻越來越遇到全球治理赤字的嚴重困擾,以致引發逆全球化暗流涌動,國際貿易增速趨緩,國際投資波動不定,尤其是美國主導的發達國家越來越傾向于產業回歸、資本回流、技術保守、貿易保護,導致新興市場崛起面臨的外部環境整體趨于惡化。而在“世界政府缺位”的背景下,完善全球治理主要依靠大國協調,而無論是愈演愈烈的中美戰略競爭,還是遠超預期的美俄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沖突,都使協調難度越來越大,甚至有觀察認為世界目前正面臨“全球分裂”的危險。
與此同時,全球經濟正面臨“綠色轉型”的巨大壓力和“數字轉型”的強大動力。而對廣大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面對轉型造成的沉重壓力,“后發優勢”逐漸喪失,“后發劣勢”又已凸顯,越來越成為其繼續保持增長優勢的巨大障礙。
近憂:防疫鴻溝阻礙復蘇,西方調整損害增長 迄今仍在全球肆意蔓延的“世紀疫災”,更對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勢頭造成沉重打擊。尤其是相對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群體,與發達國家存在的巨大“防疫鴻溝”,越來越成為其經濟難以復蘇的主要障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2022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優勢之所以創下本世紀最差紀錄,將降至0.5個百分點,主要問題就在于此。
更加嚴重的是,面對急劇增大的通脹壓力,美歐大國不得不對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連續加息和縮減資產購買成為主導趨勢。如美聯儲繼3月加息25個基點之后,4月又加息50個基點,幅度創下本世紀最大紀錄。西方宏觀經濟政策急速調整,勢必通過加速國際資本外流、加快本國貨幣貶值、加劇輸入型通脹壓力、加重外債還本付息負擔等多種路徑,對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造成強烈沖擊,對其崛起勢頭造成進一步傷害。目前一些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壓力,比西方大國更加嚴重。如2022年3月,俄羅斯和巴西的消費者物價同比上漲率分別高達16.7%和11.3%,明顯高于美國和歐元區的8.5%和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