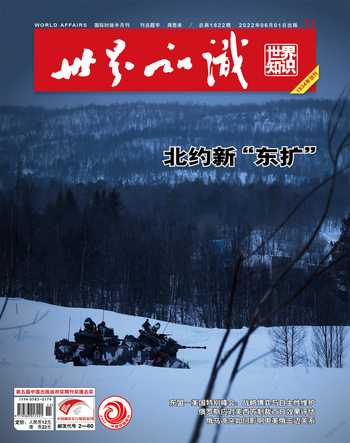日元“跌跌不休”凸顯日本經濟困境
董世國

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一(左二)。
今年3月以來,日元出現16連跌,創50年來最長連跌。日元兌美元匯率累計下跌逾11%,一度降至1美元兌換130日元,創20年來新低。日元兌換其他貨幣匯率亦持續下跌,人民幣兌日元一度突破20關口。在全球主要貨幣中,日元表現最弱,年初以來降幅僅次于俄羅斯盧布。日元迅速從避險貨幣成為市場上被爭相拋售和賣空的資產,引發各方高度關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關負責人稱,急劇的日元貶值恐將導致日本內需萎縮、交易環境惡化。
日元此輪大幅貶值是其自去年3月進入貶值通道以來的一次加速,既有美聯儲加息等直接誘因,也受到日本國際收支失衡、自身經濟結構性問題等多重因素影響。
一是日本貨幣政策與全球主要國家相左。在全球通脹加劇、美聯儲及歐洲央行等主要國家央行進入加息通道的情況下,日本央行迫于國內經濟復蘇乏力,仍堅持超寬松政策,實施固定利率購買操作,無限制購買國債以控制利率水平,導致日元與世界主要國家貨幣利率差日漸擴大,外匯市場上買入美元、賣出日元成為主流,直接壓低日元匯率。
二是國際收支失衡。疫情以來日本貨物和服務出口不振,國際旅游收入銳減;能源、糧食對外依存度很高(分別高達88%、63%),伴隨2021年下半年全球通脹,能源、糧食價格高企,日本對外貿易自去年8月起連續八個月逆差,經常賬戶余額連續四年縮水。市場普遍擔心日本今年出現經常項目逆差,日元匯率因此承壓。
三是經濟結構性問題掣肘。日本產業管制較嚴,數字化進程滯后,國內投資不足,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制造業外流加速產業空洞化,有競爭力的高附加值產業日益減少,出口產品附加價值的國內占比從1995年的94%降至2018年的83%。人口總量減少疊加人口結構老化,造成日本民間消費長期低迷,降低市場信心,削弱資本粘度,導致資金外流。日本經濟存在的上述結構性問題打擊了日本的競爭力,從而成為誘導日元貶值的長期因素。
雖然日元貶值有助于增加汽車、消費電子產品等日本主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并利好股市,被視作振興日本經濟的“福音”,但此番貶值對日本經濟整體弊大于利,正蛻變為日本經濟的“負資產”。
一是企業和民生承壓上升。受日元貶值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影響,日本企業物價指數連續13個月同比上漲,今年3月以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指數同比上漲33.4%。3/4以上日企表示目前日元匯率已跌至導致企業利益受損程度。日本國內糧食等食品上漲2%至5%以上,必要消費品上漲3%,電力燃氣漲幅達到16%至19%,民眾生活壓力劇增進一步拉低消費意愿。
二是出口提振效果減弱。受日企向海外轉移影響,日元貶值的出口促進效應已逐漸弱化。大和證券測算認為,2009年日元兌美元匯率每貶值1日元,日企經常項目盈余可提升1%,當前僅為0.4%。
三是增加金融系統風險。日元持續貶值導致日本資本加劇外流,加大日本股市下跌壓力,影響日本金融市場穩定并加劇全球外匯市場波動。此外,由于日元持續貶值,相當比例海外大型資產管理機構在避險投資組合里大幅削減日元頭寸,部分投資機構通過增持人民幣頭寸替代日元頭寸,日元避險特性受到削弱。
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日本經濟復蘇動力不足。2019年、2020年日本經濟連續兩年萎縮后,2021年轉為緩慢增長,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僅為1.6%,預計2020~2022三年平均GDP增速仍為負值。經濟復蘇前景黯淡疊加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等因素,日本政府陷入“既不能加息,也不能減息”的兩難境地,調控手段和空間相當有限。
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一公開稱此輪日元貶值為“惡性貶值”。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多次表示不希望匯率出現急劇變動,將密切關注市場動向。然而,在日元已貶至歷史低點的背景下,日本央行于4月28日召開金融政策會議,決定繼續維持大規模寬松貨幣政策,每天以固定匯率無限購買國債,抑制長期利率上漲壓力。由此可見,當前日本政府政策重點仍是促復蘇,而非穩匯率。盡管日本政府擔憂日元急速貶值的負面影響,但卻只能停留在“口頭干預”上。
據媒體報道,日本決策層人士曾表示,日本政府只有面臨貨幣、股票與債券市場遭受“三重拋售”、引發資本急劇外流時,才會選擇干預匯率。市場預測,在美聯儲堅持緊縮、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高企的情況下,日元匯率還將繼續走軟,今年底明年初或將跌破1美元兌140至150日元。
日元作為地區主要貨幣,有較強示范作用和外溢影響。1997年、2012年和2014年的三輪日元貶值均帶動地區多國貨幣大幅貶值。伴隨此輪日元下跌,今年3月以來亞洲主要貨幣均出現不同程度貶值,韓元、泰銖、馬來西亞林吉特、菲律賓比索、印度盧比兌美元分別貶值3%、3.3%、2%、2.1%和1%。
當前,亞洲經濟體總體經濟增長動力趨弱,經濟金融脆弱性不斷顯現。有觀點認為,在美聯儲加速退出寬松貨幣政策、全球貨幣市場收緊背景下,需警惕日元貶值引發“亞洲貨幣貶值潮”,甚至引發新一輪亞洲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