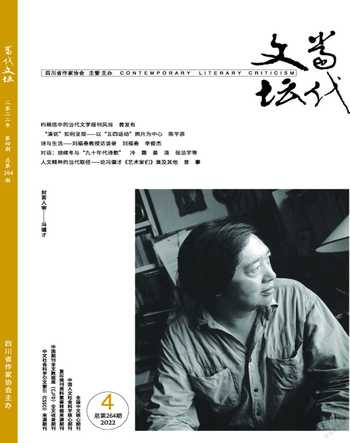關于《桑樹坪紀事》的話劇改編
周珉佳
摘要:《桑樹坪紀事》是1980年代“戲劇新時代”的首部改編劇,陳子度等人組成的編劇團隊在徐曉鐘戲劇美學的影響下,在朱曉平原著的共情中,對人物和情節進行了有機布排,獲得了技術性和藝術性的雙重成功。從小說改編為話劇,編劇重視在劇情推進過程中尋找人物與他人和時代的對應關系,把視點放到了更為廣大的社會生活中,以更大的容量包涵了生存的種種形態與方式,表現了作者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的冷峻審視。其合理的改編思路也體現了重要的經驗價值,在當下具有重要的指導性。
關鍵詞:《桑樹坪紀事》;劇本改編;經驗價值
以往論及話劇《桑樹坪紀事》①,研究者大多圍繞徐曉鐘“兼收并蓄”的戲劇美學觀念和它在1980年代重要的地位來闡述,關注點集中于舞臺導表演。然而被人忽視的是,《桑樹坪紀事》是1980“戲劇新時代”的首部改編劇,從小說改編為話劇,編劇對宏觀思路和細節處理的技術性和藝術性,都是這部話劇獲得成功的前提。追溯并總結陳子度等人是如何在徐曉鐘戲劇理念的影響下、在朱曉平原著的共情中,對人物和情節進行有機布排,具有重要的戲劇改編經驗價值。
一? 徐曉鐘為何選擇“桑樹坪”系列
1980年代初,中國戲劇界對“探索戲劇”研討與創作出現了一個小高潮,戲劇理論家和創作者們在吸收西方戲劇理論的基礎上,積極開拓演劇觀念和舞臺藝術表現形式,豐富了戲劇的現代性和藝術審美性;同時,注重戲劇敘事方法的創新,積極調動多種藝術表現手段和舞臺語匯,使現代戲劇將寫實與寫意、情與理、表現與再現交融在一處,恢復舞臺假定性在戲劇中的應有地位,重復發揮詩意和想象的表達空間,進一步解決形式與內容合一的問題。1950年代畢業于蘇聯盧那察爾斯基戲劇學院導演系、1983年就任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主任的徐曉鐘彼時剛剛導演完成了《馬克白斯》和《培爾·金特》,無論是舞臺藝術的先鋒姿態還是對民族文化心理的表達,都達到了空前高度。他認為中國的現代話劇應該持“打開”的態度,不僅要吸收,還要與世界高質量的戲劇平等對話,表現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遵循“以新現實主義為主、兼收并蓄地吸收一切有價值的其他藝術流派的成分”的總體美學原則。
經歷了歷史轉折,徐曉鐘對現實人生以及民族文化心理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認為中國的戲劇雖然要在美學意義上大膽創新,但仍不能丟掉表現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現實主義基底。“繼承現實主義美學傳統,在更深層次上學習與繼承我國傳統藝術的美學原則,有分析地吸收國外現代戲劇的一切有價值的成果,以‘我為主,辯證地‘兼收并蓄,孜孜以求戲劇藝術的不斷革新。”②有了相當的理論儲備,徐曉鐘自然想通過一部具體的創作演出實踐自己的戲劇理論、表達自己的戲劇理想。他想在戲劇觀大討論深化之際,以一部表達自己理論觀點的代表性作品作出一個回應甚至一場“答辯”,在這部作品中,不僅要在戲劇表現形式方面有大膽探索,還應從文化批判的角度表現人的復雜性,追求哲思表達。前文說到,徐曉鐘在1981年和1983年分別成功改編了《馬克白斯》和《培爾·金特》兩部外國戲劇,他十分期待創作一部中國原汁原味的、能夠代表中戲權威性的現代性戲劇作品。恰時,同樣積極參與戲劇觀大討論的理論家譚霈生向正在考慮劇本來源的徐曉鐘推薦了剛剛嶄露頭角的知青作家朱曉平,認為其“桑樹坪”系列小說有機會進行改編。
其實,從當時整體的創作態勢來看,由小說改編話劇的想法既是冒險的也是穩妥的:1980年代國內戲劇舞臺上尚未有十分成功的本土改編作品,幾乎都是直接選用國外經典話劇作品進行中國化的改編,如《高加索灰闌記》《馬克白斯》《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培爾·金特》等,沒有先驗的本土改編案例可以把握;但如果創作團隊能夠選擇一個相對成熟完整的高質量故事胚胎,這比從無到有地創作一個全新的劇本要有保障,正如李健吾先生所說,改編是戲劇獲得成功的一條捷徑。如此來看,選擇中國作家在1980年代中期創作的小說改編的確可行,且更有本土化的創作意義。
回顧當代文學史,1985和1986年是小說界異彩紛呈的兩年,無論是短篇、中篇還是長篇小說都井噴式爆發。1985年,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王安憶的《小鮑莊》、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接連問世,同年,李準的《黃河東流去》、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劉心武的《鐘鼓樓》獲茅盾文學獎。1986年,王蒙的《活動變人形》、莫言的《紅高粱》、張煒的《古船》、鐵凝的《麥秸垛》、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先后發表。在這般爭奇斗艷的喧鬧中,朱曉平的“桑樹坪”系列小說顯得存在感并不強,面影平靜甚至反響有些寡淡。而徐曉鐘為何出人意料地選擇朱曉平的“桑樹坪”系列作為自己的“答辯”之作呢?
朱曉平1978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文學系,1982年本科畢業留校工作,1985年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工作,而1985年發表于《鐘山》第3期的中篇小說《桑樹坪紀事》正是其處女作。“院長徐曉鐘”選擇“青年教師朱曉平”的作品作為改編藍本,其中當然有 “就地取材”“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量,作為學院領導樂于看到這樣的創作團隊——從故事胚胎到改編劇本,再到后期舞臺導表演,都是由中央戲劇學院全員完成,但更重要的是,徐曉鐘對改編劇本的故事胚胎有明確的挑選標準。
在那個時代,戲劇需要帶給中國人什么?作為“戲劇新時代的開場白”,徐曉鐘對戲劇故事胚胎的要求是比較高的——最基礎的要求即它必須是一個能夠“落地”的故事,題材具有合理性,人物的行為和命運軌跡具有說服力,一般受眾能夠承認故事背景和情節的真實存在,但其故事深層本質卻又超乎一般觀眾的認知程度,能講出戲劇性和震撼感;其次,故事可以靈活擴容或濃縮,可以適應戲劇現代藝術表現形式的表達需要;更高層級的要求是,故事胚胎要有厚度和深度,它具有可延長的生命力和社會歷史透視性,對生活真諦、現實生活、人性等有嚴肅的思考。
說回朱曉平的“桑樹坪”系列小說,它們圍繞著陜北一個名叫桑樹坪的村莊而展開,朱曉平通過自己下鄉知青的視角詳細書寫了這個“活化石”般的存在,塑造了男女老少各色人物,真實呈現了1968—1969年陜北黃土高原的封閉蒼涼和貧瘠困苦,揭示了現實生活的凝重和對民族歷史命運的思考。“桑樹坪”系列小說具有徐曉鐘要求的多個對標特征: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
首先,朱曉平的創作初看上去是知青文學,實際上又跳出了知青文學的格局;寫1960年代末,卻又超越了時代記錄本身;寫西北農民“貧”與“困”的現實景象,又輻射了政治、經濟、法治、生產、分配、婚嫁等諸多內容——這是一個容量極大的故事體系,或薄或厚、或多或少,都能夠成立,有足夠的靈活性和合理性。又因朱曉平小說是“繡像”散片結構(中短篇小說散篇),所以它在未來還有補充的可能性。
其次,小說深刻揭示了中國農村權力與秩序的關系——閉鎖麻木、狹隘保守的國民精神和心理并沒有隨著改革開放而徹底革除,先人的勇武與子孫的冥劣在自然條件惡劣、生產力低下落后的鄉村像是一場滑稽戲時時上演。在戲劇藝術和技術手段探索創新的時候,戲劇創作者更不能忘卻題材的現實意義,也就是說,戲劇藝術觀念要徹底落地,需要選定厚重的、有延伸性的主題,表達對歷史、民族、國民劣根問題的思考。農業、農民、農村是中國文學、文藝、文化永恒的話題,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有重要的現實性和關注的必要。
最后,徐曉鐘將朱曉平筆下的桑樹坪喻為“活化石”③。什么是“活化石”?生物體經歷了嚴重的甚至是滅絕的變故而存活下來,保留了過去的生命體征和原始特性,然而因為其近緣類群多數已滅絕,幸存的物質體比較孤立,所以停止進化或者進化緩慢,在漫長的時間內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如今看來,這個比喻實在精妙,它突出了桑樹坪所有內在的特征:“她太古老,太厚實,太穩重,千百聲呼喚,也只聽見自己那細弱的回聲,嗡嗡地響一聲便沉寂在無言的深谷了。”“我不知道,這塊土地可曾有過年輕俊美的時候。許是歲月無情,給這塊蒼涼凄冷的黃土地印下條條紋路。……這溝溝壑壑,梁梁峁峁便象一道道繩索,把個小村桑樹坪捆縛得鐵緊。外面的風一絲兒吹不進來,里面的氣也一縷兒透不出去……”④彼時的改革開放進程已經全面開啟,社會歷史潮流滾滾向前,這一現實與桑樹坪這塊“活化石”之間呈現出巨大的張力,彰顯重大的藝術發現和文化影響。
除卻以上幾點,徐曉鐘選擇一個知名度并不十分高的小說作為創作藍本,也是因為關注度不高,二度創作的自由度更高,也有助于將原著推到前臺獲得關注。若是選擇一個相對更有影響力的作品,改編也是掣肘的。
總之,徐曉鐘在充分的戲劇理論建構基礎上,找到了一個有生命力的高質量故事胚胎進行改編創作,又選定了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畢業并任教的青年教師陳子度作為主力編劇,當時在中央戲劇學院學報做編輯的楊健和小說原作者朱曉平作為輔助編劇,共同完成劇本創作,為接下來的實驗戲劇創作做好了前期準備。
二? 陳子度對劇本內容的重組
在具體分析陳子度等人的改編創作之前,先要梳理朱曉平“桑樹坪”系列小說的創作發展體系,這樣才能明確劇本內容的選取和組織方式。
從小說到話劇,編劇要把小說的人物和情節加以提煉、取舍、拼接、組合,再加入自己的想法和閱讀感受,外化為戲劇性強烈的情節矛盾,在尊重原著和展露個性之間,還要考慮如何在后期排演過程中盡量減少劇本的創意折損,更要配合徐曉鐘的戲劇探索理念和風格積累。鑒于此,陳子度的改編選材必然是廣泛的,在更為豐富的作品篇目中甄選合適的人物和情節,逐漸明晰自己的改編思路和敘事策略。因此可推斷,陳子度、楊健和朱曉平的改編是從內容更為立體豐富的《好男好女》中選取內容:1987年暑假,話劇編劇之一陳子度體驗生活采風,秋天開始創作。按出版周期推算,應是朱曉平的《好男好女》吸收了《桑樹坪紀事》(《鐘山》1985年第3期)、《桑塬》(《中國作家》1986年第2期)、《福林和他的婆姨》(《小說家》1986年第4期)先行定篇結集,之后才有話劇《桑樹坪紀事》的劇本,甚至還考慮到了1986年12月在《北京文學》發表的《私刑》,而非此前許多研究成果所謂的“圈定《桑樹坪紀事》《桑塬》和《福林和他的婆姨》三部作品而改編”。明確這一點,對于研究《桑樹坪紀事》的改編方法有一定的佐證作用——改編者在確定戲劇結構、捏合人物形象、鋪展對應關系之前,需要對大量素材進行淘洗、加工和重塑,范圍越廣,選擇余地就越大,精準度就相對更高,這一前期工作是極為必要且重要的。而“一對一”式的選取改編材料,顯然過于理想化了。
陳子度的劇本改編思路側重明確故事線索和結構序列,錨定戲劇主人公,處理人物性格的漸次表達,捏合重塑人物形象。劇本相對小說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小說是以“我”這個下鄉知青的視角和在桑樹坪的見聞作為敘事動力,所以在《好男好女》中不難發現,朱曉平的創作以紀事單元為體例,每一個單元都相對獨立,甚至隨意調整順序或插入別個紀事單元也不影響整體性;而話劇則是以李金斗為主體線索,他存在于每一個角色的生活和命運軌跡中,例如福林、彩芳、月娃和王志科等,甚至于每一個人物的悲劇都或多或少有李金斗的參與和推動。雖然都是“人物繡像式”的呈現,但因李金斗這個人物本身承載了極為豐富的戲劇性和復雜性,所以編劇在改編時循序漸進地呈現李金斗的一個又一個隱秘的性格側面。
序幕后的第一場戲是李金斗與劉主任圍繞莊稼估產而展開的“推手戲”,當李金斗苦不堪言地說出“可咱莊稼人辛苦一年,就是連口白饃饃也吃不上,還叫咱農民活不活哩”⑤,觀眾很容易認為李金斗就是一個窩囊無力卻又真心為村民著想的善良、忠厚、正直的農村干部。然而很快在第二場戲中,李金斗領著知青朱曉平尋麥客到桑樹坪割麥,觀眾又從一來一往的砍價中看到了李金斗的精明。隨著劇情推進,李金斗勸誘彩芳接受“轉房親”,又建議讓月娃做了童養媳;以“拐騙民女”的罪名把“勾引”彩芳的榆娃送到公社“群眾專政”學習班;為了一口破窯洞而污蔑王志科是“現行反革命”——觀眾不由對李金斗這個核心人物升起了疑團:這個“既是一只為人抽打的羔羊,又是一只吞噬生靈的惡虎”的人物究竟為何如此復雜?
陳子度在話劇劇本中的表達方式與朱曉平在小說中的書寫存在明顯的差異——小說中更凸顯李金斗性格中的強勢,其領導才能和莊稼把式都體現了他有能力為村民解決生計難題,殊不知他生存的本領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他壓榨程度最深、封建思想最濃,在那個環境中最具權威性;而在話劇劇本中,陳子度對李金斗的處理要“溫和”很多,以對彩芳的態度為例剖析:小說中,李金斗在兒媳彩芳守寡之后趕緊認了她作干女子,把控著彩芳的改嫁自由,金斗為了讓彩芳嫁給自己患有拐子病的小兒子倉娃,好幾次把彩芳捆起來逼其與倉娃同房,彩芳有要出逃的苗頭便被虐打。小說將其封建大家長的獨斷專行、冷酷兇狠、自私虛偽表露無遺。然而在話劇劇本中,編劇把小說中金明為搶救飼料而被軋斷腿的情節移植到了李金斗身上,他成了斷了一條腿的英雄,于是有了被同情的可能性,他一瘸一拐地走向彩芳,然后用示弱賣慘的方式“請求”彩芳答應“轉房親”:“彩芳是好娃,知道疼大(爸)。你倉娃兄弟(彩芳小叔子)跟你一塊長大,雖說落下個拐子病,可也不耽誤吃飯過營生,你應下這‘轉房親,就跟倉娃他一塊過,等生下一兒半女,給咱李家接了香火,你再走也成啊。彩芳,我的好娃,你就應了爸,大——大求你咧,求你咧!(猛地跪到許彩芳面前)”⑥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
這是劇本改編巧妙之處,李金斗人物本質絲毫沒有改變,但通過為難、仁義的表象表現“軟刀子殺人”的殘酷,把封建家長的玲瓏四方懷柔八面的偽善極具彈性地呈現出來,更彰顯了村落內權力運作的可怖。李金斗發自內心地憎惡痛恨那些盤剝農民的“腦系”,但他自己又何嘗不是這個村子的“腦系”?如此對比,話劇中李金斗的這種表現更內化。焦菊隱在談小說改編劇本時提到:“在改編時,請把情節再壓縮一下,把篇幅讓給人物的刻畫吧。寧肯劇情的曲折少些,不讓人物的面貌變淡。”⑦陳子度對李金斗的處理就契合了焦菊隱的這一要求,劇情的曲折性讓渡于人物形象的本質,令戲劇的矛盾沖突更為集中。
陳子度在劇本中更加強調矛盾的“對應關系”。許彩芳在小說體系中是最早的悲劇,她只不過是金斗用幾十斤苞谷和幾十元錢換來的童養媳。小說中,她的“對應關系”僅有李金斗的壓迫摧殘和榆娃的真摯愛情;而在話劇中,陳子度進一步延展了彩芳的人物功能,通過彩芳刺激保娃和媳婦兒,為自己無辜忍受的屈辱找到宣泄的出口和攻擊的對象,同時展開了保娃這個形象。在小說中,保娃是一個非常模糊的人物,他身上既無李金斗的莊稼能耐,也沒有李金明的仁義憨厚;但在話劇中,開槍打死耕牛豁子的是保娃,王志科也是保娃帶人抓捕的,種種細節都表現了他的潑賴、兇殘、狠毒和看客劣根性。在窮苦的桑樹坪,“保娃們”的身上披露著先人的勇武與子孫的冥劣產生的反差,不禁令人唏噓:若連后生們都沒了“人”的屬性,而只剩獸的動物性,那么,民族的文明和未來還有何指望?
小說中人物情節單元是相對獨立的,陳子度在劇本中巧妙突出了人物之間的交叉性,將彩芳和青女對應起來。小說中,青女這一形象是作者傾注了強烈的同情來塑造的,在巨大的命運悲劇的扼壓下,她的人生被毀棄殆盡。編劇又通過青女對應上青女娘。在劇中,青女娘是個幻覺中的人物,無論青女如何哭訴,青女娘都不斷重復一句話:“娃呀,不哭咧……不把你聘出去,你兄弟的親事又該咋辦呢?”青女又對應著月娃,李金財為了給兒子福林娶親,把女兒月娃出聘成了童養媳,婚姻嫁娶完全成了買賣。李福林大呼:“我的婆姨!錢買下的!妹子換下的!”青女哭訴:“我不是人啊,我是人家買來的牛!我是人家牽來的馬……”⑧無論是青女娘還是李金財,都既是買方也是賣方,幾乎每家人戶都在這樣的環套中掙扎,所以在桑樹坪,無論嫁娶似乎都感受不到歡心和喜慶,全都是愁和淚凝結下的無可奈何。
客觀來講,話劇中青女的性格特征被弱化了,小說中她的悲劇命運更為觸目驚心。青女過門不足一年半,就從一個一汪水般的俊俏姑娘變成了一束枯草。她在忍受福林的瘋癲和村里人的謾罵之后,被迫接受婆家安排的轉房親,給福林的大弟弟做婆姨。在小說中,“青女聽這消息,憋悶了許久的心火,找到了一個發泄的機會。她的苦已經吃盡了,如今又要‘轉房。青女渾身一陣顫抖,大聲叫罵著:‘我是人呀還是豬狗!兩眼灼灼逼人。”⑨而關于對婚姻、人權、自主意識的極度蔑視和踐踏的轉房親,話劇中雖一筆帶過,卻用了一個極富震撼力的象征再現了女人是如何在極度貧苦、沿襲封建宗法制度卻違背倫理綱常的落后鄉俗中被蹂躪的——“一尊殘破卻潔白無瑕的侍女古石雕出人意外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它令人想起遠古,它讓人想起多少代殉葬的女人……扮演許彩芳的演員將一條黃綾肅穆而凝重地覆蓋在古石雕上,村民隨著一起跪倒在古石雕的四周。”⑩李福林的癲狂將這個矇昧鄉村的遮羞布徹底扯了下來,控訴了桑樹坪人習以為常又難以直言的陋俗——女性就是用來買賣的,這一場戲也以再現的藝術表現方式極盡呈現了桑樹坪的閉鎖和荒蠻。
話劇從李金斗延伸到彩芳,又從彩芳輻射對應了青女、青女娘、月娃和福林,最終,又回到彩芳和榆娃,很好地完成了人際關系群像,書寫了人與人的交往與角斗過程。榆娃和彩芳的自由愛情淳樸而炙熱,是桑樹坪唯一的亮色和希望。榆娃在這個嚴酷貧苦的生活環境中依然保持樂觀的天性,依然有勇氣追求愛情,認為所有的貧苦都會過去,只要真心相待,所有的困境都可以熬過去,這是桑樹坪僅有的活力和生機。在小說中,彩芳和榆娃的愛情是較早出現的情節,但在話劇中,編劇安排彩芳在尾聲處投井自盡,通過顛倒情節敘述順序,將彩芳的生命動線拉長。編劇讓她與青女交談感受,支持青女打離婚;讓她刺激保娃的看客劣根性,還讓她與朱曉平有一段告別:“等過了埡口,就把咱這窮荒地方忘他個光光的。”她對桑樹坪這個地方有發自內心的痛恨和無奈,她逃不脫,于是希望有機會逃脫此處的人都離開這個地方,這些都增強了這個人物的韌性和生命力。如此一來,結局處彩芳就因抗爭失敗自盡而表現出更深刻的悲劇性。“為著展現人物心靈變化的過程,劇本結構也更趨多樣化。在有些劇作中,人物關系和事件的發展,常常出現多層次、多線條的結構形式或跳躍發展,或分切、閃回有時人物之間的外部沖突和人物內心意識的活動并行交替。時空概念有了新的發展。時序的顛倒,空間的多變,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表現事件發展的過程,而且常常用來更好地揭示人物心理活動的層次不但構成戲劇發展的活潑節奏,也往往產生類似‘蒙太奇技巧的效果,加強了觀眾窺探人物內心隱秘的興趣。”11編劇重視在劇情推進過程中尋找人物與他人和時代的對應關系,把視點放到了更為廣大的社會生活中,以更大的容量包涵了生存的種種形態與方式,表現了作者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的冷峻審視。
三? 由“形象種子”生成的劇本寫意空間
朱曉平的“桑樹坪”系列小說因過度強調紀實美學的質樸,從而規避了乖張、刺激和緊張的戲劇性因素,導致表現的單向性明顯。徐曉鐘曾經考慮化用一個戲劇性較強的中心事件把“桑樹坪”系列松散的單篇集合起來,但是他發現,松散的戲劇結構和鮮明的人物實際上并不沖突,甚至可以留出足夠的空間發揮導演在舞臺上的藝術創作。最終他建議編劇團隊“每一章有一組主要人物被推到前景,其他人物或斷或續穿插其間,他們將在另外的章節中循序地被聚焦,推到前臺”12,而隱匿貫穿其中的是徐曉鐘“形象種子”的戲劇創作觀念。
“形象種子”為這部戲提供了假定性表達和象征寫意的思維動力,尤其在人物的動物性和動物的客體性方面,輸出了重要的戲劇主旨。《桑樹坪紀事》的“形象種子”定位在“圍獵”,小說中與“圍獵”直接相關的情節只有李金明打牛,陳子度沿著這個思路進行了大膽的聯想和表現,運用了人和動物的互文表達,呈現了人仿佛畜生、甚至人不如畜生的殘酷真相。“捉奸彩芳榆娃”“殺牛”“圍捕王志科”等情節都是在“圍獵”的基礎上展開的,一群追逐命運的人,像野獸一樣被人“圍獵”又自相“圍獵”,極大程度地發揮了戲劇寫意的功能。尤其是王志科的單元,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農民在現實中“圍”與“困”的掙扎。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
在劇中,桑樹坪人為了表示對“腦系”的不滿而含恨瘋狂地打牛,之后又極度地痛苦和悲傷;緊接著,桑樹坪人為了趕走王志科,違背良心“給他把反革命的帽子帶上”,要求將其逮捕法辦。為了王志科住的那孔窯安石磨,桑樹坪的人不惜要了王志科的命。人對牛尚有深厚的感情,人對人竟殘酷地自相殘殺,兩廂對比,人物的動物性和動物的客體性便揭示出來了。尤其是李金斗準備在密告王志科的狀子上按手印時,“放著狀子的桌子突然被用力過猛的李金斗按倒,隨之倒下的李金斗趴在地上依然死死地在狀子上按上了手印”。13舞臺上李金斗的身體姿態正是牲畜趴臥的姿勢,象征著李金斗的獸性和冷血,也映射了“做人”而不得的痛苦。羅伯特·科恩指出:“如果一個作家能夠創造出一場非常有說服力的場面,在這個場面中沖突白熱化,而且進入每個相關人物的內心世界,他就有很好的機會把這個場面塑造成一部令人激動的作品的核心。如果這一場面中再糅進某些微妙細膩的成分,而不是完全地依靠大喊大叫和公開對罵,那就更容易成為作品的核心。”14而這個“人與牛”的對比場面,正通過“形象種子”生成了深刻的精神指向,把小說中痛苦回憶的窒息感轉變為戲劇舞臺上厚重遼闊的蒼涼悲壯。
在朱曉平的原著中,桑樹坪農民的韌性是有兩面性的,但是在話劇中,編劇更加突出這種韌性的負面作用,即“遭著、忍著、熬著、延續著”,就這樣一輩一輩延續下去,甚至不想改變、不想離開,只要不是更糟,就不盼望更好。觀眾不禁會思考一個問題:王志科為何不離開桑樹坪?首先,他去其他村莊或者回隴東老家,都沒有親人可依靠,境況不會比在桑樹坪更好;其次,他對妻子李福綿有深厚的感情;再次,王志科作為一個耿直剛硬的漢子,要和桑樹坪不合理的宗族制度殊死抗爭。桑樹坪人對王志科的強烈排斥,實際上就是因自私和狹隘而產生的閉鎖和排外,歸根結底是對生存資源和生產材料的保護,以及對既有“秩序”的強制把守。王志科的悲劇命運擊中了桑樹坪“貧”與“困”的深層原因——貧瘠的生存環境與頑固的封建思想。徐曉鐘設計了一個圓形轉動舞臺,象征著封閉、阻塞的生存空間,困境在回環往復,但其中的人又走不出這個循環。喬治·桑塔耶納說:“外在自然的機械組織是我們心中的統覺形式的來源。”圓形轉臺顯示了徐曉鐘對主人公及其生存環境的內在領悟與審美把握,擴大了表現廣闊生活圖景的可能性,豐富了自己的藝術語匯,增強了話劇藝術的表現力,給藝術接受者以情緒刺激和精神啟迪。
話劇中加入了由桑樹坪村民組成的歌隊,合唱既是西北山村的山歌勞動號子,也如史詩的齊聲朗誦。戲劇音樂、尤其是歌隊的創造是蘇聯話劇導演手中強有力的手段,多用來展示和揭示人物;揭示和渲染人物關系,推動事件和沖突的發展;描繪環境或氣氛。15徐曉鐘1950年代畢業于蘇聯盧那察爾斯基戲劇學院,對蘇聯戲劇音樂元素有深刻的理解和體會,也善于借鑒。話劇《桑樹坪紀事》開篇便是桑樹坪人和陳家塬人的對罵,粗魯、鄙陋、難以入耳,所有的混亂被一聲炸雷和傾盆大雨叫停,對罵的村民隨即四處逃去。村民們鄙陋卻從未自知,這時,身穿現代服裝的歌隊邊唱邊走到前臺:“中華曾在黃土地上降生,這里繁衍了東方巨龍的傳人。大禹的足跡曾經布滿了這里,武王的戰車曾在這里奔騰。穿過一道道曾緊鎖的山峰,走出了這五千年的夢魂。歷史總是提出這樣的疑問,東方的巨龍何時才能猛醒?盡管前面有泥濘的路程,盡管有多少山峰需要攀登。總是這樣不斷地自問,總是這樣苦苦地追尋。”16這段合歌在劇中反復出現,從較深層次把握了現實社會的歷史走向,在歷史、文化、民族、心理等大背景上給戲劇場景以擴容。編劇更含蓄地通過高遠的視角和歌隊的演唱表達了深刻的自省和對未來的希望,避免了生硬拔高和刻意貼近時代的突兀。正如林克歡所說:“創作實踐從來都是主體與對象在共同矛盾運動中所組成的一個不斷生成、不斷發展的運動系統。”17
四 《桑樹坪紀事》改編的價值
1988年,曹禺在看過《桑樹坪紀事》后給予很高的評價:“看了這個戲有幾點感想:海是裝不滿的,人的路是走不盡的,花是不謝的,感情的長河是流不完的。對于徐曉鐘的導演藝術我有這么一種感覺,在他的導演藝術中看不見徐曉鐘,但看見其完美的藝術。”18而這種完美的藝術表現具有延續性和可借鑒的啟示意義。就經驗價值來看,借助于原作提供的背景快速形成劇本,要想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需要強大的感受力、理解力和創造力。可以說,改編不僅要展示出原作的特點,還要去深化原作的立意。真正成功的改編要穿透小說原作表面的情節性,發掘、體現甚至深化原作對于生活的本質認識,表達出改編者有創意的闡釋和演繹。
在當下,由小說改編話劇劇本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推拿》《長恨歌》《杜拉拉升職記》《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塵埃落定》《活動變人形》等,作品頻出。不難看出,如今的改編劇都熱衷于選用影響力更大、更有口碑的當代經典小說進行改編,制作方往往認為這會是話劇成功有力的保障。然而現實卻是,1990年代以來的改編劇大多并不亮眼,從藝術傳播的角度真正能夠讓觀眾記住的作品并不多。人們似乎已經忘卻了1980年代《桑樹坪紀事》改編的成功經驗,也找不準改編失準的癥結,只是一味依賴原著作家的地位聲望和演出前后的大力宣傳。回到戲劇創作本身,改編者必須“戴著腳鐐跳舞”——“編劇要忠于原著,導演忠于劇本,演員忠于劇作和導演意圖”19,同時要做到、做好這三點,難度不言而喻。由王安憶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長恨歌》,由當代著名劇作家趙耀民擔任編劇,曾在2003年首演,2021年由周小倩導演復排。趙耀民作為一名成熟的職業話劇編劇,深諳戲劇敘事結構布局,將劇中王琦瑤四十年間的情愛生活通過近乎對稱的頭尾結構展露出來,從話劇的技術規范性來說完成度極高,然而劇中王琦瑤的戲劇行為卻與她的內在人物性格有所背離。原著中,這個舊時的上海名媛一生不曾主動追求過男人,一方面是因選美獲得“上海小姐”第三名的自信;另一方面因為王琦瑤是一個并不風華絕代且出生平凡的姑娘,這是隱藏在自信下面的自卑,再加上她在步步攀爬更高社會階層的過程中有“臣服于世俗名利”的被動,所以這樣的王琦瑤始終是“靜默的、隱忍的、心事重重的”,即便是后期頻繁參加社交聚會也并不張揚,“她穿著那么得體,態度且優雅,一點不掃人興的,一點不礙人事情的。她就像一個擺設,一幅壁上的畫,裝點了客廳”。但是在劇中,后期的王琦瑤在情愛方面變得異常主動甚至盲目,帶有交際花般的行為舉止和性格特征,這種轉變是缺乏有力的合理的劇情轉折支撐的,只是將原著的某些表象元素夸大變形,以獲得一種戲劇張力,如此反而混亂了王琦瑤這個人物的性格走向。因此,《長恨歌》是一部完成度較高的當代話劇,但卻難稱優秀的改編劇。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
貌似省力的改編事實上頗考驗功力,改編者對原小說的刪改、修整與舞臺呈現時常顧此失彼,高度濃縮的情節的迅速推進、多種形式元素的運用與戲劇性的刻意強化,在吸引了觀眾注意力、獲得一定的劇場效果的同時,也流失了許多有價值的戲劇場面和人物情感的細膩表達。小說與話劇無論在審美出發點、沖突解決途徑和價值判斷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異,若無法抓住小說原著的主旨和核心人物,就無法在舞臺上呈現小說內在的張力。有的編劇選擇加入很多想象關系以強化場面沖突的激烈程度,這樣的做法雖然豐厚了情節,但往往失去了靈魂,因淡化或變異而造成改編失衡。
回到《桑樹坪紀事》,陳子度等人很明顯抓住了桑樹坪“貧”和“困”的現實狀態和歷史背景,更在徐曉鐘的啟發下把握了“形象種子”的深層含義,將“圍獵”作為矛盾爆發的戲劇行為,不僅揚長避短,規避了因過于平實的講述而產生的遲緩枯燥,還豐滿了立體的人物形象,使其服務劇作情節發展。成功的改編創作,來自編劇對故事本身深刻的理解和精彩的詮釋:“戲劇的現實主義將更深地植根于千姿百態的生活,它仍將保持它崇尚理性的基本特征,遵循生活的邏輯,尊重人物心理動機、思維和意志的邏輯。”20陳子度等人沿著徐曉鐘的導演意念,遵循原著人物的心理動因和行為意志,將小說中的矛盾交叉放大了,令悲劇情緒疊加,展露了現實生活的荒誕與悲慘。若改編者未能自然貼切地以戲劇意象表現作品的精髓,那么無論票房、口碑如何,都很難算是一次真正成功的“舞臺寫作”。除此之外,隨著歷史和社會的變遷,即使是同樣的故事、同樣的主人公,其主旨、事件和人物等的表現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因此,如何賦予原作以時代精神,亦是改編者需要重視的問題。
小說的話劇改編之路如何走得更踏實、長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深耕數十年、又任職上海戲劇學院的楊揚教授所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例子或可作答,他認為斯氏的成功與他和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世界級文學大師的密切交往有不可忽視的關系。斯氏并不僅僅將文學巨擎們的作品作為自己戲劇創作可選取的文本資源,而是通過密切的交流,將這些文學家的思想和小說文本作為自己的學習資源。21文學大家們對人性的理解、對人物性格的理解加深了斯氏對藝術問題的深入思考,更鍛煉了他觸類旁通的創作思維,促成了從舞臺形象到哲學層面的全面提升。今天的中國劇壇,僅靠簡單的“拿來”顯然是不夠的,在“改”之前要先“懂”,在“懂”之前尚需“心同道同而學同”。
注釋:
①1988年1月29日,話劇《桑樹坪紀事》由中央戲劇學院1986級表演干部專修班首演于中央戲劇學院逸夫劇場(1990年代后改稱“實驗劇場”)。作品由徐曉鐘、陳子度執導,陳子度、楊健、朱曉平編劇,劉元聲等擔任舞美設計。
②徐曉鐘:《在兼容與結合中嬗變——話劇〈桑樹坪紀事〉實驗報告》(上),《戲劇報》1988年第4期。
③首見于徐曉鐘:《在兼容與結合中嬗變——話劇〈桑樹坪紀事〉實驗報告》(上),《中國戲劇》1988年第4期。
④⑨朱曉平:《福林和他的婆姨》,《小說家》1986年第4期。
⑤⑥⑧⑩1316陳子度、楊健、朱曉平:《桑樹坪紀事》,《劇本》1988年第4期。
⑦焦菊隱:《和青年作家談小說改編劇本》,《劇本》1958年第7期,后收入《焦菊隱戲劇論文集》,華文出版社2011年版。
11徐曉鐘:《堅持在體驗基礎上的再體現的藝術》,《戲劇報》1984年第7期。
12徐曉鐘:《在兼容與結合中嬗變——話劇〈桑樹坪紀事〉實驗報告》(下),《戲劇報》1988年第5期。
14〔美〕羅伯特·科恩:《戲劇》,費春放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頁。
15徐曉鐘:《蘇聯話劇演出中的音樂運用——學習札記》,《戲劇報》1961年第8期。
17林克歡:《活的形式》,《戲劇報》1988年第4期。
18曹禺:《向“表現美學”拓寬的導演藝術》序言,中國戲劇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1921楊揚:《從小說到戲劇——從話劇〈狂人日記〉〈長恨歌〉〈塵埃落定〉說起》,《戲劇評論》2021年第1輯。
20徐曉鐘:《戲劇界應該做屬于他應該做的事——我對話劇現狀和未來的一些看法》,《戲劇報》1985年第4期。
楊揚:《從小說到戲劇——從話劇〈狂人日記〉〈長恨歌〉〈塵埃落定〉說起》,《戲劇評論》2021年第1輯。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責任編輯:趙雷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