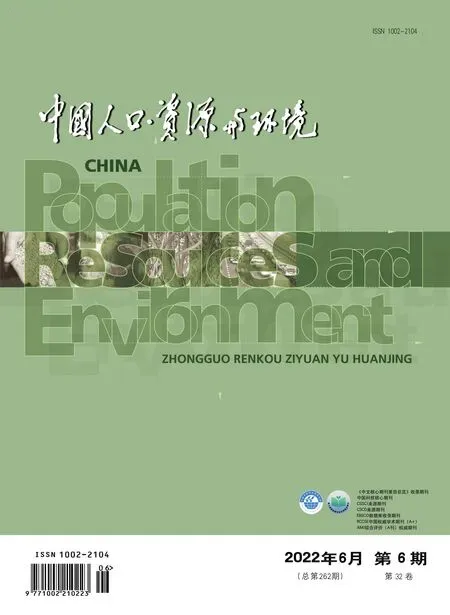“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價及中國合作建議
區(qū)浩馳,郭凱迪,王 燦,3
(1. 清華大學環(huán)境學院,北京 100084;2. 團結香港基金會,香港;3. 清華大學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院,北京 100084)
1987 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委員會發(fā)布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首次提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定義,即“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同時又不損及后代滿足其需要的發(fā)展模式”[1]。2015年,聯(lián)合國193個會員國共同簽署通過《2030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承諾在2030 年達成17 項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SDGs 又稱“全球目標”,共包含169 項具體目標和247 個指標,廣泛覆蓋了減貧、氣候變化、經(jīng)濟不平等、可持續(xù)消費、和平與正義等領域[2]。SDGs致力于通過協(xié)同行動確保人類享有和平與繁榮,但發(fā)展中國家普遍面對缺乏技術和人才、國家監(jiān)管體系和組織協(xié)調(diào)能力不足、社會財政資源短缺等問題,在落實SDGs 上面臨巨大挑戰(zhàn)[3]。2013 年,我國提出倡議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4]。“一帶一路”的“三大合作原則”(共商、共建、共享)、“五大合作重點”(即“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lián)通、貿(mào)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思想[5],與《2030 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的5個核心因素——“人類”“地球”“繁榮”“和平”和“合作”,以及17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相輔相成[6],成為推動發(fā)展中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國際合作機制。
在全球碳中和愿景背景下,推動發(fā)展中國家實現(xiàn)綠色轉型顯得更為緊迫。2019年,146個“一帶一路”國家碳排放總量約占全球30.8%,且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會使其未來碳排放規(guī)模持續(xù)上升[7]。但大部分國家產(chǎn)業(yè)結構落后,自身轉型動力不足,因此借助“一帶一路”投資合作平臺成為推動和協(xié)助其加快綠色轉型,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手段。而對沿線各國可持續(xù)發(fā)展水平進行綜合評估是引導“一帶一路”綠色投資的關鍵決策支撐,也是評估“一帶一路”建設成果的關鍵因素。沿線各國大部分為發(fā)展中國家,社會制度、經(jīng)濟基礎、文化傳統(tǒng)、自然環(huán)境等存在巨大差距,各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可得性和質量也參差不齊,難以滿足《2030 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中提到的17 個SDGs的全面評估需求。因此如何在現(xiàn)有公開可得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選取合適的評估指標和研究方法,既覆蓋17個SDGs的評估理念,又精煉易操作,是當前背景下對所有沿線國家進行可共享、可擴展、可延續(xù)的綜合評估的緊迫需求。
該研究以世界銀行公開數(shù)據(jù)庫為數(shù)據(jù)來源,組成環(huán)境-經(jīng)濟-社會-氣候四個評估維度,通過秩和比(Rank-Sum Ratio,RSR)方法構建了針對“一帶一路”歐亞非三大洲112個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估框架,分析了沿線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現(xiàn)狀和特征,識別其發(fā)展需求,并提出了中國未來在“一帶一路”進行綠色投資及合作的建議。
1 文獻綜述
目前關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估的相關研究涵蓋縣級、城市級、省級、國家級和全球各個地理尺度,主要研究思路包括對標聯(lián)合國17 項SDGs 的評估、選取環(huán)境-社會-經(jīng)濟三個基本維度及其擴展維度的綜合評估以及對國家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和環(huán)境效率的評估。縣級市是聯(lián)合國重點選擇的SDGs 指標評價研究試點地區(qū),中國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陳軍[8]2017 年與聯(lián)合國合作在浙江省德清縣開展的SDGs 進度監(jiān)測試點,結合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地理空間信息數(shù)據(jù),最大程度對標SDGs全球框架,選取了102項指標評估德清縣可持續(xù)發(fā)展進程。城市尺度的研究受限于SDGs 指標在小空間尺度的適用性,又難以像縣級尺度一樣精確獲取數(shù)據(jù),因此很難全面對標SDGs 全球框架。大部分針對城市的研究采用主觀選取指標并劃分到不同維度的方法,也有研究使用復雜網(wǎng)絡方法量化分析個別指標對城市系統(tǒng)的影響和影響路徑[9],使用數(shù)據(jù)包絡方法分析城市系統(tǒng)投入產(chǎn)出效率等[10]。典型評估指數(shù)包括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與中國同濟大學研究團隊共同發(fā)布的包含16 項具體指標的中國城市發(fā)展指數(shù)[11],麥肯錫、哥倫比亞大學和清華大學研究團隊發(fā)布的包含22 項具體指標的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數(shù)[12]。省級和國家層面的研究能夠從官方統(tǒng)計報告中獲得較齊全的開放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廣度和深度足夠進行時空進展評價并對標SDGs。Xu等[13]對中國進行了2000—2015 年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時空進展分析,使用119項指標量化評價了中國國家尺度和省級尺度的SDGs 進度,其中直接反映SDGs 全球指標框架內(nèi)容的指標占39 項,作者自行構建指標占55 項。全球尺度的研究多以國際組織公開數(shù)據(jù)為主,官方開放數(shù)據(jù)缺失較多,歷史數(shù)據(jù)不齊全,較難進行高SDGs 指標覆蓋率和全球覆蓋率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時空進展分析。張宇涵等[14]選取30 項指標對100 個國家落實SDGs 的現(xiàn)狀和進展進行定量評估和比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從30 個指標中挖掘出4 層解釋意義,Eustachio 等[15]從系統(tǒng)分析和決策的角度選取47 項指標對219 個國家進行評價,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將其組合成14個主成分維度。
“一帶一路”涉及百余個國家,且以發(fā)展中國家為主,因此針對“一帶一路”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估往往面臨著指標全面性、國家覆蓋率及評估時間尺度間的取舍。Feng等[16]選取了102項SDGs具體指標進行評估,但只針對中國、越南、印尼和印度四個“一帶一路”國家。還有一類研究使用數(shù)據(jù)包絡、計量回歸等方法分析“一帶一路”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效率間的關系。Khan[17]以最小二乘法分析1990—2016年間信息及通信技術(ICT)和實際收入對5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將國際貿(mào)易和外商直接投資(FDI)作為控制變量;張君等[18]引入歐盟成員國生態(tài)創(chuàng)新績效評估方法,使用數(shù)據(jù)包絡(DEA)方法對3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綠色發(fā)展評價;高贏等[19]采用數(shù)據(jù)包絡法對3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996—2015年的低碳發(fā)展效率進行了靜態(tài)及動態(tài)分析,并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模型進一步探究了其影響因素。黃天航等[20]采用考慮非期望產(chǎn)出的Super-SBM模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水平進行測度,利用全局ML指數(shù)(GML指數(shù))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水平的動態(tài)變化及其構成進行計算,并進一步采用Tobit模型識別沿線國家整體及各類別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水平的影響因素。
綜合來看,對標聯(lián)合國17個SDGs進行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估是學術界、國際組織和政府部門共同認可的全面、可比的評估方法,但受限于數(shù)據(jù)可得性,在不同評估尺度上選取的原始指標和替代指標數(shù)量不同,學者們往往將所選指標進一步劃分為環(huán)境、經(jīng)濟、社會等維度進行分析。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價方法依賴于系統(tǒng)科學的指標體系的建立和合理的指標權重的確定[20],目前在指標權重的確定上有客觀賦權方法如灰色關聯(lián)度法、TOPSIS法、RSR 法、主成分分析法等[21-23],但指標選取的過程往往是在數(shù)據(jù)可得的指標中,根據(jù)理論分析和文獻篩選等方法確定,存在較強的主觀性。這種選取方法一方面難以保證所選指標能全面刻畫可持續(xù)發(fā)展對應的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三個維度,另一方面指標所反映可持續(xù)發(fā)展特征的重復和冗余也沒有客觀判斷標準。“一帶一路”沿線很多發(fā)展中國家數(shù)據(jù)可得性較差,因此如何在有限數(shù)據(jù)內(nèi)選取能全面準確覆蓋各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特征的指標成為評價“一帶一路”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價的重要挑戰(zhàn)。
2 研究方法
2.1 PLS-SEM評估模型
由于數(shù)據(jù)缺失問題嚴重,世界發(fā)展指標數(shù)據(jù)集缺乏跟SDG1、SDG10、SDG13、SDG16 相關的可用數(shù)據(jù),因此,無法按照“SDGs 全球指標框架”進行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評價。為此,將篩選出的84 個指標分別劃分到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和氣候四個維度,進行指標降維和內(nèi)生性消除,可以既保持可持續(xù)發(fā)展評價的系統(tǒng)性,又盡可能地減少數(shù)據(jù)需求。根據(jù)文獻方法[25],從每個維度中選擇3~5 項指標進行因子分析、模型信度和效度檢驗及模型區(qū)分效度檢驗,按檢驗結果決定指標去留。模型構建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模型建立流程圖
PLS-SEM 模型是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PLS)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的縮寫。PLS通過最小化方差(誤差平方和),尋找數(shù)據(jù)與函數(shù)之間的最佳匹配;而SEM 則是一種包含回歸分析、因子分析、路徑分析、多元方差分析的多元統(tǒng)計分析方法,能夠對理論進行假設檢驗。PLS-SEM 建模的優(yōu)勢在于:①只需要最少30 個樣本;②不要求輸入數(shù)據(jù)服從正態(tài)分布;③同時適用于反映性、形成性或兩者混合測量模型[25]。與主成分分析法類似,PLS-SEM 方法也具備把大量指標轉換成數(shù)個綜合指標的降維能力,測量變量在意義上接近原始指標,潛變量在意義上接近主成分,建模過程中需要進行因子分析、建設信度和效度分析,以及區(qū)分效度分析檢驗,可以解決指標之間的信息重疊問題。
2.2 基于秩和比法的指標聚合
選取秩和比(RSR)作為綜合評價方法。在一個n行(n 評價對象)m列(m個評價指標或等級)矩陣中,通過秩轉換,獲得無量綱的統(tǒng)計量RSR,以RSR 值對評價對象的優(yōu)劣進行排序,從而對評價對象做出綜合評價。該方法的優(yōu)點是無需大樣本或正態(tài)分布;消除異常值干擾,可以解決指標值為零時在統(tǒng)計處理中的困惑,能在充分利用原有信息的基礎上起校正作用。缺點是在指標轉化為秩次時會損失部分原始指標數(shù)據(jù)信息,但在個別指標存在極端異常值干擾時,該方法能把異常值的干擾一并去除。
對各項評價指標進行編秩時,同一指標內(nèi)秩值相同者編為平均秩,效益型指標從小到大編秩序,成本型指標從大到小編秩序,得到指標編秩矩陣Rij,RSR 值的計算公式如下:

考慮不同指標的權重Wij時,加權RSR 值的計算公式如下:

2.3 指標賦權
采用主觀賦權與客觀賦權相結合的方式將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指數(shù)(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Integrated Index,SDI)分為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指數(shù)(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SED)和環(huán)境氣候可持續(xù)指數(shù)(Environment &Climate Sustainability Index,ECS)兩個二級指數(shù),每個二級指數(shù)均賦予0.5的權重。采用等權重的主要考慮是,大部分客觀賦權法如TOPSIS 法、灰色關聯(lián)度分析法(GRA)和熵權法等[23]對權重的確定都會受到指標數(shù)據(jù)離散程度等的影響,從而使權重分配出現(xiàn)較大差異。對二級指數(shù)平均分配權重是保證評估框架合理性和客觀性的常見做法,如聯(lián)合國可持續(xù)發(fā)展解決方案網(wǎng)絡與貝塔斯曼基金會聯(lián)合發(fā)布的覆蓋164個國家的SDG指數(shù)就對SDGs目標的指標權重進行了平均分配[28];Xu 等[13]在使用可持續(xù)發(fā)展儀表盤評價中國各省份可持續(xù)發(fā)展水平時對17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進行等權重分配以保證各個目標的重要性得到同等體現(xiàn);文獻[28]和文獻[29]進行可持續(xù)發(fā)展評估時也對各維度采用等權重分配的方法。
每個二級指數(shù)下具體指標的權重由熵權法確定[30]。相關計算公式如下:
假設矩陣中有m個評價對象(“一帶一路”國家)和n個評價指標,信息熵為:

指標權重W為:

2.4 數(shù)據(jù)標準化
選取極差法進行數(shù)據(jù)標準化。極差標準化方法則能夠有效處理存在負值的數(shù)據(jù)樣本,例如各國每年的GDP變化,更有利于在匯聚各種數(shù)據(jù)類型的世界銀行公開數(shù)據(jù)平臺上進行指標篩選[26]。極差標準化法的計算公式如下:

3 “一帶一路”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價結果及地區(qū)分析
3.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112 個與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官方合作文件的亞洲、非洲和歐洲國家。研究按聯(lián)合國地名專家組語言地理標準將112 個研究對象劃分為12 個比較地區(qū):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歐亞(地理和文化上橫跨歐洲和亞洲的國家,以及歐盟定義的“其他歐洲國家”)、歐盟、中非、東非、北非、西非和南非。研究地理覆蓋范圍符合歷史絲綢之路、歷史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歐班列,以及部分冰上絲綢之路的走線,并涵蓋大部分重大“一帶一路”基建工程項目。根據(jù)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研究對象中有76%為發(fā)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低于12 376 美元),包括了全球74%中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低于3 995 美元)和61%最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低于1 025 美元),這些國家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需求最為迫切。
3.2 數(shù)據(jù)來源
研究數(shù)據(jù)來自世界銀行公開數(shù)據(jù)平臺世界發(fā)展指標,該指標集共有超過1 500項世界指標數(shù)據(jù),覆蓋217個國家,歸類成6個主題數(shù)據(jù)集(貧窮與不公、人口、環(huán)境、經(jīng)濟、國家與市場、全球連接)。為彌補全球SDGs 評估的數(shù)據(jù)缺口,世界銀行將世界發(fā)展指標數(shù)據(jù)集中的404項指標納入SDGs 相應目標下,為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具體指標在該平臺上找到相應的參考指標作為監(jiān)督工具[24]。考慮到指標的冗余性,剔除同一指標下性別、年齡細分指標等,該研究從404 項世界發(fā)展指標中選取了181 項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相對應的世界發(fā)展指標,并選取了“平均能源碳強度”和“人均預期壽命”兩項不在此數(shù)據(jù)庫但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密切相關的世界發(fā)展指標,獲得了183 項初始指標。183 項指標中,考慮數(shù)據(jù)橫向可比性和時效性,淘汰112個待評估國家中數(shù)據(jù)缺失度高于20%(24個國家)的指標和最后更新年份早于2013 年的指標,最終建立了一個包含84個指標的可用指標池。
3.3 綜合評估指標體系
經(jīng)過基于指標缺失度的第一層指標篩選,以及使用PLS-SEM 進行的基于指標降維和消除內(nèi)生性的第二層指標篩選,選取覆蓋經(jīng)濟機會、社會福祉、環(huán)境質量和氣候行動四個維度,包含15 個具體指標的評估指標體系。經(jīng)濟機會和社會福祉兩個維度共同構成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指數(shù)(SED),環(huán)境質量和氣候行動兩個維度共同構成環(huán)境氣候可持續(xù)指數(shù)(ECS)。SED 和ECS 兩個指數(shù)內(nèi)的各具體指標權重由熵權法計算得到,兩個指數(shù)分別以50%的權重共同構成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指數(shù)(SDI)。各指標、數(shù)據(jù)年份及權重見表1。

表1 基于PLS-SEM方法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指數(shù)構成指標及其權重
3.4 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價結果
表2列出了分地區(qū)的各項指數(shù)得分及其排名情況。歐盟SDI 得分為0.819,排名第1,屬于高水平地區(qū),同時歐盟SED 也在各地區(qū)中排名第一;南非、西亞和東南亞的得分在0.593~0.608 之間,屬于中高水平地區(qū);歐亞、東亞、中非、東非、南亞和中亞的得分在0.488~0.819 之間,屬于中水平地區(qū);北非得分為0.439,屬于中低水平地區(qū);西非得分為0.338,屬于低水平地區(qū)。從地理和收入分布來看,SDI 得分的前20 名國家中,歐洲國家占90%,高收入國家占85%;在排名前40名國家中,歐洲國家比例降至62.5%,亞洲國家比例升至30%,高收入國家比例降至60%,中高收入國家比例升至37.5%,西亞國家比例升至15%。

表2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指數(shù)及其社會經(jīng)濟與環(huán)境氣候指數(shù)
統(tǒng)計3 個指數(shù)在各個水平的國家分布情況,如圖2 所示,可以看出:不同指數(shù)在5 個水平的國家分布狀況存在明顯差異。SED 不同水平類別的國家數(shù)目接近,呈“平均分布”;ECS 的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國家數(shù)量最多,高水平和低水平國家數(shù)目最少,呈“M 型分布”;SDI 的則是中水平國家數(shù)目最多,高水平和低水平國家數(shù)目最少,呈“正態(tài)分布”。這表明反映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水平的SDI指數(shù)可能由不同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狀況組成,例如在SDI 評價中均屬于中高水平地區(qū)的西亞和東南亞地區(qū),西亞在SED 中屬于高水平地區(qū)但在ECS 中屬于低水平地區(qū),代表該地區(qū)可能正在以過度損耗環(huán)境資源為代價實現(xiàn)高度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東南亞則在SED 和ECS 中都屬于中水平地區(qū),代表該地區(qū)在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資源損耗之間取得較合理平衡,二者面臨著不同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需要不同的發(fā)展策略。因此,為了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是否和環(huán)境損耗脫鉤,需要有針對性地識別其可持續(xù)發(fā)展短板并提出相應策略,下文將在更精細的顆粒度上進行分析。

圖2 三大指數(shù)國家數(shù)目分布
4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特征及短板
結合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FDI)存量數(shù)據(jù)來分析各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指數(shù)”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指數(shù)”兩個維度上的表現(xiàn),有助于充分利用“一帶一路”項目投資推動沿線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建設。研究選擇了兩軸四象限方法,把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指數(shù)投入X 軸線,把環(huán)境可持續(xù)指數(shù)投入Y軸線,建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特征識別坐標系。右上角象限Ⅰ區(qū)域是“高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高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的國家,右下角象限Ⅱ區(qū)域是“高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低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的國家,左上角象限Ⅲ區(qū)域是“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高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的國家,左下角象限Ⅳ區(qū)域是“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低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的國家。分類結果如圖3所示,圖中圓點直徑越大表明中國對該國投資越多。

圖3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兩軸四象限分類圖
4.1 象限Ⅰ國家:基本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增長與環(huán)境資源損耗脫鉤
象限Ⅰ(高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高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共有24 個國家,整體上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較高,各國基本實現(xiàn)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增長與環(huán)境資源損耗脫鉤。該象限典型代表是歐盟地區(qū)發(fā)達國家(79%);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各占該地區(qū)國家的一半;產(chǎn)業(yè)結構上,象限Ⅰ各國前三大支柱產(chǎn)業(yè)中最多出現(xiàn)的是食品加工(12%)和紡織(11%)等輕工業(yè),重工業(yè)如汽車(10%)、鋼鐵(8%)、冶金(8%)、機械(8%)和化工(6%),資源業(yè)如采礦(7%)和農(nóng)林牧漁(5%)等占比較低;象限Ⅰ國家產(chǎn)業(yè)結構以服務業(yè)主導,輕工業(yè)領先,貿(mào)易較平衡,70%的象限Ⅰ國家的服務業(yè)GDP 占比在三大產(chǎn)業(yè)中最高;凈出口國和凈進口國各占50%。中國對該象限國家累計直接投資額為215億美元,平均每國約9億美元。
象限Ⅰ國家各維度評價得分雷達圖如圖4(a)所示。各國整體上在各評價維度中表現(xiàn)出色而平均,發(fā)達國家在經(jīng)濟機會、社會福祉和環(huán)境質量3個維度明顯表現(xiàn)優(yōu)于發(fā)展中國家,在氣候行動維度則表現(xiàn)接近。
4.2 象限II 國家:過度損耗環(huán)境資源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高增長
象限Ⅱ(高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低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共有35個國家,整體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高,但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較低,該象限內(nèi)很多國家仍處在以過度損耗環(huán)境資源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高增長的模式。象限Ⅱ以亞洲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為主,亞洲國家占比超過一半(57%),其中有12個是西亞國家,在各區(qū)域中占比最高(34%);中高收入國家占比最高(46%),其次是高收入國家(43%);產(chǎn)業(yè)結構上,象限Ⅱ各國前3大支柱產(chǎn)業(yè)中占比最高的是石油化工(17%)和化工(10%)這類重工業(yè),之后是農(nóng)林牧漁(8%)、采礦(7%)、冶金(7%)等資源業(yè);66%的象限Ⅱ國家工業(yè)GDP 占比在三大產(chǎn)業(yè)中最高;象限Ⅱ各國中凈出口國和凈進口國分別占68%和29%,原油凈出口國占52%。總體而言,象限Ⅱ國家產(chǎn)業(yè)結構以工業(yè)主導,石油化工業(yè)領先,為出口導向。中國對該象限國家累計直接投資額為1 132億美元,平均每國約32億美元。
象限Ⅱ國家各維度評價得分雷達圖如圖4(b)所示。各國在經(jīng)濟機會、社會福祉和環(huán)境質量3個維度的表現(xiàn)遠比氣候行動維度表現(xiàn)出色,發(fā)達國家明顯表現(xiàn)優(yōu)于發(fā)展中國家,這主要是由于該區(qū)域國家對石油工業(yè)的高度依賴。
4.3 象限Ⅲ國家:低社會經(jīng)濟增長和低環(huán)境資源損耗
象限Ⅲ(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高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共有34個國家,整體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較高,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低,該象限國家大部分處于工業(yè)發(fā)展階段前期,尚未進入以損耗環(huán)境資源謀求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可持續(xù)模式,“一帶一路”項目應當助力該區(qū)域國家走出符合各國特色的高質量、可持續(xù)的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象限Ⅲ以非洲中低收入國家為主,非洲國家占比超過一半(65%);該區(qū)域內(nèi)幾乎全為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占比分別為56%和38%;產(chǎn)業(yè)結構上,象限Ⅲ各國前三大支柱產(chǎn)業(yè)中最多出現(xiàn)的是農(nóng)林牧漁(17%)和采礦(14%)等資源業(yè),其次是食品加工(15%)和紡織(12%)等輕工業(yè),最后是化工(14%)、石油化工(7%)和冶金(6%)等工業(yè);該象限內(nèi)76%的國家農(nóng)業(yè)GDP 占比在三大產(chǎn)業(yè)中最高;象限Ⅲ各國中凈出口國和凈進口國分別占9%和91%,原油凈出口國占18%。總體而言,象限Ⅲ國家的產(chǎn)業(yè)結構以農(nóng)業(yè)為主導,資源業(yè)領先,為進口導向。中國對該象限國家累計直接投資額為541億美元,平均每國約16億美元。
象限Ⅲ國家各維度評價得分雷達圖如圖4(c)所示,各國在氣候行動維度表現(xiàn)遠比經(jīng)濟機會、社會福祉和環(huán)境質量3 個維度出色,亞洲國家在社會福祉和環(huán)境質量2個維度的表現(xiàn)明顯優(yōu)于非洲國家。需要說明的是,象限Ⅲ國家的典型代表是東非落后國家,處于低資源投入低經(jīng)濟產(chǎn)出的狀態(tài)。在缺乏經(jīng)濟和產(chǎn)業(yè)擴張的條件下,人均能源需求和物質消費都很低,能夠只依賴水電或是效率較低的可再生能源支持社會運作,人均碳排放也自然比較依賴化石能源支持經(jīng)濟活動的其他象限區(qū)域國家更低,所以盡管該區(qū)域很多國家在“氣候行動”這一維度上表現(xiàn)出色,但這并不代表真的采取了積極對抗氣候變化的行動。

圖4 不同象限國家評價表現(xiàn)比較雷達圖
4.4 象限Ⅳ國家:高環(huán)境資源損耗無法推動社會經(jīng)濟增長
象限Ⅳ(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低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共有19 個國家,各國整體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較低,大部分國家處于過度損耗環(huán)境資源但無法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有效增長的惡性循環(huán)模式。有研究認為,該區(qū)域國家因經(jīng)濟水平落后而無法推動農(nóng)業(yè)技術改革,低技術種植造成土質受損、森林破壞、水資源浪費和溫室氣體大量排放等問題,且隨著非洲大陸人口的快速增長和糧食需要的不斷增加,如果農(nóng)業(yè)技術得不到有效提升,則該區(qū)域將同時面臨嚴峻的環(huán)境問題和社會經(jīng)濟危機[31]。該象限以非洲中低收入國家為主,非洲國家占比超過一半(53%),其次是亞洲國家(42%);該區(qū)域幾乎全部為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占比分別為63%和32%;產(chǎn)業(yè)結構上,象限Ⅳ各國前三大支柱產(chǎn)業(yè)中最多出現(xiàn)的是紡織(19%)和食品加工(17%)等輕工業(yè)、農(nóng)林牧漁業(yè)(13%)、石油化工(11%)和采礦(9%)等資源業(yè);農(nóng)業(yè)在該區(qū)域國家產(chǎn)業(yè)結構中依舊占比較高,58%的象限Ⅳ國家的農(nóng)業(yè)GDP 占比在三大產(chǎn)業(yè)中最高;象限Ⅳ各國中凈出口國和凈進口國分別占17%和83%,原油凈出口國占32%。總體而言,象限Ⅳ國家產(chǎn)業(yè)結構以農(nóng)業(yè)主導、輕工業(yè)領先、為進口導向。中國對該象限國家累計直接投資額為236億美元,平均每國約12億美元。
象限Ⅳ國家各維度評價得分雷達圖如圖4(d)所示,各國整體上在各評價維度中表現(xiàn)落后,亞洲國家在經(jīng)濟機會、社會福祉和環(huán)境質量3個維度明顯表現(xiàn)優(yōu)于非洲國家。象限Ⅳ國家的典型代表是西非落后國家,這些國家投入了大量資源和產(chǎn)出了大量污染,但并沒有獲得相應的經(jīng)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回報,是典型的不可持續(xù)發(fā)展路徑。
5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重心方向及中國綠色投資合作建議
象限Ⅰ國家擁有高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和高環(huán)境可持續(xù)水平,進出口貿(mào)易發(fā)展均衡成熟,是其他象限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標桿,不需要在產(chǎn)業(yè)結構上進行大幅度調(diào)整,也無需外部資金和技術就一般交通基建和產(chǎn)業(yè)項目進行投資合作。象限Ⅰ國家在氣候行動和經(jīng)濟機會兩個維度的評分分別稍落后于象限Ⅲ和象限Ⅱ,因此可在這兩個領域進行持續(xù)優(yōu)化。象限Ⅰ國家可針對優(yōu)化“氣候行動”專注推動可再生能源、成熟電力輸送基建和自然災害應急的合作項目,以及針對優(yōu)化“經(jīng)濟機會”專注推動科研和高新產(chǎn)業(yè)的合作項目。
象限Ⅱ國家工業(yè)GDP 占比過高,嚴重依賴石油業(yè)推動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進出口貿(mào)易不平衡,貿(mào)易GDP占比有提升空間,因此應繼續(xù)推動交通基建合作項目,促進貿(mào)易連接能力和產(chǎn)業(yè)多樣化。象限Ⅱ國家的“氣候行動”評分最低,“環(huán)境質量”評分稍落后于象限Ⅰ,因此應在這兩個領域進行深度調(diào)整。象限Ⅱ國家應大幅度調(diào)整其“氣候行動”,逐步放棄投資化石能源相關基建項目,引導投資流向可再生能源領域,同時推動公共設施和自然災害應急項目。
象限Ⅲ國家農(nóng)業(yè)GDP 占比過高,嚴重依賴農(nóng)業(yè)和礦業(yè)維持經(jīng)濟和社會運作,進出口貿(mào)易嚴重不平衡,貿(mào)易GDP 占比過低,嚴重缺乏資金和技術推動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可積極推進交通基建及工業(yè)產(chǎn)業(yè)合作項目,促進工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象限Ⅲ“氣候行動”評分雖高但主要由其經(jīng)濟發(fā)展緩慢導致,未來可結合地區(qū)發(fā)展戰(zhàn)略,適當投資化石能源,但仍應著力發(fā)展可再生能源,避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象限Ⅲ的“經(jīng)濟機會”“社會福祉”和“環(huán)境質量”評分最低,應該推動住房、商業(yè)建筑、自然災害應急和公共設施等所有類型的社區(qū)建設合作項目。
象限Ⅳ國家以資源投入型產(chǎn)業(yè)為主,但大量的資源消耗和排放并未帶來相應的經(jīng)濟增長,未來應當依靠國際貿(mào)易及合作推動產(chǎn)業(yè)深度變革,大力發(fā)展工業(yè)經(jīng)濟、投資清潔能源并加強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投入,同時注意環(huán)境治理和修復,促進可持續(xù)發(fā)展。
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綠色技術、清潔能源等的投資是助力發(fā)展中國家實現(xiàn)綠色轉型、推動全球實現(xiàn)碳中和目標、體現(xiàn)大國擔當?shù)闹匾e措。結合沿線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狀態(tài)特征,未來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投資需要增強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首先,提高對Ⅲ、Ⅳ象限國家綠色基礎設施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比例,加強綠色技術合作,增強“一帶一路”投資資金的綠色邊際效益。大部分Ⅲ、Ⅳ象限的發(fā)展中國家能源結構依賴于傳統(tǒng)化石能源,產(chǎn)業(yè)及技術相對落后,它們面臨不同程度的資源、人口、資本、競爭力及制度性約束[32],加大對這些國家綠色基礎設施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可以推動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并避免其走上傳統(tǒng)的高碳發(fā)展路徑,推動全球氣候目標的實現(xiàn)。麥肯錫全球研究院[33]發(fā)布報告表明,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領域進行同等規(guī)模的投資將創(chuàng)造比投資在傳統(tǒng)能源行業(yè)三倍的工作機會。此外,大量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產(chǎn)生的技術溢出效應提高了沿線國家的生產(chǎn)效率[34-35]和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36-38],并且有利于促進沿線國家的產(chǎn)業(yè)結構升級[39]。因此,建議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可增加在象限Ⅲ、Ⅳ國家的投資比例,提高“一帶一路”投資對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邊際效益。
其次,根據(jù)各國綠色發(fā)展需求引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流向。中國企業(yè)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通、產(chǎn)業(yè)和能源合作項目時應盡可能地進行需求匹配,在象限Ⅰ國家推動零排放交通項目,在象限Ⅰ和Ⅱ推動生態(tài)產(chǎn)業(yè)園項目,在象限Ⅰ、Ⅱ和Ⅳ推動近零排放燃煤發(fā)電項目,在象限Ⅲ和Ⅳ推動氣候智慧型農(nóng)業(yè)項目等,整體推動傳統(tǒng)基建項目脫碳化、低碳化、自動化和智能化,契合當?shù)乜沙掷m(xù)發(fā)展現(xiàn)狀,助力沿線國家進行深度化和精細化的能源和產(chǎn)業(yè)結構調(diào)整。
最后,采用國際標準進行投資項目的環(huán)境社會影響評價,促進國際合作,保障中國企業(yè)在“一帶一路”投資中的財務支持、知識共享與風險分擔。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jīng)濟形勢蕭條影響,海外投資項目的資金預算減少,落地實施難度增加。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yè)進行“一帶一路”海外投資時更應注重項目的環(huán)境社會影響評價:一方面能夠降低項目實施風險,增加項目的可持續(xù)營利性;另一方面可以促進東道國實現(xiàn)綠色復蘇;最后則能夠爭取更多國際投資者的支持,加大融資規(guī)模,降低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