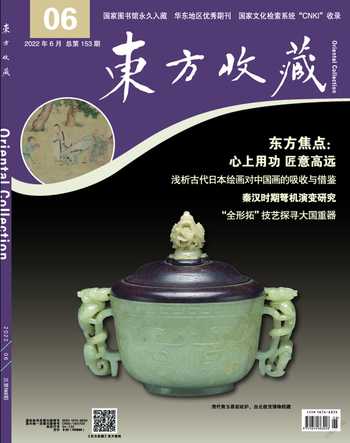淺析古代日本繪畫對中國畫的吸收與借鑒
摘要:中國與日本雖為不同的國度,但卻因同屬一個文化圈而很早就開始文化藝術的交流,繪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內容。古代日本繪畫的誕生緣于中國移民帶來的繪畫藝術,其發展也深受中國畫的影響,對中國畫尤其是唐代的人物畫和南宋的水墨畫多有吸收和借鑒。正是在這吸收和借鑒的過程中,古代日本繪畫實現了創新,逐漸產生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風格。
關鍵詞:日本繪畫;中國畫;人物畫;水墨畫
“同屬東亞文化圈”[1]的中國和日本隔海相望、一衣帶水,早在2000多年前就開始了文化交流[2],而繪畫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目前學界已經從多個角度對中日兩國的繪畫交流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產生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在部分課題上仍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本文擬從中國畫對日本繪畫誕生的影響、中國人物畫和水墨畫對日本繪畫的影響等方面,分析日本繪畫對中國畫的吸收與借鑒,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國畫對日本繪畫誕生及發展的影響
專研日本繪畫藝術的英國東方文化學者勞倫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曾指出:“日本的藝術史是這樣的一部藝術史,它從中國取得了最初的靈感,逐步發展自己的性格,并且接受了新的題材。”[3]勞倫斯·比尼恩的這一觀點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首先,日本藝術之所以能夠“逐步發展自己的性格”,是以從中國藝術中獲得的靈感為前提,這就形象地揭示中國藝術對日本藝術誕生的影響;其次,日本藝術又有自己獨特的“新的題材”,不完全同于中國藝術。
顯然,日本逐步消化吸收了來自中國的藝術,并最終完成創新,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藝術,而這種創新只是“在華夏文明之上的衍生和發展”,根子上“始終保留著中華文化的精髓”[4],古代日本繪畫則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公元3至6世紀間,移民日本的中國人將中國繪畫藝術帶入日本,為日本繪畫“撒下了第一批中國傳統繪畫的種子”[5]。可以說,正是在中國畫的哺育之下,古代日本繪畫才最終得以誕生,并從誕生之初就打上了深深的中國烙印。
此后1000多年的時間里,日本繪畫不斷發展,伴隨著這種發展的是中國畫對日本繪畫兩次大規模的影響:
第一次發生在唐朝,當時日本向中國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這種使團的隨行人員中就有大量的畫師和畫工。除此之外,還有大量來中國學習唐朝先進文化的日本留學生,最有名的當屬唐高宗時的日本僧人空海,他在回日本時帶去了唐朝著名畫家李真的名作《真言五祖像》,對日本繪畫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也有大量的僧侶、文人等前往日本,最著名的當屬天寶年間的鑒真東渡,鑒真大師在弘揚佛法的同時,對日本宗教雕塑和繪畫的發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正是在這種“走出去,請進來”的文化交流中,平安時代的日本襲仿唐代繪畫而形成了著名的“唐繪”。
第二次發生在南宋時期,日本正處于鐮倉時代。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武士階層控制政權,甚至一度取代皇權政治。政治上的這種變化逐漸波及到藝術領域,變革也就成為勢所必然。此時在中國蔚成風氣的飽含禪宗意味的水墨畫,恰好迎合了包括禪宗僧侶在內的日本社會上層的審美趣味,于是,日本大量引入、移植牧溪、梁楷等南宋畫家的作品并著意創新,形成了被稱為“漢畫”的日本水墨畫[6]。
二、日本人物畫對中國畫的襲仿
唐朝繪畫傳入日本后所形成的“唐繪”,主要是以各色人物畫為主[7],這些人物畫所具有的風格特點是對中國唐代畫風進行吸收和借鑒的結果。關于這一點,1972年在奈良發掘的飛鳥時代后期貴族高松冢墓葬壁畫,就是最好的例證。
高松冢墓的年代為7世紀后期至8世紀前期,相當于中國的盛唐時代,與初唐的永泰公主墓極為相似。將高松冢墓壁畫(圖1)與永泰公主墓壁畫(圖2)加以對比就會發現,高松冢墓西壁上畫的四名侍女像基本是“八頭等身比例”[8],與真人大小相同,且侍女們面部神情各不相同,形象惟妙惟肖、生動優雅,能看出明確的遠近透視關系。無論是人物形象還是構圖技法,高松冢墓壁畫都與永泰公主墓壁畫極其相似,顯然是模仿了永泰公主墓。
另外,從侍女所持花傘的紋樣中同樣可以看到屬于初唐時期的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壁畫(圖3)的影子。將二者加以對比可以發現,高松冢墓壁畫風格偏柔和婉麗,迥異于唐代壁畫雄強茂密的風格,日本畫風之源頭當在于此。
高松冢墓所處時代之后的日本人物畫作品,也有很多借鑒、吸收唐代繪畫的痕跡。7世紀后期的奈良法隆寺金座壁畫中,第六號壁畫《阿彌陀凈土變》的線條描法類似于中國南朝著名畫家張僧繇的“鐵線描”[9]。壁畫首先在15厘米厚的壁面上由白石灰粉刷三次,然后再用與敦煌發現的相同的“紙彩”貼在壁面,紙形背后涂上黑、紅兩種灰粉,將輪廓拓描在壁面上,按照描好的輪廓用尖筆描畫成凹線,再按凹線描畫,之后朱線上再覆以黑線。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稱贊張僧繇的線描畫法是“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10],法隆寺金座壁畫即是采用這種富有彈性的、有立體感的“鐵線描”技法。
同高松冢墓壁畫柔和婉麗的風格一脈相承,日本的這種“鐵線描”技法同樣十分柔和優雅,其后續發展為以“唐繪”為源頭但又有較為明顯差異的“大和繪”,這是一種無論題材、方式還是技法制作,都更富有日本特色的本土畫種,“大和繪”的代表作品當屬完成于11世紀的《源氏物語繪卷》(圖4)。如果說前述高松冢墓壁畫和法隆寺金座壁畫還保留有中國古典題材的痕跡,那么《源氏物語繪卷》則明顯區別于中國的唐畫,是一幅具有濃郁日本風格的故事長卷,表現的完全是日本的風土人情。該畫作構圖視角獨特,畫面中園林風景、建筑和人物的排列采用的是“脫頂鳥瞰式”構圖[11],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斜視角構圖,能夠充分表現主體空間感。值得注意的是,《源氏物語繪卷》中的建筑物均不畫屋頂,就像是呈現于觀者眼前的大舞臺,又好像屋頂是被刻意掀掉的,室內貴族的私密生活一下子就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某種程度上滿足了觀者的窺視心理與觀看需求。
《源氏物語繪卷》既不見漢畫的雄渾,也沒有唐畫的雍容,更缺乏宋畫的崇高,展現出的是細膩華美的繪畫形式,這是一種與日本風土環境相適應的“日本美”,成為江戶時期表現世俗生活的浮世繪版畫的先聲。
三、日本水墨畫的中國元素與民族趣味
如前所述,日本水墨畫的源頭是南宋的水墨畫,因由禪林畫僧移植而來,故又稱為“禪畫”。到室町時代(相當于中國明代),隨著五山禪林的高僧倡導禪文學[12],日本水墨畫趨于興盛,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水與墨于紙上揮灑交融而形成的幻化圖像,極好地契合了禪所要表達的境界,所以漢字書法在日本興盛之后,水墨畫又得以在日本生根開花”[13]。
當然,在中日水墨畫的交流中,日本并沒有全盤接受從中國傳來的水墨技術,而是有選擇地吸收,充分表現出其民族特色。具體而言,北宋那種雄偉大氣的水墨山水在當時并未引起日本畫家的共鳴,反倒是南宋畫僧牧溪那種有明確輪廓、多染少皴、帶有禪意和朦朧的“沒骨畫法”[14],深受日本人追捧,被日本尊為“畫圣”。
另外,被譽為“南宋四家”的李唐、劉松年、馬遠和夏圭的作品同樣深受日本民眾歡迎,尤其是師法李唐、并稱“馬夏”的馬遠和夏圭,二人均擅長“大斧劈皴”[15],這是一種與畫家活動區域的實景山水關聯極其密切的皴法。相對于多高山大川的北方,馬、夏二人所在的臨安城更多的是細碎的山石與雜草,多雨濕潤的氛圍成就了馬、夏二人的風格特點,他們用書法意味很強的濃重墨線勾勒出山石,用“大斧劈皴”塑造結構,將畫面收于一角或半邊,表現出臨安山水一片、煙雨迷蒙的景色。室町時代后期的狩野元信在師法馬、夏二人作品的基礎上,開創了日本水墨畫中最具代表性的“狩野派”[16] 。
日本民眾對于馬、夏二人作品的喜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產生了共情。日本京都地區的地理環境、山水地貌與臨安頗為相似,日本民眾在欣賞馬、夏二人的畫作時,可以體會到“身臨其境”之感,而不僅僅是欣賞“中國”的山水;同時,馬、夏二人構圖精簡、筆墨直白的畫風特點,有助于日本民眾上手學習水墨畫,其風俗性、社會性的畫面易于在日本民眾中產生共鳴。
不過,此時的日本畫家已經不再滿足于對中國畫的簡單襲仿和移植,而是著意創新,當然,他們也已經有了這樣的能力。正如開創水墨畫現代化的著名畫家橫山操所言“日本水墨畫始于雪舟(世界著名的日本“宋元派”水墨畫家雪舟等楊——引者注)”[17],正是在雪舟等楊的努力之下,日本水墨畫實現了“脫中國化”。“雪舟等楊這一畫名的登場,標志了日本畫家從亞洲畫家群中獨立出來的開端,自雪舟開始,日本開始脫離亞洲”[18],民族風格日益凸顯。
日本水墨畫的民族風格在雪舟等楊的《四季山水圖》中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特別是其中《夏景圖》的設計。在《夏景圖》中,除了矗立在中央的巖石與遠景中隱隱約約的山峰呈直立狀外,其他景物均呈微微歪斜之勢。值得注意的是,右上方的大斜面弧度絕非一般,而銜接這一斜面的并非中央稍偏左的那一條細細的瀑布,而是中央下方五棵樹的枝葉,用瀑布是中國的山水畫法。雪舟等楊沒用瀑布的一個有力佐證,就是坐在畫面右方的男子姿勢,瀑布雖在男子眼前,但他并不是在觀賞瀑布。
應該說,雪舟等楊的畫作在早先的中國是沒有的,其有意識地導入了一種“動態的觀點”,使得畫面突破了二維紙面的限制。這種動態效果在他的《仿夏圭山水圖》(圖5)中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一個“仿”字似乎明白地告訴世人,該作品是對夏圭《山水圖》的“模仿”。但就畫作體現的內容來看,雪舟等楊并未完全模仿夏圭,而只是采用了夏圭畫作中展示“動態”山水的表現手法,這種表現手法是中國畫的一個顯著特征——山水畫中巖石、高山均透露出靈動的生機感。
在雪舟等楊的作品中,與《仿夏圭山水圖》風格類似的還有《山水長卷》(圖6)與《天橋立圖》等,這些作品充分體現了雪舟等楊“取之中國而又跳出中國”的藝術風格和高深造詣。
考察雪舟等楊的經歷就會發現,他這種藝術風格的確立發生在明成化三年至五年(1467—1469)的中國之行后。此次中國之行,雪舟等楊受到了明憲宗的熱情款待,訪問了明朝的宮廷畫院,并向宗法夏圭、馬遠的宮廷畫家李在和張友聲等學習了“浙派”山水技法[19]。通過這次訪問,雪舟等楊熟練地掌握了“傳移模寫”的畫法,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山水畫中有哪些因素可以借用,哪些因素又可以舍棄,之后將彼地的景色與此地的景色進行對比后再進行替換。雪舟等楊將這種繪畫的“編輯”工作引入了山水畫領域,從事實和形式中自由地導出形象,即制造出變化,改變相互之間的關系,從而提取并創造出新的意義。
日本是一個非常擅長這種“編輯”工作的民族,無論是最澄、道昭和空海等佛教界高僧,還是有“歌圣”“歌仙”美譽的柿本人麻呂、大伴加持、藤原定家和紀貫之等文藝界明星,均是深諳此道的高手。這種“引用與獨創”的妙法是日本文化史蘊藏的獨特方法,其與日本水墨畫融匯在一起,使得畫面展示出了日本的民族趣味。
四、總結
對于日本繪畫與中國畫的關系,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美術理論家、中國畫研究專家伊勢專一郎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一切文化,皆從中國舶來,其繪畫也由中國分支而成長。恰好比支流的小川對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國美術上更增一種地方色彩,這就成為日本美術。”[20]顯然,古代日本繪畫在中國畫的影響之下誕生,然后對中國畫進行持續的吸收和借鑒,通過“襲仿——移植——創新”的發展路徑,最終實現了“民族化”和“本土化”。
古代日本繪畫的發展歷程表明,一種新文化要產生與發展,絕不能僅僅滿足于對現存另一種文化的簡單模仿,而是要因地制宜,將具有本文化特色的關鍵元素融入其中。作為當下文化創造者的我們也應該明白,如果只是在畫布上一味地模仿現有的藝術,那就永遠都無法擺脫其束縛,要想創造一種新的藝術,唯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在現有藝術形式的基礎上,不斷將具有時代色彩的內容融入其中。
參考文獻:
[1]陳維東.中國漫畫史[M].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89.
[2]王婷,韓雪.日本社會文化探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18.
[3](英)勞倫斯·比尼恩.亞洲藝術中人的精神[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95-96.
[4]方志平.中國南宗繪畫對日本繪畫的影響——從董其昌到富岡鐵齋[D].中國美術學院,2014:7.
[5][6]王蓮.宋元時期中日繪畫的傳播與交流[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2(03):168-170.
[7]徐靜波.解讀日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83.
[8][13]趙文江.中國山水畫與日本風景畫構圖研究[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1:50.
[9]余輝.秀骨清像——魏晉南北朝人物畫[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77.
[10][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80.
[11]劉小羊.中國平面設計史論稿[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274.
[12]高文漢.中日古代文學比較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515.
[14]杭州市文史委員會.杭州佛教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130.
[15]李鄉狀.山水畫技法與欣賞[M].長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6:60.
[16]仇賢峰.寧波絲路日本書畫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18.
[17][18](日)松岡正剛著,韓立冬譯.山水思想——“負”的想象力[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7:45.
[19]林士民,沈建國.萬里絲路——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M].寧波:寧波出版社,2002:269.
[20]嬰行.中國美術在現代藝術上的勝利[J].東方雜志,1930,27(1).
作者簡介:
于曦湲,女,2019級本科生,專業:中國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