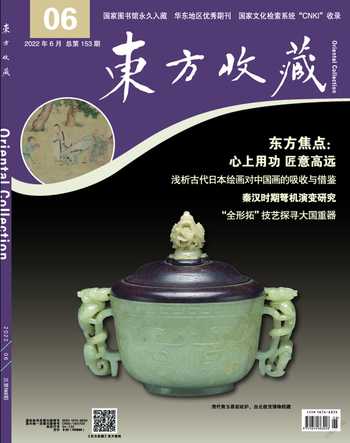焉然系而不食 吾豈匏瓜也哉
曹珺 徐宗發(fā)
摘要:“揚州八怪”的殿軍羅聘,習畫精勤,技法全面。雖以鬼畫聞名,但其蔬果、人物、佛像等無所不工,作品極具個人特色。江西省博物館館藏的羅聘《蔬果圖》《鐘進士役鬼圖軸》,為其不同時期的作品,本文以羅聘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與經(jīng)歷為背景,對畫作的藝術風格及創(chuàng)作理念等進行探討。
關鍵詞:羅聘;蔬果圖;鐘進士役鬼圖軸
清代中期,商業(yè)繁盛的揚州,隨著以商人、鹽戶為主的市民對繪畫作品的需求,出現(xiàn)一些順應繪畫商品市場的職業(yè)畫家。區(qū)別于純粹的職業(yè)畫家,這些畫家是具有文人畫家特質(zhì)的職業(yè)畫家,他們的創(chuàng)作風格以“怪”聞名,被稱為“揚州八怪”;相較于風雅的正統(tǒng)文人畫,揚州八怪在繼承傳統(tǒng)水墨寫意畫的同時,提倡繪畫風格的獨創(chuàng)和個性表現(xiàn),他們“突破了傳統(tǒng)雅俗觀念的桎梏,迥別于正統(tǒng)派的藝術趣尚,以不拘泥古法、敢于領導標新為特色,呈現(xiàn)出不同于前人的意蘊與風貌。”[1]如“揚州八怪”中羅聘的《鬼趣圖》,題材構思新奇有趣,在考慮市場需求的同時,畫作又有諷世警俗意味。作為揚州八怪中最年輕的畫家,羅聘的繪畫才能是比較全面的,他的作品造型準確、題材多樣;畫作中不僅有“揚州八怪”縱筆揮灑的寫意特點,同時還表現(xiàn)出極強的個人特色,作品構思考究獨特、發(fā)人深思。
羅聘(1733—1799),字遯夫,因原籍安徽歙縣呈坎村,此地在黃山之麓,近于天都、蓮花二峰,故號“兩峰”。早年曾夢入花之寺,仿佛前身是其寺中的主僧,故又號“花之寺僧”。其為金農(nóng)入室弟子,金農(nóng)晚年嗜佛,自號“蓮身居士”,所以羅聘又號“師蓮居士”。羅聘出身中產(chǎn)之家,其父和叔父都曾任縣令,羅聘不滿周歲時其父過世,“其父、叔皆喜金石書畫,與當時著名文人有一定交往,生活在這種文化氣氛很濃的家庭環(huán)境中,羅聘自幼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2]而同鄉(xiāng)馬氏兄弟“小玲瓏山館”豐富的書畫藏品,為年少的羅聘提供了書畫根基必要的養(yǎng)分。1752年羅聘娶妻方婉儀,方婉儀是一位賦有才情的女子,并且兼長于書畫,夫婦二人經(jīng)常合作,對于羅聘的藝術道路,方婉儀給予了很多幫助。1756年羅聘拜師金農(nóng),被稱為“揚州八怪”之首的金農(nóng)時年已71歲,作為一位已成名的老藝術家,他對羅聘在藝術上的指導是多方面的,金農(nóng)“修養(yǎng)廣博,工詩文、精鑒賞、善篆刻、長漆書,后則作畫,四君子、蔬果、山水、人馬、佛像、肖像無不擅長。作品造意新奇,構境別致,筆墨樸秀,巧拙互用,耐人尋味。”[3]羅聘年少時即已才氣顯露,習畫精勤,技法全面;而金農(nóng)豐富的藝術素養(yǎng)、詩人的情懷,以及對書法的“奇”“怪”創(chuàng)新和對繪畫不拘成法、標新立異、超塵脫俗的繪畫風格,也給年輕的羅聘以創(chuàng)作方向上的啟發(fā)和思考。由于金農(nóng)年逾半百才開始作畫,繪畫技巧并不十分全面,加之精力有限,故畫作多由繪畫技巧全面的羅聘代筆。為師代筆,自古有之,但金農(nóng)作品都是自身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構圖構思,嚴格來說,師徒合作的意味更多一些,金農(nóng)畫作的“異”“趣”和在繼承傳統(tǒng)同時對“獨創(chuàng)”的追求,在師徒合作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羅聘,這也為其之后別出心裁的鬼神畫提供創(chuàng)作條件。
“文人畫家從事繪畫,盡管說是勢不可逼,利不可取,但是,為了生計又不得不以賣畫為業(yè),靠賣畫糊口又很難保證生活,所以他們大都困頓潦倒。”[4]金農(nóng)去世后,羅聘為生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次北上京城,這不僅為羅聘拓展了藝術市場,也為其提升了一定的聲譽,并在畫壇形成了頗高的影響力。羅聘在金農(nóng)過世之前,從未離開揚州,而其后進京或是受金農(nóng)壯年時游歷山水的影響,除去市場的考慮,北京之行使其開闊了眼界,豐富閱歷的同時也增進自身的學識。“胸中有萬卷書,目飽前代奇跡,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5]一定的文學修養(yǎng),對傳統(tǒng)藝術的研究,生活經(jīng)歷的豐富,羅聘的藝術歷程印證了創(chuàng)作基礎與自身的藝術、文化、思想等修養(yǎng)息息相關。
江西省博物館館藏羅聘《蔬果圖》(圖1),紙本,縱33、橫117厘米。畫面簡潔、造型準確,筆墨線條流暢,畫面看似隨意,卻對細節(jié)頗為注意。此時的作品雖然暫無后期生拙古逸的特點,筆墨功力有限,但相較羅聘更早期的《水仙扇面》,《蔬果圖》的畫法已擺脫其初學時的稚嫩,以及畫法過于工整的缺點;《蔬果圖》筆法簡括的特點,也延續(xù)為后期的創(chuàng)作風格。《蔬果圖》左上自題“焉然系而不食,吾豈匏瓜也哉。壬申秋日。兩峰道人。”壬申時羅聘20歲,娶才女方婉儀為妻,風華正茂又才華橫溢。“焉然系而不食,吾豈匏瓜也哉”出自孔子《論語》陽貨篇第七章,羅聘以此感嘆懷才不遇,希望有所作為的境況;匏瓜即為葫蘆,與畫中處于中心的葫蘆相呼應,點明主題。
以畫家為審美主體,審美主體對現(xiàn)實的觀照,將審美情感投入其中,這就是通常說的“移情”[6],畫作融入畫家的審美及情感,借景借物抒發(fā)創(chuàng)作者的思想意識。自北宋以來,借物抒情在文人畫作品中表現(xiàn)得較多,為表達自身思想的深切,畫家在借助比喻、象征手法抒發(fā)感情的同時,也會使所繪的物象人格化,而清代畫家更是借助形象的夸張和對某些特定細節(jié)來表達畫外之意,如清初的八大山人,以怪誕而富有寓意的景物來借喻自身、詠物抒情,其創(chuàng)作思想對清中期的“揚州八怪”有一定的影響;而聚集在揚州地區(qū)賣畫為生的畫家如鄭板橋、黃慎、汪士慎等,作品數(shù)量眾多且流傳廣泛,這些揚州八怪的前輩們,對后來作為“揚州八怪”殿軍的羅聘不無影響。“焉然系而不食,吾豈匏瓜也哉”,畫作題款言真意切,弱冠之年的羅聘即有學有所用、進取入世的儒家思想,這與世俗化、個性化的“揚州八怪”是相契合的。在創(chuàng)作《蔬果圖》幾年后,羅聘以詩為禮,拜師被稱為“揚州八怪”之首的金農(nóng)。
江西省博物館館藏的另一幅羅聘畫作《鐘進士役鬼圖軸》(圖2),紙本,縱91、橫41.5厘米。“五月五日祓不祥,何須按劍髯怒張,畢竟終南鐘進士,能教鬼服到文章”,題款“羅聘戲墨”,蓋“羅兩峰印”朱印,下蓋四枚收藏章,分別是“青霞館珍藏印”“上元余氏考藏金石書畫之印”“頤情館印”“宋燦之印”(圖3),象征五月五日端午節(jié)除災求福,是一幅具有祈福寓意的畫作。羅聘在《鐘進士役鬼圖軸》中,刻畫的鐘馗猶如常人,表情豐富、生動,畫作富有情節(jié)引人遐想。畫中鐘馗滿面虬髯,目光炯炯,怒視前方,右手按劍欲拔之,身后抱書小鬼安然自若。鐘馗與小鬼,一動一靜、一強一弱,強烈的視覺沖突,使鐘馗的藝術形象鮮明;畫家筆觸沉穩(wěn)灑脫,技藝精湛老練,畫面的表達極富創(chuàng)作激情,讓人印象深刻。鐘馗粗重概括的身姿對比其細致的面部刻畫,在抓住觀賞者視線的同時,引導著觀賞者對畫中人物神態(tài)的注意。“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后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7]抓住人物獨有的特征,以形寫神,以自身對人物的內(nèi)在精神的理解與人物外在神態(tài)的描繪,情理統(tǒng)一使人物“氣韻生動”,而“畫龍點睛,言物之神全在睛之生動也。人物寫真,點睛最要”[8],畫中鐘馗眼神聚焦,逼視前方,身后小鬼也尾隨著他的目光,雖無大幅度的動態(tài),但通過眼睛與神態(tài),把鐘馗不怒自威、令人生畏的形象表現(xiàn)得傳神而自然。
從《蔬果圖》到《鐘進士役鬼圖軸》,羅聘對于物象的描繪從熟練工整,到縱筆揮灑、物我交融;“焉然系而不食,吾豈匏瓜也哉”是羅聘對于自身藝術道路的追求,畫作《鐘進士役鬼圖軸》中的生拙氣是其筆墨技法成熟的表現(xiàn)。羅聘拜師金農(nóng),但從繪畫技法上說,金農(nóng)未必能給予多少指導;羅聘研究繼承傳統(tǒng)繪畫,按照自身的藝術追求,進行藝術實踐,并根據(jù)自己的審美意識,吸收金農(nóng)、石濤、華喦等筆墨技法,最終形成生拙蒼厚、構思獨特的創(chuàng)作特點。此外,羅聘的繪畫題材廣泛、技法多樣,成名于鬼神畫,但其人物、梅花、蘭竹、山水等皆是精通。而其師金農(nóng)畫作中超脫、拙簡,和詩意融合的自然而然的畫境,以及極富個性又隨性無意的構圖,觸動著羅聘對繪畫的創(chuàng)作理念由外至內(nèi)的思索,促使其創(chuàng)作心境的自然變化。從《蔬果圖》中“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9]的融情入境,到《鐘進士役鬼圖軸》中不刻意寫物而極盡物態(tài)的回歸自然,畫作技法的成熟與轉變,創(chuàng)作心境的任情恣性,《蔬果圖》中充滿主觀色彩的匏瓜和《鐘進士役鬼圖軸》中天人合一的鐘馗,羅聘兩個完全不同階段的畫作,反映其藝術修養(yǎng)的不同境界。
“焉然系而不食,吾豈匏瓜也哉”是年輕的羅聘對展現(xiàn)其繪畫才能的渴望,而跟隨金農(nóng)學詩作畫,金農(nóng)的“標新立異”與其“吾豈匏瓜也哉”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之后的創(chuàng)作思路。此外,相較于傳統(tǒng)文人畫標舉“士氣”“逸品”,講求筆墨情趣,“聊寫胸中逸氣”和自娛遣興的墨戲,揚州八怪“以賣畫為生,所有的衣食住行皆需仰仗他人,不得不選擇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這種游蕩南北、左右周旋的生活,對他們的人格畫格皆有一定影響”。[10]
羅聘身在其中自然也無法避免畫家入世的世俗性,但“美術家所要表現(xiàn)的自我不是一個與外界無涉的純封閉、純主觀的自我,而是一個受外界社會諸因素的影響和充實的飽滿的自我。”[11]這其中應包括現(xiàn)實溫飽的世俗的影響;能直面世俗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制約,將繪畫的個性化和商業(yè)化融入詩情畫意之中,羅聘并未屈于時流,失我天真;其筆墨之間更多的是擺脫宮廷保守畫派的藩籬后,不拘繩墨,敢于別創(chuàng)新格的繪畫創(chuàng)作。“美的創(chuàng)造活動,實際上就是實現(xiàn)創(chuàng)造者的審美理想的實踐過程”[12],不隨流俗、不落窠臼,強烈的創(chuàng)作激情以及一生對繪畫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透過畫中個性鮮明的生動意象展示其必然的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
[1]歐陽云編.揚州八怪繪畫藝術讀解與鑒賞[M].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3.
[2][10]楊惠東.中國名畫家全集——羅聘[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6.
[3]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中國美術史教研室編著.中國美術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84.
[4]《中國畫》編委會.中國畫(第一期)[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52.
[5]葛路.中國古代繪畫理論發(fā)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89.
[6]鄧福星.美術概論[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27.
[7][12]劉叔成,夏之放,樓昔勇等著.美學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61+327.
[8]鄭昶.中國畫學全史[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369.
[9]李潤生.多視角美術賞析——中西名作解讀教程[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154.
[11]王宏建,袁寶林.美術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