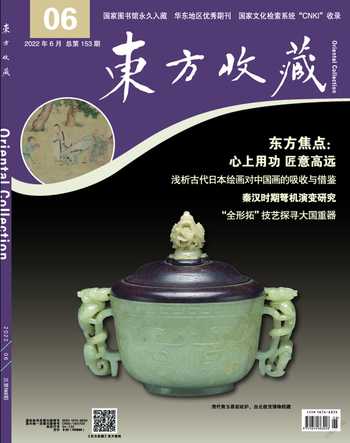遷安徐流口長城出土萬歷十二年閱視題名同建碑考證

摘要:長城,凝結了古人無可比擬的聰明智慧,是中國古代乃至世界最偉大的防御工程之一,乃華夏文明和中華精神的象征。長城的修建,始于春秋時期的燕國,終于明代。現在我們所說的萬里長城大部分是明代修建的,而遷安境內的45公里長城除了一段北齊時期的長城,其他大多屬于明長城。長城附屬的文物作為研究長城歷史的最重要佐證,逐漸被考古發掘出來。其中,石碑是最重要的研究載體,上面的文字以最為客觀的角度訴說著當時的歷史,可以說是長城歷史“活”的講述者。
關鍵詞:長城石碑;閱視題名;文化研究
古往今來,長城都是文人墨客歌詠的對象——“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霜落長城萬草枯,三邊兵甲盡防胡”“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中國的長城,于國人或者外國人來說都是一項偉大的建筑奇跡。長城主要是中原人用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防御性工事,因地勢關系,北方群山巍峨,利于長城的修建,所以河北、山西、甘肅、陜西等北方省市大多留有長城遺跡。河北省作為保存長城遺跡的重要省份,境內長城綿延2498.54公里,其中明長城1338.63公里,唐山境內綿延228.44公里,為我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文物和文字財產。
長城的修建,始于春秋時期的燕國,終于明朝。現在我們所說的萬里長城大部分是明朝修建的,而遷安境內的45.3公里長城也大多屬于明長城。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幾乎都沒有停下對長城的加固增修,在當時情況下,沒有現代化機械設備,憑借百姓的手推肩扛完成所有工程,且長城所選地點多地形險峻,崇山峻嶺、峭壁深淵,十分艱難,讓我們不禁慨嘆古人的智慧與毅力。
通過史料記載和文人墨客的睹物抒情,字里行間,仿佛看到了長城的滄桑與磅礴。隨著近現代考古學的興起與發展,它的“身世”面紗一層層被揭開,長城文物逐漸成為新的研究佐證。雷石、火銃已不足為奇,箭鏃、鐵炮比比皆是,然而比它們更有歷史研究價值的便是長城上以及長城沿線發現的銘石碑刻,上面的文字以最為客觀的角度訴說著當時的歷史,可以說是目前最具有研究價值的實物資料。
2022年3月,遷安就新發現一方閱視題名的同建碑,是修建長城工程竣工后檢查驗收時所立,用來公示工程負責人的姓名及職務,按照職位由高到低的順序排列。無論是秦朝還是明朝,長城的修筑都是一項十分浩大而繁重的工程,古代勞動人民充分發揮高超的智慧,不僅在長城的規劃設計方面契合設防的需要,“因地形,用險制塞”,而且在原材料供應、施工監管、施工流程諸多方面都極盡發明創造的智慧。可以說,利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如此重要的防御工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不可小覷。據明史相關資料記載,當時修建長城采用分區片、分段承包方式,每修完一段長城便將官員及工匠姓名、部隊番號、施工任務、長城長度、修建時間等刻碑上并嵌于墻內,此舉旨在便于日后統治者開展獎懲、追責。長城完工后,當即派兵駐守,沿線諸鎮所管轄的重要關隘、城堡,除了派遣總兵駐地,還分遣參將把守。
經過拓印研究,現將碑文內容整理如下:
甲申 孟夏 吉旦,
欽差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 兼理糧餉 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佳胤;
欽差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 兼巡撫順天等府 北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張國彥;
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 張文熙;
欽差 巡關 直隸監察御史 蘇鄼;
欽差 整飭永平等處兵備 (兼)管驛傳屯田 馬政 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 成遜;
欽差 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 地方總兵官 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 楊四畏;
欽差 協守薊鎮東路等處 地方分理練兵事物 副總兵官都指揮 楊邵勛;
欽差 分守薊鎮燕河營等處 地方副總兵署 都指揮僉事 徐從義;
撫院總督工程委官 原任游擊都指揮 李逢時;
提調 冷口關地方以都指揮 陳仲;
燕河路中軍指揮僉事 張承蔭;
官上步援千總百戶 葉珊;
把總百戶馬道成、李時芳、張學詩,同建。萬歷十二年五月望日立上(堂)工旗*張貞。
經后期調查,石碑原埋藏在徐流口段長城平臺北側的第1個敵樓中,當地人稱為小井子樓,發現時碑面保存完好,文字清晰。此碑文首時間為萬歷十二年(1584)農歷四月,吉旦一般指每月農歷初一,后來泛指吉祥的日子,文末的時間是五月望日,望日即每月的十五、十六,月圓之日,從落款時間得知是萬歷十二年分修長城而造。此碑青石制,碑正面四周陰刻卷草紋,正文陰刻楷書,皆豎行排列右起書字,通篇約300字,刻有明朝著名將領張佳胤、張國彥、張文熙、楊四畏等15名官員的官職。經研究發現,這些人名可能是明朝建造此段長城主要將領以及后期戍守長城的將領,自秦漢開始,就有將監制長官和承制工匠的名字刻在磚上的先例,為的就是有據可查,制作精良的是受功封賞的證據,粗制濫造的便是承辦處罰的證據。由此可見,遷安發現的這塊題名碑既是參加修筑監督長城官員榮譽的體現,也是當時一種獨特的質量監督手段。
這塊碑文不論從內容還是格式看都十分考究,通文小楷雋永秀麗,從右至左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官員職務和管轄范圍,凡職務內有“欽差”二字的,其書寫位置更是高于其他,這凸顯了欽差由皇帝直接任命派遣履職的重要性,更標榜了皇權至上的封建制度,為我們研究古代官職提供了實物佐證。
古代的書寫順序是從右至左,碑刻最右側所刻“欽差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 兼理糧餉 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佳胤”便是石碑所記載的最大的官員了。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簡稱薊遼總督,主管署理軍務。薊遼,舊指現在的北京,經山海關到錦州直至遼河一帶的地區。據史料《大明會典》記載,薊遼總督管轄有3個巡撫,即順天巡撫、保定巡撫、遼東巡撫。其中順天巡撫下屬又包含薊州兵備、昌平兵備、永平兵備、密云兵備、霸州兵備各一名,永平兵備分管:永平府灤州、盧龍、遷安等地兵馬、錢糧、兼屯田。太子少保,轄屬東宮,是副職,主要負責教習、保護太子,后來已是名、職分離,最終演變成榮譽職號。兵部尚書,負責統管全國軍事,屬于正二品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也是正二品。明朝時,中央設立左都御史一人、右都御史一人,任職于督察員長官,負責監察、糾劾事務,以及協助審理重大案件、考核官吏。
職務最高的張佳胤(1526—1588),為重慶銅梁縣人,由于明朝的總督和巡撫并不是常設官員,而是屬于臨時官員,本身并沒有官品,所以碑文中記載的“總督”并不是他的固定官職,兵部尚書才是張佳胤的官職,授太子太保銜。他擅長詩文,為明文壇“嘉靖后五子”之一,著有《崌崍集》。明萬歷八年(1580),修筑長城一萬六千九百四十尺(約合十余里),升為兵部右侍郎。萬歷十年(1582)春,因鎮壓浙江杭州兵變有功,受神宗傳詔嘉獎,升遷為兵部左侍郎,加封右都御史。 萬歷十一年(1583),任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薊、遼及保定軍務。此碑所載紀年為萬歷十二年,此時的張佳胤恰好管轄此地,修建長城建碑記功也順理成章了。
張國彥(1525—1598),邯鄲人,整飭薊州等處邊防事務兼管巡撫順天等府,又稱順天巡撫、薊州巡撫,管轄區域包括永平府、順天府。監管喜峰口、松棚谷、太平寨、馬蘭谷四路。監督副參等官,分管薊州、遵化、豐潤、玉田四周縣,薊州鎮朔(薊州鎮北部,設鎮朔衛),遵化營州右、東勝右、忠義中、興州前、開平中屯、興州左屯六衛,寬河一所,兵馬錢糧兼屯田(《永平府志》卷六)。巡撫主理民政,在明朝又兼任中央一級都察院的都御史一職。
張文熙,廣西桂林人。永樂元年(1403)后,一省即為一道。每年八月各省(道)分別派出監察御史出巡,考察吏治,稱為巡按御史,也稱按臺。巡按御史的品級是正七品,雖然級別不高,但實為代表天子出巡,各省、府、州、縣行政長官都被列為考核對象,小事即可現場處理,大事需奏請天子裁決,權力很大。張文熙作為監察御史,有監察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刑獄、肅整朝儀等之責,所以石碑上名字排列靠前。
蘇鄼,巡關御史為明朝官職。明朝中央政權設有監察機構即都察院,下屬分十三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在京城都察院稱內差;如若奉命外出,有時巡鹽,有時巡漕,有時巡關,皆稱外差。奉命巡視關防者,即巡關御史。然邊防事務,各有所司,故巡關監察御史之職重在監督。
成遜,《永平府志》記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任永平兵備道,進士出身,河南長垣縣人。明朝,兵備道是制于各省重要地方設整飭兵備的道員(是省以下府州以上的官,也稱道臺)。萬歷十二年(1584)初,山海關衛兵部分司主事王邦俊、永平兵備副使成遜主管建山海關東羅城。永平兵備,管轄石門寨、山海關、燕河營、臺頭營四路。負責監督副參等官員,分管永平府撫寧、昌黎、樂亭、灤州、盧龍、遷安五縣。
楊四畏(1530—1603),《永平府志》記載其為鎮守薊州總兵官,遼東人。因它能征慣戰、屢摧勁敵,歷職山海關守備、寧前游擊將軍、開原參將、薊鎮馬蘭峪參將、遼陽副總兵等。隆慶二年(1568)調任昌平鎮總兵,與戚繼光相佐,固守北疆。后戚繼光被貶,他又先后任職薊鎮、保定總兵,深得皇帝寵信,進秩中軍都督府右都督,特遷榮祿大夫,官至正一品,“為天子鎖鑰之臣”。在八達嶺長城85號敵樓發現的鼎建碑上便刻有楊四畏的名字,碑文所載年代為1571年,這說明楊四畏擔任總兵時,曾在多地督造過長城。總兵、副總兵皆為官名。明朝初年派遣將士出征開始設置總兵官、副總兵官職務,這之后軍務日漸繁冗。總兵官統領士兵鎮守一方,于是總兵官成為武官的要職,簡稱為總兵,副總兵官簡稱為副將。總兵所轄部隊(如薊鎮),副將所轄者(如建昌協),所以俗稱總兵為總鎮,副將為協鎮。
“欽差 協守薊鎮東路等處地方分理練兵事物副總兵官都指揮 楊邵勛”,楊紹勛,《永平府志》記載時任東路協守副總兵,廣寧前衛人。次建昌營,轄燕河營、臺頭營、石門寨、山海關四路。都指揮使司,正二品,其下有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僉事等輔官,掌管一省軍務、屯田、刑獄等。主管一省軍戶衛所番漢諸軍,聽命于兵部和五軍都督府。
“欽差分守薊鎮燕河營等處地方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徐從義”,徐從義,《永平府志》記載燕河營參將,綏德衛人。都指揮僉事,負責協助辦理衛所中的政事,主要負責文書工作(文牘)。參將,明朝鎮守邊區的統兵官,不固定人員,職位僅次于總兵、副總兵,分守各路。燕河營為盧龍管轄。
“撫院總督工程委官原任游擊都指揮李逢時”,撫院是巡撫的別稱,總督是起源于明朝的官職,側重于管理軍事。李逢時可能就是修建這段長城的實際督導官。游擊也是官名,是游擊將軍的簡稱,位次于參將,亦無定員,分掌駐在地的防守應援。
“提調冷口關地方以都指揮陳仲”,提調是明朝邊防關隘哨所負責管理、調度的低級軍官,也就是實際指揮修建長城的軍官。
“燕河路中軍指揮僉事張承蔭”,張承蔭為陜西榆林人,承襲其父張臣的功德,任延綏副總兵,后鎮守遼東,在后金與大明的戰役中戰歿。“燕河路”的“路”不是一般的道路的路,而是明朝的行政區劃。
“官上步援千總百戶葉珊;把總百戶馬道成、李時芳、張學詩”,千總何把總,明清時各地總兵屬下的低級軍官。百戶,掌兵武官,每戶定編112人。葉珊,浙江義烏人,據說當年戚繼光在義烏招了3000名義烏兵,修建戍守長城,葉珊就是眾多義烏兵其中之一。
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會建立相應的官員管理制度,明朝文職稱總督,武職稱總兵。從明初時,總兵作為臨時任命的一軍統帥,慢慢地變成常設鎮守地方的軍職,后來又變成地方軍區的二把手,職責為管理軍官和鎮戍地方。 據《明會典》記載:“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設官統兵鎮戍。其統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御、領班、備倭等名。”明朝洪熙(明朝第四位皇帝)年之前,總兵這個職務有臨時差遣的性質,洪熙年之后,總兵的職務系列已經形成,擁有實實在在的職務品階。明朝隆慶萬歷年間,南受倭寇騷擾,北有胡虜侵襲,邊疆危機嚴重,軍事活動頻繁,所以,此時鎮戍邊關的總兵權力很大,而且社會地位也很高,據筆者研究得知,鎮戍總兵制下設官員官職大小依次為:總兵—副總兵—參將—游擊—都司—鎮守—分守—守備—千總—把總—提調—備御等。鎮戍總兵制下,大凡五人為伍,五十人為隊,五百人為司,千人為哨,三千人為一營。一營之中又設一坐營,三千總,六把總,六十管隊。
石碑上記載的官員職務名稱清晰完備,可幫助我們窺探明朝官兵制度,碑面保存完好,是遷安長城沿線目前發現的保存最完好、紀年最早的一塊長城碑刻,它以無聲的方式真實地記載著長城的歷史,為深入挖掘研究長城文化和明朝的官階制度提供寶貴的實物資料。
參考文獻:
[1]遷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遷安縣志譯注.[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6.
[2](明)申時行著.明會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9.10.
作者簡介:
郭力菲,大學本科學歷(文物保護專業,管理學學士),研究方向:博物館陳列展覽和文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