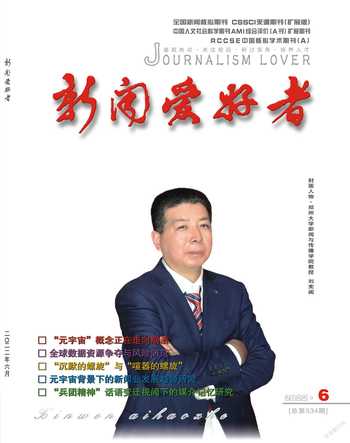全媒體語境的經典轉化與戲曲現代性建構
桓曉紅
【摘要】全媒體語境下,從不同視角切入,曲劇《魯鎮》體現出編劇對魯迅多部經典進行整合熔鑄、繼承升華從而實現創造性轉化的深厚功底,該劇具備互文本、超鏈接、時空多維化、邊敘邊釋等現代性特征,樹立了戲曲現代性的典范和標尺。
【關鍵詞】互文本;超鏈接;多維時空;邊敘邊釋
在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由國家一級編劇陳涌泉、實力導演張曼君等共同打造,由河南省曲劇藝術傳承保護中心推出的曲劇《魯鎮》于2021年12月28日晚在鄭州與觀眾見面,并進行了同步直播。該劇從編劇、導演到演員、音樂、服化道等,各環節完美配合,各角色表現出眾,場面震撼,曲調妥帖,唱腔圓潤,情節動人,熔鑄經典的同時又造就了經典的新形態新高峰。從不同角度細品該劇,它具備多重現代性特征和創新之處。
一、多部小說熔鑄升華的互文本
《魯鎮》由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風波》《藥》《明天》等多部作品融合改編而來。劇本主體是祥林嫂的悲劇故事,故事隨著祥林嫂命運的不斷轉變,主要有狂人“吃人”的警醒、“放開她”的施救嘗試、“快改了吧”的呼吁、“人肉宴又擺上了”的悲嘆和“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當面是人背后是鬼”“外表是人內心是鬼”“一會兒是人,一會兒是鬼”“人比鬼更可怕,人比狼更難防”等的靈魂對話,輔助有咸亨酒店為代表的市井百態,有魯鎮各色人等對祥林嫂的不同對待,有魯定平的施以援手,有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嘆,有孔乙己的酸腐道白和阿Q的精神勝利,更有人血饅頭所代表的愚昧麻木冷血無知和諸多看客的局外旁觀。如此種種,把《魯鎮》建構成了文本內外都充滿互文性的互文本,既重新詮釋又超越升華了魯迅付諸自己作品中的多重意味。
“互文”原本是我國文學尤其是古詩文創作中經常使用的獨特修辭手法,是語言表達方面的技巧之一,后逐漸發展出詩詞文中的用典、意象、借喻等創造作品互文性的技法和理念。隨著現代文學研究的不斷拓展和深入,以及中西文藝理論的交流,人們越來越發現任何一部作品的誕生和意義解讀,都不是在一個自主自足的文本中實現的,任何作品的創作都離不開對其他作品以及傳統文化乃至世界文學文化傳統的回憶、吸收、借鑒、引用、暗示、模擬戲仿,任何作品的解讀都需要讀者調度自身所儲備的閱讀經驗、文學文化素養、民族記憶等各種語境來實現。正如“互文性”提出者法國學者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所說:“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1]作者創作、讀者閱讀的作品,不是一個單純獨立、封閉、固定的作品,而是處在豐富復雜的相互指涉關系的作品,文學理論界稱文學作品所存在的這種屬性為“互文性”,把這種情形下的文學作品稱為“互文本”。在法國學者羅蘭·巴特眼中,寫作是言語活動在說話,是按照讀者的利益在說話,[2]“作者已死”,任何文本的意義都是在重寫、重讀的循環擴展中誕生和無限再創造[3],文本永遠處在互文性下無限開放、不斷生成意義的未完成狀態。
理論界所發現的文學的互文性,主要關注點在作品本身、作品間及作品和讀者間的自然聯系,“互文本”創作則是通過建構作品互文性從而提升作品可讀性豐厚性的創新性書寫。像當下文學領域的同人小說、接龍游戲類文學、網帖型文學、非線性類文學以及像《過把癮就死》雜糅王朔三部小說而成的影視文學等,便帶有鮮明的互文本創作的“預謀”性。而像《魯鎮》這樣融會多部經典小說而成一部優秀的戲劇新作品的互文本創作,更是鳳毛麟角。這種戲劇劇本的新編在手法上既繼承了古典文學的互文性創作,又突破了古典創作的修辭技法,將同一經典作家的多部作品熔鑄于一篇文本之中。一方面,使新作品與多部原作之間形成直接的互文指涉關系,也使新作品與《祝福》《阿Q正傳》《孔乙己》《狂人日記》等的其他影視或戲曲話劇改編作品之間形成天然的互文關系;另一方面,新作品融合多元角色、多元話語、多元文化于一身,不但使新作品自成獨立的互文性文本,還使其內部所引入、熔鑄的各作品之間形成相互詮釋注解對話象征的互文關系。而正是在這種無意與有意之間、天然與人為之間,通過編劇的二度創作基礎上的再創作,一部文本內外都充滿互文性、比每一單個原著都更豐厚更多義更具批判啟蒙和象征意味的跨文本式新作品誕生了。
二、虛擬化、省略化、空白化的超鏈接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文學藝術研究也通過吸納計算機技術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超鏈接、超文本便是從計算機技術術語發展為文藝評論范疇的典型。網頁文本的超鏈接主要指的是網頁文本中的某些文字被插入超鏈接模式,點擊這個超鏈接,網頁便會跳轉至同一網頁或不同網頁的連接目標,這個目標可以是對被設置超鏈接模式的文字的解釋或相關內容的文檔,也可以是圖片、郵件地址或應用程序等。一個網頁文本中可以根據需要設置許多超鏈接,包含許多超鏈接的文本即“超文本”,我們只需要點擊一個個超鏈接,便可以閱讀到網頁文本以外諸多與網頁文本相關的文件、圖片、郵件甚至應用程序等,有了鏈接內容的支撐,對網頁文本的解讀則會更完全、更豐富、更靈活,所以大量鏈接內容的存在帶來了與傳統文本所不同的“超文本”的誕生。
中國戲曲區別于西方的一個很突出的特色,便是虛擬性,既虛擬動作、時間、空間,更虛擬環境、事件乃至情節,甚至以省略空白作為虛擬。所謂“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萬雄兵”“頃刻間千秋事業,方丈地萬里江山”便是虛擬;一個圓場即空間轉換,一個S形臺步即穿越大街小巷,更是虛擬。《魯鎮》作為一部現代戲曲作品,它凝聚融合了魯迅多部小說作品,形成了諸多的虛擬化的、空白化的、省略化的超鏈接。劇情鋪展之中,當祥林嫂、賀老六、魯四老爺、魯四太太、魯定平等《祝福》中原有人物登臺的時候,他們客觀上分別以個體和群體的形式,甚至以整個故事的形式變成了一個個超鏈接,鏈接到了魯迅《祝福》所講述的人和事乃至那整個時空歷史中;狂人在舞臺上的一舉一動一席席話,無論與原著同或者異,皆成為一個個超鏈接,鏈接到《狂人日記》的文本乃至電影戲劇話劇中;咸亨酒店、被抽離主干故事僅為點綴的孔乙己,更是作為超級鏈接,鏈接到了《孔乙己》所描寫的種種及其影視戲劇話劇中;九斤老太、阿Q、華老栓、人血饅頭被從原作中抽離出來放到《魯鎮》中,都具有了超級鏈接的功能。只不過這種超級鏈接不像網頁那樣,真的可以打開鏈接的目標文本、圖片或視頻等,而是一種虛擬化的鏈接,這個虛擬的鏈接以空白、省略的形態為觀眾提供了一種可能,一種受此誘發隨時隨地展開網絡搜索達到實際文本或影視戲曲話劇等視頻的可能,并借助這種可能增進對《魯鎮》劇情的實際解讀、共鳴和思考。中國藝術包括戲曲追求虛擬,追求留白、省略以及以虛生實、虛實相生,《魯鎮》的這種虛擬化、省略化、空白化的超鏈接所引導實現的正是一種別樣的以虛生實、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應。而通過這種超鏈接,《魯鎮》成功實現了對經典的創造性轉化,打造出了經典基礎上的新經典。
三、融會貫通、立體交互、虛實相生的多維時空
《魯鎮》是以《祝福》為主、兼容多部小說而成的新作,新作雖以魯鎮為故事主要發生地,但實際上在互文本、超鏈接下,劇目所建構的時空卻呈現出多維化的特征。這種多維性既體現于舞臺之內,也體現在由舞臺之內所興發的舞臺之外的時空場域,還體現在由直播所形成的現場時空和視屏時空的共在,體現在以上諸多時空融合升華而成的戲曲時空,更體現在以上諸種時空的立體并存。
劇目一開始,各個房門一打開,便向觀眾呈現了一個既相對獨立又互為一體的隱喻時空。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單四嫂子、N先生、華老栓、趙太爺、魯四老爺、魯四太太……說的說,唱的唱,不同故事時空中的人物齊聚于《魯鎮》之中,同時又被一扇扇打開的相對獨立的門所隔開,帶給觀眾一種他們從不同時空穿越于“魯鎮”(魯迅筆下為虛擬)這一共同時空的感覺。伴隨著不同角色的出場,觀眾看到了不同角色所代表的清末的魯鎮、秋瑾犧牲時的魯鎮、辛亥革命前的魯鎮、辛亥革命前后變化著的魯鎮、辛亥革命后的魯鎮,這些構成了一個歷時性的“魯鎮”動態時空;看到阿Q,觀眾會虛擬化地看到阿Q從常住的江南未莊土谷祠穿越或游蕩到了魯鎮,看到N先生,觀眾虛擬化地看到N先生從張勛復辟背景下的江南水鄉穿越或跋涉到了魯鎮,這又構成了橫向的具有共時性特征的“魯鎮”時空……縱橫交錯、歷時共時立體并存的時空特征成為《魯鎮》經典化的重要支撐。看得見的舞臺時空為實,看不見的想象時空為虛,戲曲舞臺的多維時空便有了實和虛的立體交融、虛實相生的美學效應。加上直播手段的采用,使戲曲的舞臺在現場之外增添了媒介傳遞的終端,使戲曲的接受場域呈現出直觀的現場互動與虛擬的視屏互動共在的情形,兩種不同的時空類型共在于一臺戲曲藝術的欣賞過程之中,帶來戲曲藝術互動時空的多維性。
在虛實相生的演繹過程中,《魯鎮》以《祝福》為故事主體,以狂人為主要象征和注解,以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街坊鄰居看客等為輔助,完成了故事的完整講述和意義表達與建構。《祝福》與狂人故事的融合妥帖無縫,伴隨著祥林嫂命運的重要轉折,狂人都適時參與其中,他的瘋言瘋語、阻攔、呼吁、批判、堅持雖看似無用卻發揮了預言、注腳、救贖、暗示一樣的重要作用,推動著故事的發展,體現出編劇重構故事的超強駕馭能力。除了狂人,《祝福》以外其他原著中的人物在《魯鎮》中很少有故事內容的展開和對故事情節發展的推動,他們在故事中更多以符號化的狀態存在,而正是這種符號化的角色存在,才打造出這些角色的象征性和所代表的時空的獨立性、立體性,以及“吃人”的更廣泛的隱喻性,才和《祝福》與狂人故事形成虛實相生的演繹效應,大大擴展了《魯鎮》故事的敘述時空。
總之,這種既并存又立體交互融為一體的多維時空,打造出了故事的典型性,完美實現了祥林嫂主體故事的重建和多元升華,也讓祥林嫂故事成為劇目所關涉的所有文本的延伸、增殖和價值實現的基礎。
四、邊敘邊釋、新意義隨時生成的敘事格局與手法
傳統故事講述夾敘夾議皆來自故事中的一個敘述者或者講書人,后現代先鋒派小說的元敘事是作者或敘述者在故事講述中站出來發表見解,進而揭露故事的虛構性。劇中符號化存在的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N先生等這些《祝福》故事之外的角色,既是祥林嫂故事的直接參與者、見證者,又象征化地成為故事評判者、故事意義的詮釋者;既直接揭示了故事所表達的觀點傾向,又掩蓋了講述者的敘述動作,掩蓋了故事的虛構性,呈現出邊演繹邊不斷完成新故事、不斷且隨時誕生新的故事意義的講述模式,使故事具有無限的開放性、自生性,跌宕起伏、錯落有致、饒有興味,由此也實現了對原有故事的解構和解構基礎上的再建構。比如《祝福》中的“我”,既是故事講述者,也是故事中人,他與魯鎮、與祥林嫂命運的關系是離開—歸去—離開,最終刻畫出有進步思想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傳統封建社會的不相容,“我”即使是批判者,也無法真正改變現狀。但在改編中,魯定平卻是經歷了帶著長辮子走出去、帶著長辮子回歸、又帶著長辮子走出去、最終卻以剪掉長辮子留著齊耳發仍不夠徹底的革命犧牲者身份回歸,把革命者的生命獻祭于魯鎮這片熱土,并發出了具有號召性的、革命性的、充滿希望的堅定的呼吁。最特別的是編劇加入了狂人,他說著“你們快改了吧,真心改。你們要不改,你們終究也會被吃盡的”。“你們快改了吧,要知道將來的社會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也會吃人”“快看啊,人肉宴席又擺上了”“不要害怕鬼,鬼不是最可怕的”“鬼的模樣好認,小心尚可以防;可人……讓你防不勝防!”“人憑嘴就能把你碎尸萬段,軟刀子殺人血不沾……一旦你被擺上人肉宴,吃了你骨頭不剩一點點”。“記住:人比鬼更可怕,人比狼更難防!”每一句出現得都是那么準確到位,一句句準確到位的呼喊使狂人一步步成為整個故事的參與者、推動者、見證者、評判者、批判者、堅定的啟蒙者。作為一個別人眼中的瘋子,狂人是和魯鎮共存、見證祥林嫂等被吃命運的人,與祥林嫂這個半瘋子形成了戲劇化的同形不同質的對比關系,祥林嫂是因被吃而致瘋,狂人是吃人者階層中的清醒者、改變者、批判者、呼喊者、啟蒙者,是因為另類而被同階層的吃人者視為瘋子。兩個瘋子,最后一個真的被吃掉死于紛紛大雪之中,一個覺醒而堅持啟蒙的吃人者又見證了一次吃人的場面,并繼續發出他一貫的呼喊。象征了魯鎮從狂人批判者、啟蒙者到資產階級不徹底的革命者的歷史演變,預示著在堅持不斷的啟蒙革命中徹底的革命者的必將誕生,隱喻著魯鎮在演變中誕生的徹底革命者必將帶來光明的前途和方向。
在全媒體語境下,《魯鎮》以其鮮明的現代性特征,成功地為我們營造了一個集互文域、超鏈接域、隱喻象征域、意義無限生成的多維時空場域等為一體的多元載體,為現代戲曲成功樹立了傳統繼承、經典轉化、創新發展的典范和標尺,切實踐行了以文化人、立德樹人、培根鑄魂的初心使命。
參考文獻:
[1]朱莉亞·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論對結構主義的繼承與突破[J].黃蓓,譯.當代修辭學,2013(5).
[2]羅蘭·巴特.S/Z[M].屠友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8.
[3]羅蘭·巴特.作者的死亡[C]//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294.
(作者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研究員)
編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