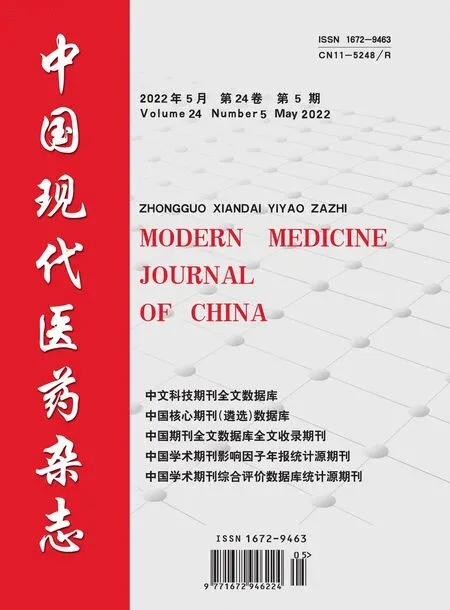兒童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后合并膜性腎病1例并文獻復習
陳翠姹 王文紅 劉喆
患兒,女,14歲,主因“發現白細胞增高20余天”于2019年5月30日就診于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醫院,確診為慢性粒單核細胞白血病(FAT1突變、PRDM1突變、CREBBP突變、DIS3突變),患兒與其胞兄HLA配型10/10相合,完善移植前相關準備,2019年8月27日開始移植預處理,2019年9月5日順利回輸其兄外周血干細胞,隨后相繼植入細胞成分,病情穩定,順利出倉,后續定期予地西他濱化療6個療程,并予環孢素、阿昔洛韋、伏立康唑、磺胺等治療,過程順利。患兒停用環孢素口服、地西他濱化療(2020年8月)后4周出現雙下肢浮腫、低白蛋白血癥、大量蛋白尿,考慮腎病綜合征,無皮疹、脫發、口腔潰瘍、惡心、嘔吐、關節痛等表現,就診于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醫院,復查骨穿,評估骨髓為完全緩解狀態,加用甲潑尼龍24mg bid治療3周未緩解,監測尿蛋白仍提示大量蛋白尿,為進一步完善腎臟穿刺活檢,于2020年10月27日就診于我院。既往史及家族史:否認既往腎臟疾病、風濕免疫疾病、肝炎病史及相關家族史。入院查體:BP 120/85mmHg,P 84次/min,R 20次/min,T 36.5℃,全身皮膚無皮疹、出血點,雙下肢輕度指凹性浮腫,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口腔粘膜光滑,心臟、肺部、腹部及神經系統查體未見異常,正常女性外陰,尿道口無充血,未見分泌物。
輔助檢查:血常規正常。尿常規:尿蛋白定性+++,24h尿蛋白定量6.72g;血白蛋白18.7g/L,總膽固醇13.97mmol/L;血清IgG 0.21g/L,補體C3 0.89g/L,IgA、IgM、C4正常;肝炎全項、HIV、TP均陰性;EBV、CMV、HBV、HCV-DNA均陰性;CMV、EBV-IgM陰性;ANA+ENA、ANCA陰性;風濕三項陰性;腹部超聲肝、脾、腎未見異常;心臟超聲未見異常。2020年11月3日行經皮腎穿刺活檢術及光鏡、免疫熒光、電鏡檢查(見圖1)。光鏡:送檢腎穿刺組織,可見50個腎小球,腎小球系膜細胞和基質輕度彌漫增生,腎小管上皮空泡顆粒變性,腎間質小動脈未見明顯改變,結合免疫熒光考慮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相關膜性腎病(Ⅰ期),待電鏡進一步檢查;免疫熒光:可見3個腎小球,IgG(++)、IgA(+~++),毛細血管襻顆粒狀沉積,IgM(-)、C3(-)、C1q(-)、Fn(-);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電鏡:腎小球系膜細胞和基質輕度節段增生,上皮下及系膜區電子致密物沉積,上皮足突廣泛融合,腎小管上皮細胞空泡變性伴溶酶體增多,腎間質無明顯病變,診斷:符合不典型膜性腎病(MN),繼發性腎小球腎炎可能性大。

圖1 經皮腎穿刺活檢鏡下表現
治療及隨訪情況:完善腎臟病理檢查后,加用嗎替麥考酚酯(塞可平)聯合甲潑尼龍(尤金)口服,并輔以對癥治療,尿蛋白明顯減少,2020年12月18日復查24h尿蛋白降至1.88g,2020年12月31日合并呼吸道感染,監測24h尿蛋白總量(3.76g)較前升高,予對癥控制感染后監測尿蛋白逐漸下降,2021年7月10日監測24h尿蛋白降至0.27g,甲潑尼龍減量至8mg qd,嗎替麥考酚酯0.5g bid,患兒一般情況可,仍在繼續隨訪中。
討論 造血干細胞移植后合并腎病綜合征比較罕見,檢索國內外相關文獻,多以病例報告和小型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形式報道,目前國內外共報道180余例,大多數為成人,且為多系統受損,本例為兒童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后合并腎病綜合征(NS),僅表現為腎臟受累,無其他系統受累。
HSCT后合并腎損傷表現為急性腎損傷(AKI)和慢性腎臟病(CKD),大多數HSCT后AKI發生于HSCT后10~21d,HSCT后AKI定義為腎小球濾過率(GFR)下降至少50%和(或)血清肌酐水平升高超過1倍,HSCT后AKI最常見的原因是急性腎小管壞死、鈣調磷酸酶抑制劑等藥物毒性和肝竇阻塞綜合征(SOS),該患兒移植過程較順利,無HSCT后AKI。HSCT后CKD發生率變化很大,在HSCT至少6個月后發生率為0~60%,常見的病因為血栓性微血管病、鈣調磷酸酶抑制劑、NS。HSCT后NS多發生在HSCT后8~14個月,表現為突然起病,發展迅速,常伴有cGVHD廣泛性多系統、多部位受損,如皮疹、肝損害、腹痛、腹瀉等。cGVHD為HSCT后期的常見并發癥,傳統上以移植后100d為臨界值,分為急性和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由于認識到急性和慢性GVHD的跡象可能會在這些指定時期之外發生,目前更多使用臨床表現,而不是使用固定的時間段來區分[1]。HSCT后NS與免疫抑制劑減量或停止有關,其發生距開始減量或停止使用免疫抑制劑的時間通常為1~5個月,該患兒為移植后12個月、停用免疫抑制劑1月余合并NS。一項研究中約47%的患者可以觀察到NS與cGVHD同時出現,提示NS與cGVHD相關,NS可能是HSCT患者cGVHD的唯一表現[2],本例患兒僅表現NS而無其他cGVHD癥狀,支持NS可能是HSCT患者cGVHD的唯一表現。然而,Hu等[3]研究質疑GVHD與HSCT后NS之間的關聯。
移植后合并NS發病率為0.3%~6.1%[4],導致其發生的高危因素與HLA配型、干細胞來源、預處理方案、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腎臟以外臟器cGVHD、免疫抑制劑的使用狀態及CMV感染狀態等有關,不同移植方式發病率差異較大,非清髓高于清髓,外周血干細胞移植高于骨髓干細胞移植。英國Srinivasan等[5]觀察到,在163例連續接受非清髓性HSCT手術的患者隊列中,NS發生率較高,累計發生率為6.1%。日本報道過2 136例患者接受骨髓移植后共有8例發生NS,發生率為0.3%[6]。有研究回顧性統計了1988~2015年報道的116例患者HSCT后NS,其中77.8%為外周血移植物來源,20%為骨髓來源[4],本例患兒為外周血造血干細胞移植。國內陳瑤等[7]分析1996~2009年1 405例患者行HSCT后8例合并NS,發病率為0.6%,比較了干細胞來源,即單純骨髓、外周血以及骨髓聯合外周血干細胞各自的移植模式,未顯示干細胞來源與NS發生有關。譚亞敏[8]統計了2007~2018年1 130例行HSCT患者中10例發生NS,發病率為0.885%,移植后NS的發生與HLA配型、供受者關系、GVHD、移植前血清甘油三酯及膽固醇水平、移植后半年甘油三酯水平、移植后1年膽固醇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HSCT后NS最常見的腎臟病理類型為MN,其次為微小病變性腎病(MCD),其他少見病理類型為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癥(FSGS)、膜增生性腎炎(MPGN)、IgA腎病(IgAN)。可能發病機制為移植物中對腎小球抗原有反應性的同種反應性供者淋巴細胞導致了免疫失調。Beyar等[4]報道116例HSCT后NS腎臟病理類型,MN 76例(65.5%)、MCD 22例(19%)、FSGS 9例(7.7%)、MPGN 6例(5.2%)和IgAN 3例(2.6%)。Saddadi等[9]報道前瞻性研究HSCT后合并NS 14例,隨訪10年,其中10例(71%)活檢顯示MN,其余4例為FSGS、MPGN、MCD。本例患兒腎臟病理光鏡及免疫熒光考慮cGVHD相關膜性腎病(Ⅰ期),電鏡提示不典型膜性腎病,符合移植后NS常見的病理類型。
目前尚無統一的治療方案,文獻報道多采用糖皮質激素聯合免疫抑制劑治療,部分難治性病例應用利妥昔單抗,Beyar等[4]統計116例HSCT后NS的治療情況,大多數患者病程相對良性,對免疫抑制劑反應良好,90.3%的患者使用糖皮質激素,61例(54%)聯合應用鈣調磷酸酶抑制劑,63.5%的NS患者達到CR,13例應用利妥昔單抗,其中7例達到CR,5例PR,1例無效。羅曉丹等[10]報道5例HSCT后NS,應用激素聯合環磷酰胺治療,隨訪2年,1例CR,4例PR。
HSCT后合并NS相對少見,一般發生在移植后8~14個月,大多數為成人,兒童罕見,常伴有cGVHD多系統受損,可僅表現為腎臟受累,多發生在免疫抑制劑減量或停用時。治療上多采用激素聯合免疫抑制劑,對免疫抑制劑反應良好,目前相關研究報道尚少,需進一步提高對該病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