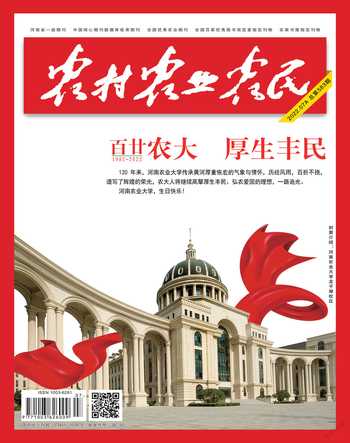“粟”說歷史 “粟”然起敬
趙曉嬌



在中國農業博物館的藏品庫房里收藏著這樣一件文物,它看起來是一個普通的新石器時代繩紋灰陶罐,但里面盛放的東西可大有來頭——它們是出土于我國內蒙古敖漢地區距今8000年前的碳化小米顆粒標本。這些8000年前的碳化粟標本,為何要收藏在博物館里,我們還要從粟的誕生說起。
“粟”是古人對谷子的書面泛稱,谷子屬禾本科一年生植物,廣泛種植于我國北方,去殼后俗稱小米,由狗尾草人工馴化而來。狗尾草也叫莠,它的植株形態和谷子十分類似,幼苗很難區分,所以就有了“良莠不分”的說法。粟在古代位于五谷之首。五谷指稷、黍、麥、稻、菽,其中“稷”就是古人對谷子的另一種叫法。稷為百谷之長,本義為稷谷,因此帝王奉稷為“谷神”。在古代,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語,社稷就是國家民生,所以“江山社稷”逐漸演變成國家的代名詞,由此也看出粟在中國古代的地位。在小麥和水稻被培育之前,小米肩負著養育華夏兒女的神圣使命,被譽為“中華民族的哺育作物”。《黃帝內經》記載“五谷為養”,同是種子,數量越多則能量越大,滋補力就越強。小米不需精制,保存了維生素、礦物質和胡蘿卜素,含有不飽和脂肪酸,熬成粥素有“代參湯”的美譽,不僅調養脾胃、滋陰補血,還能助眠安神、緩解壓力和緊張情緒。《本草綱目》記載,小米“治反胃熱痢,煮粥食,益丹田,補虛損,開腸胃”。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胃為太倉,水谷氣血之海。脾胃不和百病生,脾胃功能的強弱,直接影響到人體生命的盛衰,可見小米的養生作用顯著。
粟哺育了中華民族,滋養了華夏文明,也使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綿延數千載而依然燦爛輝煌。金黃色的小米滋養了磁山文化、興隆洼文化、仰韶文化、紅山文化等,溫潤的小米粥是喂養中國北方古文化源源不斷的乳汁。夏朝和商朝因廣泛種植粟又被稱為粟文化王朝。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關于谷子的記載,當時的谷子泛稱“禾”。在兩千多年前的著名農書《氾勝之書》里,谷子被列為五谷之首;公元6世紀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里,谷子仍然排在五谷之首。明代以后,由于小麥種植面積的擴大及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種植才相對減少。但是,谷子在我國北方地區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現有證據已經證明“粟”是在中國最早被馴化的。1976年,考古人員在太行山東麓、南洺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中發現了數量眾多的石鏟、石鐮、石墨盤、石墨棒等遠古生產工具。通過碳14的測定,確定其年代為距今7400年左右,其時處于新石器時代早期。在隨后的發掘中,陸續出土的糧窖震驚了世界。在遺址范圍內,共發現窖穴548個,其中有8個糧食窖穴里面還有糧食遺存物,多以粟和黍為主,當然它們都早已碳化成粉末。生活在內蒙古敖漢的遠古先民,春播、秋收,率先沐浴在文明的旭日下,早在近萬年以前,先民們就已經開始了粟的種植。考古學界泰斗蘇秉琦先生曾說:“敖漢,是中華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2002年,植物考古學家在敖漢旗興隆溝新石器時代早期村落遺址發現了1000多粒粟和黍的碳化標本,經鑒定,是世界范圍內最早的谷子和糜子,距今8000年左右。2012年8月,敖漢旗的旱作農業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2014年至2021年,敖漢旗連續召開八屆“世界小米起源與發展會議”,會議達成共識——敖漢旗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小米起源地。近年來的考古研究以及各類實驗證明,無論是東亞還是歐洲,當地的小米都來自中國北方這個起源地。因此,小米是人工栽培形態最早的谷物,更是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的實證,它為游牧民族轉化為農耕民族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只有青山干死竹,未見地上旱死粟”,說明小米的抗旱能力超群。現實中的小米源遠流長,更滋養了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在武裝革命斗爭時期,小米作為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糧食,成為黨領導全國軍民取得戰爭勝利、建立人民政權的重要物質基礎,堪稱“紅色作物”。黨中央在陜北革命根據地的13年中,陜北小米滋養了我黨無數革命戰士,戰士們又用生命換來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毛澤東在1946年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指出:“我們依靠的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后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1947年3月,毛主席率中共中央機關轉戰陜北時深情地說:“長征后,我黨像小孩子生了一場大病一樣,是陜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養我們恢復了元氣。”轉戰途中,警衛員弄來一點小米,蒸了一碗小米干飯給毛主席送去。在那種特殊情況下,主席要與同志們同甘共苦,哪怕是一碗小米干飯,他也不肯接受。1973年6月,周恩來總理來到延安,午餐時,他端起小米湯喝了一口感嘆道:“真香啊!”隨后他滿懷深情地說:“延安的小米好啊,是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們,哺育了革命。”當延安人民為了表達心意,送給他一點小米和豆子時,他按價如數付了錢和糧票。延安的人民群眾都激動地說:咱總理還是“老延安”!小米不僅好吃,其革命故事更是讓人深受感動。我們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的優良作風,永葆艱苦奮斗本色。
不僅如此,人們耳熟能詳的“小米加步槍”一詞在當時承載的更是一種我黨在艱苦條件下,憑借人民群眾的支持,率領軍民自力更生、為中華民族解放和自由頑強戰斗的革命精神。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會議上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時說:“你們吃飽了面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愿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么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1947年,賀龍同志轉述晉綏軍區建軍會議總結報告再次說道:“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依靠群眾來建黨、建政、建軍,來戰勝一切敵人。沒有階級性、群眾性的單純建設軍隊,是不行的。毛主席說,我們的力量就是小米加步槍,如果看不見小米,即群眾力量,這支步槍,一定不會有任何作用。”
“小米加步槍”蘊含著毛主席對我黨獲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勝利兩個必要因素高度概括且通俗的語言藝術,即小米代表的經濟手段和步槍代表的軍事手段在革命事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其中,小米代表的經濟手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小米與屯墾戍邊。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在1936年后,新四軍、八路軍等部主要駐扎在陜甘寧邊區。從農業發展水平和軍事地理格局來說,北方農田尤其是山地的灌溉條件較差且沒有足夠肥料,不足以產出大量糧食滿足軍隊需求,于是屯墾制再次興起。小米作為當地最耐旱的一種主糧,春種秋收,得天地之氣最全,得土地之氣最厚,成為我黨軍隊最可靠的糧食來源,屯墾生產的重點也圍繞它進行。二是小米與“糧本位”政策。小米營養豐富、外殼堅硬、貯藏長久,晾干后的體積和重量之間比例相對穩定,自古就是“戰備糧”的首選。1941年,為擺脫太行根據地的經濟困境、改善軍工人員生活,我軍后勤部將以貨幣為單位計算工資改為以實物為單位計算工資,并為此發明了專有名詞——饻,寓意將衣食結合在一起,說明了我黨始終將老百姓最實際的問題——衣、食放在心上。正是有了這種新交易模式的出現,我黨才能在那段最困難的時期生存下來。抗日戰爭的政治經濟條件也促使我黨從抗戰中期開始,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始終堅持將小米作為唯一的“通貨”。隨著戰爭不斷獲得勝利,我黨長期依賴小米建立的“糧本位”財政體系也繼續推向大城市。1947年后,解放軍攻占中等城市和周圍的平原地區,控制大片麥田和玉米地,但“小米本位”依然維持較長時間。后來,因工資制在全國施行,以實物為基礎的小米本位制才在歷史上徹底消失。
小米是中華民族起源和發展的主要種植作物,更是營養價值高、環保價值高的雙高作物,重要指標皆優于大米、玉米、小麥等主糧;因其抗旱耐瘠、水資源利用程度高、適應性廣等特性,面對日益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形勢,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高度上,小米將為中國農業發展繼續作出獨特貢獻。近年來,小米借力養生潮的東風,從粗糧升級為營養品,成為我國主糧里單價較高的品種。據統計,我國現在大約種植各類谷子2100萬畝,其中大部分在山東、山西、河北、內蒙古,畝產量300~1000斤不等,總產量約500萬噸,同比2000年種植面積稍小,但產量大幅度提高,主要是通過節水灌溉和雜交谷子創新取得畝產量提高。
由古至今,地位跌宕起伏的小米其實是中國社會變遷和國民生活水平發展的實物見證。小米留給后人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智慧更加激勵我們走好新時代的農業發展奮斗路,用實際行動為黨的二十大獻禮。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