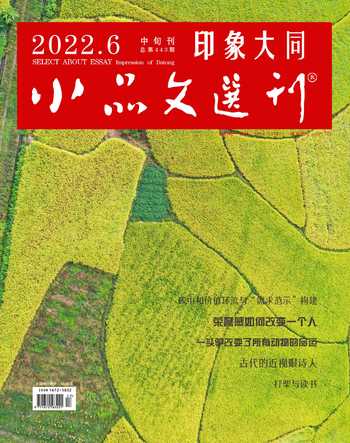一頭驢改變了所有動物的命運
馬利洪

當受害者——一頭驢被帶到法庭時,人們倒吸了一口涼氣。有些人笑了,法庭辦事員們興奮地竊竊私語。被告比爾·伯恩斯對驢子嗤之以鼻,但受害者的傷勢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當時的繪畫所顯示的那樣,驢子的腹部血肉模糊,可以看到一條條的肋骨;驢子頭部的鬃毛上沾滿了鮮血;背部布滿了長長的傷口。看到這樣一頭傷痕累累的驢子,陪審員都震驚了,但是起訴律師理查德·馬丁波瀾不驚,他手握韁繩,心里明了伯恩斯的殘忍已經得到了證明,從此之后動物權利的歷史將永遠改變。
動物在不列顛群島的生活從來都不是很好。盡管很久以來英國人就認識到畜牧業很重要,但是從事農業很辛苦等原因助長了一種殘酷對待牲畜的文化。到16世紀后期,倫敦隨處可見各種虐待動物的行為。屠宰和毆打動物司空見慣,城市周圍還有許多“景點”,好奇的游客可以在這里看到從扔公雞(參賽者朝拴在柱子上的公雞扔一種叫“公雞棒”的特制加重棍子。如果沒有“公雞棒”,其他棍棒也可以拿來使用。觀眾可下注。如果參賽者把公雞砸暈,只要他能在公雞醒來之前將其抓住,就能把公雞帶回家)、斗狗到斗猴子等一切殘忍的娛樂活動。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人都樂在其中。據說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非常喜歡斗狗,她為此飼養了多條獒犬。她的繼任者詹姆斯一世則在倫敦周圍建立或擴大了許多熊坑(把熊綁在鐵樁上限制它們的活動,然后將一群狗放出來抓咬熊,直到熊受傷倒下)。很多人意識到這些娛樂活動對動物很殘忍,17世紀的英國作家和政治家塞繆爾·佩皮斯將前往泰晤士河畔的“熊園”(有各種耍把戲的熊或熊相斗的表演)描述為“粗魯和令人討厭的樂趣”。
當然,并不是每個人都虐待動物。早在古代,就有人為動物發聲。雖然亞里士多德認為動物沒有思想、理性和信仰,從而將它們視為次等的生命形式,但是同樣具有深遠影響力的畢達哥拉斯則認為人們死后靈魂會“遷移”到動物身上,因此要求人們同情動物。希臘植物學家提奧夫拉斯圖斯則認為人們最好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不要剝奪其他生物的生命。
事實證明,《圣經》中有關動物的記述是最有影響力的。在創世故事中,亞當和夏娃被賦予了管理地球上所有野獸的權力,然而,正如創世故事所表明的那樣,動物仍然是上帝的創造物。對于不列顛群島的許多人來說,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對于那些福音派或清教徒來說,這表明,雖然人類可以隨意殺戮和食用任何他喜歡的動物,但他仍然必須充當大自然的管家,善待動物。也就是說,虐待動物意味著道德的墮落。
16世紀中葉,英國辯論家羅伯特·克勞利寫了一首詩,哀嘆養“一只獒犬和一只丑陋的熊”,只是為了看它們打架,這是非常愚蠢的。盡管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喜歡看斗熊,但還是禁止在星期天舉行這種“娛樂活動”,理由是這不符合安息日的神圣性。1635年,愛爾蘭議會禁止對動物“殘忍”,因為這是一種惡習。英格蘭共和國護國主奧利弗·克倫威爾也采取了同樣堅定的立場,禁止斗雞和斗熊。
到18世紀早期,歐洲一些哲學家認為保護動物免受傷害是為了動物自己,而不是出于任何先驗的原因。笛卡爾等機械宇宙論者認為,“無理性”的動物是沒有靈魂的機器,但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則認為,既然是動物肯定會感到痛苦,僅憑這個原因,它們就不應該受到傷害。
對于大多數動物權利倡導者來說,哲學理論沒有什么意義。到1754年,前文提到的理查德·馬丁出生時,當時的社會已經將殘忍對待動物視為一種惡習。畫家威廉·霍加斯的著名系列版畫《殘忍的四個階段》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在這一系列畫作中,霍加斯將虐待動物視為通往更嚴重罪行的第一步。在第一幅畫中,當時還是個孩子的湯姆·尼祿殘忍地虐待一只狗;在第二幅畫中,尼祿是一個身材魁梧的年輕車夫,他把自己的那匹老馬打得眼睛都睜不開;在第三幅畫中,尼祿從傷害動物上升到謀殺了懷孕的情人;在第四幅畫中,尼祿因為他的罪行被絞死,尸體被放在解剖臺上,外科醫生在進行解剖。
到了18世紀,不列顛群島進入了工業革命的時代。紡織業實現了機械化,大片土地被圈起來養羊,農村土地的租金上漲;鐵路在延長,運河也在延長;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集中在城市中,城市的生活條件往往極其惡劣。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一個新的富有的資產階級開始出現,他們的品味和理念與地主貴族不同。
這些都對動物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雖然不同社會階層的娛樂活動一直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到了18世紀變得更加明顯了。狩獵逐漸成為鄉紳貴族的活動,而傳統的“血腥娛樂”,如斗雞和斗牛,則成為城市工人階級的選擇。與此同時,城市中的寵物迅速增長,哈巴狗尤其受中產階級的歡迎,另外倫敦的眾多工匠和店主家中養著很多不同尋常的寵物。根據一項1730年至1750年的調查,藥劑師布拉德伯里先生有一只貓鼬,而助產士凱農夫人有一只環尾狐猴和狨猴。
社會的變遷深深影響了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上層和中產階級遠離了熊坑,去往松雞獵場,或者回到起居室的寵物身旁,因此對動物更加同情的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此期間涌現出了大量捍衛動物權利的著作,呼吁對待動物更加“人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漢弗萊·普里馬特的《慈善的職責和殘酷對待動物的罪行》(1776年),他的論點基本概括了后來幾個世紀的動物保護運動的主要思想,直到今天還在被重復。另外,托馬斯·楊的《動物性隨筆》(1798年)也影響深遠。
于是,保護動物的呼吁變成了對動物權利立法的運動。與此同時保護動物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盡管虐待動物的情形存在于社會的各個階層,但不同的社會群體喜歡不同的消遣,這一事實也將動物保護,這一主要涉及道德層面的運動披上了階級斗爭的外衣。動物保護的倡導者——除了極少數例外,往往來自富裕的基督教中產階級家庭——往往無視自己階級的偏好,將虐待動物視為窮人道德敗壞的案例,類似于酗酒和賣淫一樣。結果,消除虐待動物的行動就成了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那就是提高窮人的道德水平。
在英國議會通過禁止虐待動物的立法阻力很大。仍有許多政治家和地主認為動物只是財產,阻止一個人把自己的馬打死,就是最壞的雅各賓主義。因此,在1800年4月18日,當蘇格蘭議員威廉·約翰斯通·普爾特尼提出禁止“狗逗牛戲”時,引起了激烈的反對。該法案僅以兩票之差被否決,還被未來的外交大臣喬治·坎寧稱為提交給下議院的“最荒謬的法案”。坎寧甚至暗示:既然“狗逗牛戲”給觀眾帶來了“消遣,令人興致勃勃”,那么,禁止這項活動實際上會削弱國民的活力。
1809年,前大法官厄斯金勛爵進行了第二次立法嘗試,這次是在上議院。厄斯金是一位動物愛好者,他最珍視的伙伴是一只鸚鵡、一只狗和一對漂亮的水蛭。他很現實,不想引起激烈的反應,于是他專注于禁止虐待具有明確農業用途的動物,而不是所有動物。為了讓議員們放心,他的法案還包括一項規定:只有傷害動物的人才會受到起訴—這意味著動物的主人和肇事者可能的雇主是安全的。厄斯金的法案在上議院獲得通過,但在下議院卻遭到了冷遇。下議院的議員溫德姆意識到,這會為更廣泛的動物權利立法鋪平道路,所以就用厄斯金自己的邏輯來反對該法案。他說,該法案會重罰那些在路上鞭打驢的農民,而對在莊園里毆打馬匹的貴族卻放任不管,因此,這項法案實際上是一項“騷擾和壓迫某些下層階級的法案”。大多數議員同意溫德姆的意見。
接下來就輪到理查德·馬丁接棒了。馬丁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徒家庭,但他在新教徒家庭中成長,成了一名新教徒,后來從政并過上了豐富多彩的生活。他在上流社會很受歡迎,是一位熱情的劇院觀眾、才華橫溢的演說家,但他也是窮人、天主教徒和動物權利的堅定捍衛者。因為他極有同情心,他的好友英王喬治四世甚至稱他為“仁慈的狄克”。1821年,理查德·馬丁試圖通過一項禁止虐待牲畜的法案,但以失敗告終。他沒有退縮,在第二年再次嘗試。這一次,他提出禁止任何人“肆意毆打、虐待”農場動物,例如馬、牛、羊和驢。他指出,由于動物會感到疼痛,因此它們有權不受傷害。他受到了慣常的嘲笑。正如《泰晤士報》報道的那樣,在下議院他講了一只猴子與一只狗搏斗的故事,讓國會議員們哈哈大笑。但是,這就是他的魅力和機智,他的法案在下議院得以通過。
馬丁知道,真正的挑戰是執法。他的法案規定傷害某些動物是非法的,也規定私人可以向地方法官指控某人虐待動物。于是,他立即對倫敦一位名叫比爾·伯恩斯的叫賣小販提起了訴訟,因為他抓到伯恩斯在毆打他的驢。馬丁決定將驢子帶上法庭,這頭驢子的傷勢太嚴重了,地方法官別無選擇,只能認定伯恩斯有罪。
這是第一次有人因侵犯動物的權利而被定罪。從此之后動物不再僅僅是某人的財產,至少一些動物受到了法律的保護,有了越來越多的人來保護它們。不到兩年,馬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致力于禁止那些“殘忍對待動物的做法”。如今,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動物福利組織之一。
選自《世界博覽》
- 小品文選刊·印象大同的其它文章
- 唱給西湖的歌
- 最是花影難掃
- 時光不老,青春正好
- 梅渡
- 一位英使眼中的大運河
- 向內“卷”,還是向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