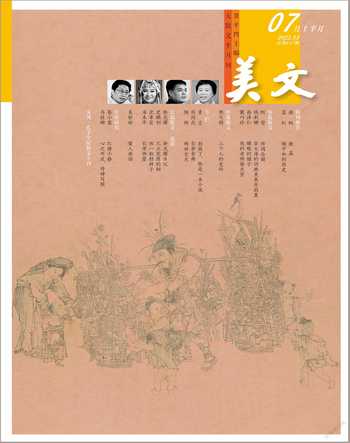心之所及,傳神寫(xiě)照
馬佳娜
因愛(ài)讀《紅樓夢(mèng)》,也喜歡張愛(ài)玲的文字,對(duì)《紅樓夢(mèng)魘》也便興味甚濃。此書(shū)記有張愛(ài)玲所言之人生“三大恨事”:一恨鰣魚(yú)多刺;二恨海棠無(wú)香;三恨《紅樓夢(mèng)》未完。《紅樓夢(mèng)》之“未完”,想必也是天下愛(ài)《紅樓夢(mèng)》者共同之“恨”。前輩今人,于此皆做過(guò)細(xì)致的考辨索隱工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曹雪芹所作還是高鶚?biāo)m(xù),爭(zhēng)議仍然不斷。細(xì)讀該書(shū)甚久,自然不難覺(jué)察其在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容上一定程度的“殘缺”——“形”之缺失與“意”之未盡兼而有之。無(wú)論是作者未克完成,還是于流傳之中有所缺失,《紅樓夢(mèng)》終究留給我們太多的未竟之謎。如張愛(ài)玲年少時(shí)就開(kāi)始讀《紅樓夢(mèng)》,“看到八十回后,一個(gè)個(gè)人物都語(yǔ)言無(wú)味,面目可憎起來(lái)”,每隔幾年讀一遍,讀來(lái)讀去,對(duì)《紅樓夢(mèng)》的殘缺始終縈繞于心、難以釋?xiě)眩踔玲劤伞皦?mèng)魘”。
比對(duì)、研究了《紅樓夢(mèng)》的多個(gè)版本后,張愛(ài)玲始終認(rèn)為,現(xiàn)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終究是經(jīng)過(guò)他人統(tǒng)合、增刪、修改甚至續(xù)寫(xiě)的,種種細(xì)節(jié)都可以見(jiàn)出與脂評(píng)本的違和之處。張愛(ài)玲一系列的《紅樓夢(mèng)》考據(jù)文章,用心用力極深,將散文寫(xiě)得如論文般嚴(yán)謹(jǐn),過(guò)人的才華時(shí)時(shí)閃光,實(shí)可見(jiàn)其對(duì)《紅樓夢(mèng)》未完之恨已成心病。同為才情卓異的寫(xiě)作者,白先勇卻認(rèn)為后四十回不是續(xù)作,并對(duì)后四十回中的“黛玉之死”和“寶玉出家”充滿(mǎn)了欣賞之情。記得我第一遍讀《紅樓夢(mèng)》,正是青春年少,完全沉浸在少男少女卿卿我我、離合悲歡的生命故事中,并未覺(jué)得后四十回有何不妥。此后多年間,《紅樓夢(mèng)》也是讀了一遍又一遍,幾乎每年都要細(xì)細(xì)重溫一遍。與《紅樓夢(mèng)》一般,它的讀者也會(huì)長(zhǎng)大。突然有一天,覺(jué)得后四十回的語(yǔ)言和人物怎么看都不對(duì),簡(jiǎn)直無(wú)法忍受。從此以后,再讀《紅樓夢(mèng)》,就只讀到前八十回。
和很多深?lèi)?ài)《紅樓夢(mèng)》的讀者一樣,我也曾深憾《紅樓夢(mèng)》未完,也曾在各種評(píng)點(diǎn)本和研究著作中尋找蛛絲馬跡,希望找到曹雪芹當(dāng)年究竟要為后四十回安排什么樣的情節(jié)和故事,如何讓生活于好似現(xiàn)實(shí)的虛擬世界的這一些鮮活生動(dòng)的人物一一有個(gè)落腳處。但正如諸多研究者和愛(ài)好者一樣,所有的努力終究難成定論。但有一天,突然覺(jué)得,也許《紅樓夢(mèng)》的一種重要魅力甚至魔力,就在于“未完”,世界漸次構(gòu)成,人物悉數(shù)出場(chǎng),卻未有“了局”。這“未完”,留給了后人多少的想象和言說(shuō)空間。你讀我讀他讀,你說(shuō)我說(shuō)他說(shuō),人人說(shuō)得出自家的一部《紅樓夢(mèng)》。正如蘆雪庭聯(lián)句時(shí),王熙鳳起了一句“一夜北風(fēng)緊”,大家贊道:“這正是會(huì)作詩(shī)的起法……留了多少地步與后人。”《紅樓夢(mèng)》未完,也留了多少地步給后人。因此,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紅樓夢(mèng)》,張愛(ài)玲如是,白先勇也如是。正如蔡小容所說(shuō),“《紅樓夢(mèng)》是曹雪芹的,也是王立平的,也是劉旦宅的,也是大衛(wèi)·霍克斯的”,自然,也是蔡小容的。更可以是如你我般熱愛(ài)《紅樓夢(mèng)》的。這樣的讀者,以后還不知會(huì)有多少,也不知會(huì)見(jiàn)出多少樣的《紅樓夢(mèng)》世界。
讀《紅樓夢(mèng)》,愛(ài)那些僅見(jiàn)于文字的人物,如何能壓抑得了為其“賦形”的沖動(dòng)。心之不同,則目之色異,人人眼中皆有個(gè)寶玉、黛玉、寶釵,甚至賈璉、薛蟠、夏金桂、寶蟾一干人物,于讀時(shí)也都有個(gè)形象。有多少個(gè)讀者,也便有多少個(gè)形象。蔡小容的《紅樓小拾》源自曹雪芹的《紅樓夢(mèng)》,也是源自劉旦宅的“紅樓人物畫(huà)”,劉錫永、江南春、董天野等人的連環(huán)畫(huà),更是源自自己的生命和審美經(jīng)驗(yàn)。書(shū)中人和畫(huà)中人與蔡小容心中的人物交融在一起,相互印證、難分彼此,各自心之所及,筆下傳神寫(xiě)照。映照的,仍然是自家所見(jiàn)的形象。文與畫(huà)各自的妙處,約略也可見(jiàn)于此處。
“文字可寫(xiě)意,繪畫(huà)則須具體”,但具體并非一味寫(xiě)“實(shí)”,還得有氣韻,有格調(diào),有人物自?xún)?nèi)而外散發(fā)的韻致和活力。蔡小容對(duì)此體悟頗深,她明了文字與繪畫(huà)、寫(xiě)意與具體之間的藝術(shù)奧妙,故而別有所見(jiàn)。如她所說(shuō),林黛玉是《紅樓夢(mèng)》中最寫(xiě)意的形象,原著對(duì)她外貌的描寫(xiě),只有神情,而非面貌。“她的形象飄渺,但又確定,每個(gè)人心中都有一個(gè)模糊而相近的形象,要說(shuō)誰(shuí)長(zhǎng)得像林黛玉,幾乎所有人都有共識(shí)。”林黛玉的描寫(xiě)用筆極寫(xiě)意,形象卻又極具體,似極虛,卻又極實(shí),以虛寫(xiě)實(shí),又以實(shí)證虛,恰是蔡小容文字與連環(huán)畫(huà)作可對(duì)應(yīng)發(fā)明處。
且看她如何說(shuō)黛玉。《紅樓夢(mèng)》對(duì)林黛玉的形象描寫(xiě)是以虛寫(xiě)實(shí),而這種虛緲的形象要落實(shí)在畫(huà)紙上,必得升騰出些寫(xiě)意之氣,才能表現(xiàn)出黛玉的仙逸韻致。“劉旦宅畫(huà)的黛玉,黛玉倚坐在山石上,足下菊花,身后竹枝。孤芳自賞的黛玉,疏離人世的交往而執(zhí)著于內(nèi)心的孤行,一意往美、高邈、深細(xì)、幽微處走去。她有她的哲學(xué),她需要某種意境,這種‘境’,她用全部生命去養(yǎng)成——看這幅畫(huà),黛玉就在她最準(zhǔn)確的‘境’中,極美。她的面龐,清逸孤標(biāo)、目下無(wú)塵,又俊美無(wú)儔,是你絕對(duì)想不出,而一看就認(rèn)定,這幾乎是理想的林黛玉。”而江棟良的連環(huán)畫(huà)中的黛玉形象,更值得尋味。畫(huà)面中黛玉的床榻、陳設(shè)、衣著、配飾都極繁復(fù),似與黛玉的仙逸之氣不符,但依蔡小容的分析細(xì)細(xì)看來(lái),卻發(fā)現(xiàn),黛玉的身體和精神、生活和思緒、情和夢(mèng)都是依托在這些具體的情境與物件中。畫(huà)面越實(shí),黛玉的孤獨(dú)與愁緒表現(xiàn)得越突出。“好一個(gè)幽雅舒適的小天地,林姑娘在里面住著,錦衣玉食,為什么心上只是不快活?為什么十頓飯她只吃五頓?為什么她總是哭?”這種以實(shí)寫(xiě)虛的表現(xiàn)方式,正與《紅樓夢(mèng)》原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紅樓夢(mèng)》的落筆之處盡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生活細(xì)節(jié),表現(xiàn)的卻是人類(lèi)命運(yùn)的大虛空與大悲涼。還如她說(shuō)書(shū)中人物常做女紅,晴雯、雪雁、紫鵑自不必論,連寶釵、探春也做得。唯有黛玉似乎與此道緣分不深,那些個(gè)寂寞、惆悵,幾不知所為何來(lái)又如何遣去的春恨秋愁,如何打發(fā)?女紅所累為“身”,身既為此所累,一顆心便省著了。惜哉惜哉,“林姑娘,要是你懂得這個(gè)道理就好了。”
一部《紅樓夢(mèng)》,寫(xiě)出多少少年男女紛紛情思,那情思多化煙化灰,如云散去,其中的大寂寞大悲涼,于此最讓人神傷。但《紅樓夢(mèng)》并非僅有“春夢(mèng)”,那春夢(mèng)中原本便有斷不能避免的“破壞者”。即如文中所述田曉菲的說(shuō)法:“《金瓶梅》所寫(xiě)的,正是《紅樓夢(mèng)》里常常一帶而過(guò)的,而且總是以厭惡的筆調(diào)描寫(xiě)的中年男子與婦女的世界,是賈璉、賈政、晴雯嫂子、鮑二家的和趙姨娘的世界。”即便用心用筆皆不在這一個(gè)世界。寶玉、黛玉、寶釵,誰(shuí)又能自外于此??jī)刹繒?shū)面對(duì)的是類(lèi)似的現(xiàn)實(shí),卻因不同的“世界觀取景”而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每個(gè)人讀《紅樓夢(mèng)》,其實(shí)也有不同的取景。《紅樓小拾》給我們呈現(xiàn)的也正是蔡小容取景之下的紅樓世界。在蔡小容筆下,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紅樓夢(mèng)》中幾位重要女性在各自生命處境中的隱痛。透過(guò)文與畫(huà),蔡小容真切地揣摩到黛玉雨夜獨(dú)臥的千愁萬(wàn)緒。這個(gè)中國(guó)文學(xué)中最美的女孩,在“鳳尾森森、龍吟細(xì)細(xì)”、精致得如上等書(shū)房的的瀟湘館內(nèi),感受到的卻是“風(fēng)刀霜?jiǎng)?yán)相逼”,放不下的是無(wú)望的愛(ài)情期待。寶釵處事圓滑周致,集俗世中的萬(wàn)千美德與智慧于一身,但也難以逃脫生活中的種種難題與難堪。“赫赫揚(yáng)揚(yáng)”的鳳姐,機(jī)關(guān)算盡、萬(wàn)事妥帖,但“平生痛處,還真不少:丈夫急色濫情、自己又總無(wú)子嗣、身體多病、辛苦做事卻招人恨”,就連尤二姐,蔡小容也在董天野的一幅圖中,細(xì)細(xì)體察到了她新婚燕爾,眼角眉梢藏不住的幸福感,以及這種幸福如春天般轉(zhuǎn)瞬即逝。俱往矣!美好的總不能長(zhǎng)久,雨打風(fēng)吹、風(fēng)流云散,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所幸有《紅樓夢(mèng)》,有《紅樓夢(mèng)魘》,有那一幅幅或?qū)嵒蛱摚蚓⒒蜷煷蟮漠?huà)面,可于文字隱然不及之處做些個(gè)顯影的工作,心之所及,傳神寫(xiě)照,那文字與圖畫(huà),也皆如沈從文所言,足以成為“連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借此,“歷史如相連續(xù)”,那些“為時(shí)空所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后還如晤相對(duì)”。如此,如此而已。
(責(zé)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