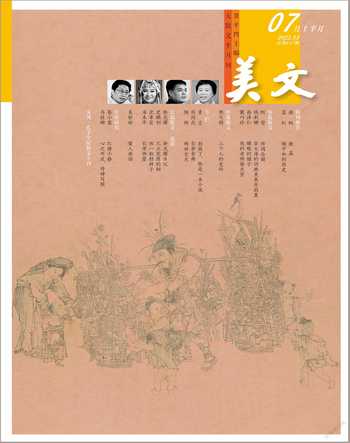“自然的”與“文化的”

張華
前些日,應邀參加了美國哈佛大學舉辦的幾場全球校友學術活動。舉辦這樣的活動,是哈佛大學一個延續了許多年的傳統,我在《閱讀哈佛》中有所記述。活動多由關系大學“經濟命脈”的校友會(HAA-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負責規劃和操辦,新冠疫情之前幾乎每兩個月都會分別在全球各大區域安排組織此類活動,并提前至少三個月甚至半年向全球校友發布通知,邀請注冊參加。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的此類活動多數是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舉行,本次活動也是如此。活動方式與常規的大型學術會議沒什么兩樣,有校長演講、主旨發言和圍繞不同主題的會議分論壇等,一般會持續三天左右。除此種類型的活動之外,哈佛大學還有各類其他組織主辦的學術活動,這些組織多半與校友會關系密切,甚至不少都是校友會的分支機構,而主辦的學術活動也是規模大小不一,形式多樣。比如,約翰·哈佛社群(JHS-John Harvard Society)上月就主辦了一次主題為“深層歷史”的線上學術活動。
“深層歷史”實際上是哈佛大學歷史學科兩位教授馬修·利布曼(Matthew Liebmann)和丹尼爾·洛德·斯梅爾(Daniel Lord Smail)所講課程的名稱。活動開始,主持人尼克· 薩克拉里亞迪斯和朱莉·薩克拉里亞迪斯(Nick and Julie? Sakellariadis)對活動和主講人作了介紹,然后便分別是兩位課程教授的講座和他們的兩位學生的期末項目分享。整個過程中,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的期末項目分享引起我極大興趣。
這位男生的期末項目有關婚姻和身體,在身體部分他提到了中國,展示了一幅古代婦女裹足的圖片,并說“足”是身體的一部分,是自然的(natural),而通過裹布使其變小則是文化的(cultural)的行為。這讓我想起北京語言大學和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合作出版的刊物《中美比較文學》,其中2017年第3期是“身體與性”特刊,這期特刊的主題與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CLA)2015年年會的主題一致,文章也是精選自這屆年會。美國薩拉·勞倫斯學院的翁蕾華博士,以《身體與性:在比較研究中審視存在并探索可能的替代方案》為名,專門為此特刊撰寫了導語。她寫道,在文學研究領域,圍繞各種文化、社會和政治話語的對話非常活躍且持續不斷,這些對話一直在相互碰撞和激蕩,以對身體和性畫出邊界、作出定義。然而,作為“自然的”生物和物理實體的身體和性,本質上是沉默寡言的,永遠無力參與對話。因此,在文學和文化文本中所表達和揭示的身體和性的“文化的”現象,必然呈現出豐富的復雜性和激烈的爭議性。這期“身體與性”特刊包括六篇文章,以不同的語言探討身體與性,展現了文學文本和文化材料中所體現的多重意義。希望通過探討古羅馬、十三世紀中國和當代中國、現代日本、歐洲和北美的身體和性話語,這期特刊能在某種程度上傳遞出一種比較研究的信息,即審視現有的,探索可能的。
事實上,這樣的探討與學術領域內“文化的”導向(或語言主導)轉向“自然的”導向(或物質主導)是有關的,也就是有學者更多主張物質(包括身體)本身的功能(Matter matters)。我作為《中美比較文學》雜志的中方主編,不妨把這期特刊中六篇文章的要點在此作一綜述,綜述也參考了翁蕾華博士為特刊撰寫的導語。
除了導語之外,特刊另收錄了翁蕾華博士的一篇文章。文章將宋明理學中的“修身”概念和福柯所勾勒的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自我關照”相比較,討論了新儒家哲學和政治修養概念中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關注的是身體的概念是如何被吸收和強化的;而艾琳·維克里(Eileen Vickery)的《企業家的男子氣概和新厭女癥》則著眼于當代中國小說,認為這些小說展現了中國放任自由經濟發展如何強化了男性特權,并且同時剝削那些試圖適應新經濟次序的女性,刻畫了經濟發展給中國人及其社群帶來的變化。在這些小說中,人們以女主人公的性魅力評估她們的價值。艾琳·維克里分析了作為中國經濟一部分的女性形象如何被異化為欲望對象,被異化為欲望對象的女性身體如何成為男性展現其新的經濟身份的象征,以及被欲望化的女性身份如何反映經濟和社會價值極速變遷所帶來的社會焦慮。
然而,關于身體和性的論述,一旦正常化,甚至制度化,是否會主導學術并拒絕其他聲音?對于這個問題,本期特刊的文章給出了不同的回答。泰勒·特拉維利安(Tyler Travillian)的文章是對拉丁文本《普里亞佩亞頌歌》的另一種解讀,闡述了如何以兩種方式對主導力量發揮作用。泰勒·特拉維利安的文學分析表明,羅馬人的性行為及其所有的偏差,不能簡化為一個單一的系統。中尾誠吾(Seigo Nakao)在《亂倫的欲望》一文中,探討了十九世紀的歌舞伎作品與二十世紀谷崎潤一郎的作品,研究了這類作家作品里亂倫主題的心理含義和社會文化含義,并且討論這些作家冒著觸犯道德禁區的危險描繪亂倫現象的創作動機。中尾誠吾認為,在一個極端父權制的社會中,男性對母權制的壓抑渴望有時會以亂倫的形式出現。班尼特·傅(Bennett Fu)在他的《一束中國百合》中討論了首位北美華裔作家伊迪絲·莫德·伊斯頓(Edith Maude Easton,1865-1914)以筆名水仙花所寫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夫人》,探討了《春香夫人》作品中某些關鍵的族裔與性別議題,試圖提出新的閱讀方法,分析水仙花在書寫中如何挑戰將女性隱形或限制于傳統角色的性別規范。班尼特·傅認為,受困于維多利亞的標準與中國文化的體統兩種關于情欲互相沖突的價值,水仙花似乎更能認同中華傳統,便可能選擇了中國“自然的”姊妹情誼作為壓抑情欲的偽裝。在水仙花多數故事里的核心關注是那些走出父權社會陰影下的女人,班尼特·傅的論文對水仙花筆下女人主體性與族裔性相關問題的作出洞察和分析,指出性別角色與情欲,在當代亞美文學研究中仍是重要的議題。
實際上中尾誠吾和班尼特·傅都是在十九世紀日本和二十世紀北美的文化背景下探討性的越軌本質,特別關注了女性氣質與主流社會文化話語之間的齟齬和不協調,以及前者如何挑戰后者并對后者進行修正和解構,而弗雷德里克—查爾斯·拜廷格(Frédéric-Charles Baitinger)則將對女性的討論提升到了一個更具理論性的層面。在《相信哭泣:海倫·西蘇與拉康、巴塔耶和德里達一起書寫女性》中,弗雷德里克-查爾斯·拜廷格討論了后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家西蘇如何機智而富有成效地利用巴塔耶的理論。正如拉康的性化理論那樣,西蘇對“女性”的定義也被人們指責有本質主義的弊端,因為它們都被認為是通過重現父權來定義“女性”的陳詞濫調,雖然這樣的重現是以一種倒置的方式進行的。弗雷德里克-查爾斯·拜廷格反對這樣的閱讀方式,他認為拉康在后期教學中通過脫離俄狄浦斯情結的臨床研究,就已對“女性”的視角有所改變;而如果我們透過拉康后期思想架構來重新閱讀西蘇,就能發現她為對“女性”的闡釋提供了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方式,而這一方式恰恰不能簡化為本質主義對“女性”的定位,因為這種方式并沒有從跟菲勒斯(the Phallus)缺失關系的角度去定義“女性”。弗雷德里克-查爾斯·拜廷格認為,拉康的定義是基于對陽具的更消極的關系,而德里達的定義則與拉康顯然不同。于是,弗雷德里克-查爾斯·拜廷格在文中重新勾勒了西蘇對“女性”的概念和實踐,介紹了女性主義背景和心理分析背景,并在此基礎上,展現出西蘇的女性概念如何通過運用巴塔耶的普遍經濟學理論及德里達的書寫概念,來超越拉康對“女性”的具體闡述。
顯然,在所有這六篇文章中,后現代理論,尤其是米歇爾·福柯的理論占有很大比重。翁蕾華對新儒家自我修養的考察,是在與福柯對希臘“自我關照”探究的比較中進行的。艾琳·維克里、中尾誠吾和班尼特·傅在對中國、日本和美國文學的文本分析中也使用了福柯的理論或概念。盡管泰勒·特拉維利安在他關于羅馬性行為的文章中沒有明確說明,但其中關于性和社會權力結構的討論也是從福柯的角度進行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弗雷德里克-查爾斯·拜廷格的研究更是如此。
除了獨特的視角和一套研究話語外,我們還可以從哪些方面借鑒福柯的研究?如果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在各自的文學研究中討論和考察的社會和文化話語構成的,那么通過我們的工作,我們每個人是否只是在各自現有的文學研究中增加了另一層話語系統?我們對性行為的“文化的”研究還有其他目的嗎?翁蕾華博士在特刊導語部分發出了上述疑問。隨后,她寫道,這期特刊中涵蓋不同討論主題的文章,作為一項比較研究項目,將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通過描述和審視這些話語,我們可以探索過去沒有過的可能性。雖然沒有在現實中呈現,但仍然可以通過我們對現有話語的考察向人們揭示“身體和性”。根據福柯的理論,話語伴隨著權力。當我們描述一種文化和社會現象時,我們很可能會將其歸屬于某種形式,并重申其存在,因此,這樣做可能會排除其他可能的選擇。但是,如果我們以對這些選擇的充分敏感性來開始我們的研究,并在比較的框架內進行,即在我們的研究范圍內進行比較,定會展現出一定的前景,畢竟“身體和性”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
福柯晚年在他的性史研究中轉向了古代希臘羅馬,因為另一種倫理學建立在主體自身的意志之上,而不是像現代倫理學那樣服從于先前存在的社會規范和秩序。換句話說,后來的福柯致力于通過其他方面進行探索。在探索當代現有現代倫理的可能替代方案時,它與此時此地存在的倫理在時間上或地理上都是不同的。我們是否能夠將他在其他文化中探索替代方案的方法應用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和文學比較研究中?如果可以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僅僅是通過各自的研究來重申什么是性話語,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將進行自我反思的探索,通過對“他者”語言和文化中的文本進行比較研究,尋找其他可能性的選擇。
(責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