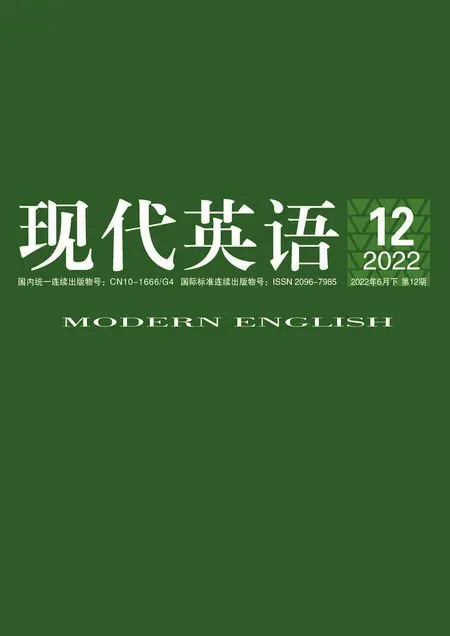基于CiteSpace對國際詞匯附帶習得的可視化分析
段桂紅
(西安外國語大學,陜西 西安 710000)
一、引言
詞匯在語言學習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詞匯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學習者的口語、聽力和閱讀水平。詞匯附帶習得和有意習得是學生擴大詞匯量的兩種基本方式。詞匯有意習得是指學生以習得詞匯為目的而有意識地開展學習。詞匯附帶習得是指學習者在完成有意義的語言活動時,詞匯作為附屬品而偶然習得。相較于有意習得,詞匯附帶習得的效率低,但可以有效彌補課堂時間不足的問題。因此學者不斷研究探討提高詞匯附帶習得效率的方式(李辛和雷蕾,2021)。[1]
詞匯附帶習得領域的綜述類研究已不在少數,但主要以國內相關研究為主,缺乏國際視野(苗麗霞,2013);[2]且以多數研究以定性為主,有主觀性太強之嫌(苗麗霞,2014)。[3]將這一領域作為整體進行研究的文章還不多見。因此,文章運用CiteSpace可視化技術,對詞匯附帶習得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以期幫助研究者厘清該領域的研究動態、研究熱點以及前沿趨勢。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一)數據來源
文章以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的網絡數據庫Web of Science(WOS)為數據來源,以“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incidental word acquisition” “incidental word learning”為檢索詞,在 SCI,A & HCI,以及 SCIEXPANDED子庫中進行主題檢索,時間跨度不限,文獻類型僅限于論文和會議論文,并經過CiteSpace軟件除重,最終得到556篇文章,引文數據庫最后的更新時間為2021年12月31日。
(二)數據分析和討論
CiteSpace具有分析文獻共引,繪制知識圖譜功能(李杰和陳超美,2016)。[4]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軟件的可視化技術,從發文量,核心文獻著手,分析詞匯附帶習得領域的研究動態,并利用突變功能,了解該領域的研究前沿。
三、研究動態分析
(一)文獻發文數量以及年度分布
WOS數據表明,國際詞匯附帶習得開始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第一篇相關文獻產出于1963年,但在1960~1970十年間,無其他相關文獻發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詞匯附帶習得的萌芽期,其間共有9篇論文發表,發展相對緩慢。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詞匯附帶習得迎來了其蓬勃發展期,自1992年發文量穩步上升,1990~2010年間共有213篇文獻發表。2011年以來,詞匯附帶習得進入了其高潮期,十年間共有332篇相關文獻,2020年的發文量到達峰值,共56篇文獻發表。該領域不同年度的發文量有不同程度的波動,但總體上呈增長態勢(見圖1)。說明該領域日益受到國際學術圈的關注且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待學者進一步挖掘。

圖1 文獻發文數量及年度分布
(二)高被引文獻及作者分析
高被引文獻體現了該文獻的影響力以及領域內學者對該文獻的認可度。筆者整理CiteSpace生成的共被引聚類分析知識圖譜后,抽取分析被引頻次最高的十篇文獻。
十篇文獻中,Webb作為一作有三篇文獻入圍,分別位于3,8,10位。通過對比精讀與泛讀對詞匯附帶習得的影響,Webb發現在視聽材料的輔助下泛讀的優勢更為明顯(Webb& Chang,2014),[5]且學生的基礎詞匯知識對學生通過泛讀習得詞匯的效率有很大影響(Webb& Chang,2015)。[6]Webb和Paribakth(2015)[7]證明不同文本的詞頻廣度差異較大,且文本詞頻廣度與學生在閱讀理解、聽力或者完形填空的得分皆呈弱相關甚至不相關關系。
Pellicer-Sánchez共有三篇文獻居于列表,2016年基于“眼動”所做的研究位于榜首,該研究證明了英語為母語和英語為二語的讀者之間詞匯附帶習得最終效果并無差異,但是一語讀者的習得速度更快(Pellicer-Sánchez,2016)。[8]Pellicer-Sánchez 與Schmitt(2010)[9]的研究表明閱讀小說可以擴大詞匯量,但加以教學等手段效果更佳。Pellicer的另一研究表明,詞組可以通過閱讀而附帶習得,并且詞形,詞義之間的習得效率沒有顯著差異;輸入頻率對習得效果無顯著影響(Pellicer-Sánchez,2015)[10]。
Peter入圍的兩篇文獻分別位于第二位和第四位。Peter與Webb(2018)[11]研究了完整的電視節目對詞匯附帶習得的影響,結果表明,完整的電視節目對習得詞匯的各個方面都有促進作用。Peter,Heynen與Puimege(2016)[12]探究了一語與二語字幕對詞匯附帶習得的影響,最終證明詞匯可以在短視頻中習得;二語字幕更有助于學習詞形;詞頻以及基礎詞匯量都與詞匯附帶習得效果成正相關關系。
位于第六位的Godfroid(2018)[13]以小說作為輸入文本,基于“眼動”研究了在自然閱讀情境下一語與二語閱讀者詞匯習得效果的差異。證明了一語閱讀者在詞義認知測試中表現更加;詞形認知中二者無明顯差異。隨著詞頻的增加,讀者在目標詞匯上停留的時間逐漸縮短,這與讀者對該詞的熟悉度有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讀者遇到目標詞匯時的心理加工過程。
位于第七位的Vidal(2011)[14]對比了聽力和閱讀兩種模式對詞匯附帶習得的不同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英語水平較低者通過閱讀的習得效果更佳,但是隨著學生英語水平的提高,閱讀與聽力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閱讀中,對習得發生作用的主要是詞頻。不論聽眾還是讀者,明示的詞匯解釋都更有利于詞匯習得。作者指出,各種因素都是通過“投入量”來發生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盡管Webb,Pellicer-Sánchez和Peter的影響力較大,但最高的被引頻次僅有23次,表明該領域仍缺少具有極高參照性的文獻。“眼動”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方法也被應用到了該領域,從側面反映了目前該領域的研究方法與時代共進。
(三)研究熱點分析
文章利用CiteSpace中突發詞探測算法來分析揭示詞匯附帶習得領域的階段性以及新興研究熱點(見圖2)。

圖2 突變關鍵詞
數據顯示,第一個高頻關鍵詞突現于1990年,“回想”和“記憶”是國際詞匯附帶習得領域最早的研究熱點。但其不能完整解釋以及促進詞匯附帶習得,“語言模型”于2003年成為研究熱點。雖然詞匯附帶習得始于一語學習,但很快便被引入二語詞匯附帶習得中,因此“學生”受到了該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前期多以“詞形”習得為研究重點。值得注意的是,“閱讀理解”以及“電視”成為目前新興研究熱點。詞匯附帶習得在閱讀理解中最先受到關注,但隨著科技的發展,電視字幕與影像對詞匯習得的影響逐漸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
四、結語
綜上所述,詞匯附帶習得目前正處于發展高潮期,目前該領域已出現了影響力較大的學者,且研究多數集中到了二語教學。
國際詞匯附帶習得研究結果日趨豐富,但仍存在諸多不足,如高被引文獻中心性不高。多數研究集中于閱讀理解而忽視了“聽力”對詞匯附帶習得效果的影響。希望文章能幫助國內詞匯附帶習得新手研究者及時了解詞匯附帶習得的研究熱點與發展前沿,并結合國內情景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