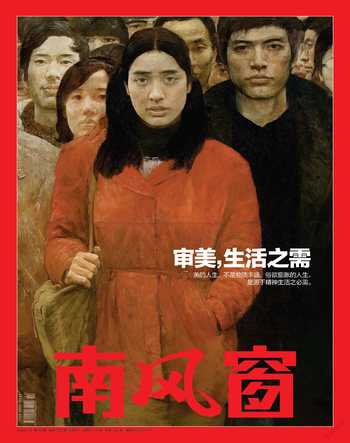俄羅斯傳統的獨特性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
俄羅斯作家彼得·恰達耶夫談到他的國家時說:“我們既不屬于西方也不屬于東方,也沒有兩者的傳統。可以說,我們置身于時代之外,沒有受到人類普遍教育的影響。”
那是在1829年。這個“包裹在一個大謎團中的中謎團里的小謎團”(溫斯頓·丘吉爾在一個多世紀后描述俄羅斯之語),至今仍未解開。
哲學家約翰·格雷最近寫道,在這個西方思想所無法理解的世界里,戰爭始終是人類經驗的永久組成部分,領土和資源的致命斗爭隨時可能爆發,人類為了神秘的幻象而殺戮和死亡。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我們民族神話的俘虜,只是俄羅斯的民族神話與眾不同。它錯過了歐洲現代化的三個關鍵要素:宗教改革、民族國家、自由資本主義。
正如尤里·謝諾科索夫所寫,俄羅斯從未經歷過宗教改革或啟蒙運動。謝諾科索夫認為,這是因為“農奴制直到1861年才被廢除,而俄羅斯的專制制度直到1917年才崩潰”。結果,俄羅斯從未經歷過確立歐洲立憲國家輪廓的資產階級文明時期。
俄羅斯在自由資本主義方面的經驗,很短暫且有限。試圖自上而下實現俄羅斯西化的彼得大帝,要求俄羅斯男人剃掉胡須,指示他的貴族“不要像豬一樣狼吞虎咽;不要用刀清潔牙齒;切面包的時候不要把面包放在胸前”。列寧繼承了偉大的改革派沙皇的傳統,推出了“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的革命公式。
俄羅斯與歐洲的關系,早在19世紀,就隨著新人(New Man)的理念而有了一個新的維度—一種熱衷于科學、實證主義和理性的、與啟蒙哲學密不可分的西方類型。
新人是伊凡·岡察洛夫1859年的小說《奧布洛莫夫》中的斯托爾茨,是伊凡·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中擁護科學、反對家族非理性傳統虛無主義的“兒子”巴扎羅夫。強烈影響了列寧的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辦?》,想象了一個建立在科學理性之上的玻璃和鋼鐵社會。
只是,由于俄羅斯傳統文化根深蒂固,這些未來主義的預測激起了真正的農民的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0年代出版的《地下室手記》,不僅成為基督教斯拉夫主義的經典著作之一,也對現代性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質疑。
布爾什維克做出了將“新人”從文學中帶入世界的最偉大的集體嘗試。他們和彼得大帝一樣,明白改造一個社會,需要改造其中的人。他們齊心協力,在當時最重要的前衛藝術家的參與下,試圖使人們的思想現代化,培養他們的革命意識。按照這一設想,俄羅斯人將成為有助于建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具有科學和集體意識的新人。
這一嘗試也許遭遇了空前的失敗,但歐盟前外交官羅伯特·庫珀在2003年出版的《國家分裂》一書中卻認為,俄羅斯的未來仍然是開放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的簽署以及后來俄羅斯謀求加入北約的舉動,就是證明。
雙方這種和解的失敗,是因為西方的傲慢還是俄羅斯的格格不入,將長期存在爭議。到2004年,俄羅斯領導人已經擺脫了大部分自由化傾向,開始接受傳統主義。在羅伯特·庫珀的分類中,俄羅斯是一個現代前現代(modern pre-modern)國家。
1968年布拉格事件之后,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拒絕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改編為劇本。昆德拉說:“陀氏的夸張姿態、諱莫如深和咄咄逼人的多愁善感,讓我感到厭惡。”其實,正是在這些諱莫如深處,在理性的外表背后,我們才能窺探俄羅斯的前現代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