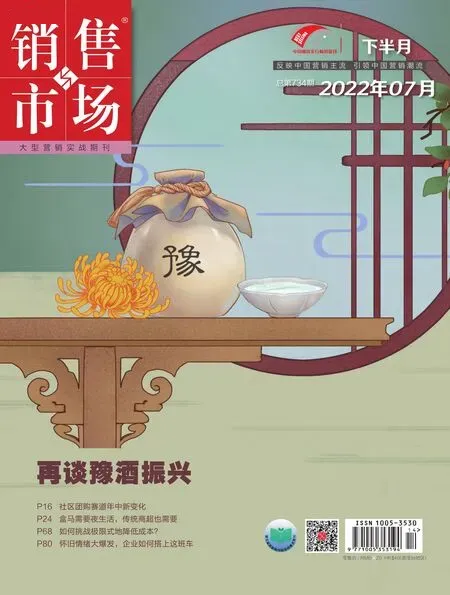重生:TCL三大變革之道
文/楊繼剛
要么等死,要么重生
16年前的初夏,廣東惠州,身為TCL 總裁的李東生,正在遭遇職業生涯最艱難的挑戰。
彼時的TCL,在陸續完成對德國施耐德電子,法國湯姆遜電視、阿爾卡特手機的收購后,出現了嚴重的“消化不良”:全球主流彩電廠商已從CRT 電視向LCD 電視轉型,TCL 悲催地成為湯姆遜CRT 技術的“接盤俠”;由于對歐洲市場的制度與文化環境不熟悉,TCL 的海外并購出現國際化經營不善問題;在國內手機市場,曾推出包括鉆石手機在內的明星機型,一度風生水起并請金喜善做代言的TCL 手機業務快速下滑,包括萬明堅在內的手機業務高管先后離職;TCL 股份在2005年、2006年分別虧損3.2 億元、19.3 億元,還被戴上了*ST 帽子……來自市場、股東、合作伙伴、團隊成員的質疑不斷,重壓之下的李東生在公司內部論壇上,引用《美國國家地理》所講述的一個故事,以《鷹的重生》為題,借用老鷹在40 歲時通過脫喙、斷趾、拔羽重獲新生的故事,向公司上下做自我反省,表達勇敢面對危機、堅定文化變革與堅定推進國際化戰略的決心。從此,以“鷹的重生”作為企業獨特IP的TCL,開始了又一輪再創業之路。
16年后,TCL“鷹的重生”戰績如何?
根據TCL(集團)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TCL(集團)營業收入和利潤均取得歷史最好成績。整體營收2523 億元,同比增長65%,整體規模已達到世界500 強;凈利潤171 億元,同比增長129%。在業務層面,TCL(集團)已經成長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智能高科技產業集團,通過TCL 科技和TCL 實業兩大主體布局半導體顯示、新能源光伏與半導體材料、智能終端三大核心產業。其中,TCL 科技實現營業收入1635.4 億元,同比增長113%,實現凈利潤149.6 億元,同比增長195.3%;TCL 實業實現營業收入1056.4 億元,同比增長18%,實現凈利潤42.1 億元,同比增長74%;TCL 半導體顯示業務實現營業收入881 億元,同比增長88.4%,實現凈利潤106.5 億元,同比增長339.6%。主業務賽道清晰,又處于風口浪尖,市場布局與增速遙遙領先,“鷹的重生”初見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當下,中國企業正在經歷包括逆全球化、供應鏈不暢、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產業鏈深度調整、國內消費不振與人口出生率下滑等諸多挑戰,對很多企業而言,這不亞于一場“鷹的重生”。就像李東生在那篇流傳甚廣的文章《鷹的重生》中提到的,“要么等死,要么經過一個十分痛苦的更新過程,完成蛻變”,對于那些正在經歷轉型與變革的中國企業而言,TCL“鷹的重生”之路或許能給大家更多啟發。
變革之道一:要機會,不要機會主義
關于機會,小米創始人雷軍那句“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曾引發巨大爭議。
贊成的一方說,風口就是機會,機會當然重要。以福布斯每年發布的世界500 強排行榜為例,幾乎是每過10年,都會涌現出一大批同屬于一個新崛起行業的優秀企業。為什么它們會批量崛起?顯然,這要歸功于風口(機會)的價值。反對的一方說,等風停了,摔死的都是豬。意思是,練內功對企業非常重要,那些完全憑運氣成功的企業,只要機會窗口過去,往往會一地雞毛。其實,對大多數企業而言,風口很重要,“長翅膀”也很重要—優秀的企業,往往既能抓住機會順勢而為,又能不斷提升內功持續增長。對于前者,大多數企業要回答的問題是:要敢于抓住機會(長期的行業發展趨勢與產業周期,首先需要具備抓住機會的能力),而不要機會主義(短期的投機取巧和“下注”,沒有對照自己的能力水平)。
對大多數企業而言,風口很重要,“長翅膀”也很重要——優秀的企業,往往既能抓住機會順勢而為,又能不斷提升內功持續增長。
以TCL 國際化戰略為例。對TCL 而言,國際化是機會嗎?當然是。早在2002年,TCL 就意識到國內彩電市場的發展瓶頸,無論是技術升級還是市場拓展,國際化都是繞不開的一條路。于是,TCL 就通過收購德國施耐德電子,法國湯姆遜電視、阿爾卡特手機,開啟國際化之路。相比而言,這要比聯想(并購IBM 電腦業務)、吉利(收購沃爾沃)、海爾(收購三洋電機)、三一重工(收購普茨邁斯特)、海信(收購東芝電視)等企業的國際化之路早得多。但結果卻很打臉,因國際化并購所導致的持續虧損、經營不善以及在國內A股市場被*ST,都讓TCL 痛苦不堪,李東生一度懷疑自己的國際化戰略是否有問題。

銷售與市場抖音
為什么明明是機會,但TCL 國際化(后來還收購過手機品牌黑莓)卻出師不利?有人說,TCL 是“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這是句正確的廢話,真正的問題在于:機會當然要抓住,但機會能否轉化為成果,還需要企業“長翅膀”—與國際化并購相關的國際化經營與管理能力。這一點,實事求是地講,TCL 真的沒有準備好。不僅TCL 沒有準備好,包括后來的聯想、吉利、海爾、海信的國際化并購,都經歷過一段曲折。這不僅涉及國際化的管理人才儲備,還有對所并購企業所在的地區法律、政策、制度、文化的了解(比如工會組織,吉利汽車與福耀玻璃在海外并購與國際化戰略推進中,都遇到過工會組織問題)。另外,TCL 還有一個致命的誤判,在收購湯姆遜電視時,全球彩電行業已開始從CRT 向LCD 電視轉型,TCL 選擇大手筆并購湯姆遜,難道就是為了鞏固“全球CRT 王者”的市場地位?如果不是的話,是當時沒有看到這個趨勢,還是認為CRT 技術還可以在江湖征戰多年?如果不是沖著產能或技術去的,那么是沖著人才、研發、管理體系去的嗎?時至今日,TCL 早就交夠了收購湯姆遜電視的“國際化學費”,但到底復盤了什么結論,外界不得而知。我們能看到的是,后來TCL 在投資華星光電、收購中環股份和奧馬電器過程中,無論是機會的把握,還是投資并購后的經營管理,都有了自己清晰的打法和路徑,在業績回報和持續增長方面,有了很大改觀。TCL 在順勢而為方面,愈加成熟和穩健。
變革之道二:要進化,不要留戀過往
達爾文的進化論主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企業界,這一進化規律同樣適用。只不過,與自然界相比,人性要復雜得多,留戀過去,特別是留戀過去的美好時光,成為很多企業進化路上最大的障礙與絆腳石。
更確切地說,人類社會的進化,到處充滿了被逼無奈,而不是主動為之。企業界更是如此。能“躺贏”當然不需要改變,天天收錢多好,為什么非要瞎折騰?所以,你見過哪個壟斷企業,或者事實上處于壟斷狀態的企業,真正在思考危機和進化?諸如三星、華為那樣的危機驅動型企業,畢竟是少數,大多數情況下,企業都是被趕到了懸崖邊,再不進化就活不下去了,這才是企業進化的原始動力。在《鷹的重生》文章中,李東生是這么說的:“作為世界上壽命最長的鳥類,鷹必須在40 歲時做出困難但卻重要的決定:(因為身體老化)要么等死,要么很努力地飛到山頂,在懸崖上筑巢,用150 天的時間,用喙擊打巖石,直到其完全脫落。然后,靜靜地等待新的喙長出來。再用新長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個一個啄掉。繼而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等待長出新的羽毛。經過這個痛不欲生的階段后,鷹獲得重生,可再度飛翔于天空,迎接生命中更加璀璨的30年。”
16年前,我第一次在《中國經營報》上讀到這篇文章時熱淚盈眶。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勇氣,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折磨。彼時的李東生對自己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為什么我們對很多問題其實都已意識到,但卻沒有勇敢地面對和改變……回顧這些,我深深感到我本人應該為此承擔主要的責任。我沒能在推進企業戰略與文化變革中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角色;我沒有勇氣去完全揭開內部存在的問題,特別是這些問題與創業的高管和一些關鍵崗位主管、小團隊的利益攪在一起的時候,我沒有勇氣去捅破它……對此,我深感失職與內疚。”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TCL 開始了新一輪組織與文化變革,用“重生”的勇氣和膽識,助推TCL 再創業。
首先是止損。通過對海外業務的重組,重新定位歐洲、北美業務的戰略屬性與市場策略,在國際化層面不斷進化,實現了2007年到2009年的凈利潤增長;在國內,通過關閉和調整集團下屬非核心業務,更加聚焦主業,全面鞏固競爭優勢。其次是拓新。吃一塹長一智,但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TCL 在投資并購方面更加注重順勢而為以及對自身產業優勢的補充,先后投資華星光電,并購中環集團(以硅材料為主體的光伏、半導體雙產業鏈企業)。以華星光電為例,TCL 果斷抓住全球半導體顯示器產業鏈轉移的機會窗口期,投資成立華星光電生產液晶面板。經過10年的發展,華星光電已成為半導體顯示領域的重要一極,與京東方一南一北構成了全球液晶面板的中國力量。再次,TCL 對自家原有的電視產品進行智能化升級,并和智能手機(目前有TCL、阿爾卡特、黑莓三個品牌,分別對應不同的區域市場)、家電產品一起,組建智能終端業務群,成為面向消費者業務的智能生態平臺。經過這三步,TCL 戰略變革初見成效。
吃一塹長一智,但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變革之道三:要情懷,不要一廂情愿

無論身處全球哪個細分市場和業務賽道,優秀企業都有一個特點:經營企業,不僅要投入資源、時間和精力,還要有企業家(團隊)的情懷。贏利當然是企業經營的底線,但在此基礎上,情懷與使命驅動的企業,往往要比單純只靠收入和利潤驅動的企業,更能打動客戶,凝聚人心,實現持續增長。
情懷是什么?可不是一個企業家的一廂情愿。情懷最大的體現,就是公司的使命、愿景與核心價值觀。在這方面,特斯拉、蘋果、三星、亞馬遜、谷歌、西門子、飛利浦、殼牌、華為、阿里巴巴、佳能、比亞迪、長城、京東等一大批企業,都有鮮明的情懷驅動印記。以TCL為例,以“領先科技、和合共生”為公司的使命與愿景,致力于為用戶帶來前瞻性的科技體驗和智慧健康生活,堅持“變革、創新、當責、卓越”的核心價值觀。從使命、愿景與價值觀層面,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什么TCL 會勇于實踐“鷹的重生”,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為什么會義無反顧地向產業鏈中最有技術含量的領域遷移,為什么同時期成長起來的長虹、創維、康佳、海信們,有的銷聲匿跡,有的苦苦掙扎,還有的長期徘徊在業績天花板,唯有TCL 可以破局重生,這與李東生個人的責任感、使命感與成就感密不可分,也是TCL 使命、愿景與核心價值觀的最佳實踐。
情懷驅動,意味著企業不能什么賺錢做什么,要考慮自己的競爭優勢與核心競爭力;也不能遇到問題就逃避,為了所謂的面子與和諧,選擇妥協與退讓;更不能掩飾企業的弊端和危機,假裝一切都未發生,為了眼前的利益犧牲長遠。情懷不能飄在天上,要落實到企業的投資決策、市場布局、業績考核與員工行為上;情懷還需要接受市場、客戶、股東、員工的檢驗,用營收和利潤來驗證市場與客戶的認可度,用股價、分紅和權益增值來驗證股東的認可度,用薪資漲幅、離職率、獲得感來驗證員工的認可度。在這方面,TCL仍面臨兩個關鍵挑戰:
挑戰一:業績持續向好,股價卻不見起色。這也是讓李東生與TCL 高管團隊不解的地方。2019年8月12日,TCL 集團公布了重組完成后的首份半年報,在剝離了消費電子、家電等智能終端資產,聚焦半導體顯示及材料業務之后,TCL 實現了2019年上半年營收與凈利潤的同比增長。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這份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但掌門人李東生卻發出了“靈魂之問”:“為什么TCL(股價)和同業比會低那么多?PE 只有同業的1/3,分紅率是同業的3 倍,各項經營指標都比同業優異,我就是想不通為何股價會那么低。”看來,要將情懷轉化為股價,TCL 還需要繼續努力。
挑戰二:對標三星、LG 等行業領軍者,TCL 還需要厚積薄發。一方面,TCL 已成為三星智能手機OLED 面板供應商,還通過收購三星蘇州工廠等方式,與三星保持戰略合作,可以更好地學習和借鑒三星電子的戰略路徑與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對比三星、LG 等行業領軍者,TCL 在技術研發、供應鏈、全球化布局、海外市場拓展等方面,還有不小的差距。在半導體顯示領域,TCL 不能重蹈當年收購湯姆遜電視的覆轍,特別是在半導體領域超級內卷下,TCL 在制造領域的重資產布局,決定了其在產業風口轉換階段的負重前行,產能過剩、反壟斷、原材料成本的不可控等等,都會影響TCL 的戰略轉型。因此,保持足夠的戰略敏感度,搶先布局和研發下一代半導體顯示技術,并構建自己的產業鏈上下游聯盟生態,這對TCL非常重要。
“鷹的重生”依然在繼續,李東生與TCL 仍會有精彩故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