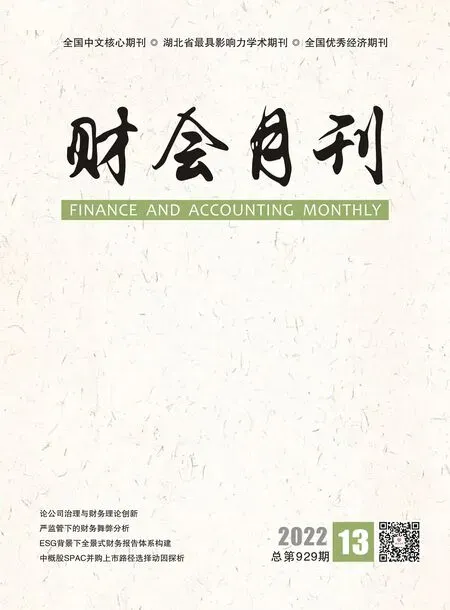嚴監管下的財務舞弊分析
——基于2020~2021年的舞弊樣本
葉欽華,黃世忠(博士生導師),葉 凡(博士),徐 珊(博士)
一、引言
資本市場是個巨大的利益場,監管與反監管、舞弊與反舞弊反復博弈,財務造假與審計失敗周期性發生。受經濟周期下行、經濟結構調整、商業模式創新等市場環境因素的疊加影響,近年我國資本市場再次進入財務舞弊高發期。如何防范和識別財務舞弊成為業界和學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財務舞弊事件高發背后的問題復雜多樣[1],既有企業的利益驅動以及中介機構勝任能力不足和職業道德缺失之過,也有制度設計不完善、處罰失當和行業監管不足之失。
2020年3月1日新《證券法》正式生效,新法規提出了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并對提高財務舞弊違法成本、加大投資者保護等做了全面規定,標志著“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①。在新法規和“零容忍”的嚴監管背景下,A股市場財務舞弊處罰數量、處罰周期及處罰金額有哪些新動態?財務舞弊類型、舞弊手法又有哪些新變化?注冊會計師在嚴監管環境下,是否提高了識別財務舞弊的能力?財務舞弊公司有哪些新的異常識別特征?基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本文在黃世忠等[2]對2010~2019年度財務舞弊公司特征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選取和整理2020~2021年度因財務舞弊被證監會處罰的66家上市公司的相關資料②,對財務舞弊的新手法、審計意見與監管新趨勢等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以期增進對新《證券法》實施效果的了解。
二、財務舞弊監管新動態
本文首先從處罰力度、處罰時效、處罰金額、審計意見等角度,透視新《證券法》實施以來針對財務舞弊的監管動態。
1.處罰力度分析。表1列示了2010~2021年度樣本公司因舞弊被處罰年度的分布情況。2018年之后,監管部門的處罰力度呈明顯加大的趨勢,特別是新《證券法》實施后的2020年度和2021年度,兩年累計處罰上市公司多達66家,與2010~2019年度累計處罰的113家公司相比,處罰力度大幅上升。與2010~2019年度相比,2020~2021年度處罰的上市公司數量占上市公司總數的比例也有明顯提高,凸顯了新《證券法》實施后“零容忍”的嚴監管政策導向。

表1 舞弊處罰年度分布
2.處罰時效分析。表2列示了樣本公司舞弊從發生至受處罰的間隔時間,從中可以發現,一家公司從舞弊發生到被監管部門處罰一般存在3年以上的滯后期。新《證券法》實施后,3年以內被識別出財務舞弊的樣本公司占比從36.31%提高至51.52%,這是明顯的進步,表明對財務舞弊的查處變得更加及時。財務舞弊查處時效性的高低,關系到對舞弊公司的震懾力。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舞弊查處時效性越高,則對舞弊的震懾力越大。

表2 舞弊從發生至受處罰的間隔時間
3.處罰金額分析。表3列示了樣本公司因舞弊受到監管部門行政處罰③的金額分布情況。2020~2021年度,在涉及行政罰款的45家舞弊樣本公司中,有43家樣本公司處罰金額均超過舊《證券法》頂格罰金60萬元,其中:19家樣本公司處罰金額在500萬~1000萬元區間,9家樣本公司處罰金額超過1000萬元。

表3 舞弊公司處罰金額分布
此外,2021年度樣本公司處罰金額明顯大于2020年度,其中:2021年度29家舞弊公司共被處罰金2.52億元,平均處罰金額約為869萬元(如ST宜生被處罰金額高達3885萬元);2020年度16家舞弊公司共被處罰金3281萬元,平均處罰金額約為205萬元。盡管新《證券法》對財務舞弊的處罰金額明顯增加,但與財務舞弊的收益相比仍然不夠高。在這種情況下,監管部門應當更加積極地引進民事訴訟機制,扭轉舞弊收益大于舞弊成本的局面,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抑制上市公司的財務舞弊,更好地保護投資者權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財務舞弊是舞弊者對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的權衡和博弈,如果舞弊者認為舞弊收益遠大于舞弊成本,就可能鋌而走險,訴諸舞弊。新《證券法》不可能無限度地提高處罰金額,通過民事訴訟提高舞弊賠償金額更為可取和現實。
4.審計意見分析。表4、表5分別列示了2020~2021年度、2010~2019年度樣本公司在舞弊發生前一年和舞弊發生當年的審計意見分布情況。對比表4和表5可知,外部審計在識別財務舞弊方面發揮的作用有所提升。2020~2021年度,注冊會計師對舞弊公司發表的非標審計意見占比由舞弊發生前一年的12.12%大幅提升至舞弊發生當年的22.73%,一舉扭轉了2010~2019年間非標審計意見占比(從舞弊發生前一年的17.7%降至舞弊發生當年的15.04%)不升反降的尷尬局面。這表明作為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看門人”的注冊會計師,在嚴監管的背景下對財務舞弊的專業懷疑態度有所上升,在新《證券法》實施后的兩年中,其敢說“不”的能力有所提升。盡管如此,舞弊發生當年注冊會計師發表的非標審計意見比例(22.73%)仍然偏低,說明注冊會計師發現財務舞弊的能力仍有待提高。

表4 2020~2021年度舞弊樣本審計意見分布

表5 2010~2019年度舞弊樣本審計意見分布
三、財務舞弊公司新特征
新《證券法》實施后,監管部門對財務舞弊的監管出現了新動態,同時上市公司財務舞弊也呈現出一些新特征,值得監管部門和注冊會計師持續關注。
1.舞弊行業分布。表6列示了舞弊樣本公司的行業分布情況。由表6可知,在過往12年(2010~2021年度)的舞弊樣本公司中,“制造業”“農林牧漁業”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上市公司中涉及財務舞弊的較多,分別達到110家、16家和15家。結合相對數來看,在舞弊公司數量達10家以上的(子)行業中,“農林牧漁業”舞弊公司有16家,行業占比最高(9.58%),“制造業”二級行業“醫藥制造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的舞弊公司行業占比較高(分別為4.56%和4.25%),“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舞弊公司行業占比緊隨其后(4.05%)。

表6 舞弊樣本行業分布
從新《證券法》實施后的2020~2021年度看,財務舞弊公司出現的一個新特征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與“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舞弊公司數量和比例大幅提升,成為財務舞弊高發行業。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可能與并購游戲等輕資產公司帶來的巨額商譽暴雷壓力相關,如任子行(300311);“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可能與疫情影響下的公司業績下滑或業績對賭壓力相關,如華誼兄弟(300027)。
2.舞弊類型分布。表7列示了樣本公司的舞弊類型分布情況。從表7可以看出,過往12年(2010~2021年度)財務舞弊主要集中在對利潤表的粉飾和操縱上,其中:收入舞弊成為財務舞弊的“重災區”,占比為64.25%;費用舞弊和成本舞弊成為第三和第五大舞弊類型,占比分別為17.88%和11.17%。特別令人關注的是,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資金舞弊、資產減值舞弊已然成為第二和第四大舞弊類型,占比分別高達25.70%和16.20%。

表7 舞弊類型分布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2020~2021年度財務舞弊類型呈現出從利潤表操縱向利潤表與資產負債表聯動操縱的變動趨勢,特別是貨幣資金舞弊與資產減值舞弊的占比分別高達33.33%和24.24%,僅次于收入舞弊。已有研究表明,財務舞弊一般是以調節利潤表收入、毛利率項目為抓手,相應地會在資產負債表中留下諸多痕跡,并且這些痕跡的“消化”過程可能在跨年度、不同時點下呈現出不同的特征[3]。因此,一家公司在實施財務舞弊之后,為了“消化”虛增利潤表所帶來的資產類科目的“異常”,一般會選取合適時機進行“洗大澡”或通過“科目調節”轉移異常,以應對注冊會計師和監管部門對異常資產科目的重點關注。
可見,在新《證券法》實施后的兩年中,一方面監管部門與審計機構大幅增大了查辦財務舞弊的決心,主動識別舞弊公司在資產類科目存在的減值舞弊特征;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亦持續“升級”造假手法,例如與真實客戶、供應商等串通舞弊,借助貨幣資金完成業務流與資金流的“閉環”,以減少資產類科目的異常特征、掩蓋財務舞弊的真實面目。
3.收入舞弊手法分析。本文將收入舞弊區分為會計操縱類和交易造假類兩種類型進行進一步分析,相關數據的統計情況如表8所示。其中:會計操縱類主要表現為上市公司管理層通過選擇對自身更有利的會計判斷,以達到操縱業績的目標,最常見的手法就是提前確認收入;交易造假類主要表現為上市公司管理層虛構交易以達到虛增收入的目標,最常見的手法是通過與客戶或者隱性關聯方串通合謀虛構業務和收入。如表8所示,收入舞弊以交易造假類為甚,占比高達70%。

表8 收入舞弊具體手法
從具體實施手法的分布情況可以發現,近兩年來交易造假類收入舞弊的實施手法呈愈發隱蔽的趨勢,協助實施財務舞弊的“幫兇”從關聯方、隱性關聯方向真實客戶、供應商轉換,即從“無中生有”走向“真真假假”。例如,長園集團(600525)虛構與海外真實客戶銷售業務,并與海外客戶簽訂“陰陽合同”、備忘錄、承諾函或聲明,表示只是協助免稅清關,不存在付款義務等。這種變化一定程度上將大幅加大注冊會計師及監管部門識別舞弊的難度。對此,本文建議在修訂《會計法》時,從法律上明確配合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供應商、客戶和金融機構的民事和刑事責任,為注冊會計師發現財務舞弊營造更好的審計環境。
4.財務舞弊識別特征。本文基于五維度財務舞弊識別框架[3],利用公開披露數據,對66家樣本公司從舞弊發生當年至監管處罰前一年的財務異常特征和非財務異常特征進行統計分析(如表9所示),共涉及253個公司年度樣本,即一家公司可能涉及多個年度。由表9可知,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舞弊公司的非財務異常特征出現次數(885次)是財務異常特征(239次)的3.7倍之多。

表9 舞弊公司異常識別特征
在財務異常特征中,涉及會計估計的資產減值及研發支出類科目出現異常的次數最多,與收入舞弊相關的收入、毛利率、貨幣資金、存貨等科目和指標聯動異常特征的出現次數次之。
在非財務異常特征中,控股股東高股權質押等行為異常、前五大客戶/供應商出現關聯方/隱性關聯方、前五大客戶/供應商規模特征異常、公司頻繁收到非處罰類監管問詢等異常特征的出現次數最多。
四、結論與啟示
以上分析表明,新《證券法》出臺后,監管部門實行的“零容忍”嚴監管政策和注冊會計師執業時審慎性的提高,在發現和處罰上市公司財務舞弊方面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進展和成效,財務舞弊愈演愈烈的勢頭有望得到遏制。
1.制度出臺后打擊舞弊效果顯現。隨著新《證券法》及其配套法規的出臺與實施,監管部門打擊財務舞弊的力度前所未有,近兩年處罰公司數量大幅增加;雖然財務舞弊被發現仍存在滯后期,但處罰周期大幅縮短,3年以內發現財務舞弊的樣本公司占比從36.31%提高至51.52%;處罰金額大幅提高,例如作為首例適用新《證券法》的案例——廣東榕泰(600589)被處以300萬元罰款,董事長被處以330萬元罰款,財務總監、董秘和多位監事、董事、獨立董事被處以20萬~160萬元不等的罰款,累計罰款1450萬元,遠高于舊《證券法》下對康美藥業案件的累計595萬元的頂格處罰,而且廣東榕泰還將面臨投資者的民事索賠訴訟。盡管外部審計在發現財務舞弊方面的能力還有待提升,但注冊會計師在上市公司實施舞弊當年發表非標審計意見的比例從15.04%提升至22.73%,扭轉了2010~2019年度實施舞弊當年非標審計意見占比對比舞弊前一年非標審計意見占比不升反降的局面,表明注冊會計師發現財務舞弊的能力有所提升,審計期望的鴻溝有所縮小。
2.財務舞弊識別需密切關注行業特性。財務舞弊發生的頻率與行業特性有關,“制造業”和“農林牧漁業”的上市公司由于存貨與在建工程等資產難以核實、購銷環節較為復雜,依然是財務舞弊高發行業。此外,“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輕資產行業更易產生巨額商譽舞弊風險,“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受疫情影響的典型行業更易因業績下滑引發舞弊動機。注冊會計師和監管部門對這類新出現的財務舞弊高發行業的上市公司亦應當保持高度關注和警惕。為此,注冊會計師應當深入了解企業所在行業的如下幾個方面:(1)商業模式,包括其獲取營業收入和現金流量的主要方式,以及價值鏈中特別是購銷環節涉及的主要上下游企業;(2)財務結構,特別是資產負債和成本費用結構;(3)會計慣例,特別是收入確認方法;(4)經營情況,特別應關注企業的營業收入增幅、毛利率、銷售利潤率、產銷率等是否明顯與行業存在背離現象;(5)風險領域,對于企業的賒購和賒銷政策、結算方式和結算周期明顯有別于行業慣例,庫存水平和存貨周轉率明顯高于行業平均水平,或資產減值計提比例明顯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的現象,必須保持高度的職業懷疑態度,必要時追加審計程序,或者擴大審計范圍。
3.財務舞弊手法呈聯動化、隱蔽化趨勢。近年的財務舞弊類型呈現出鏈條拉長的趨勢,即從利潤表操縱向利潤表與資產負債表聯動操縱的方向發展,特別是2020~2021年度貨幣資金舞弊與資產減值舞弊占比分別高達33.33%和24.24%,僅次于收入舞弊。可見,將利潤表科目與資產負債表科目進行聯動指標核查的方法值得嘗試,對于涉及資產類科目“洗大澡”或“存貸雙高”等異常特征的年度尤其如此。
同時,操縱收入仍是上市公司慣用的伎倆,實施財務舞弊的“幫兇”從關聯方、隱性關聯方向真實客戶、供應商轉換,即從“無中生有”走向“真真假假”,收入舞弊手法與路徑愈發隱蔽。該變化一定程度上將大幅加大監管部門與注冊會計師識別財務舞弊的難度,有必要明確配合相關造假者的民事和刑事責任。因此,注冊會計師除了要重點核實隱性關聯方,還應重點核查已有客戶和供應商的交易規模與資金流,以便有效發現并遏制愈演愈烈且愈加隱蔽的收入操縱行為。
4.非財務信息的充分利用確有必要。現有企業財務舞弊識別模型主要基于企業披露的財務信息,而對非財務信息的利用不足[4]。從上文的分析可知,非財務異常特征對識別財務舞弊的作用已大幅超過財務異常特征,特別是大股東行為、高管行為、客戶與供應商等方面的異常特征。可見,僅僅依靠財務信息難以識別財務舞弊。監管機構應要求上市公司加大信息披露力度,特別是與財務信息緊密相關的非財務信息披露,如強制披露前五大客戶供應商名稱等;注冊會計師亦需提高對非財務信息的關注、獲取與利用程度,提升識別財務舞弊相關審計程序的不可預見性,加大上市公司應對注冊會計師舞弊審計的難度。
5.智能反舞弊迫在眉睫。利用智能技術識別財務舞弊行為,需要合適模型及足夠數據的支撐,而這一點又有賴于近期計算機科學在大數據領域的高速發展[3]。在實務工作中,財務數據相對容易獲取和處理,如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及附注的表格信息。而與大股東行為、高管行為、客戶和供應商異常特征相關的非財務信息來源較廣,如行業研究網站、工商信息網站、裁判文書網站等,且基本為非結構化數據。基于大數據技術及計算機技術的結合,能夠實現對大量非結構化數據的采集、存儲和處理,讓模型可以基于多源、多維數據進行高效分析。例如,針對游戲或平臺類互聯網企業的個人客戶充值IP地址分布、時間分布的大數據分析,該類反舞弊程序若僅僅依賴傳統人工審計模式,則往往效果不佳或者“有心無力”。
目前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在行業數據庫購置、舞弊識別模型構建以及信息化審計人才隊伍培養等方面都較為薄弱。從上文分析可知,常規的外部審計在發現財務舞弊方面雖有進步,但總體成效仍然有限,2020~2021年度的樣本公司中尚有77.27%的舞弊公司在當年未能被注冊會計師所揭發。這說明構建財務與業務相結合、會計數據與大數據相結合的財務舞弊識別模型,開發智能反舞弊工具確有必要。
【注 釋】
①摘自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252885605040062&w fr=spider&for=pc)。
②財務舞弊樣本公司主要來源于證監會的處罰公告,具體的數據來源于W IND數據庫。樣本選擇過程如下:從W IND數據庫中導出2020~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違規事件,并針對“違規類型”和“具體違規行為”字段進行手工處理,篩選出符合“財務舞弊”定義的上市公司66家,其中有3家上市公司(皇臺酒業、ST銀河及中創環保)存在重復舞弊的情況。
③新《證券法》實施后,除了大幅提高對財務舞弊的行政處罰金額,還引入了中國特色的代表人訴訟機制,大幅提高了舞弊處罰金額;此外,2020年12月發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亦大幅提高了舞弊相關的刑事罰金。本文僅統計因舞弊受到監管部門行政處罰的金額分布。
【主要參考文獻】
[1]黃世忠.上市公司財務造假的八因八策[J].財務與會計,2019(16):4~11.
[2]黃世忠,葉欽華,徐珊,葉凡.2010~2019年中國上市公司財務舞弊分析[J].財會月刊,2020(14):153~160.
[3]葉欽華,葉凡,黃世忠.財務舞弊識別框架構建——基于會計信息系統論及大數據視角[J].會計研究,2022(3):3~16.
[4]葉康濤,劉金洋.非財務信息與企業財務舞弊行為識別[J].會計研究,2021(9):3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