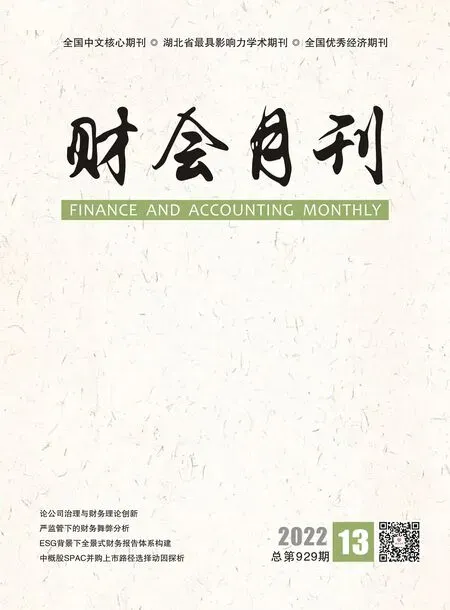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會影響創新戰略嗎
——基于創業板上市企業的檢驗
王曉亮(教授),吳金柯
一、引言
2020年10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做了重要報告,并指出“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從國家層面上看,基礎性創新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力量[1]。在此背景下,企業要更加重視創新戰略的制定,加大創新投入,推動國家目標的實現。從公司治理層面上看,股東和管理層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代理問題,管理層出于自利動機可能會抑制企業創新,不利于企業持續發展。有學者提出企業的委托代理問題越嚴重,企業創新投資越少[2],也有學者認為非控股股東參與公司決策,可以監督經理人,促進企業創新[3],還有學者認為非執行董事發揮監督效應,能降低代理成本,推動技術創新[4]。可見,如何有效抑制管理層的自利行為并提高企業創新戰略,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董事會由股東派代表組成,具有決策和監督管理者的職責,有學者認為董事政治身份、董事會規模與董事會獨立性的增加都有利于企業創新[5]。現有關于董事會治理與企業創新的研究大多將董事會視作一個整體,認為董事會是同質的。但事實上,董事會內部存在一種隱性層級結構即非正式層級,這會對企業創新戰略產生顯著影響。然而,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是否能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創新戰略仍需進一步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微觀層面的董事會治理為切入點,分析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戰略的影響。首先,本文分析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認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能夠發揮監督職能,降低代理成本,進而提高創新戰略。進一步分析中,本文就董事會正式層級、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做了差異分析;此外,還就不同股權集中度、不同兩職合一情況和不同產權性質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做了比較分析。最后,采取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再次驗證了本文的研究結論。
本文的研究貢獻表現在以下方面:①基于創業板上市公司分析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既豐富了非正式層級對公司治理的研究,也拓展了影響企業創新戰略的文獻;②在大力倡導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以微觀的董事會治理為切入點,試圖打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黑箱”,發現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促進效果以及作用路徑;③以往關于董事會治理行為相關文獻認為董事會成員是同質的,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獨立性等結構特征會對企業戰略、經營績效和投資決策產生顯著影響。但事實上,董事會對外兼職董事與是否具有政治關聯即社會資本顯著不同,這種差異會在董事會內部產生隱性的層級關系,影響董事會成員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對企業創新戰略產生顯著影響。
二、文獻回顧
(一)董事會治理行為對創新戰略的影響研究
關于董事會治理行為對創新戰略的影響,現有研究大多從董事會特征、董事會資本和董事會職能入手。從董事會特征來看:有學者對創業板上市公司進行分析,發現董事會規模與技術創新戰略呈倒U型關系,同時董事會獨立性越強,技術創新效果越顯著[6];也有學者認為,獨立董事占比高的董事會有利于企業創新活動,在非國有控股公司和法律制度更健全的企業中,增加獨立董事的數量能促進創新投入[5];還有學者認為,董事會中存在的兩職合一能夠提高企業創新決策,增加研發產出,提高研發效率[7]。從董事會資本來看:有學者根據資源依賴理論和管家理論進行研究,發現董事會社會資本有助于研發戰略[8],董事會人力資本的廣度對研發戰略具有消極作用,董事會人力資本的深度對研發戰略具有積極作用[9];也有學者從委托代理理論角度進行分析,認為董事會資本的廣度和深度對創新戰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可以提高企業創新投入,但是增加創新投入又可能引發沉沒成本、影響企業績效,管理層出于防御動機會采取保守策略以避免增加創新投入以及未來經營決策的不確定性,高管激勵可以使管理層認識到自身利益不會因為研發失敗而受損,反而可能會獲得長期利益,進而高管會改變以往抵制創新的態度,逐步與股東目標趨同[10]。從董事會職能來看:有學者認為,董事會監督可以遏制高管的投機行為,緩解企業創新不足問題,但是過多的監督反而會降低創新績效,因此董事會監督與創新戰略存在倒U型關系[11];也有學者認為,董事會與管理層關系越好,越能提升董事會的服務職能水平,增強高管和董事會創新意識,從而有利于促進創新戰略[12]。可以看出,現有學者關注董事會結構、董事會資本和職能等靜態因素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忽視了董事間的交流過程以及董事會成員的異質性。事實上,董事會成員間的交流過程對決策具有重要作用,在董事會決策之前,需要董事之間彼此交換信息,展開深入溝通,非正式層級形成的等級差異更好地揭示了成員間的互動交流過程。因此,相比于以往學者對董事會決策結果的研究,本文彌補了對董事會決策過程的研究。
(二)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決策行為的影響研究
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源于成員的影響力差異,促使董事間形成信任與尊重的等級排序,進而導致高位董事對低位董事的支配行為[13]。目前,學者們對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研究已取得豐富的成果。有學者認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績效有正相關關系:當董事會規模較大或者公司過去經營業績較好時,這種正相關性表現得更弱;當行業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這種正相關性表現得更強[14]。也有學者認為,非正式層級中的高位董事為了維護自身的社會聲譽,會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本為企業提供專業的知識和信息以及科學決策,監督低位董事瀆職行為,從而降低企業違規風險[15]。還有學者認為,非正式層級增強了低位董事的順從行為,減少了成員間的沖突,非正式層級的清晰度越高,越能降低董事會會議頻率、減少時間成本,董事會就越能快速達成一致意見,從而提高決策效率[16]。為進一步研究非正式層級對公司治理的作用,還有學者關注企業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認為非正式層級清晰度的增強,不僅可以降低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程度,而且能夠促進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調整速度[17]。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現在學術界和實務界已經認識到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重要作用,但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非正式層級可以提高企業決策效率和改善經營狀況上,沒有將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聯系起來,忽視了創新能力對公司長久發展的重要性,而且只有積極的創新才可以幫助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保持競爭力,并占據有利地位。鑒于此,本文試圖探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是否可以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促進創新戰略。
綜合來看,本文彌補了已有文獻的不足,從董事會成員個人背景的微觀層面入手,關注董事會成員間的動態交流過程,分析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是如何影響企業創新戰略的,有助于完善董事會治理與企業決策行為關系的研究,對企業緩解代理沖突、提高創新能力、制定創新戰略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三、研究假設
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社會經濟學認為契約雙方無法將所有事項納入正式契約之中,此時出于信任與尊重形成的關系契約會在實現組織任務和維系成員關系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8]。關系契約理論強調契約參與方的相互信任、相互監督和相互合作。在現實生活中,契約的執行更多地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尊重,當遇到社會地位更高的成員時信任感和尊重度自然也更高。在董事會團隊中,對實現公司目標貢獻更大的董事會成員會主動與其他成員建立聯系,其他成員也會更加信任和尊重這類董事,從而在董事會內部建立起信任和尊重的差異次序[14,19]。這種基于信任與尊重形成的等級次序維持和改善了董事會成員之間的關系,提高了董事會的工作效率。在董事會內部,高位董事利用自身兼職董事身份和政治關聯可以獲得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源,有能力幫助企業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由于董事間的信任和尊重存在差異,使得低位董事對高位董事具有依賴性,會順從高位董事的戰略決策,這種依賴和順從加深了其對高位董事的尊重和信任,高位董事出于實現公司目標的動機也會積極地領導低位董事,展示個人才華[20]。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領導與被領導行為會形成清晰的隱性層級關系,即非正式層級。
由于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目標不同,會引發代理問題。企業創新往往具有耗時長、風險高等特點。管理層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可能會逃避創新,減少研發投入,傾向于非創新活動。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可以提高董事會的監督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促進企業創新。具體來說:其一,非正式層級可以提高董事會對管理者的監督效率,緩解代理問題,促進企業創新。如果董事會內部缺少可以協調董事間競爭和對抗的成員,那么董事會成員會因為地位之爭產生矛盾和分歧,陷入競爭沖突[21]。在這樣的情況下,董事會內部缺少凝聚力和制衡度,極易淪為管理層的“附庸”,被管理層“控制”。董事會非正式層級通過關系治理加強了成員間的溝通交流,提高了董事會的凝聚力、制衡度和獨立性,避免董事會被管理層利用,加大了董事會與管理層的合謀成本,進而提高了董事會監督效率,抑制了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17]。現有研究表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清晰度越高,董事發表異議的可能性越低,當董事間地位差距較大時,組織內部受尊重的差異比較明顯,低位董事會自覺聽從高位董事的意見,有利于統一組織內部意見,增強董事會凝聚力,更好地發揮董事會監督職能[16]。如果董事會內部層級混亂,無法抑制管理層的自利行為,就會增加企業代理成本,不利于企業創新。
其二,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清晰度的提高能夠促進信息多元化交流,提高董事的認知水平,促進企業創新。董事會作為一個會議組織,往往需要在短時間內做出高質量的專業化決策[19]。非正式層級是基于董事間相互信任和尊重而形成的隱性機制,這種隱性機制有利于形成清晰的溝通渠道,促進董事間的信息和知識分享,降低了信息不對稱風險[22]。高位董事會利用其地位,促進董事會成員間的溝通交流,緩和成員間的矛盾沖突,并在日常交流中引入建設性沖突和批判性思維,激發創新活力,促進創新決策[23]。同時,低位董事也會積極配合高位董事決策建議,提高了溝通有效性[16]。非正式層級也為董事會會議提供了隱性的規則程序,協調與引導成員間的交流合作,比如明確董事會成員與誰交流、何時交流以及如何交流等問題[14]。可見,非正式層級促進了董事間的動態交流,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提高董事對企業創新的認知水平,增強企業的創新活力和創新協同能力。
根據以上討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 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呈正相關關系。
四、數據來源及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由于創業板上市公司大多是中小企業、高科技企業和新興企業,看重企業成長性,偏向于創新活動。因而本文選取2010~2018年創業板上市公司數據作為樣本,并作如下處理:①剔除具有退市風險的公司;②剔除金融行業公司;③剔除信息缺失的樣本。本文關于董事會政治背景相關數據來自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其他相關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剩余缺失值手工收集補全。對所有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回歸分析通過STATA15軟件進行。
(二)被解釋變量
本文研究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戰略的影響,選擇研發投入作為企業創新戰略的替代變量,衡量研發投入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種使用研發投入與營業收入之比表示創新戰略投入[25],用Rd1表示;第二種使用研發投入與企業總資產之比表示創新戰略強度[26],用Rd2表示;第三種通過研發投入取自然對數的方法表示創新戰略規模[24],用Lnrd表示。
(三)解釋變量
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是本文的解釋變量,以Gini表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最佳的表示方法是通過問卷的形式調查董事之間的尊重程度,但是這種方式耗時較長,成本較高,難以采用。所以,本文使用基尼系數表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其度量方法參見公式(1):

其中:Gini表示基尼系數;y表示董事影響力,用各個成員兼任其他公司董事數量和政治關聯之和計算,兼職其他公司董事數量以具體兼職數量取值,擔任過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ry表示根據董事會影響力在董事會內部對每一位董事的排名;cov(y,ry)表示二者的協方差;N是董事會成員個數;yˉ是y的平均數。
(四)控制變量
本文借鑒陳仕華和張瑞彬[16]等的研究方式,選取以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公司績效(Roa)、財務杠桿(Lev)、流動負債率(Dar)、資產有形性(Tan)、盈利能力(Pro)、管理費用率(Mer)、營運效率(Laz)和現金流(Cf)作為控制變量。此外,董事會規模會影響非正式層級的清晰度;股權集中度越高,說明公司少數股東掌握的權力越大,股權集中度越低,越能體現民主決策,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公司治理作用越明顯;董事會會議越多,說明董事會決策耗時越多,效率越低。因此,本文還引入董事會規模(Bsize)、股權集中度(Scen)和董事會會議頻率(Bmeet)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五)模型構建
為驗證H 1,研究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本文構建多元回歸模型一,具體參見公式(2):

其中,β0是常數項,β1~β23是各個變量對應的系數,?是隨機擾動項。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創新戰略的均值分別為0.071、0.018和17,三者的標準差分別為0.061,0.02和0.94,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雖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董事會結構,但是各個公司創新戰略各不相同;Gini的標準差為0.15,均值為0.23,說明不同公司的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存在顯著差異。本文涉及的其他控制變量的統計量與其他學者基本保持一致,不再贅述。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
利用公式(2)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可以看出:Gini與Rd1、Rd2和Lnrd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29、0.007和0.356,且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清晰度越高,越能提高企業創新戰略的投入、強度和規模,就越能促進企業創新。

表3 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分析
(三)不同代理成本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
前文實證結果表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本部分將探討在不同代理成本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促進作用是否存在差異。通過STATA軟件將高代理成本設置為2、低代理成本設置為1,分析高代理成本和低代理成本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大小。參照王曉亮等[17]的研究,使用“(管理費用+銷售費用)/營業收入”度量企業代理成本,用Agc表示,控制變量與前文一致,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第(1)、(3)、(5)列表示代理成本較低時的回歸結果,第(2)、(4)、(6)列表示代理成本較高時的回歸結果。從第(1)和第(5)列可以看出,當代理成本較低時,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呈正相關關系,第(3)列說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呈正相關關系但不顯著。當代理成本較高時,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可以緩解代理問題,降低代理成本,促進企業創新。

表4 不同代理成本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
(四)進一步回歸
1.董事會正式層級、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影響的差異分析。正式權力和非正式權力組成了領導者的權力影響力。受組織制度安排影響而產生的董事間等級差異構成了董事會正式層級[27]。企業是否創新不僅會受到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影響,還會受到董事會正式層級的影響。正式層級中權力最高的董事往往是重要的企業利益相關者,他會更加關注企業未來發展,也會鼓勵其他董事增強創新戰略決策,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層級的存在可激勵成員努力工作,職權高的董事在實現低層次需求時,會積極追求更高的成就,將自我價值與企業價值結合在一起,做出符合企業長期發展的高質量決策。職權低的董事為提高在正式層級中的地位,也會努力工作,并做出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決策。所以,董事會正式層級會積極地推動企業創新戰略的制定以及創新投入的增加。那么,董事會正式層級和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哪個更大?本文對此差異進行分析。使用對董事會正式權利賦值的方式表示董事會正式層級[28],對于既不是總經理也不是董事長的成員賦值為1,對于是總經理或者董事長的成員賦值為2,對于既是董事長又是總經理的賦值為3,進一步計算出董事會正式權利的均值和標準差,均值與標準差的商即為董事會正式層級,以董事會正式權利分布的變異系數衡量董事會正式層級,用Bfp表示。為了研究董事會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本文構建模型二,具體參見公式(3):

本文首先求出董事會正式層級和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回歸系數,用回歸系數除以標準差得出變異系數,然后通過比較變異系數的大小,分析董事會正式層級和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影響的差異,如表5所示。從第(1)、(2)列可以看出,Gini和Bfp對Rd1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29和0.03,且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和正式層級的清晰度都可以提高創新戰略投入,非正式層級的變異系數4.143大于正式層級的變異系數3.333,說明與正式層級相比,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投入的正向影響更大。從第(3)、(4)列可以看出,Gini和Bfp對Rd2的回歸系數均為0.007,且分別在0.01和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和正式層級的清晰度都可以提高創新戰略強度,非正式層級的變異系數3.5大于正式層級的變異系數2.333,說明與正式層級相比,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強度的促進作用更大。從第(5)、(6)列可以看出,Gini與Lnrd的回歸系數為0.356,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Bfp和Lnrd的回歸系數為0.159,但不顯著,說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規模的正相關關系更顯著,與正式層級相比,非正式層級對提高創新戰略規模的作用更大。

表5 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影響的差異
2.不同情境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分析。本部分分析不同股權集中度、是否存在兩職合一和不同產權性質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投入Rd1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股權集中度用Scen表示,低股權集中度取值為1,高股權集中度取值為2,回歸結果如表6第(1)、(2)列所示,可以看出:低股權集中度下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09,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高股權集中度下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04,但不顯著,說明股權集中度較低時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投入的影響更大,可能是因為股權集中度較低時不同董事可以自由發表各自看法,有利于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兩職合一用Dual表示,設定方式為當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時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回歸結果如表6第(3)、(4)列所示,可以看出:當存在兩職合一時,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08,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可能是因為公司設定兩職合一之后董事長和總經理由同一人擔任,能夠有效抑制管理層的自利動機,從而使得股東、董事會和經理層三者目標一致,有利于企業增加創新投入;當不存在兩職合一時,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05,但不顯著。公司產權性質用State表示,非國有控股公司取值為0,國有控股公司取值為1,回歸結果如表6第(5)、(6)列所示,從中可以看出,非國有控股公司中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07,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國有控股公司中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23,但不顯著,說明非國有控股公司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投入的影響更大。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非國有控股公司市場化程度更高,比國有控股公司面臨的市場環境更加激烈,所以非國有控股公司更加重視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作用,更愿意增加創新投入以占據有利的市場競爭地位。在國有控股公司中,公司決策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預,使得董事會的作用被削弱了。

表6 不同情境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結論的準確性,本文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
1.工具變量回歸。考慮到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可能存在因果關系,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本文將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用L.Gini表示。一般來說,滯后一期的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當期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存在相關性,但當期的創新戰略不會影響上一年的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即該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的條件,弱識別檢驗表明該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第二階段回歸結果表明,L.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76,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L.Gini和Rd2的回歸系數為0.016,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L.Gini和Lnrd的回歸系數為0.673,也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得出的結果與前文結論一致。

表7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2.PSM檢驗。為了克服樣本選擇偏差和遺漏變量造成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首先根據中位數大小對董事會非正式層級進行分組,高分位組取值為1,低分位組取值為0,結果變量為創新戰略,協變量為本文的控制變量。然后采用1∶1近鄰匹配方法,檢驗通過之后就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表明,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24,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Gini和Rd2的回歸系數為0.008,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Gini和Lnrd的回歸系數為0.369,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得出的結果與前文結論一致。

表8 PSM回歸結果
3.固定效應模型。為了消除不能觀察到的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異質效應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同時控制年度和行業,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12,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Gini和Rd2的回歸系數為0.004,且在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Gini和Lnrd的回歸系數為0.073,但不顯著,不過仍然可以證明模型一和模型二的穩健性。

表9 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4.剔除獨立董事重新計量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考慮到獨立董事的特殊地位,在計算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時剔除獨立董事,僅計算非獨立董事的兼職董事和政治關聯數量,仍使用基尼系數來表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并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限于篇幅,控制變量結果略,下同)。Gini和Rd1的回歸系數為0.025,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Gini和Rd2的回歸系數為0.004,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Gini和Lnrd的回歸系數為0.214,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剔除獨立董事之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依舊可以發揮公司治理作用,并提高創新戰略。

表10 剔除獨立董事回歸結果
六、研究結論、啟示與局限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論和關系契約理論,通過分析2010~2018年創業板上市公司數據,考察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得出的主要結論有: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能降低代理成本,促進創新戰略;進一步分析發現,與正式層級相比,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更顯著,對創新戰略的影響更大;在不同情境下分析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可以發現,在低股權集中度、存在兩職合一和非國有控股公司情形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創新戰略的影響更大。
研究結論對公司管理的啟示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企業要積極發揮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作用,優化董事會成員結構,吸收社會資源豐富和個人能力強的成員進入董事會,形成清晰的董事會層級。在等級觀念的社會環境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越清晰,對企業創新戰略決策的作用越大。二是優化董事會溝通渠道。良好的溝通可以使董事會快速達成一致意見,提高決策效率,比如定期召開董事會會議、董事之間有序發言等。三是企業在制定創新戰略時要積極考慮股權集中度、兩職合一等因素的影響。董事長和總經理不宜由同一人擔任,同時股權不宜過于集中。
本文研究的局限主要在于:僅以創業板上市公司為樣本得出的結論是否適用其他上市公司還有待考證;在衡量創新戰略時僅考慮了資金投入,未考慮人力資本投入,還可以使用研發人員占員工總數之比表示創新戰略,分析其與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關系;在分析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戰略的關系時,并未直接研究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創新產出、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對此需繼續研究。
【主要參考文獻】
[1]周文能.關于原始性創新與國家競爭力的思考[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11):53~60.
[2]左晶晶,唐躍軍,眭悅.第二類代理問題、大股東制衡與公司創新投資[J].財經研究,2013(4):38~47.
[3]李姝,翟士運,古樸.非控股股東參與決策的積極性與企業技術創新[J].中國工業經濟,2018(7):155~173.
[4]陳險峰,陳志強,李佳賓,胡珺.非執行董事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J].管理學報,2019(8):1188~1196.
[5]葉志強,趙炎.獨立董事、制度環境與研發投入[J].管理學報,2017(14):1033~1040.
[6]徐向藝,湯業國.董事會結構與技術創新績效的關聯性研究——來自中國中小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2):35~41.
[7]黃慶華,陳習定,張芳芳,周秝宸.CEO兩職合一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J].科研管理,2017(3):69~76.
[8]嚴子淳,薛有志.董事會社會資本、公司領導權結構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研究[J].管理學報,2015(4):509~516.
[9]馬璐,彭陳.過度自信調節下董事會人力資本與企業R&D投入關系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7):144~149.
[10]李小青,王夢潔,王玉坤.董事會資本、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R&D投入——基于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證據[J].工業技術經濟,2016(8):154~160.
[11]鐘熙,宋鐵波,陳偉宏,翁藝敏.董事會監督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基于監督復雜性的調節作用[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9(1):77~86.
[12]許強,王利琴,茅旭棟.CEO—董事會關系如何影響企業研發投入?[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9(4):126~138.
[13]馬連福,高原,杜博.隱形的秩序: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研究述評及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9(4):111~125.
[14]He J.,Z.Huang.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Exploring a tacit structure guiding boardroom in?teractions[J].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2011(6):1119~1139.
[15]劉振杰,顧亮,李維安.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公司違規[J].財貿研究,2019(8):76~87.
[16]陳仕華,張瑞彬.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董事異議的影響[J].管理世界,2020(10):95~111.
[17]王曉亮,鄧可斌.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會提升資本結構決策效率嗎[J].會計研究,2020(8):77~90.
[18]Johnson S.,K.Schnatterly,J.F.Bolton,C.Tuggle.Ante?cedentsof new director social capital[J].Journal of M anagement Studies,2011(8):1782~1803.
[19]謝永珍,張雅萌,張慧等.董事會正式、非正式結構對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影響——非正式溝通對董事會行為強度的調節作用[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5(4):15~28.
[20]Volonte C.,Gantenbein P..Directors'human capital,firm strategy,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 anagement and Gov?ernance,2016(1):115~145.
[21]Huse M..Boards governance and value creation:The hu?man si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2007(4):439~444.
[22]何瑛,馬添翼.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并購績效[J].審計與經濟研究,2021(2):74~84.
[23]薛坤坤,武立東,王凱.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如何影響企業創新?——來自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預測,2021(3):25~31.
[24]馬連福,張燕,高塬.董事會斷裂帶與公司創新戰略決策——基于技術密集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預測,2018(2):37~43.
[25]李井林,陽鎮.董事會性別多元化、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技術創新——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9(5):34~49.
[26]周建,李小青.董事會認知異質性對企業創新戰略影響的實證研究[J].管理科學,2012(6):1~12.
[27]李長娥,謝永珍.董事會權力層級、創新戰略與民營企業成長[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7(12):70~83.
[28]衛旭華,劉詠梅,岳柳青.高管團隊權力不平等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J].南開管理評論,2015(3):2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