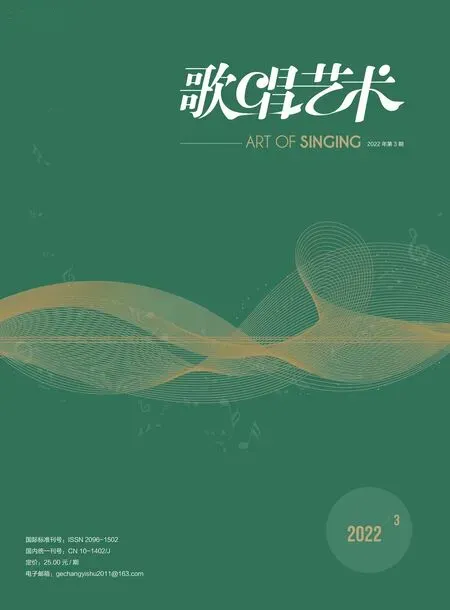陪伴歌者
—— 和鄧垚老師聊鋼琴伴奏
徐艷玲整理
訪談者:俞子正,男高音歌唱家,《歌唱藝術》常務副主編。
嘉賓:鄧垚,鋼琴家,作曲家,中國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2003——2005年,連續三屆榮獲“中國音樂金鐘獎”之“全國最佳伴奏獎”。2007年,榮獲“中國音樂金鐘獎”之“特殊貢獻獎”。2012年,榮獲文化部“第十屆全國聲樂比賽”之“鋼琴藝術指導獎”。
(下文中,俞子正教授簡稱“俞”,鄧垚老師簡稱“鄧”。)
鄧垚好!好久不見,出于疫情的原因,演出和比賽少了,所以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是啊,但是您說要和我在《歌唱藝術》上聊聊,我很高興,也確實有很多話可以和學習聲樂的朋友們聊聊。
您現在很“火”,幾乎所有上規格的比賽和演出都有您的身影,很多歌者都非常崇拜您。有歌手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讓鄧垚老師彈一次伴奏,此生無悔,您感覺如何?
我不敢用“火”這個字。實際上,鋼琴伴奏這個職業,我覺得是服務性行業的典型代表,我就是為大家服務的。一些上規格的比賽和演出都有我,是因為我覺得大家需要我。更多大家沒看到的,一些小規模的比賽和演出,我也在。比如說,我也經常為考學的孩子們彈伴奏,而一些程度比較差的孩子,我也愿意盡我所能地為他們服務。我覺得鋼琴伴奏,首先就是要陪伴,這些孩子從聲樂愛好者到最后成為歌唱家,慢慢地陪伴他們的這個過程,讓他們能成才。所以,我不能叫自己藝術指導,我其實就是一個踏踏實實的鋼琴伴奏,從點點滴滴做起,陪伴歌者、陪伴教師、陪伴未來的歌唱家。于我而言,我希望以后更多的就是陪伴,陪伴中國聲樂的發展時間長一些,期待他走向世界。
現在很多人自詡為“藝術指導”(coach),有些人伴奏彈得一塌糊涂,也說自己是藝術指導。一夜之間,“鋼琴伴奏”紛紛搖身一變,成了藝術的“指導者”。我聽您還是說自己是鋼琴伴奏,您是謙虛呢?還是……

說到藝術指導,我覺得首先要加上“鋼琴”兩個字,鋼琴伴奏最多能叫“鋼琴藝術指導”,但是為什么很多人都管自己叫“藝術指導”呢?這可能是借鑒了國外歌劇界、聲樂界的慣例。因為,在國外的藝術指導,他們被統稱為藝術指導,實際上已經超越了鋼琴伴奏。尤其像國外的歌劇藝術指導,簡直太棒了,他們不僅能彈能揮,自己還能唱,所以它包含了語言,像德語、意大利語、法語等;再加上歌劇的角色、內心、對白,在合樂隊之前都給走臺了,藝術指導是這么一個角色。我們現在統稱的藝術指導,是因為看到了這個名詞而統一過來。
那么,目前我們能不能做到藝術指導呢?實際上,是不能的。我并不是謙虛,因為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鋼琴伴奏,在某些歌上,我可以給學生一些指導,所以最多只能叫作鋼琴藝術指導。我并不能做到像咬字、外語,或者更全面的一些指導。所以,我認為鋼琴伴奏就是鋼琴伴奏,服從于主課教師,不能越位,既不能講得太多,也不能不講。因為聲樂教師是宏觀的,他們對學生的發展有較全面的計劃,一年級唱什么歌,二年級唱什么歌,直到五年級。有時候我確實好心,可能對一年級的孩子講了五年級的概念,他們反而不會唱了,所以應該慢慢來啊。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本色”問題,一點點地配合主課教師,把主課教師對孩子的期待,或者他想讓孩子在什么程度呈現什么樣的作品去完成好。
我在很多比賽和演出中看到您確實很忙,但是您又創作了很多好聽的歌曲,您覺得創作和演出之間有什么聯系?譬如,通過演出可以知道大家喜歡什么樣的風格,您是投其所好,還是堅持自己的個性、自己的音樂語言,使得大家都喜歡您的作品?
確實忙,所以我并不是職業創作的,有時候一首歌要構思很長時間才下筆。比如說,這段時間我想給張群航寫一首歌,詞的靈感是電視劇《甄嬛傳》里一個訣別書的詞,我希望能寫一段屬于張群航的古詩詞歌曲,所以我也在思考,兩者的關系是什么呢?有句古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彈了很多的伴奏,我也從其中汲取了很多營養,在創作的時候就特別有幫助。雖然我本身是學作曲的,但是現在的職業是鋼琴伴奏。我是這么定位的——職業是鋼琴伴奏,事業是作曲。我一生都會給大家彈伴奏,但是我的目標還是能寫出更好的歌,希望大家喜歡。
至于風格,我在不同的時間段有不同的風格,通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和感知,對某個風格比較喜歡,我就進行創作,并沒有固定模式。關于我的音樂語言,相對來說,我認為自己從2008年開始寫了兩首新歌至今,我的音樂語言就是偏通俗、流行,因為中國聲樂在進步,演唱在進步,所以中國聲樂作品的創作在進步,鋼琴伴奏也在進步。現在的伴奏帶都已經非常“流行”了,非常與時俱進了,包括鋼琴伴奏的織體和語言。“抖音”經常有人說我彈琴有點兒“垚里垚氣”的,這個可能有褒義也有貶義,但是我覺得也挺合適,能給大家帶來一些新的感知。
我也關注到您出現在民族聲樂賽場比較多,相比之下,“美聲”賽場可能少一些,也許是我在“美聲”賽場當評委,太期待您出現了。那么,您跟那么多民族聲樂歌唱家和選手合作,您對目前民族聲樂作品的創作水平有怎樣的評價?從作曲專業角度說說。
這個我可以“凡爾賽”一下,為什么呢?“美聲”我也彈,但是后來確實民族聲樂彈得太多了。以前,“金鐘獎”是“民族”“美聲”“流行”一起比,所以“流行”我也彈。比如說,我彈的“流行”(歌手)獲金獎的有周強,就是現在火箭軍政治部工作部文工團的周強。我彈的“美聲”獲金獎的有楊陽,真可惜,他已經不在了。我其實彈過很多,包括戴玉強老師等。后來,“金鐘獎”比賽就分開了,“美聲”是“美聲”,“民族”是“民族”,“流行”還拿出去比,所以我就沒法都彈了。那我彈的比較多的是“民族”,我就固定在“民族”場地彈了,如果兩個場地同時比,我也串不開場。
至于“美聲”的鋼琴伴奏,我覺得首先要尊重原譜,尤其是藝術歌曲,德奧藝術歌曲。歌劇也是這樣,必須嚴謹。比如說,彈莫扎特的歌劇選段,必須要尊重當時的年代感,風格必須要統一。
至于對民族聲樂作品的評價,我覺得就是既要傳承,又要創新,我內心其實是有一個模板吧。我也有自己的偶像,比如說,趙季平老師,就是既要好聽,又要有民族性。我那會兒要考趙季平老師的博士,后來因為他身體不好,那年就沒考。其實在2003年,王夢潔老師和李雙江老師作為見證人,我跪地磕頭,敬茶拜了趙季平老師為干爹。但我并沒有拜師父,為什么?因為我個人更崇拜他,所以也想孝敬他。他就是我的榜樣和模板,他寫的這種音樂,像“新三國”,每次聽起來都耳目一新。實際上,我最早的創作靈感很多都是他給予的。我認為民族聲樂作品首先還是要有民族性,但也要接軌現在的流行音樂,包括大家愛聽的,因為還有廣大的受眾群體。
我聽您的伴奏,之所以讓那么多歌唱家和選手喜歡,當然,首先是您人品好、專業好。其次,在技術上,您能夠給歌者更多的情緒依托,也比較熟悉歌者的呼吸和樂句。學習聲樂的人和學習器樂的人不同,讀譜常常不嚴謹,有時候很自由,甚至“自由化”,所以彈聲樂伴奏不太容易。我聽您伴奏里有很多即興的成分,包括音型的變化、和聲的變化,是根據歌者的情況做出的補救,還是根據您自己的愛好事先設計好的?
哈哈,人品好是必須的。我又要說到服務性行業了,因為鋼琴伴奏的工作性質就決定了你必須得人品好,要配合,是永遠的綠葉。那么,您說到是不是根據歌者的情況做出的補救呢?實際上,我不是要根據歌者的能力去做變化,我會在之前有大概的設計。在合伴奏的時候,我已經為這個歌者量身定做了鋼琴伴奏,調整和即興也都是提前設計過的,不是真的即興。如果是考生,相對來說,我會注意簡單一點,或者哪怕我特別即興的右手給旋律,這也是為了考生,為了他們的音準。比賽又有比賽的考慮,這都是要提前跟歌者溝通。舉個例子,《敕勒歌》中間的轉調,我一定要先把調轉過去,再讓歌者張嘴唱,為什么?因為我已經把調轉好了,再張嘴唱就不會跑調。如果只是為了有效果,就應該間奏不轉調,這樣處理會有意外的效果,但是所有的處理都跟歌者提前商量過了。所有的變化、所有的自由都是提前設計好的,我并不能絕對的自由。個別音,某些音,有沒有即興的成分呢?有!但整體布局是必須提前思考的。所以很多人說,聽鄧老師彈琴,可能是即興彈的,但聽起來卻比正譜好。這個問題,我一點兒都不含糊,絕對彈得是比正譜好,簡單、有效果,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我覺得這也跟作曲(功底)分不開。因為學了配器,我會更全面地考慮音樂的整體效果。因為學了復調,我能夠更好地處理聲部間的呼應。因為學了和聲,我能夠讓歌曲的和聲色彩更豐富。因為學了曲式,我對歌曲的結構有了更宏觀的把握。我所考慮的不僅僅是一首歌,有時比賽可能要唱兩三首,考研要唱四首。有時要彈音樂會,得整體布局,才能引人入勝,才能讓聽眾慢慢地、靜靜地聽歌者唱下去、聽我彈下去,什么時候是鋪墊,什么時候是高潮,什么時候要滿足你所有的審美體驗。
我在“抖音”上經常關注您的動態,您的短視頻里有許多很有趣的場面,譬如“釣魚要到島上釣”“終于練成了用意念翻譜子的功力”,等等。可以看出,您是一個快樂的人,一個勤勞的人,一個有趣的人,一個浪漫激情的人。而聽您伴奏的音型、和聲色彩,您是一個內心豐富的人,我非常喜歡!那么,您覺得生活中最大的樂趣是什么?
生活中最大的樂趣是什么呢?對我來講,最大的樂趣是吃,我非常喜歡美食。我全國各地去過不少地方,但是讓我說風景名勝,我真的記不住,但可以問我去哪兒吃。我覺得我首先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因為愛吃;其次,就是音樂家一定都是美食家。因為我自己在不忙的時候,也會燒燒菜、做做飯。這跟創作是有相通之處的,也有靈感。所以我經常說吃過的好吃的,我一定要能自己也能做出來。
哈哈,這個我有同感,對于人生來說,吃喝都馬馬虎虎,那還能“樂業”嗎?我有些朋友喜歡關在家里“做學問”,對吃喝沒有要求,粗茶淡飯,比較簡單,而不是精致。偶爾相聚,也是只談學術,即使笑,也不會暢懷大笑,真的很讓人佩服他們是如何堅持成了習慣的。您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我們的生活應該是豐富多彩的,有開心也有失落,有溫暖也有傷感。現在我們來談談您的學習經歷,是一帆風順的,還是經歷磨難的?
我是1991年上的中國音樂學院附中,1994年上的大學,一直學的是作曲專業。學習上來講,我也沒有太受什么磨難,只不過就是在選擇工作上。大學畢業以后,我雖然是搞創作,但是一個作曲系的本科生的確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就選擇去文工團彈鋼琴伴奏。彈了20年鋼琴伴奏,得到大家的肯定,同時也寫歌。后來這個文工團解散了,我現在又來到了中國音樂學院。我還是很知足的,因為我覺得始終是為大家服務,大家需要我啊。不管是彈伴奏還是寫歌,只要大家喜歡,我就愿意一直這樣下去,為更多的人服務。
中國聲樂界大部分“名家”,您都合作過,我覺得您無形中成了鋼琴伴奏這個專業中的榜樣或者說是標桿。您也許謙虛、不承認,但事實如此。作為一個榜樣,您想對全國的鋼琴伴奏同行說點什么?
不能說自己是榜樣,我只能說我爭取做一個中國聲樂、民族聲樂的領頭羊吧。真的不能說是榜樣,我只是想給大家多一些在音樂上的思考。我1992年開始從附中彈伴奏至今,30個年頭。起初,我也沒想到,通過自己能改變民族聲樂的一些理念、觀點、表現手法,包括大家的聽覺。實際上,大家的聽覺這么多年還是略有改變的,也很接受這種相對有一些變化的、比較新穎的鋼琴伴奏的和聲和織體了,我想一直努力下去。
很多人都說,鄧老師,你怎么不多寫點歌、多配點器呢?我覺得是這樣的,很多這種創作靈感都來自鋼琴伴奏,所以我要多彈點兒。我要跟我的同行說什么呢?要大量地積累曲目,首先要多彈。我也慢慢開始帶研究生了,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帶博士。我理想中的鋼琴藝術指導這個專業方向就應該是全能的,但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中國歌、外國歌都能彈,包括流行、音樂劇,這是一個鋼琴藝術指導全面發展的方向,但又術業有專攻。比如說,跟我們佳林老師多切磋,張老師的“美聲”作品彈得好。所以,我們要成立藝術指導學會,當然這也是愿望啊。然后,給廣大的鋼琴伴奏者普及一下“美聲”鋼琴伴奏、民族聲樂鋼琴伴奏,也多普及即興鋼琴伴奏。在中國音樂學院,以龔荊憶老師為帶頭人,還有我和任卓。任卓主要講中國歌劇的鋼琴伴奏,龔荊憶老師主要講中國藝術歌曲的處理,我主要講即興伴奏。我們仨是個小團隊,也去過很多學校講學,特別受歡迎。因為我們的側重點不一樣,又都是圍繞中國聲樂。我要說的就是任重而道遠,希望大家整體提高,團結一心,為更多的人服務。鋼琴伴奏其實是這么多年并不被特別重視的一個藝術行當,近兩年可能稍微好一點了。所以我們要努力,大家不僅要提高自身的專業能力,還要提高服務水平,讓大家既重視我們,又欣賞我們。
我們在舞臺上和“抖音”里看到的您總是快樂的,您有煩惱嗎?是什么?
我沒有太多的煩惱,我的煩惱其實跟大家都一樣,柴米油鹽醬醋茶。還有就是孩子,我的孩子也要考學,也要學習,也就是生活上一些簡簡單單的煩惱。在專業上,我是沒有煩惱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取得更多的好成績。比如說,“金鐘獎”能不能每屆多設定十個金獎之類的,我希望我彈的選手都能獲得金獎,這就是我的“煩惱”。在舞臺和“抖音”里,我是快樂的,我想讓我的快樂感染更多的人。
十分感謝俞老師給我這個機會,雖然這個采訪,我的回答可能有點兒簡單,但是我說的都是真話。我特別喜歡跟您多請教,跟您多聊天,有機會希望咱們見面再聊聊。
謝謝您!和您聊天很舒暢,您說的都是實話、真話,沒有一些“大師”說得挺嚇人但又嚇不到人的虛話、大話和胡話。而且,我們看到了一個在舞臺下真實的鄧垚,也給我一些啟發。譬如說,我們是否應該對目前的鋼琴伴奏課程和作曲課程進行一些反思呢?如何把研究、學習和實際運用更好地結合呢?所以我想,今天的采訪會引發全國的鋼琴伴奏者和聲樂學習者很多思考,我們還會在舞臺上和“抖音”上感受您熱情洋溢的“垚里垚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