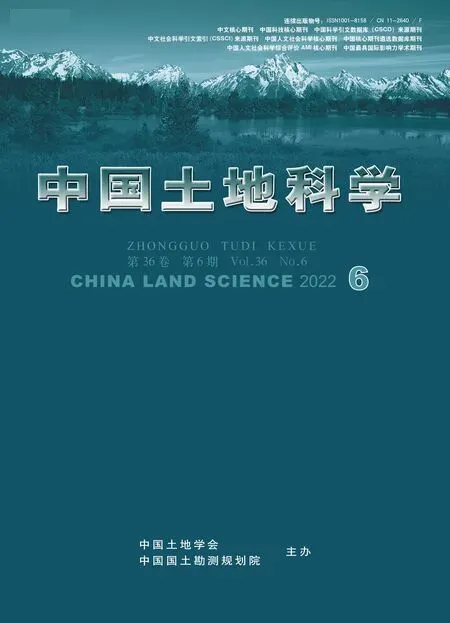廣東省城市更新績效的時(shí)空變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柯心怡,李景剛,2,李 燦,2,孫傳諄,2
(1.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 廣東 廣州 510642; 2.自然資源部華南亞熱帶自然資源監(jiān)測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 廣東 廣州 510700)
1 前言
當(dāng)前,在城市轉(zhuǎn)型升級與新增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收緊的雙重約束下,我國城市發(fā)展重心由增量建設(shè)轉(zhuǎn)向存量提質(zhì)。廣東省自2008年始與原國土資源部攜手共建節(jié)約集約用地試點(diǎn)示范省,開展以“三舊”改造為特色的城市更新工作,取得了卓越成效。據(jù)統(tǒng)計(jì),截至2019年11月22日,全省通過“三舊”改造累計(jì)節(jié)地面積13 226.67 hm2(19.84萬畝),節(jié)地率達(dá)42.7%;每畝建設(shè)用地年產(chǎn)出由2008年底的13.7萬元增加到2018年底的30.94萬元,增長125.84%①馮善書,黃敘浩.民資占比86.61% 廣東撬動萬億資本力促舊改新突破. 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1911/27/c2845263.html。。然而,隨著易拆遷、增值空間大的項(xiàng)目陸續(xù)完成,城市更新遭遇了“十年之癢”:拆遷難、成本高、政策更新滯后等問題日益凸顯,城市更新陷入停滯困境。如深圳市,截至2018年底,已列入計(jì)劃的城市更新項(xiàng)目共計(jì)746個(gè),但實(shí)施率只有37%,余下的項(xiàng)目中至少有60%因拆遷問題而擱置②王春艷.舊改10余年實(shí)施率不足40%,深圳終于對釘子戶下狠手了!https://www.sohu.com/a/409513544_120179484?_f=index_pagefocus_1&_trans_=000014_bdss_dkhkzj。。另一方面,不同地區(qū)的城市更新績效呈現(xiàn)明顯異質(zhì)性,截至2020年10月,廣東省內(nèi)的東莞、珠海、江門三市已實(shí)施的改造項(xiàng)目平均完成率超過70%,肇慶、佛山、惠州的完成率介于60%~70%,而深圳、廣州、中山三市的完成率小于60%③中指研究院.2020中國城市更新評價(jià)指數(shù)(廣東省)研究報(bào)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632055008725601&wfr=spider&for=pc。。為推動全省“三舊”改造取得突破性進(jìn)展,2019年廣東省自然資源廳制定了《廣東省深入推進(jìn)“三舊”改造三年行動方案(2019—2021年)》,繼續(xù)深化土地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對各市的改造目標(biāo)任務(wù)做出了要求。時(shí)間緊,任務(wù)重,如何高效地開展城市更新成為各級政府亟需解決的現(xiàn)實(shí)問題。為此,迫切需要對廣東省近十年來的城市更新績效進(jìn)行科學(xué)評價(jià),探尋影響因素,為城市更新科學(xué)推進(jìn)提供依據(jù),同時(shí),需要甄別和評估城市更新績效的空間異質(zhì)性,避免“一刀切”的城市更新治理策略造成效率損失。
城市更新作為一種在規(guī)劃指導(dǎo)下開展的規(guī)律性、目的性的建設(shè)活動[1],其本質(zhì)上是實(shí)現(xiàn)資源重新配置的一種空間生產(chǎn),是盤活存量土地空間、促進(jìn)資源要素有效流動的城市建設(shè)和固定資產(chǎn)投資活動[2],其核心要義在于如何在城市用地規(guī)模不增加的情況下,通過已建設(shè)用地的內(nèi)生提質(zhì)來實(shí)現(xiàn)城市功能的優(yōu)化以及空間品質(zhì)的提升[3],其基礎(chǔ)評判標(biāo)準(zhǔn)在于以最小化的土地、資金等的要素投入,實(shí)現(xiàn)土地集約和城市優(yōu)化等最大化的結(jié)果產(chǎn)出[4]。由此可見,城市更新績效的內(nèi)涵實(shí)質(zhì)上與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績效內(nèi)涵(即效率)一致,其測度問題可以轉(zhuǎn)化為對廣義投入與產(chǎn)出關(guān)系的測度,即城市更新的投入產(chǎn)出效率。近年來已有研究開始關(guān)注城市更新績效問題,主要采用“指標(biāo)體系—綜合評價(jià)”的研究范式對城市更新的綜合績效展開定量評估,但在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上尚未達(dá)成共識[5],且對于指標(biāo)的選取大多選用間接反映城市更新績效的指標(biāo)[6-8],難以充分反映城市更新的真實(shí)效果。此外,已有關(guān)于城市更新績效評價(jià)的研究在評價(jià)方法上以模糊綜合評價(jià)法[9]、AHP-TOPSIS模型[10]為主,將城市更新視作為一項(xiàng)靜態(tài)的、只注重產(chǎn)出的工作,忽略了城市更新投入與產(chǎn)出的動態(tài)性和多目標(biāo)性[11]。鑒于DEA模型在多指標(biāo)數(shù)據(jù)處理具有相對優(yōu)勢,且既不需設(shè)定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的具體形式,也不需指標(biāo)量綱一致,還可避免人為確定權(quán)重的主觀性[12],再與Malmquist指數(shù)結(jié)合,可以彌補(bǔ)DEA模型對動態(tài)效率考察的不足[13],對于城市更新績效動態(tài)評價(jià)具有較強(qiáng)的適應(yīng)性。因此,本文將綜合采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數(shù)對廣東省21個(gè)地市2008—2018年的城市更新進(jìn)行績效評價(jià),在此基礎(chǔ)上借助Tobit模型探索城市更新績效的影響因素,以期為廣東省及各地市的城市更新工作有序推進(jìn)提供理論指導(dǎo)和政策設(shè)計(jì)支點(diǎn)。
2 分析框架與理論分析
2.1 城市更新績效評價(jià)分析框架
“4E”績效審計(jì)準(zhǔn)則最初用于考察政府部門的財(cái)政支出活動,是評價(jià)政府財(cái)政支出績效的基本工具[14],主要包括經(jīng)濟(jì)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效果性(Effectiveness)和公平性(Equity)4個(gè)方面,貫穿于要素投入、產(chǎn)出、效果等過程[15]。近年來,“4E”準(zhǔn)則的評估框架已延伸到城市更新領(lǐng)域,如城市更新空間績效評估[1]、城市有機(jī)更新效果評估[7]等。從投入層面來看,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chǎn)要素的投入是城市更新項(xiàng)目啟動的基礎(chǔ),要求以盡可能低的要素投入,提供與維持既定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城市更新產(chǎn)品或服務(wù),實(shí)現(xiàn)要素投入的“經(jīng)濟(jì)性”[16];城市更新的要素投入最終能實(shí)現(xiàn)多大比例的成功改造,則體現(xiàn)了“4E”準(zhǔn)則中的“效率性”[7];城市更新的“效果性”更多體現(xiàn)在其對預(yù)期效益的實(shí)現(xiàn)程度上[17];城市更新是在城市用地緊缺的情況下所提出的釋放土地效能、改善公共配套、增加公共服務(wù)產(chǎn)品供給、提高人居環(huán)境的政策,其所帶來的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優(yōu)化和人居環(huán)境整治能否惠及更多社會人口,則體現(xiàn)了城市更新的“公平性”[18](圖1)。

圖1 城市更新績效評價(jià)分析框架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urban renew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2.2 城市更新績效評價(jià)指標(biāo)體系
基于城市更新的“4E”績效評價(jià)分析框架,本文采取“投入—產(chǎn)出”模型評價(jià)城市更新績效,并以經(jīng)濟(jì)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為一級指標(biāo)構(gòu)建城市更新績效評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借鑒已有研究,考慮到經(jīng)濟(jì)性為投入屬性,一般指資本、土地、勞動力投入[19],為此,本文以城市更新改造規(guī)模表示土地投入,城市更新的政府和社會投資額表示資本投入[11]。考慮到效率性為產(chǎn)出屬性,一般指投入與產(chǎn)出之間的轉(zhuǎn)換關(guān)系[20],因此本文以改造完成率來反映[7]。效果性衡量產(chǎn)出對實(shí)現(xiàn)最終目標(biāo)所做貢獻(xiàn)大小[21],本文根據(jù)城市更新的目標(biāo)選取了土地集約效益和城市發(fā)展效益作為其二級指標(biāo),并以節(jié)地率和節(jié)地面積代表土地集約效益[22],以單位面積土地產(chǎn)出[23]和土地出讓收入[24]表示城市發(fā)展效益。公平性要求產(chǎn)出的產(chǎn)品或服務(wù)在社會群體中無差別分配[20],因此,本文選取社會公平效益作為其二級指標(biāo),并以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作為具體表征[25]。詳見表1。

表1 城市更新績效評價(jià)指標(biāo)體系Tab.1 Index system of urban renew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2.3 城市更新績效影響機(jī)制分析
城市更新績效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jié)果。通過梳理相關(guān)文獻(xiàn),本文將從生產(chǎn)要素投入、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市場化程度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4個(gè)方面進(jìn)行分析(表2)。

表2 城市更新績效影響因素及量化指標(biāo)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urban renewal performance
生產(chǎn)要素投入。土地、資金等生產(chǎn)要素是城市更新的基礎(chǔ)。在城市更新初期由于缺乏經(jīng)驗(yàn),實(shí)施與規(guī)劃脫節(jié),生產(chǎn)要素投入難以轉(zhuǎn)化為預(yù)期的產(chǎn)出[26]。隨著城市更新政策不斷完善,規(guī)劃引領(lǐng)與計(jì)劃管理加強(qiáng),生產(chǎn)要素投入規(guī)模不經(jīng)濟(jì)的現(xiàn)象得以糾正,城市更新績效將有所提升。可見,生產(chǎn)要素投入與城市更新績效存在非線性關(guān)系,故本文選取總投資額及其二次項(xiàng)來解釋生產(chǎn)要素投入對城市更新績效的影響。
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現(xiàn)階段中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隨經(jīng)濟(jì)集聚程度提高而增加[27],較高的經(jīng)濟(jì)水平需適配高質(zhì)量的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來滿足發(fā)展的需要,從而推動了城市更新進(jìn)程。因此,本文以人均GDP表征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28],預(yù)期影響為正。
市場化程度。在市場經(jīng)濟(jì)條件下,政府對土地利用行為的過度干預(yù)會降低經(jīng)濟(jì)活力,造成效率損失[29],而市場作為要素配置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提升城市更新效率。因此,本文以城市更新社會投資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反映市場化程度,預(yù)期作用為正。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在土地資源約束下,城市往往通過促進(jìn)產(chǎn)業(yè)新陳代謝和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升級來實(shí)現(xiàn)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和空間優(yōu)化布局[30],顯然產(chǎn)業(yè)相對發(fā)達(dá)的城市對城市更新的需求更為迫切。因此,本文選取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產(chǎn)業(yè)與第二產(chǎn)業(yè)增加值的比重反映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31],預(yù)期作用為正。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壓力[32]和地方財(cái)政壓力[33]是城市發(fā)展的重要驅(qū)動因素,這些發(fā)展壓力將內(nèi)趨地方政府有效盤活存量土地,從而促進(jìn)城市更新項(xiàng)目的落實(shí)。為此,本文以人口規(guī)模和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面積作為土地利用壓力的表征,以“(一般公共預(yù)算支出-一般公共預(yù)算收入)/一般公共預(yù)算收入”反映地方財(cái)政壓力,作為控制變量。
3 模型與方法
3.1 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以廣東省21個(gè)地市作為城市更新績效的評價(jià)單元,相關(guān)社會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2009—2019年的《廣東省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城市建設(shè)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城市統(tǒng)計(jì)年鑒》、Wind數(shù)據(jù)庫等,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面積、“三舊”改造數(shù)據(jù)來源于廣東省自然資源主管部門。
3.2 研究方法
(1)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法。根據(jù)“4E”績效評價(jià)準(zhǔn)則中的經(jīng)濟(jì)性原則,城市更新應(yīng)當(dāng)以盡可能低的要素投入,生產(chǎn)出既定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產(chǎn)品或服務(wù),因此,本文選擇DEA模型中規(guī)模報(bào)酬可變(VRS)條件下的BCC投入導(dǎo)向效率模型來評價(jià)城市更新靜態(tài)績效[34]。此外,投入導(dǎo)向DEA模型要求輸入的投入指標(biāo)大于0,但本文選取的城市更新政府投資額和城市更新社會投資額兩個(gè)指標(biāo)均存在部分年份的數(shù)據(jù)等于0的情況。因此,本文將城市更新政府投資額和城市更新社會投資額兩個(gè)指標(biāo)同時(shí)加上0.001使其大于0后,再納入模型進(jìn)行測算[35]。
(2)Malmquist指數(shù)。Malmquist指數(shù)是在DEA模型基礎(chǔ)上拓展出來的計(jì)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的方法,可用于測度決策單元在不同時(shí)期內(nèi)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化。在規(guī)模報(bào)酬不變的情況下,可獲取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指數(shù)(TFPch)、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Effch)和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Techch)三方面的信息,即TFPch=Effch×Techch;在規(guī)模報(bào)酬可變的情況下,可進(jìn)一步獲得純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Pech)和規(guī)模效率變化指數(shù)(Sech)的信息,即Effch=Pech×Sech[36]。因此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數(shù)對廣東省各地市在2008—2018年的城市更新績效進(jìn)行動態(tài)的分析評價(jià)。
(3)Tobit模型。城市更新效率具有非負(fù)截?cái)嗵卣鳎瑢@類受限因變量模型的估計(jì),用OLS法會得到有偏的結(jié)果,Tobit模型更合適。固定效應(yīng)Tobit模型通常不能得到一致、無偏的估計(jì)量,隨機(jī)效應(yīng)模型更好[37]。本文建立如下隨機(jī)效應(yīng)Tobit模型:

式(1)中:Y為被解釋變量,即城市更新績效,以DEA模型的計(jì)量結(jié)果對其進(jìn)行賦值;X和Z分別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其量化指標(biāo)如表2所示;α為截距項(xiàng);β和γ分別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u代表個(gè)體效應(yīng)標(biāo)準(zhǔn)差;e代表隨機(jī)干擾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差;i(i= 1,2,…,21)表示廣東省內(nèi)的21個(gè)不同城市;t則表示不同的年份(t= 2008,2009,…,2018);j(j= 1,2,…,6)代表解釋變量個(gè)數(shù);k(k= 1,2,3)代表控制變量個(gè)數(shù)。
4 實(shí)證研究
4.1 城市更新績效的時(shí)空變化特征分析
4.1.1 基于DEA模型的城市更新靜態(tài)績效分析
本文運(yùn)用DEAP軟件,計(jì)算得到2008—2018年廣東省各地市的城市更新綜合效率,如表3所示。

表3 2008—2018年廣東省各地市城市更新效率Tab.3 Urban renewal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1)從時(shí)間維度上看,廣東省的城市更新績效并不穩(wěn)定,在不同時(shí)段呈現(xiàn)不同的特征。由圖2可知,廣東省城市更新歷年的純技術(shù)效率均處于較高水平(均值為0.941),而規(guī)模效率相對于純技術(shù)效率較低(均值為0.855),說明城市更新績效變動主要受規(guī)模效率變化的影響。其中,2008—2011年,廣東省城市更新政策聚焦于標(biāo)圖建庫、預(yù)防腐敗等方面①參見《關(guān)于在“三舊”改造過程中加強(qiáng)預(yù)防職務(wù)犯罪工作的通知》 《關(guān)于在“三舊”改造工作中加強(qiáng)廉政建設(shè)預(yù)防腐敗行為的通知》 《關(guān)于做好“三舊”改造地塊標(biāo)圖建庫工作的通知》 《關(guān)于開展“三舊”改造地塊標(biāo)圖建庫成果檢查的通知》。,對于規(guī)劃與用地報(bào)批沒有太多的指引,各地開發(fā)商拿地較為容易(2008—2011年改造用地供應(yīng)年均增長63.04%),“三舊”改造逐漸演變?yōu)榉康禺a(chǎn)開發(fā)的盛宴[38],改造用地供應(yīng)量過多,資源投入與效益產(chǎn)出不匹配導(dǎo)致規(guī)模效率低下,改造完成率從2008年的48.29%降至2011年的15.64%。為應(yīng)對城市更新過度地產(chǎn)化、進(jìn)度慢等問題,2011—2015年,廣東省適時(shí)對土地出讓、用地報(bào)批和改造規(guī)劃等問題進(jìn)行了更嚴(yán)格的規(guī)定②參見《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加快“三舊”完善歷史用地手續(xù)規(guī)劃審查工作的通知》 《關(guān)于調(diào)整“三舊改造”涉及完善征收手續(xù)報(bào)批方式的通知》 《關(guān)于開展“三舊”改造規(guī)劃修編工作的通知》。,同時(shí)適逢國家出臺房地產(chǎn)調(diào)控措施,抑制了土地交易市場,改造規(guī)模增速下降,年均增長降為11.60%,規(guī)模效率得以維持在較高的效率前沿面,廣東省城市更新績效有所改善。然而,2016年廣東省城市更新效率又出現(xiàn)了下降的苗頭,為此,廣東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發(fā)布了《關(guān)于提升“三舊”改造水平促進(jìn)節(jié)約集約用地的通知》,其中規(guī)定:“完成‘三舊’改造年度任務(wù)的,按不少于完成改造面積的20%獎(jiǎng)勵(lì)用地指標(biāo);未完成改造任務(wù)的,扣減用地指標(biāo)”,這在一定程度上激勵(lì)或督促各市加快“三舊”改造的步伐,繼而2017年廣東省城市更新效率略有回升,但2018年后再次降至改造以來的最低點(diǎn),這也說明政策紅利迅速釋放并消耗殆盡,廣東省的城市更新工作進(jìn)入了艱難時(shí)刻,當(dāng)前亟需厘清城市更新工作進(jìn)展緩慢的癥結(jié)所在,以優(yōu)化城市更新制度設(shè)計(jì),有效促進(jìn)城市更新進(jìn)程。

圖2 2008—2018年廣東省城市更新績效及其分解指標(biāo)變化趨勢圖Fig.2 Changing trend of urban renewal performance and its decomposition indicato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2)從空間上看,廣東省各地市間的城市更新績效差異顯著,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根據(jù)2008—2018年廣東省各地市的城市更新績效累計(jì)有效次數(shù),將省內(nèi)21個(gè)地市的城市更新績效水平劃分為3種狀態(tài),分別為較低水平(累計(jì)1~3次有效)、中等水平(累計(jì)4~8次有效)和較高水平(累計(jì)9~11次有效)。城市更新處于較低水平的城市主要位于珠三角地區(qū),包括佛山、肇慶、廣州、東莞、江門、湛江和梅州,這些城市的規(guī)模效率整體處于遞減狀態(tài),資源利用率相對較低。相比之下,汕尾、汕頭和茂名3座城市的城市更新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其中粵東地區(qū)的汕尾市和汕頭市自城市更新實(shí)施以來,城市更新效率一直維持在有效狀態(tài),整體表現(xiàn)最佳。其余城市的城市更新績效并未呈現(xiàn)明顯趨勢。顯見,廣東省的城市更新績效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zhì)性,應(yīng)當(dāng)理性認(rèn)識和甄別差異來源,因城施策。
(3)從指標(biāo)松弛變量分析結(jié)果可知(表4),城市更新處于較低水平的城市,改造規(guī)模、社會投資額和政府投資額均出現(xiàn)了大量冗余,改造完成率、節(jié)地率、單位面積土地產(chǎn)出、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等與有效前沿面存在較大差值。由此可見,這部分城市的城市更新產(chǎn)出增加的速度滯后于投入增加的速度,若投入繼續(xù)增加,不僅不會促進(jìn)反而會影響城市更新績效,應(yīng)當(dāng)對投入規(guī)模進(jìn)行適當(dāng)調(diào)控。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城市基本位于珠三角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區(qū)域,建設(shè)用地需求大,地方政府出于城市發(fā)展和提高政府績效的考慮,推出了規(guī)模龐大的土地改造計(jì)劃,但由于這些城市新增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相對充裕,加上改造過程困難重重,盤活存量用地的動力明顯不足,造成城市更新績效反而較低。城市更新處于較高水平的城市,如粵東的汕頭和汕尾,其規(guī)模效益基本保持不變,這是由于上級下達(dá)的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相對短缺,迫于發(fā)展壓力有較強(qiáng)的城市更新動力,但受限于資本約束,城市更新規(guī)模有限(汕尾市、汕頭市2008—2018年平均每年城市更新規(guī)模占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規(guī)模的比例僅為0.08%和0.24%),相對更為重視城市更新的有效產(chǎn)出。

表4 2008—2018年廣東省21地市城市更新指標(biāo)松弛變量分析Tab.4 Analysis on relaxation variables of urban renewal indicators in 21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4.1.2 基于Malmquist指數(shù)的城市更新動態(tài)績效分析
為進(jìn)一步了解廣東省各城市的城市更新績效動態(tài)變化趨勢及其原因,本文運(yùn)用Malmquist指數(shù)法對城市更新績效進(jìn)行分解,如表5所示。
(1)從時(shí)間維度上看,2008—2018年廣東省城市更新全要素生產(chǎn)率呈“N”型變化趨勢。其中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和Malmquist指數(shù)的變化幅度幾乎一致,而純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和規(guī)模效率變化指數(shù)的波動較為穩(wěn)定,這說明城市更新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主要受技術(shù)進(jìn)步的影響。另一方面,由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指數(shù)的分解指標(biāo)可知(表5),Malmquist指數(shù)年均下降了4.6%,而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純技術(shù)效率變化指數(shù)、規(guī)模效率變化指數(shù)年均值分別減少了0.5%、1.5%和2.7%,顯然,規(guī)模效率變化起到了“拖累”作用[39],對Malmquist指數(shù)降低的貢獻(xiàn)較大。

表5 2008—2018年廣東省城市更新全要素生產(chǎn)率指數(shù)變化分析Tab.5 Analysi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of urban renewal in different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2)從空間角度看,2008—2018年廣東省各地市的城市更新全要素生產(chǎn)率具有不同的變化特征。從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指數(shù)的構(gòu)成來看(表6),技術(shù)進(jìn)步是城市間差異的主要來源。

表6 2008—2018年廣東省各地市城市更新績效動態(tài)評價(jià)結(jié)果Tab.6 Dynamic evaluation of urban renewal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具體來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改進(jìn)(Malmquist指數(shù)>1)的城市(包括廣州、珠海、佛山、惠州、茂名、潮州、揭陽、河源和清遠(yuǎn))具有較高的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技術(shù)創(chuàng)新較為活躍。其中,位于珠三角地區(qū)的城市,經(jīng)濟(jì)實(shí)力渾厚,能為城市更新的技術(shù)與制度研發(fā)提供充足的資金、人才、設(shè)備等支持,技術(shù)創(chuàng)新能力較強(qiáng)。值得注意的是,廣州、佛山的純技術(shù)效率不變,規(guī)模效率分別減少了8.4%和11.3%,但其技術(shù)進(jìn)步分別提高12.1%和26.2%,說明技術(shù)進(jìn)步抵消了規(guī)模效率下降帶來的負(fù)面影響。其余5個(gè)位于粵東、西、北地區(qū)的城市,雖然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不及珠三角地區(qū),但能夠通過學(xué)習(xí)先進(jìn)地區(qū)的技術(shù)和經(jīng)驗(yàn)來完善自身的城市更新體系,進(jìn)而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例如,潮州市湘橋區(qū)通過對城市更新先進(jìn)地區(qū)的經(jīng)驗(yàn)借鑒,“三舊”改造策略由節(jié)點(diǎn)式改造向片區(qū)式改造轉(zhuǎn)變,使城市功能布局得以優(yōu)化①湘橋區(qū)人民政府辦公室.加快“三舊”改造推動城市更新. http://www.xiangqiao.gov.cn/xwsd/bmzx/content/post_3699379.html。。城市更新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退步(Malmquist指數(shù)<1)的城市(包括汕尾、陽江、汕頭、云浮、中山、湛江、韶關(guān)、肇慶、梅州、東莞和深圳)在四大經(jīng)濟(jì)區(qū)均有分布,其中珠三角和粵西地區(qū)城市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受到技術(shù)進(jìn)步和規(guī)模效率的雙重阻礙,粵東和粵北地區(qū)的城市則主要是因?yàn)榧夹g(shù)創(chuàng)新不足且缺少與先進(jìn)地區(qū)交流與學(xué)習(xí)導(dǎo)致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下降。
4.2 城市更新績效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軟件進(jìn)行面板Tobit模型估計(jì)(表7)。為了驗(yàn)證模型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模型1只納入解釋變量,模型2—模型4在模型1的基礎(chǔ)上逐步加入了控制變量。計(jì)量結(jié)果顯示,4個(gè)模型均通過了似然比檢驗(yàn),模型2—模型4在納入控制變量后,自變量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均與模型1類似。因此,模型的計(jì)量結(jié)果較為穩(wěn)健。本文以模型4作為基準(zhǔn)模型展開分析。

表7 Tobit模型回歸結(jié)果Tab.7 Regression results of Tobit model
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生產(chǎn)要素投入對城市更新績效有負(fù)向影響。其中,總投資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fù),其二次項(xiàng)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生產(chǎn)要素投入與城市更新績效是先降后升的“U”型曲線關(guān)系,且當(dāng)前廣東省城市更新績效仍處于隨生產(chǎn)要素投入增加而降低的階段,面臨生產(chǎn)要素投入過剩,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問題,這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變化趨勢研究結(jié)論類似[40]。
市場化程度在10%的水平上對城市更新績效有正向促進(jìn)作用,說明城市更新的市場化有利于城市更新效率的提高。對于城市更新而言,市場化運(yùn)作避免了政府主導(dǎo)下的多元目標(biāo)不協(xié)調(diào)帶來政策效果的不理想,這在農(nóng)地抵押貸款[41]等研究中得以印證。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方面,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比重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比重越高,城市更新績效越好。第三產(chǎn)業(yè)與第二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之比對城市更新績效呈現(xiàn)不顯著的負(fù)向影響,這說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升級并未起到促進(jìn)城市更新績效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在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的過程中,雖然第三產(chǎn)業(yè)比重在逐漸增加,但尚未形成以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為主的第三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未能實(shí)現(xiàn)較高的土地集約水平和較高的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因而對城市更新績效的作用不明顯。
5 結(jié)果與討論
(1)廣東省城市更新全要素生產(chǎn)率呈“N”型變化特點(diǎn),城市更新績效與政策協(xié)同演進(jìn),當(dāng)前正處于較低的效率前沿面,政策實(shí)施遭遇困境,制度紅利亟待重新釋放。
(2)廣東省城市更新績效空間異質(zhì)性顯著,規(guī)模效率不同是空間差異的主要來源,這與城市間的土地利用壓力差異有關(guān)。相較于粵東、粵西、粵北地區(qū),位于珠三角地區(qū)的城市新增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較多,土地利用壓力較小,改造積極性不足,城市更新績效相對較低。對此,這些城市更應(yīng)注重對生產(chǎn)要素投入量的把控,可以結(jié)合其新增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進(jìn)行城市更新年度計(jì)劃的制定,避免一次性推出大量的改造面積,科學(xué)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導(dǎo)致各地市城市更新全要素生產(chǎn)率產(chǎn)生退步和改進(jìn)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技術(shù)進(jìn)步,其根源是創(chuàng)新能力與學(xué)習(xí)能力的差異。其中,地處粵東、粵西和粵北的城市,依靠自身技術(shù)創(chuàng)新顯得困難,應(yīng)當(dāng)加強(qiáng)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改進(jìn)的城市的交流合作,借鑒先進(jìn)技術(shù)與經(jīng)驗(yàn)來制定適合自身發(fā)展的城市更新政策。
(3)影響廣東省城市更新績效的主要因素為生產(chǎn)要素投入、市場化程度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鑒于廣東省城市更新績效空間異質(zhì)性差異,應(yīng)當(dāng)強(qiáng)調(diào)不同城市根據(jù)自身的發(fā)展階段、資源稟賦條件以及地區(qū)特點(diǎn)進(jìn)行差異化的政策匹配。對于面臨生產(chǎn)要素投入過剩問題的珠三角地區(qū)城市,應(yīng)當(dāng)合理調(diào)整投入結(jié)構(gòu),避免資源利用的不經(jīng)濟(jì)。對于當(dāng)前城市更新市場活力不足的潮州、韶關(guān)、茂名、汕尾等城市,應(yīng)當(dāng)有效協(xié)調(diào)市場與政府的關(guān)系,通過市場化運(yùn)作以激勵(lì)城市盤活存量土地的積極性。近年來,粵西、粵北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正處于優(yōu)化升級階段,科學(xué)引導(dǎo)這些城市的產(chǎn)業(yè)向以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為主的第三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將有助于其城市更新績效的提高。
本文試圖構(gòu)建城市更新的“4E”績效分析框架并采用了與城市更新活動密切相關(guān)的“投入—產(chǎn)出”評價(jià)指標(biāo)體系以求切實(shí)反映城市更新績效,然而在操作變量選擇上碰到了一個(gè)難以回避的問題:一方面,所選的操作變量應(yīng)能準(zhǔn)確表征“4E”的內(nèi)涵,具有理論基礎(chǔ),以免陷入“概念陷阱”;另一方面,所選的操作變量需滿足數(shù)據(jù)可獲得性,以增強(qiáng)研究的可行性。但囿于面板模型設(shè)定和采集數(shù)據(jù)所限,在城市更新帶來的城市發(fā)展效益與社會公平效益兩個(gè)維度上未能甄選出既與城市更新活動密切相關(guān),又滿足數(shù)據(jù)可得性要求的操作變量。為了保證研究框架的完整性,只好在文獻(xiàn)分析的基礎(chǔ)上選擇了與城市更新有間接聯(lián)系的操作變量,不失為一種遺憾。不過從總體上來說,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仍然基本反映出廣東省及各市的城市更新的真實(shí)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