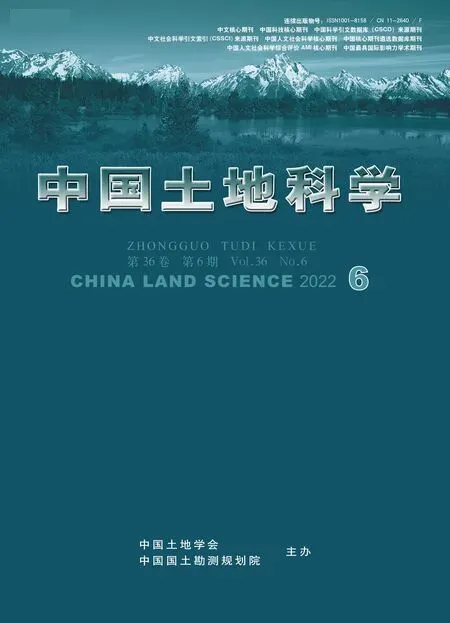地權穩定性與農戶土地投資:基于確權政策預期與 落地影響差異的討論
楊宗耀,紀月清
(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1 引言
農業投資在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改善低收入農戶生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過去,中國農村有頻繁進行土地調整的習慣,地權的不穩定一直被認為妨礙了農戶的土地投資、流轉乃至勞動力遷移決策等[1-4]。從1987年對“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到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中國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一直朝著收緊村集體土地調整的自由量裁、穩定農民承包經營權的方向發展。承包地確權政策作為近年來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的重要舉措,其主要任務是查清承包地的空間位置和面積,并以法律憑證為載體強化對農戶承包地的物權保護,在政策上確權被認為是“保持現有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基本手段”①參見《關于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工作的意見》,http://www.gov.cn/gzdt/2011-02/26/content_1811160.htm。。確權政策的投資激勵問題也成為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熱點,這些研究的基本觀點是確權政策落地通過增強土地承包權穩定性、降低與投資相伴的產權風險,能夠起到激勵農戶投資的作用。大量來自有機肥等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方面的經驗證據給予了充分的支持[5-8]。
然而,相關理論和實證少有提及的是確權推廣實施過程本身也會降低地權穩定性。盡管中央政府明確要求開展確權時“不是推倒重來、打亂重分”“不能借機調整或收回農戶承包地”,但實踐中借機進行土地調整的村莊并非個例,并且確權時土地權屬爭議和糾紛也有所增加或由擱置轉為顯現。2019年農業農村部在全國組織開展確權“回頭看”工作,主要任務是解決權證未發至農戶、暫緩確權的土地權屬爭議和承包經營糾紛以及確權信息不準確等問題,“回頭看”本身也反映了確權工作的執行和確權結果并不十分理想。根據葉劍平等[9]2016年對17省份的調查,約12%的村莊在確權期間進行了土地調整,農戶中約11%對確權程序規范性表示不滿意,約27%對確權結果存有異議。另一項2018年對31省份的調查顯示,約11%的農戶對確權工作的執行表示不滿意[10]。羅明忠等[11]揭示了確權實施過程的地權不穩定,以及農戶為避免撂荒地被村集體收回而采取的復耕行為。紀月清等[12]發現在尚未確權但預期即將確權時,一些農戶就會為避免轉出地被村集體收回而暫緩土地轉出決策。遺憾的是,目前鮮有研究關注確權推廣過程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對農戶土地投資決策的影響,缺乏對確權各階段影響差異的理論探討和實證檢驗。
在確權政策實施的不同階段,農民的地權穩定性預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預計將會進行確權時,確權期間可能發生土地調整和權屬爭議的預期會降低農民對現有承包地的產權穩定性預期;確權啟動實施并公布權屬界定方案后,那些確定不會發生權屬變更地塊的產權穩定性增加,而確定會被界定給他人的地塊則穩定性下降;確權頒證完成以后,近期再次發生權屬調整的可能性降低,農民的產權穩定性預期提高。因此,確權各階段的對土地投資的影響可能存在明顯差異。現有實證研究大多忽略了確權各階段的影響差異而僅劃分出“有確權”和“無確權”兩階段,但無論將地權穩定性下降時期劃歸哪一階段均可能產生偏誤的結論。紀月清等[12]指出在進行確權政策評估時應當區分無確權、預期即將確權、確權實施以及確權落地這幾個階段,動態觀察確權各階段的影響差異。
有如下研究疑問值得討論:確權政策從預期實施到落地完成各階段對農戶土地投資決策的影響是否存在明顯差異?如果存在差異,是否在確權預期或實施階段表現為抑制效應,而在確權落地階段表現為激勵效應?在二輪承包即將到期之際,如何制定“再延長30年”的具體方案,以持續激勵從事承包地經營農戶的土地投資?為回答上述疑問,本文將考察確權從預期到落地各階段對農戶土地投資決策的影響差異,并利用江蘇省18縣地塊層面2期調查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2 理論分析
在討論地權穩定性與農業生產投資關系時需要對農業投資進行分類討論。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土地投資,主要包括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和改變用途投資;一類是農業機械等與特定地塊無關的流動投資。研究發現,地權不穩定主要妨礙土地投資;機械等流動資本可以在土地減少后進行出租或變賣,其投資受地權穩定性的影響較小[13]。在中國土地細碎分配的大背景下,大部分基礎設施和改變用途投資往往不是農戶個體決策的領域,保持承包地產權穩定性的意義主要在于激勵有機肥等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在下面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中,本文將主要關注農戶的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
2.1 確權政策落地對農戶土地投資的影響分析
承包地確權政策旨在強化對農戶承包權的物權保護,既強調承包地塊“四至”清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又試圖賦予農戶抵押擔保等財產權能。理論上,確權政策落地可能通過增強地權穩定性、完善土地流轉市場和緩解信貸約束來促進農戶對承包地的投資。
地權穩定性一直被認為是激勵土地投資的關鍵[1-8]。如果附著在土地上的投資有可能和土地一起被他人侵占或被重新分配給集體中的其他成員,農戶顯然會缺乏投資激勵。一些學者指出,地權穩定性可分為法律、事實和主觀認知三個層面[14]。確權政策在這三個層面均可能產生影響:首先是法律層面,為進一步穩定土地產權,國家于2008年提出“保持現有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構想,并進一步在2019年出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意見》,明確規定“二輪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作為推行“長久不變”的基本手段,確權落地無疑會提高法律層面的地權穩定性。其次是事實層面,僅在法律層面規定“長久不變”并不足夠,還需要確保它的實施。作為強制性正式制度安排,確權落地不僅有助于減少土地調整的發生[15],還以法律憑證為載體明確農戶對承包權的物權,使得對承包關系的認同更加正式,效力范圍也不再局限于村組內農戶之間[16]。最后是個體認知層面,無論是法律層面的規定,還是事實層面的實施,最終都應落實到農戶認知層面。一項針對農戶認知的調查發現,相比無確權戶,確權戶對未來村里調地的預期有明顯降低[6]。不過,另一項17省份調查顯示,僅9%的農戶認為確權后村里不能再調地,似乎確權落地的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9]。
良好的土地市場對于激勵農戶進行土壤保持等投資也具有重要意義[17-18]。如果投資帶來的土地生產力長期提升能夠有效反映在地租或地價上,那么農民即使在不遠將來可能因種種原因轉出土地,他仍然有激勵進行投資。隨著中國城鄉轉型的深入,僅經營分到的小面積承包地的農戶勢必將大量減少。過去,年輕一代外出務工的農民將承包地交由家中年長的父母經營,土地流轉的發展大大滯后于勞動力轉移[19];隨著老一代農民因年老不再經營農業,土地流轉有望加速發展。對大量在不遠將來會轉出承包地的農戶而言,能否在土地轉出中通過地租或地價上漲來實現投資收益,顯然會影響當前的土地投資決策。大量研究表明,中國土地流轉市場發育不夠完善,集中表現在親友間不收租金的非正式流轉非常普遍[20-22]。外出打工者請親友代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看護土地產權,以便在非農就業受到沖擊時能夠保質保量地隨時收回土地[21-22];而這背后蘊含著對通過正式產權交易制度保障轉出地產權安全的信心的缺失。在政策上,確權的意義被描述為是建立“歸屬清晰、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產權制度”“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①參見《關于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工作的意見》,http://www.gov.cn/gzdt/2011-02/26/content_1811160.htm。。一些實證研究也發現,土地正式流轉交易的發展依賴于正式產權制度建設,確權政策的實施可以促進農戶在轉出土地時選擇收取租金[23-24]。但確權能否通過促使流轉市場更加完善來促進投資,還取決于地租能否充分反映農戶投資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如前所述,在土地分配異常細碎化的背景下,中國農戶的私人土地投資主要集中在土壤保持與改良領域;但土壤肥力難以觀測,特別是農戶承包地規模過小、進行肥力鑒定的平均成本很高,現階段很少有農戶在轉出肥力較高的土地時進行肥力鑒定來索取高租金,也很少在簽訂的土地流轉合約中寫明流轉到期時需要維持的肥力水平。因此,現階段確權通過完善土地流轉市場來促進農戶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的作用可能非常有限。
理論上,確權賦予了農戶承包權抵押、擔保權能,這可以提高農戶的信貸可獲性從而緩解農戶投資面臨的資金約束[25-26]。然而,一方面以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為代表的土地投資面臨的主要是勞動約束而非資金約束;另一方面,確權賦予抵押權能尚在試點階段、大多數地區并未建立土地抵押的金融制度,或者源于收回抵押的土地并進行流轉的交易成本太高、金融機構不愿意接受小規模承包地作為抵押物,現階段確權通過賦予抵押功能來促進承包地投資的作用也可能非常有限。
綜上,盡管在理論上確權也能夠通過完善土地市場、賦予抵押功能來促進農戶承包地投資,但由于種種現實條件的約束特別是農戶承包地規模過小的基本國情,現階段這些間接機制的實際作用可能非常有限;確權政策落地主要通過提高地權穩定性預期的機制對承包地投資產生影響。
2.2 確權政策推廣過程對農戶土地投資決策的影響分析
承包地確權作為土地權利界定與確認的過程,在推廣實施過程中存在“不穩定”因素并階段性地降低農戶的地權穩定性預期。不穩定因素主要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承包地可能在確權期間被村集體重新調整。首先,由于預期到確權后調地難度會增加,一些存在調地需求或慣例的村集體有動機在確權臨近或期間進行土地調整;其次,少數在二輪承包時沒分得地的村集體成員有正當的理由要求補回承包地,少數地方還會因農戶訴求激烈而采取打亂重分式的大調整;再次,出于解決關于因開荒復墾、規劃整理等新增地及機動地處置問題的目的,村集體也可能進行土地調整;最后,一些地方還會在確權實施過程中順勢組織農戶自愿互換并地、按戶連片經營來解決承包地細碎化問題,這在政策上也是鼓勵的。
另一方面是土地權屬爭議和糾紛,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相鄰地塊的邊界本身模糊或在確權時被更改。一、二輪承包時一些村集體并沒有建立完整清晰的土地臺賬,土地的空間位置和面積也多是處在村集體或村民小組農戶的默認狀態、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書面憑證。并且農村土地也存在不同的面積測算口徑,譬如往往小于實測面積的承包合同面積、按肥力等折算的“習慣畝”等。確權試圖解決土地“四至”不清、面積不準問題。但當以確權實測結果作為建賬依據時,相鄰地塊農戶的土地邊界界定或更改、其他口徑下少出或多出的面積都可能會引起權屬爭議[27]。特別是對于那些失去邊界標識的流轉地塊,邊界的界定依據及實測面積多少等權屬問題很容易引發糾紛。二是確權推廣中歷史遺留問題重新顯現。不少地方存在少數農戶一二輪承包時沒分得地、新增面積處置爭議以及土地臺賬不齊全等歷史遺留問題。確權會使擱置的歷史遺留問題集中顯現,而處置不當又將誘發新糾紛[28-29]。三是確權程序規范性問題。確權推廣工作涉及宣傳動員、土地實測、結果公示、簽字確認以及頒證等環節。然而實踐中一些地方存在部分環節缺失、實測不到位、頒證滯后等程序問題[9-10]。特別是在基層組織缺位或政策執行不到位時,農戶更多地表現出對政策的不理解、預期不明確[30],這也可能產生權屬爭議甚至誘發糾紛。
綜上,關于確權推廣實施過程中可能發生土地權屬調整和界定爭議的預期會降低農戶對地權的穩定性預期。在預期即將確權時,一些農戶會因權屬調整和爭議預期而暫緩對經營地的投資決策;而在確權啟動時,即使一些村集體已經立刻明示不會調地,關于權屬爭議的預期依然會使農戶傾向于暫緩上述決策,直到土地面積的測量與確認完成時為止。
2.3 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說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構建一個農戶跨期(兩期)決策模型來分析確權各階段對農戶土地投資決策的影響差異。這里主要關注無確權、確權預期與啟動和確權落地三個階段。有機肥等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形成的投資收益可供農戶多期使用,但為簡化分析,這里假定農戶如果在第一期(現期/近期)對土地進行投資(投資成本為C),投資收益只能在第二期(未來)獲得(折現后的足額投資收益為I)。在無確權階段,農戶面臨產權風險假定為r0(0<r0<1),此時農戶投資的凈收益為N0= (1 - r0)I - C。由上式可知,農戶是否進行投資取決于投資凈收益:農戶投資收益I越高,產權風險r0越低,農戶越有激勵投資土地。接下來,引入確權政策進行分階段討論。
先討論確權預期與啟動階段。在預期即將確權或確權啟動時,農戶面臨產權風險假定為r1(r1>r0)。這時,農戶投資的凈收益為N1= (1 - r1)I - C。那么相較于無確權階段,確權預期與啟動階段的投資凈收益變化為ΔN1= N1- N0= (r0- r1)I,易得ΔN1<0。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說:
H1:相比無確權階段,確權預期和啟動階段的地權穩定性更低,從而會抑制農戶的土地投資。
關注承包地確權政策的落地階段,假定這一階段農戶面臨產權風險為r2。如前所述,政策落地可以進一步提高承包權穩定性,即r2<r0,此時投資凈收益為N2= (1 - r2)I - C。那么相較于無確權階段,確權落地后投資凈收益變化為ΔN2= N2- N0=(r0- r2)I,易得ΔN2>0。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說:
H2:相比無確權階段,確權落地會促進農戶對承包地進行投資。
3 研究方法、數據來源與基本描述
3.1 研究方法
農戶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決策是以地塊為單位的,本文利用地塊層面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為檢驗確權對農戶投資決策的影響,通常的實證策略是采用雙重差分法進行估計。由于確權政策是漸次推廣的,樣本所處政策階段隨地區和時期變化而改變,因此,本文構造多期DID模型來同時檢驗本文的假說1和假說2。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式(1)中:因變量Invilt代表農戶i對經營地塊l在t年的土地投資與否決策;BeLit、HaLit和AfLit分別代表農戶i在t年處于確權預期、確權實施(包括確權啟動)和確權落地這些政策階段中第L年的0~1虛擬變量。系數αL、βL和γL分別是相應的政策年份的實際影響,值為正,表明該政策年份存在投資激勵效應,反之為抑制效應;Zilt代表影響投資的控制變量;δc和νt分別是縣域和年份固定效應,用來控制非時變特征和時變的增量以及政策推廣的地區選擇性偏差;εilt是誤差項。由于確權對自有和轉入承包地投資的影響存在差異,本文分樣本進行回歸分析。
為再次檢驗假說1,這里以“在t年本縣(市)其他村實施確權的比例”代表政策預期,分析其對未確權戶(僅保留確權啟動前的各期樣本)的影響。構造如下Probit模型:

式(2)中:Inv*ilt是決定投資與否的潛變量,可以理解為投資凈收益。Inv*ilt>0時,Invilt= 1成立,代表對地塊進行投資;否則Invilt= 0,代表不投資。Antilt代表即將確權的預期,其含義是本縣(市)內實施確權的村莊越多,未確權戶越可能產生本村即將確權的預期。系數?為負,說明確權預期會抑制投資,反之則反是。其他變量的設定和具體闡釋同式(1)。
3.2 數據來源
本文以江蘇省為研究對象。課題組于2015年7—8月開展基線調查,并于2018年1月進行追蹤調查。基期調查采用多階段抽樣法,具體抽樣方法如下:首先,從16個確權整體推進縣中隨機抽出9個縣,并在每縣所在市抽取1個非整體推進縣作為對照;其次,每縣隨機抽取2~4個村,每村隨機抽取1個村民小組;最后,每個村民小組采取“以地查戶”(隨機抽1大片耕地并列出地片上所有分得承包地的農戶名單)的方式抽取前25戶左右農戶進行調查。對于因舉家遷移等無法面訪的農戶,通過訪問親友、鄰居、村干部等知情人采集相關信息。這種方式有利于避免在數據分析中因遺漏不在家戶而導致的樣本偏誤。基期調查共搜集到66村1 722戶及其4 796個地塊樣本。2018年1月進行追蹤調查,在每個樣本村選取基線調查訪問的前15戶進行回訪,共訪問到979戶及其3 235個地塊樣本。鑒于當前江蘇省面臨的主要耕地質量問題是有機質過少,而有機肥投資是最常見的有機質提升行為,因此本文以此為考察對象。兩次調查均詳細詢問了農戶過去一年所有經營地塊的有機肥投資情況,也詢問了面積等地塊層面信息以及農戶個體和家庭層面的基本信息。調查時還詢問了村干部本村確權推廣的具體年份。數據可以滿足研究的需要。
實證模型所使用的數據有以下幾點說明:(1)剔除2018年1月仍未實施確權的村莊樣本;(2)剔除有機肥投資和確權推廣數據缺失的地塊樣本;(3)剔除控制變量缺失或異常的地塊樣本。經整理,得到如下數據用于實證分析:(1)2014年的45村867戶2 580個經營地塊;(2)2017年的45村457戶1 463個經營地塊。
3.3 模型變量設定
(1)因變量。本文主要關注農戶投資與否的決策,因此采用農戶在經營地塊上是否進行有機肥投資來衡量(投資=1,否則為0)。表1顯示,2014年和2017年進行有機肥投資的地塊比例基本持平,分別為33%和32%。

表1 模型變量的統計性描述Tab.1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確權各階段變量。結合實際調查情況,設定確權啟動前1年為政策預期階段,確權實施第1年為政策啟動階段,并以頒證作為政策落地的衡量標準。表1顯示,2014年時處于政策預期、實施和落地階段的村莊比例分別是41%、35%和1%,而2017年相應的比例則分別是0%、9%和91%。
(3)控制變量。參考已有研究[8,12],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包括:一是經營地塊特征,包括地塊面積;二是經營決策者特征,包括性別(男性=1,否則為0)、文化程度(用受教育年限來衡量)、務農經驗(用16歲前是否經常干農活來衡量)、是否常住村內以及受過農業培訓;三是家庭特征,包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和經營的耕地面積。表1匯報了這些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量。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確權的投資效應分析
表2匯報了確權政策效果估計結果。各回歸方程總體顯著性的F檢驗均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關于固定效應的檢驗發現,各方程均在1%統計水平拒絕了隨機效應的假定。表2中列(1)、列(2)和列(3)、列(4)分析的對象不同,列(1)、列(2)是農戶對經營的自家承包地的投資,列(3)、列(4)是農戶對轉入經營的他人承包地的投資。列(1)與列(2)以及列(3)與列(4)間的區別在于政策各階段的分組差異,后者進一步細分了政策年份。
先看確權預期和啟動的影響。表2列(1)、列(2)結果顯示,確權啟動前1年和啟動當年的虛擬變量的系數均為負且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即將確權的預期和確權啟動會抑制農戶對其經營的自家承包地進行有機肥投資;列(3)、列(4)結果顯示,確權預期和啟動也會抑制農戶對轉入經營的他人承包地進行有機肥投資。確權期間可能發生的承包地重新調整的預期會降低農民的產權穩定性預期,從而會抑制農戶的投資決策。這一結論對轉入的承包地也成立,因為轉出戶的承包地重新界定時,往往也意味著轉入者無法再繼續經營相應的地。上述研究結果驗證了本文的假說1。而確權實施第2年,農戶對其經營的自家承包地投資決策有促進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大部分村集體一般在確權啟動時就會明示不再土地調整,并且進行了承包地面積的測量與確認,等到確權實施第2年時大部分農戶預期近期發生權屬調整和爭議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有激勵進行投資決策。
再看確權落地的影響。表2列(1)、列(2)結果顯示,頒證第1~3年(或頒證第1、2和3年)虛擬變量對農戶在經營的自家承包地上的投資決策的影響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表明在確權落地后投資水平不僅有所恢復,還會促進農戶對承包地進行投資。本文的假說2得以成立。特別地,頒證第1、2和3年的變量系數依次增加,這意味著確權落地的投資激勵效應呈現出逐年擴大的特征。列(3)、列(4)結果顯示,確權落地對農戶轉入地投資影響并不顯著,表明在確權落地后轉入地的投資僅恢復到無確權時的水平。可以理解為由于短期流轉合約的盛行,對于轉入的土地的投資,農戶只關心近期可能發生的產權變動風險,例如即將實施的確權過程中蘊含的“不穩定因素”;對于確權落地后可能進一步降低較遠期(如二輪承包到期時)的產權變動風險,由于這些風險本就遠超流轉合約的期限,因此不再農戶的考慮范圍。

表2 確權影響農戶土地投資的估計結果Tab.2 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land titling on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至于控制變量,文化程度高、常住本村、受過農業培訓的經營決策者傾向于對經營的自家承包地的投資,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有著較寬松的勞動約束和豐富的農技知識。經營耕地面積越多的農戶會傾向于減少對轉入經營的他人承包地的投資,這可能與勞動約束有關。其他變量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4.2 機制分析
這部分討論地權穩定性預期機制。就確權政策而言,在無確權時,大部分農戶遵循或相信二輪承包“30年不變”的制度安排,地權穩定性預期處于較高水平。樣本描述顯示,大多數村莊的調地時機和中央的規定保持一致:分田以來60%的村莊進行了調地且大多發生在二輪承包時;2000年以來仍有調地的村莊比例下降至21%;而2010年以來有調地的比例更低,僅有12%。
詢問農戶土地調整預期發現(表3),僅有20.8%認為在無確權狀態下村集體未來可能會調地。在確權臨近或啟動時,土地調整或權屬界定爭議等產權風險增加,農戶的穩定性預期有所降低。數據顯示,2010年以來進行調地的村莊中有超過80%的調地時機是確權臨近或啟動時(占總樣本的10%);57%存在確權權屬糾紛,22%存在確權推廣困難;15%的承包地塊的實測面積和承包登記面積不一致。這意味著,確權推廣過程會引致農戶關于村集體可能進行土地調整和發生權屬界定爭議的預期。詢問農戶土地調整預期發現(表3),有23.3%認為在確權實施過程中村集體可能會調地,該比例較無確權時高出2.5個百分點。確權落地后,農戶的穩定性預期不僅得以恢復,還會進一步提升。如表3所示,詢問已頒證農戶當前土地調整預期發現,僅有15.3%認為在村集體未來可能會調地,較無確權時低出5.5個百分點,較確權實施時低出8個百分點。

表3 確權對農戶土地調整預期的影響描述Tab.3 Impact of land titling on farmers’ expectation for land adjustment (%)
使用本區域其他村中實施確權比例來代表農戶對確權的預期后發現,該變量會顯著降低未確權戶投資的概率,這再次驗證了確權預期是一種地權不穩定預期(表4)。

表4 確權預期影響農戶土地投資的估計結果Tab.4 Impact of policy expectation on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4.3 關于政策評估的討論
現有實證研究忽略了確權各階段的影響差異,大多以“是否頒證”為依據劃分出“有確權”和“無確權”兩階段;但是,如前所述,在確權臨近或啟動時一些農戶的穩定性預期是降低的,因此采用通常的估計方法,即將頒證前各政策階段均劃歸“無確權”階段,可能會高估確權落地的激勵效應。控制和不控制確權預期和啟動的影響(即表2和表5)的結果對比支持了上述猜想:和表2相比,表5中頒證第1~3年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水平均更高一些。

表5 確權影響農戶土地投資的有偏估計結果Tab.5 Biased 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land titling on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5 結論與啟示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保持承包地產權穩定有利于促進農戶土地投資。確權作為承包地產權界定與確認的過程,其實施過程可能發生的土地調整或權屬爭議會階段性降低地權穩定性;而確權作為保障地權穩定的重要手段,政策落地則可以進一步提升地權穩定性。因此,在政策推廣的不同階段,確權對承包地投資的影響存在影響方向上的差異。具體而言,對于仍處于承包戶自家經營狀態的承包地,在確權預期和啟動階段表現為對土地投資的抑制作用,在確權落地階段則表現為對承包地投資的激勵作用。對已經發生流轉的承包地,確權只在政策預期和政策啟動階段暫時性地抑制投資,確權落地后并不會表現出對投資的長期激勵作用。此外,如果不控制確權預期和啟動起到的作用,采用通常方法進行估計會高估確權落地的投資激勵效應。
本文從激勵農戶進行土地投資的角度,提出如下深化產權制度改革的建議。具體包括:(1)進一步保障農戶土地產權的穩定性。一方面,需要嚴格執行承包期內不得調地的規定,另一方面,需要在二輪承包即將到期之際,抓緊確定并公布具體的延包方案,以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意見》為指導,盡可能地減少土地調整與權屬再界定的范圍;對確定不調地的地區,提前公布延包方案,穩定農戶的產權預期。(2)在土地流轉和置換合并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政府需要提供土壤肥力等級鑒定的服務,以便過去土壤保持與改良投資可以充分反應在交易價格上,降低土壤質量信息不對稱對土地市場的干擾,激勵農戶對未來可能會轉出或置換出承包地也進行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