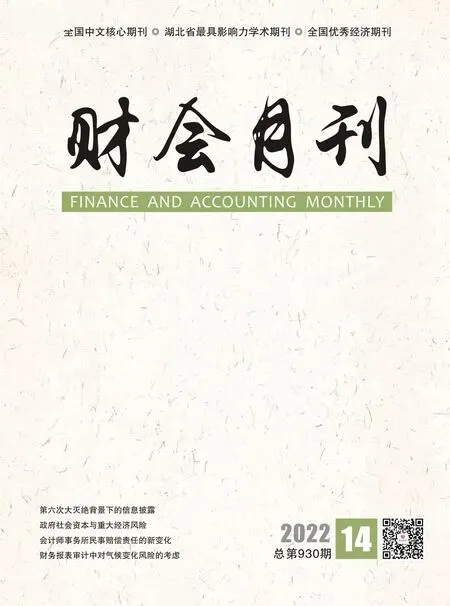第六次大滅絕背景下的信息披露——對歐盟《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準則的分析
黃世忠(博士生導師)
一、出臺背景分析
E4號歐盟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ESRS 4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簡稱ESRSE4)征求意見稿的出臺,既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面臨的嚴峻形勢有關,也與歐盟致力于實現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國際公約所規定的目標分不開。
(一)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面臨的嚴峻形勢
地球是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共同家園,這個家園本應由豐富多彩的物種群體和精妙復雜的生態系統所構成,才能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格局。人類活動最終依存于生態系統,并且嵌入自然之中,而不是游離于自然之外[1]。人類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包括供給服務(如大自然提供的淡水、木材、能源等)、調節和維護服務(如空氣過濾、水凈化、洪水控制等)以及文化服務(如審美、旅游、娛樂等)。聯合國2018年發布的《沙姆沙伊赫宣言》指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是地球所有生命的基礎設施,不僅在提供自然服務方面至關重要,而且是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根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喪失將對人類健康產生消極影響[2]。世界經濟論壇(WEF)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15%的GDP(約13萬億美元)在中等程度上依賴于自然界的饋贈,37%的GDP(約31萬億美元)高度依賴于自然界的饋贈,這兩項合計44萬億美元,占全球84.75萬億美元GDP的一半以上。此外,全世界21億人的生計有賴于生態系統的有效管理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3]。
但人類活動特別是工業社會里企業的經營活動對土地、淡水和海洋資源的過度開發與利用,以及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和物種入侵等,卻對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破壞,植物、哺乳動物、魚類和其他物種滅絕率是物種滅絕背景率①的1000倍,野生哺乳動物總數比1900年的歷史記錄下降了82%[4],被科學家稱為“生物毀滅”,已經達到了第六次大滅絕的程度[5]。Ceballos等[5]對27600種陸地脊椎動物物種的樣本進行研究,并對1900~2015年的177種哺乳動物的數量進行詳細分析,結果發現,陸地脊椎動物的數量減少了32%,177種哺乳動物的數量減少幅度超過了32%,40%的哺乳動物減少幅度超過80%。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6]中尖銳地指出,人類活動正在侵蝕生態系統根基,對陸地和海洋生態以及物種造成嚴重破壞。如圖1所示,大約有100萬種動植物物種遭受滅絕的風險,由人類活動引發的第六次大滅絕遠遠超過前五次大滅絕的程度。

圖1 人類活動導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的惡化情況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相互強化,生態系統的退化加劇了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物種數量的減少,而生物多樣性喪失反過來又加劇了生態環境退化。基于大量嚴謹的科學研究,很多科學家認為“生物圈完整性”(biosphere integrity)的地球限度已經被突破,有可能引發災難性的環境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已成為僅次于氣候變化的第二大環境問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指出,雖然經過不斷努力,但生物多樣性仍然在全球范圍內繼續惡化,如果一切照舊,這種情況預計將持續下去甚至變得更糟[7]。
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影響,既給企業帶來風險,也給企業帶來機遇,但對于絕大多數企業而言,風險大于機遇。自然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NFD)總結了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影響企業發展的作用機理[8],詳見圖2。

圖2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對企業產生影響的作用機理
(二)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國際公約致力實現的目標
面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日益嚴峻的形勢,國際社會在有識之士的呼吁下開始警醒,呼吁各國政府采取行動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促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方面,聯合國厥功至偉,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功不可沒。莫里斯·斯特朗是全世界當之無愧的環保領袖,七次當選聯合國副秘書長,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創始人和首任署長。在他的精心籌劃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又稱首屆“地球峰會”)于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在他的斡旋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此次峰會,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后首次參加的國際會議。這次“地球峰會”是世界環保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首次將環境問題提到國際議事日程上來,開創世界各國攜手治理環境問題的先河。20年后的1992年6月,莫里斯·斯特朗擔任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秘書長,協調組織118個國家元首、178個國家的1.5萬名代表參加了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簽署了《里約宣言》(亦稱《地球憲章》),通過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為緩解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改善生態環境奠定了制度框架。
1992年6月通過的CBD,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旨在保護生物多樣和生態系統的國際性公約,共有196個締約方簽署了該公約,是迄今為止簽署國家最多的國際環境公約,其意義不亞于同年通過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2017年通過的旨在緩解全球氣溫上升的《巴黎協定》。CBD開啟了世界各國攜手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先河,確立了由締約方大會主導的議事和決策機制,締約方大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共商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大計。CBD的目標在于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使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和平等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帶來的益處,包括恰當獲取遺傳資源、恰當轉移相關技術、恰當提供資金。CBD還對生物多樣性、生物資源和生態系統等術語進行了界定:生物多樣性是指來自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等所有來源的生物體的變異性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包括物種內部、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大致可分為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生物資源是指對人類具有實際或潛在用途或者價值的遺傳資源、生物體或其部分、生物群體或生態系統中任何其他生物的組成部分;生態系統是指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群體以及它們的無生命環境作為一個功能單位交互作用形成的動態復合體。
CBD簽署30年來,共召開15次締約方大會,2010年以來兩次聚焦于生物多樣性保護10年規劃的締約方大會備受矚目。
一是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第10次締約方大會。大會通過了“愛知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簡稱“愛知目標”),這是全球首個10年規劃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由5個戰略目標和20個具體目標組成。5個戰略目標是: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至政府和社會決策中以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根本成因;減輕生物多樣性的壓力并促進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通過保護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多樣性改善生物多樣性境況;增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福祉;通過參與式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提高保護工作的實施效果。具體目標中最受關注的量化指標包括:到2020年,所有自然棲息地包括森林的喪失率降低50%,在可能的情況下將喪失率降至零,棲息地退化和碎片化顯著降低;到2020年,所有魚類、無脊椎動物和水生植物按生態系統法進行可持續管理和利用,避免魚類過度捕撈,對瀕臨枯竭的物種制訂恢復計劃并采取恢復措施,漁業不再對受威脅的物種和脆弱的生態系統產生負面影響,漁業對資源、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影響維持在安全的生態界限之內;到2020年,至少17%的陸地與內陸水域以及10%的海岸與海洋得到保護[9]。2020年9月,CBD秘書處發布的評估報告顯示,由于認識局限或受經濟等條件限制,愛知目標中的20個具體目標沒有一個完全實現,只有6個具體目標部分實現。令人欣慰的是,我國作為物種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履約情況好于其他國家,生態紅線等創新實踐為世界各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改善生態環境方面貢獻了中國智慧。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要想實現向生態文明時代的轉型依然任重道遠,生物多樣性保護體制機制和法律政策體系尚不健全,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有待完善[10]。
二是2021年10月在中國昆明召開的第15次締約方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主旨演講,重申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呼吁大家要深懷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球家園,秉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構建經濟與環境協同共進的地球家園。大會閉幕后發表的《昆明宣言》承諾,締約方將確保制定、通過和實施一個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包括提供與CBD一致的必要的實施手段,以及適當的監測、報告和審查機制,以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并確保最遲在2030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進而全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2050年愿景。《昆明宣言》中提到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于2021年7月由CBD秘書處起草了初稿。該框架初稿基于變革理論,提出需要在全球、區域和國家層面采取緊急政策行動,以轉變經濟結構、建立相應的融資模式,使加劇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在今后10年(即到2030年)得到控制,并使自然生態系統在今后20年得以恢復,到2050年實現凈改善,以實現CBD關于“到2050年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景。
為此,框架初稿在F部分提出了4個2050目標(goal)和9個2030年里程碑(milestone),其中第一個目標及其三個里程碑量化得最為具體。目標A:所有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得到提升,自然生態系統的面積、連通性和完整性至少增加15%,支持所有健康和有韌性的物種種群,物種滅絕率至少降低10倍,所有分類和功能組的物種滅絕風險降低一半,野生和馴化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得到保護,所有物種內的遺傳多樣性至少保持90%。里程碑A1:自然系統的面積、連通性和完整性至少凈增長5%。里程碑A2:滅絕率的增長被遏制或扭轉,滅絕風險至少降低10%,受威脅物種的比例降低,物種種群的豐富度和分布得到保持或提升。里程碑A3:野生和馴化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得到保護,保持90%遺傳多樣性的物種比例得到增加。
此外,框架初稿還提出了2030年減少生物多樣性威脅的21個具體目標,其中的5個具體目標被量化。目標2:確保至少20%退化的淡水、海洋和陸地生態系統得到恢復。目標3:確保全球至少30%的陸地和海域,特別是對生物多樣性及其對人類貢獻特別重要的地區,通過有效和公平的管理等手段得到保育。目標6:管理外來入侵物種的引進路徑,防止或至少減少90%的引入和定居率,控制或根除外來入侵物種以消除或減少其影響。目標7:減少各種來源的污染,使其降低至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人類健康無害的水平,流失到環境中的營養物至少減少一半,殺蟲劑至少減少三分之二,消除塑料廢物的棄放。目標8:將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最小化,以生態系統方法為基礎,為緩釋和適應氣候變化作貢獻,每年至少為全球氣候緩釋努力貢獻10億噸二氧化碳的減排,并避免所有緩釋和適應舉措對生物多樣性產生消極影響[7]。
二、披露要求介紹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預計不久就會順利獲得締約方的批準,將成為未來10年乃至30年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要國際環境標準。作為CBD簽署方,歐盟歷來十分重視對國際條約的履行。為此,歐盟基于CBD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目標、里程碑和指標,制定了《歐盟203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并對成員國提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奮斗目標:到2030年無凈喪失(no net lossby 2030),2030年后凈增長(net gain from 2030),到2050年完全恢復(full-recovery by 2050)。
為了加大企業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視,規范企業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信息披露,便于利益相關者評估企業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依賴和影響,EFRAG在發布《氣候變化》(ESRSE1)征求意見稿的同時,發布了《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征求意見稿。與其他ESRS的體例一樣,該征求意見稿也是由目標、與其他ESRS的互動關系、披露要求等三部分所組成,其中披露要求是核心內容,包括5個部分:一般、戰略、治理和重要性評估;政策、目標、行動計劃和資源;業績計量;術語界定;應用指南。其中,應用指南雖然以附錄的形式列示,但與準則正文具有同等效力。至于與ESRS一同發布的結論基礎,則不具有準則效力。以下著重介紹該征求意見稿在三個重要方面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10項披露要求。
(一)一般、戰略、治理和重要性評估的披露要求
披露要求E4-1:與“到2030年無凈喪失、2030年后凈增長、到2050年完全恢復”目標相一致的轉型計劃。為了便于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的轉型計劃及其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恢復是否與“到2030年無凈喪失、2030年后凈增長、到2050年完全恢復”的目標一致,企業應當披露轉型計劃以確保其商業模式和戰略與該目標相兼容。轉型計劃不僅應當涵蓋其自身經營活動,而且應當延伸至其上下游價值鏈。企業必須披露其行政、管理和監督機構是否已經批準該轉型計劃。
企業披露轉型計劃時,應概述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驅動因素以及潛在的緩釋行動,緩釋行動可分為不同等級,如避免、最小化、恢復和抵消等。此外,企業應說明與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相關的路徑依賴以及被鎖定的資產和資源。轉型計劃應包括用于計量“無凈喪失/凈增長”的指標和工具。
企業披露商業模式和戰略是否與“到2030年無凈喪失、2030年后凈增長、到2050年完全恢復”的目標相兼容時,應描述其商業模式和戰略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方面的韌性,評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說明其商業模式是否經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情景分析的驗證。若經過驗證,則應披露情景分析所使用的情景、假設、時間范圍和分析結果等。企業可參考IPBES在2016年發布的《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情景分析和模型的方法論評估報告》、全球生物模型、水風險過濾模型、ENCORE模型等情景分析工具。
企業識別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影響、風險和機遇時,應當涵蓋:(1)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包括物種和生態系統的現狀;(2)影響生物多樣性喪失和退化的驅動因素;(3)短期、中期和長期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依賴;(4)短期、中期和長期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物理風險和機遇;(5)短期、中期和長期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轉型風險和機遇;(6)企業導致的系統性風險。
影響和依賴重要性應依據地理經營場所地點和原材料來源進行評估。如果企業自身的經營活動或上下游價值鏈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具有高影響,或者企業依賴的原材料、自然資源或生態系統服務被中斷或可能被中斷,則地理經營場所地點的影響就具有重要性。如果企業自身的經營活動或上下游價值鏈對原材料及其生態系統具有高影響,或者企業依賴的原材料生產或與其相關的生態系統服務被中斷或可能被中斷,則原材料的影響具有重要性。
評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影響時,企業至少應當考慮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對受威脅物種、受保護區域、關鍵生物多樣性區域的影響。
如果企業因尚未采納與“到2030年無凈喪失、2030年后凈增長、到2050年完全恢復”的目標相一致的轉型計劃而無法披露上述信息,則企業必須對這種情況進行披露,并提供尚未采納這種轉型計劃的理由,企業可說明其擬在什么時間范圍內準備好這種轉型計劃。
(二)政策、目標、行動計劃和資源的披露要求
披露要求E4-2:管理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執行的政策。企業應當披露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政策,以便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政策以解決實際或潛在消極影響的防范、緩釋和補救問題以及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恢復。披露這些政策還有助于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如何監督和管理因影響和依賴而產生的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重要影響、風險和機遇,以及企業如何制定“到2030年無凈喪失、2030年后凈增長、到2050年完全恢復”的戰略。
企業應說明其制定的政策旨在解決以下哪些問題:(1)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要影響;(2)導致重要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3)重要的依賴以及重要的物理和轉型風險及機遇;(4)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生產、消費和原材料采購;(5)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與供應商開展的互動和篩選;(6)與依賴和影響相關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社會后果;(7)其他。
披露上述(1)和(2)時,企業應當說明這些政策如何使企業:在自身經營活動和上下游價值鏈中避免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消極影響;將無法避免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消極影響減少和降低至最低水平;在遭遇無法避免和最小化影響的情況下恢復和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或恢復清理后的生態系統;以抵消的方式彌補剩余影響;緩解重要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披露上述(4)時,企業應當說明所采取的政策如何使企業:在獲得第三方驗證的情況下生產、采購和耗用原材料;確保原材料的生產、采購和耗用的可追溯性;來自生態系統的生產、采購和耗用得到有效管理或提升了生物多樣性的條件。披露上述(6)時,企業提供的信息應包括:使用遺傳資源的好處得到公正和公平分享;接觸遺傳資源獲得相關部門的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接觸與原住民或當地社區持有的遺傳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獲得事先知情同意;對當地和原住民社區權利的保護,尤其應認識到許多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傳統生活方式密切依存于生物資源,與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對其組成部分的可持續利用相關的利益應當與他們公平分享。
企業可說明其采取的上述政策如何與聯合國的第2、6、12、14和15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及其他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國際公約相聯系。
披露要求E4-3: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可計量目標。企業應當披露其采用的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目標,以便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擬定的目標如何支持其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政策以及處理與此相關的重要影響、依賴、風險和機遇。為此,企業應披露的目標包括:(1)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要影響;(2)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喪失的重要驅動因素;(3)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要依賴;(4)重要的物理和轉型風險。
披露上述(1)時,企業披露的目標應包括:避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喪失;減少和最小化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喪失;恢復和修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披露上述(1)和(3)時,企業披露的目標可包括:避免受關注或有滅絕風險原材料的生產、采購和消耗;減少和最小化受關注或有滅跡風險原材料的生產、采購和消耗;減少對受關注或有滅絕風險的原材料的絕對需求;增加對受關注或有滅絕風險原材料的經認證的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生產和采購;增加受關注或有滅絕風險原材料的非認證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生產和采購。
披露要求E4-4: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相關行動計劃。企業應當披露其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行動和行動計劃以及實現其政策目標和指標的資源配置,以增加企業為實現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目標以及管理相關風險和機遇已經采取和計劃采取的關鍵行動的透明度。
對于每個行動計劃或獨立行動,企業應描述:(1)行動覆蓋的地理范圍,包括對地理邊界或活動局限性的解釋;(2)獨立行動或行動計劃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名單以及他們如何參與行動或行動計劃、受獨立行動或行動計劃積極和消極影響的利益相關者名單及他們如何受到影響,包括對當地社區、小住戶、原住民群體、婦女、窮人、被邊緣化及脆弱群體和個人的影響或為他們創造的福利;(3)每個行動或行動計劃擬解決的主要影響;(4)按緩釋戰略(避免、減少和最小化、恢復和修復)劃分的行動;(5)相較于其他可能行動選擇特定行動的理由解釋;(6)對行動是屬于一次性行動還是系統性做法進行解釋;(7)行動是個別的還是集體的,對于集體行動應解釋其作用;(8)行動取得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或支持行動的其他企業;(9)關鍵行動是否會引發重大的可持續發展不利影響的簡要評估。
(三)業績計量的披露要求
披露要求E4-5:壓力指標。企業應當報告壓力指標,以便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將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和基本生態系統產生確信無疑影響的重要影響驅動因素。這些壓力指標應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利用或棲息地變化、氣候變化、污染、自然資源的利用和開發以及入侵物種。
如果土地利用或棲息地變化或者退化被企業評估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喪失的重要影響驅動因素,則企業應當報告與土地使用或棲息地變化或者退化相關的壓力指標。土地利用或棲息地變化或者退化包括土地覆被的轉換(如砍伐森林或采礦)、生態系統管理或農業生態系統的改變(如強化農業管理或森林收成),或者地貌空間結構的改變(如棲息地碎片化、生態系統連通性變化)。
如果氣候變化被企業評估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喪失的重要影響驅動因素,則企業應當按照ESRSE1的要求報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壓力指標。
如果污染被企業評估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喪失的重要影響驅動因素,則企業應當按照ESRSE2的要求報告與污染相關的壓力指標,但不限于ESRSE2所涵蓋的污染源。
如果自然資源的利用和開發被企業評估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喪失的重要影響驅動因素,則企業應當按照ESRSE3對水資源利用以及ESRS E5對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的要求報告與自然資源的利用和開發相關的壓力指標,但不限于ESRSE3和ESRSE5所涵蓋的自然資源。
如果入侵物種被企業評估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喪失的重要影響驅動因素,則企業應當報告與入侵物種控制和消除相關的壓力指標。
如果企業識別了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喪失的其他重要影響驅動因素,則企業應當報告與這些重要影響驅動因素相關的壓力指標。
披露要求E4-6:影響指標。企業應當按照重要地理經營場所地點和(或)重要原材料報告重要的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影響指標,以便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在“無凈喪失/凈增長”方面的進展,包括生物多樣性的抵消如何融入計量方法。上述影響指標應包括對物種和生態系統影響評估的描述,特別是:(1)報告對物種的影響時,企業應考慮群體規模和滅絕風險,以便評估單一物種群體的健康狀況及其對人類誘發和自然發生的變化的適應性;(2)報告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時,企業應考慮條件、程度和功能,以便評估生態系統的總體健康狀況。
披露要求E4-7:反應指標。企業應當披露其反應指標,以便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采取最小化、修復或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等舉措對已識別重要地理經營場所和(或)原材料的重要影響。
反應指標的例子包括:(1)企業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受保護或被恢復棲息地的面積和地點,在恢復棲息地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否經過獨立的外部專家認可;(2)報告期末處于永久保護狀態的土地地域;(3)報告期末處于保護狀態的土地地域;(4)重新創建的環境表層(通過管理層的行動創造原先不存在的棲息地);(5)增加生物透明度的項目和場所的百分比(如安裝魚類通道或野生動物走廊)。
選擇性披露要求E4-8: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消耗和生產指標。企業可披露其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消耗和生產指標,以便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哪些原材料的消耗和生產符合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標準。
為此,企業可披露:(1)經第三方認證的原材料使用清單及其數量占生產和消耗總數的百分比;(2)可溯源至工廠或種植園的原材料供應數量及百分比;(3)來自受管理從而提升了生物多樣性條件的生態系統的原材料數量及百分比,受管理是指生物多樣性水平及其增長或喪失得到定期監控和報告。
選擇性披露要求E4-9:生物多樣性抵消。企業可披露在價值鏈內外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緩釋項目所采取的行動、開發情況和融資支持,便于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在多大程度上開發和投資于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以彌補其價值鏈內外無法避免、無法減少或消除、無法最小化的生物多樣性喪失。
抵消生物多樣性消極影響的信息應包括:(1)抵消的目的和所采用的關鍵業績指標;(2)以貨幣單位表示的與生物多樣性抵消相關的資金投入(直接和間接成本);(3)對抵消的描述,包括生物多樣性抵消所涉及的地域、類型(如保育、恢復等)、質量標準和其他標準。
披露要求E4-10:生物多樣性相關影響、風險和機遇的潛在財務影響。企業應當披露源自生物多樣性相關影響和依賴的風險和機遇所產生的潛在財務影響,便于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生物多樣性相關影響、風險和機遇在短期、中期和長期對企業發展、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創造價值能力的影響。
披露該類信息時,企業應當考慮這些潛在財務影響在報告日可能不滿足在財務報表反映的確認標準。這類不符合會計確認標準的信息,是《歐盟分類法》所要求的補充信息。企業在這方面的披露可包括對短期、中期和長期遭受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風險的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市場規模評估,并解釋如何界定這些遭受風險的產品和服務、如何估計財務金額以及使用哪些關鍵假設。
三、總結與啟示
雖然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環境退化已成為嚴重的環境問題,但企業對其重視程度遠不如氣候變化,突出體現為與此相關的信息披露遜色于氣候信息披露。氣候披露準則理事會(CDSB)審閱了歐盟最大50家公司2020年按照非財務報告指令(NFRD)披露的報告,結果發現只有46%的公司在其報告中提供了生物多樣性信息,而披露了氣候變化信息的公司比例高達100%。此外,只有10%的公司披露了生物多樣性的指標,而披露了溫室氣體排放和水資源指標的公司比例高達100%和90%[11]。歐盟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保護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其轄區內的大企業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方面的信息披露尚且如此,其他地區和較小規模企業的信息披露可想而知。可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信息披露任重道遠。《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付諸實施后,有望從根本上扭轉這方面信息披露嚴重滯后的局面。《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是世界上首個強制性的區域性準則,可望得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借鑒,其產生的溢出效應將助力全球范圍內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保護、恢復和修復行動。歐盟制定《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思路,至少可給予我們三點啟示。
(一)影響重要性甚于財務重要性
綜觀《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正文、應用指南和結論基礎,可以發現該準則通篇貫穿著影響重要性甚于財務重要性的思想。在10項披露要求中,有8項披露要求主要聚焦于披露企業經營活動及其價值鏈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只有2項披露要求側重于披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對企業的財務影響,其中第10項為強制性披露要求,而第8項為選擇性披露要求,第10項披露要求言簡意賅,篇幅有限,應用指南和結論基礎均為對該項披露要求所作的進一步補充、說明和拓展。可見,該準則對由內到外的影響重要性(inside-out impact materiality)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對由外到內的財務重要性(outside-in financial materiality)的重視程度。
根據歐盟《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的要求,EFRAG在制定ESRS時必須秉持雙重重要性(double materiality)原則,與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秉持的單一重要性(single materiality)原則形成鮮明的對比。相較于ISSB所秉持的單一重要性原則,筆者更贊同EFRAG所秉持的雙重重要性原則,因為提供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初衷是確保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滿足資本提供者評估環境和社會議題如何影響企業價值的信息需求[12]。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而言,準則制定的出發點和信息披露的著力點首先應當放在影響重要性上,其次才應當放在財務重要性上,這正是EFRAG的做法。ISSB如果不放棄單一重要性的立場,完全從單一重要性的角度制定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準則,可以想象所制定的準則將本末倒置、重心失焦,而且會與ESRS存在巨大差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準則如此,氣候變化、污染、水資源與海洋資源、資源利用與循環經濟亦然。
值得慶幸的是,2022年3月24日ISSB與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簽署了合作協議。雖然ISSB和GRI均秉持單一重要性原則,但GRI秉持的是單一影響重要性原則,明顯有悖于ISSB的單一財務影響重要性原則。但愿與GRI的戰略合作能夠淡化或對沖ISSB的單一財務重要性思維,使其制定的可持續發展披露準則更加契合ESG或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初心和使命。
(二)地點特定性甚于企業總體性
CDSB在《生物多樣性相關披露應用指南》中總結出了生物多樣性信息披露必須考慮的6個特征:空間維度(spatial dimension)、時間維度(time dimension)、多重特質(multi-faceted qualities)、相互連通性(interconnectivity)、參與和合作(eng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方法論(methodologies)。其中的空間維度特征是指生物多樣性的依賴、影響、風險和機遇具有地點特定性(location specific)。某一特定地點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地理境況不僅關系到該地區的生物多樣性狀況,包括現行生態系統和物種、保護地狀態和生物多樣性價值,而且關系到該地區生物多樣性的基礎設施、社會條件(包括社區傳統和生計)、經濟條件(如與自然相關的生產力、就業和收入)、治理與管制、地緣政治(跨國界的生態地區)和合作行動。譬如,與一個地區魚類過度捕撈相關的風險與當地就業和收入對生態系統的依賴程度以及社區傳統、捕魚設施和技術、管制和合作活動密切相關。換言之,同等規模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在物種豐富度和生態脆弱性存在重大差異的不同地區可以產生重大的差異性影響。
正是出于對地點特定性的考慮,ESRSE4征求意見稿要求企業按地理經營場所(包括工廠和工地等)的地點以及原材料的生產、采購和消耗來源地評估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相關的影響和依賴重要性。按地點評估的重要性即使占企業整體生產經營活動很小的一部分,也應被視為具有重要性。譬如,在卡梅隆導演的電影《阿凡達》中,2154年因地球環境惡化、資源匱乏,人類組建了資源開發公司到資源豐饒的潘多拉星球開采礦物,由此造成的對潘多拉星球的生態系統破壞對于人類毫無影響,但可能給潘多拉星球的原住民帶來滅絕風險。因此,根據ESRSE4征求意見稿的要求,此事項必須評估為具有影響重要性的事項并予以披露。
除了重要性評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征求意見稿的第2~8項披露要求還在不同程度上要求企業披露的信息必須考慮地理經營場所和原材料來源的地點因素,地點特定性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該征求意見稿要求企業對地點特定性的考慮,不應僅限于企業自身的經營活動,而應延伸到企業的上下游價值鏈,目的是促使企業發揮其在價值鏈中的影響力,督促其上下游合作伙伴關注和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三)準則操作性甚于準則原則性
生物多樣性包括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具有“肉眼可見”的顯性特點,而基因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則具有“肉眼不可見”的隱性特點,因此,基因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喪失往往不像物種多樣性喪失那樣引起我們的關注。這說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與此相關的準則制定,不應過于原則導向,否則操作性堪憂。換言之,針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這類專業性很強的準則制定,不宜過分偏重于原則導向,而應注重原則導向與規則導向的有機結合。
EFRAG在制定ESRS時,原則導向與規則導向結合得非常好。以《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和《氣候變化》為例,這兩個準則的正文分別只有9頁和10頁,但應用指南長達19頁和25頁。EFRAG的這種做法值得肯定和借鑒,對于企業比較生疏而專業性又很強的環境和氣候相關準則,只有在正文之外提供比較詳盡的應用指南,才具有可操作性。
正是意識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具有很高的專業性,而企業對此又十分生疏,EFRAG在應用指南和結論基礎中建議企業在信息披露過程中可參考國際專業組織的情景分析方法和其他評估方法。在結論基礎部分,EFRAG特別推崇TNFD的LEAP(Locate,Evaluate,Assess and Prepare)分析框架(圖3),建議企業參照該分析框架尋找企業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連接,評價企業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依賴和影響,評估企業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要風險與機遇,準備好企業應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保護的舉措和報告機制。

圖3 LEAP分析框架
【注 釋】
①Pimm等學者將沒有人類活動影響的物種滅絕率稱為物種滅絕背景率(background rate of speciesextinction),他們主要根據化石記錄、分子進化學以及多樣性數據,確定的物種滅絕背景率為每百萬物種年滅絕0.1,即0.1E/MSY。他們采用群組分析法(cohort analysis)得出的研究結果是,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物種滅絕率已經達到100E/M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