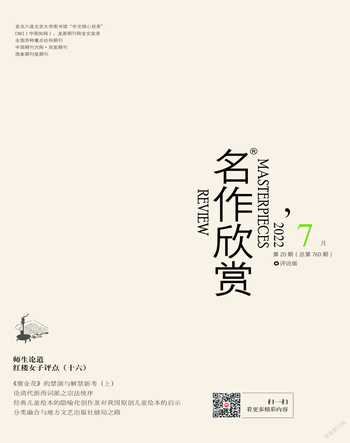王詵《煙江疊嶂圖》唱和詩中的歸隱情結
雒貞 吳曉棠
關鍵詞:王詵 《 煙江疊嶂圖》 蘇王唱和詩 歸隱情結
北宋著名畫家王詵的山水畫《煙江疊嶂圖》后的兩組唱和詩歷來為人所關注,多數研究者從其藝術角度出發,探尋《煙江疊嶂圖》唱和詩歌的藝術價值,本文擬從思想意蘊的角度,探究分析這四首詩中的歸隱情結。
一、《煙江疊嶂圖》及背景介紹
《煙江疊嶂圖》是北宋畫家王詵的畫作,現存兩個版本,一本為小青綠本,一本為水墨本,都藏于上海博物館。畫中云山高疊,雜樹叢生;煙江浩渺,高士、琴童、漁樵點綴其間,描繪了一幅人間仙境般的山水圖。圖后有蘇軾行書詩二首并跋,及王詵唱和詩二首并跋。
《煙江疊嶂圖》的作者王詵,字晉卿,生于宋仁宗景祐年間,山西太原人,后居河南汴京( 今開封)。王詵是將門之后,宋代開國功臣王全斌是他的先祖,因娶神宗之妹魏國公主而被封為駙馬都尉。王詵博學多才,琴棋笙樂書畫樣樣精通,是北宋著名畫家之一,與當時很多權貴名士如宋徽宗、蘇軾、黃庭堅等交往密切。
此畫的收藏者是王鞏,字定國,曾向蘇軾學習寫作,并時有唱和。王鞏出生于衣冠望族“三槐王氏”,是張方平的女婿。蘇軾因從小師從張方平,所以與王鞏自幼相知,相交甚密。王詵和王鞏均與蘇軾交往密切,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臺詩案獲罪,二王均因此而蒙難。元祐元年(1086),三位好友先后返回汴京。
四首唱和詩的來源是:元祐三年十二月,蘇軾在王定國家中看到王詵精心繪制的《煙江疊嶂圖》,此時的蘇軾在歷經牢獄之災和貶謫之苦的磨煉后,對社會有了更加透辟的認識,對人生有了更多思考,對藝術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在生死之交的友人面前,他揮毫落筆,作了題畫詩《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此詩引起了王詵強烈的共鳴,使他回憶起了被貶時的種種遭遇,萬千感慨下,揮墨寫下和詩《奉和子瞻內翰見贈長韻》,并在末尾答應為蘇軾再畫一幅《煙江疊嶂圖》,并期待蘇軾的題畫詩作,這就為下一次唱和埋下了伏筆。當蘇軾收到王詵饋贈的水墨卷《煙江疊嶂圖》時,興奮不已,寫下了《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仆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并借詩歌寬慰勸解友人;作為蘇軾詩歌的回應,也為表明自己歸隱的心志,王詵作了和詩《子瞻再和前篇非惟格韻高絕而語意鄭重相與甚厚》。因此,二人圍繞這幅畫共進行了兩次唱和,四首詩在情感的傳達和流動中都表現了明顯的歸隱情結,且這種歸隱之心也經歷了不斷強化的過程。
詩中蘇軾與王詵的這種歸隱情結,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析:首先,從二人的人生經歷來看,他們曾同遭政治患難,“烏臺詩案”是他們人生的關鍵轉折點,之后二人雖然回朝被重新起用,但對朝廷的失望使他們不再熱衷于官場,轉而留戀于貶謫之地的閑適自由生活。其次,從二人的思想觀念來看,蘇軾將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融合互補,為其所用,形成了寵辱不驚、進退自如的達觀心境。因此,蘇軾不同于以往文人單純地避世,而是亦仕亦隱,在《煙江疊嶂圖》唱和詩中他也這樣勸慰王詵。這也表明宋代文人的隱逸心理已超越前代“進與隱”的對立矛盾狀態,而進入更廣闊的空間領域。最后,從二人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他們所處的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統治方略,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道家思想,厚遇隱士;同時,在批判吸收儒、釋、道思想基礎上形成的理學,要求士人加強內在修養,注重“慎獨”,實現內在的超越,為隱逸之風提供了思想理論支撐;此外,宋代的士人階層與僧侶、道士、隱士們的交游極為廣泛密切,這在理學成為顯學的宋代社會是一種時尚,這一切都使得隱逸之風在當時大為盛行。而北宋激烈的黨爭使文人們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們被迫寄喻山水,從而暫時放下沉重的現實關懷,這一點也反映在當時蘇門文人產生的大量山水題畫唱和詩詞中反復高歌的“歸去”一詞中。
二、蘇王唱和詩中的歸隱情結分析
兩組唱和詩以《煙江疊嶂圖》中的內容為起點,以蘇軾的題詩為首,結合詩人自身經歷,抒發了詩人的內心感受和意欲歸隱的人生選擇。
蘇軾第一首詩題為《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書)全詩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詩的第一部分主要描繪畫中景,開頭兩句“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云煙”,粗線條勾勒出畫面的總體輪廓,然后將讀者的視線從畫面的上部一步步引向下部,由遠景、中景引向近景,而后又拉向遠景,“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這段精妙絕倫的景物描寫也為后文情感的抒發做足了鋪墊。
詩的第二部分,由寫畫轉入抒情,詩人通過回憶和想象,描繪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環境,即“ 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a 一句中遠離官場紛爭和塵俗的生活。蘇軾認為“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陶淵明筆下桃花源式的佳景勝地人間就有,武陵的人未必都是神仙,結合上句中的“留”
字,進一步表達了他對黃州生活的贊美和懷念,形象地反映了他身處逆境,渴望歸隱山水的心境。
最后四句寫詩人對現實的無奈,江山的美好誘人,使處境不堪的“我”更加殷切的退歸山水,可是又“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只得“還君此畫三嘆息”痛惜自己的不幸,并借用陶淵明的“歸來篇”收束全詩,表明心志,這就將他的歸隱之心渲染得更充分。
由《煙江疊嶂圖》的畫境,寫到黃州四時之景的實境,再寫到桃花流水的幻境,這畫境、實境、幻境,交疊相映而又連成一氣,最后歸結到“江山清空”,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圖畫,成為詩人理想的生活環境。《煙江疊峰圖》中的行人和漁人,實際上都是避世脫俗的隱士形象,成為詩人高風絕塵,蕭散恬淡的理想化身。
讀罷《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王詵往事涌上心頭,感慨萬千,揮墨寫下和詩《右奉和子瞻內翰見贈長韻》。
這首詩同樣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中,王詵回憶了自己被貶在外時的悲涼心境“平生未省山水窟,一朝身到心茫然” ,“幾年漂泊漢江上,東流不舍悲長川”。他和蘇軾都曾是皇帝身邊的得意臣子,從小生長在京都,忽而謫居此地,與親人朋友分散流離難以相聚,且自身前途未卜,因此那種期盼皇帝赦免回朝的等待是痛楚的。
第二部分詩人著重寫了流放時的自然美景:“山重水遠景無盡,翠幕金屏開目前。晴云冪冪曉籠岫,碧嶂溶溶春接天。”詩人置身大自然中,才真正感受到山重水遠、碧嶂溶溶之美,并得到了取之不盡的畫材。但“晴云冪冪曉籠岫,碧嶂溶溶春接天”,“籠岫”
一詞的使用,b 加上后面一句中帶有壓抑色彩的“碧嶂”,可以看出王詵雖享受均州的四時美景,用心體會山水,用筆描繪生活,但仍不乏被貶的苦悶情緒。
第三部分寫了詩人回朝后對現實生活的無奈感慨和歸隱的傾向。他認為自己這樣一個蒼顏華發的士大夫忘掉余年煩憂的最佳消遣途徑就是“戲墨”,這成為王詵聲言要度過余生的生活方式,但“蒼顏華發何所遣,聊將戲墨忘余年”,一個“聊”字,也表明他的選擇是在現實不如愿面前的無奈之舉。“豈圖俗筆掛高詠,從此得名因謫仙”,“謫仙”一詞可以看出,王詵與蘇軾一樣,把李白的自由灑脫作為理想人格,因此面對現實困境,他姑且選擇了歸隱,“愛詩好畫本天性,輞口先生疑宿緣”。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既對貶謫生活感到苦悶,又享受和留戀貶謫時山水的王詵形象,因此在對現實生活的無奈面前,他被迫選擇“戲墨忘余年”
這樣一種歸隱心態來度過余生。
正如王詵最后一句所愿,當蘇軾看到其饋贈的水墨卷《煙江疊嶂圖》時,很快進行了“醉筆揮長篇”
并附了序:“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仆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閏十二月晦日醉后》,是蘇軾針對王詵上一首詩歌中的苦悶進行的寬慰和勸解,也為王詵對歸隱的抉擇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這首詩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詩的開頭“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云煙。歸來長安望山上,時移事改應潸然”。蘇軾將王詵被貶時企盼回朝,而還朝后時移事改、物是人非的感嘆和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并借用“渥洼”c“鹽車之厄”d 等故事來對其做出積極勸慰,相信王詵這匹千里馬會終遇伯樂一展其才,接著蘇軾贊嘆王詵的畫功絕妙“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
第三部分蘇軾感嘆人生如夢,華年已逝,勸勉王詵“山中幽絕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幽絕不可久”
是說想要歸隱,沒有必要高遁山野遠離人間,現在的處境也可以過一種閑適逍遙的日子。在如何化解現實政治環境中的不快與壓力、在出世與入世之間,蘇軾找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中間道路——“平地家居仙”,并期望王詵“愿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囚山篇”e,警示王詵即使現在已經擺脫了那種困厄處境,也不要忘記被貶時的痛苦,更警戒他不要再次卷入政治旋渦和再次因與自己過分“親近”而重蹈覆轍。
王詵讀蘇軾詩歌后深為感動,說蘇詩“非惟格韻高絕語意鄭重,相與甚厚”,再和以下詩篇《元祐已巳正月初吉晉卿書》這首詩是王詵針對蘇軾在詩中做出的勸導和藝術贊揚而給予的集中回應,充分展現了王詵的藝術觀,也表現了他人生觀的轉變。“憶從南澗北山邊,慣見嶺云和野煙。山深路僻空吊影,夢驚松竹風蕭然”。王詵回憶了自己貶謫期間“慣見嶺云和野煙”的孤苦生活,于是做了“杖藜芒履謝塵境,已甘老去棲林泉”的決定。就“隱”這一點而言,王詵寫此詩時的“隱逸”思想似乎比蘇軾“要作平地家居仙”更為決絕與徹底。王詵所追慕的“康伯”f“稚川”g 的故事,以及“ 漁樵每笑坐爭席,鷗鷺無機訓我前”h 的生活狀態,說明王詵已與鄉野百姓打成一片,與自然融洽親近,這充分表現了王詵對脫塵絕俗的隱逸理想的追尋,甘愿“老去棲林泉”的態度。
接著寫了詩人被貶到回朝的心路歷程“一朝忽作長安夢,此生猶欲更問天。歸來未央拜天子,枯荄敢自期春妍”。他做夢都想被皇帝重用,但回來后遭遇心灰意冷的處境,從而引出王詵的感嘆“造物潛移真幻影”,在酒醉恍惚間,他用畫筆追憶貶謫地的自然景色,“醉來卻畫山中景,水墨想象追當年”,表示自己不愿再為生活中的種種得失而耗費心力、痛苦掙扎。王詵也深感自己的“屠龍學就本無用”,報國之志無法實現,便決意隱退,醉心藝術,聊以自慰,只想在年老力衰時“依金仙”,會隨從蘇軾選擇一種“平地家居仙”式的生活。并在末句巧用《詩經》中的《木瓜》一詩,給他們的深情厚誼做了精彩的總結:這不是禮尚往來的相互贈答,而是“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蘇軾與王詵這兩度詩歌唱和,不僅是二人在繪畫藝術方面的交流,更是身處逆境的兩位好友間的相互傾訴和勸勉,是一次完美的心靈對話。詩中處處可見二人在歷經政治劫難后意欲歸隱的情結,且這種歸隱之心的強化在王詵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通過對四首題畫唱和詩中歸隱情結的分析,可以獲知蘇王二人真摯的情誼和共同的志趣;同時也可知,在歸隱風氣充盈而又激烈動蕩的時代背景中,在文化的熏陶感染和政治的逼迫壓力下,在個人歷經仕途沉浮和思想斗爭后,歸隱,是北宋士人的自然選擇。因此,蘇王二人的歸隱情結,是時代賦予的,更是個人在歷經劫難后自我超脫的人生抉擇。這種亦仕亦隱的生活狀態,體現了以蘇軾為代表的“仕隱”一代,雖歷經艱辛,但仍心系天下的高尚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