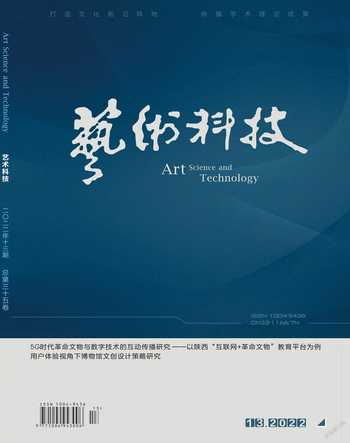數(shù)字化背景下傳統(tǒng)紋樣的新生
姚世珍 程港龍










摘要:當(dāng)今數(shù)字化雕塑技術(shù)成熟,以3D打印的方式呈現(xiàn)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成為設(shè)計主流。文章將3D打印技術(shù)與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相結(jié)合,探索、傳承與創(chuàng)新古滇青銅器文化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中的設(shè)計與應(yīng)用,以助推云南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在新時代呈現(xiàn)個性化、多元化的發(fā)展面貌,是對創(chuàng)新訓(xùn)練項目實施中科技與藝術(shù)融合的經(jīng)驗總結(jié)。
關(guān)鍵詞:3D打印技術(shù);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古滇青銅器
中圖分類號:TB47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13-00-04
1 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的發(fā)展現(xiàn)狀
云南古滇青銅器是云南傳統(tǒng)雕塑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造型生動奇特,呈現(xiàn)出內(nèi)容多樣、紋飾細(xì)膩復(fù)雜的特點,所蘊(yùn)含的藝術(shù)信息豐富,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藝術(shù)瑰寶之一。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青銅器所呈現(xiàn)的豐富內(nèi)容、精美紋飾與深刻內(nèi)涵需要得到傳承與創(chuàng)新,同時,為了滿足人們?nèi)找嬖鲩L的精神文化需求,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應(yīng)運(yùn)而生。
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是新時代以創(chuàng)造力為核心的新興產(chǎn)業(yè),不僅體現(xiàn)了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也為傳統(tǒng)文化在新時代煥發(fā)新面貌提供了機(jī)會。云南省博物館針對古滇青銅器,大力開發(fā)了一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先后推出了與貯貝器
造型相仿的貯貝器存錢罐,富含青銅器紋樣的冰箱貼,直接將青銅器造型縮小、放大、換材質(zhì)而形成的羽人形象耳環(huán)、滇王之印紀(jì)念章等文創(chuàng)產(chǎn)品。
目前,博物館對古滇青銅器系列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有所欠缺,僅停留在開發(fā)一些具有實用功能的小物件上,且文創(chuàng)整體造型大多直接照搬青銅器形象,缺乏產(chǎn)品種類的多樣性、文化內(nèi)涵的獨特性、“異想天開”的創(chuàng)意性。距云南省不遠(yuǎn)的三星堆青銅博物館積極開發(fā)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三星堆人物盲盒、縱目萌萌杯、青銅面具冰激凌、青銅系列聯(lián)名彩妝等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見圖1、圖2、圖3、圖4),使三星堆青銅文化以多樣的形式載體“走出”博物館,重新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力。
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在我國的發(fā)展趨勢向好,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逐漸成為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主力軍。云南坐落于祖國的西南邊陲,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內(nèi)勁逐年增強(qiáng),且擁有深厚的青銅文化,應(yīng)大力發(fā)掘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形成獨特的文化標(biāo)簽和別具一格的文化風(fēng)貌,使古滇青銅文化以新的面貌進(jìn)入大眾視野。
2 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意靈感來源
古滇青銅器的造型美、形式美、意蘊(yùn)美是毋庸置疑的,但古老的青銅器無法與新時代接軌也是不可否認(rèn)的事實。形式主義美學(xué)家克萊夫·貝爾認(rèn)為“美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所以,在以科技、創(chuàng)意為推動力的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設(shè)計和制作過程中,應(yīng)積極賦予古老的古滇青銅器有意味的形式。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靈感來源于中國傳統(tǒng)的象棋文化。中國象棋大約成型于戰(zhàn)國時代,項目團(tuán)隊在象棋原本內(nèi)涵的基礎(chǔ)上,將古滇青銅器與象棋融合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出豐富的屬于滇族本土的象棋形象,講述了一個千年以前發(fā)生在云南這片神秘大地上的戰(zhàn)爭故事。
3 古滇青銅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滇人象棋》的形象特征與等級關(guān)系定位
3.1 對古滇青銅器人物形象造型語言的借鑒
古滇國生活淳樸,項目團(tuán)隊借用了許多生活元素來塑造兵卒形象。在當(dāng)時,古滇國最低階級的士兵一般由田間勞作的農(nóng)民組成,穿著最為簡陋,根據(jù)最為真實的情況來塑造人物形象,亦是不能篡改的事實。
以棋子“兵”為例,該角色主要借鑒古滇青銅器的人物造型,士兵原型為古滇青銅器“戰(zhàn)爭場面貯貝器”中的士兵。“戰(zhàn)爭場面貯貝器”表現(xiàn)了滇人和昆明人之間一場激烈的戰(zhàn)爭,編著長發(fā)的昆明人被氣勢高昂的滇族士兵打得潰不成軍。在“戰(zhàn)爭場面貯貝器”一角,有一滇族士兵身著盔甲,左手拿盾牌,右手持劍,面部表情猙獰,身體作跨步狀,似乎是想在防御的同時伺機(jī)發(fā)動攻擊,表現(xiàn)出了滇族士兵誓死保家衛(wèi)國的決心。如此豐富的造型內(nèi)涵為棋子“兵”的形象塑造奠定了一定的造型基礎(chǔ)。團(tuán)隊分析了此士兵的裝備、服飾、造型形式,借助數(shù)字雕塑的手段進(jìn)行了形象還原與二次創(chuàng)作。項目團(tuán)隊在二次創(chuàng)作中,一方面保留了原始具象寫實的風(fēng)格,另一方面保留了青銅雕塑中所營造出的猙獰氣氛與原始沖動,并將士兵安排在富有古滇特色的銅鼓棋座上,這樣,一個在藝術(shù)造型上具有典型性,在文化內(nèi)容上又具有代表性的“兵”就變得栩栩如生了。
以棋子“炮”為例,該角色為原創(chuàng),脫離了古滇青銅器人物的具體形象。作為象棋中威力第二大的棋子,“炮”攻守兼?zhèn)洌椖繄F(tuán)隊在了解古滇國歷史和古滇青銅人物造型語言的基礎(chǔ)上,對其形象進(jìn)行了獨特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在構(gòu)圖上,采用三角形構(gòu)圖,首先保證其人物的穩(wěn)定性,增強(qiáng)棋子本身的莊嚴(yán)、挺拔之感,在此基礎(chǔ)上,以銅矛形成的尖角為引向,豐富“炮”所應(yīng)該具有的運(yùn)動感和沖刺感[1]。在內(nèi)容上,作為重武器的“炮”,首先在外在形象上應(yīng)是一個極具威懾力的戰(zhàn)士形象,所以項目團(tuán)隊將“炮”設(shè)計為一個壯碩的戰(zhàn)士,同時輔以重裝鎧甲,增強(qiáng)其形象上的張力和力量感。其次在武器上,弓箭不太適合這位身形健碩的戰(zhàn)士,所以將具有神秘色彩的“吊人銅矛”融入其中,“吊人銅矛”為這位從外表上看就已經(jīng)威懾力爆表的戰(zhàn)士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3.2 對古滇青銅器紋樣造型語言的借鑒
以棋子“車”為例,“車”是象棋里威力最大的一個,因為它橫線、豎線均可行走。關(guān)于“車”的形象,最初設(shè)想是將其塑造為具象的戰(zhàn)車形象,并輔以一定的紋樣裝飾。但根據(jù)資料考證,當(dāng)時的云南地形復(fù)雜,山路崎嶇,并不適合行駛戰(zhàn)車,所以該想法與歷史不符。“船紋”的出現(xiàn),使項目團(tuán)隊眼前一亮,當(dāng)時云南各民族的水上活動頻繁,如果民族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可能就會出現(xiàn)戰(zhàn)船的身影。在“船紋”[2]中,“羽人”的紋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雖然“羽人”的祭祀屬性更強(qiáng)一些,但“羽人”未嘗不可是一個威風(fēng)凜凜的將士。因此,“車”的基本造型為一個站在戰(zhàn)船中的“羽人”形象。戰(zhàn)船的形象,如果單以一種普通船的形象來塑造,可能略顯枯燥,缺乏民族特色。而青銅器中“孔雀銅鎮(zhèn)”[3]昂首挺胸的造型就恰似戰(zhàn)船的船頭,飽滿的身體就像巨大的船身,孔雀本身又代表著云南本土特色,這三點給了項目團(tuán)隊很大的啟發(fā)。將“孔雀銅鎮(zhèn)”造型和船相結(jié)合,再將羽人安排到孔雀戰(zhàn)船上,這樣一個在形式和內(nèi)容上都極具古滇特色、云南特色的“車”造型就呼之欲出了。
在古滇青銅器上,有非常多的紋樣表現(xiàn)了動物和動物之間廝殺的狀態(tài),而有些紋樣在表現(xiàn)動物之間互相搏斗的同時,逐漸產(chǎn)生了符號化傾向,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蛇紋”[4]、由“蛇紋”演變而來的“龍紋”以及受蛇紋影響的“虎紋”。受這些紋樣的影響和啟發(fā),部分棋子的造型也發(fā)生了獨特的變化。以棋子“炮”為例,“炮”是象棋中具有第二大威力的棋子,攻擊距離遠(yuǎn)且殺傷力較大。遠(yuǎn)古時代,火器還沒有出現(xiàn),具有遠(yuǎn)距離殺傷力的兵種只有弓箭手,所以,“炮”的形象來源于古代弓箭手。在人物造型上,為了使其更具有內(nèi)在張力,項目團(tuán)隊參考了布德爾的雕塑《拉弓的赫拉克勒斯》,并且在人物使用的武器上,受“蛇紋”“龍紋”的影響,項目團(tuán)隊賦予了弓箭更多的動物造型,使一把原本普通的弓箭,升級為了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弓箭。這樣,象棋中第二大威力的棋子“炮”的形象也明朗起來,即一名正在拉弓射箭的弓箭手。
3.3 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兵將等級定位
項目團(tuán)隊根據(jù)古滇國森嚴(yán)的等級制度與中國象棋各棋子的定位,將二者進(jìn)行匹配,各棋子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如下:
將——古滇王莊蹻
車——古滇國騎士階級(一往無前、直殺直退的“車”,擁有古滇國騎士精神,勇猛無畏的騎士將是戰(zhàn)場上戰(zhàn)無不勝的大將。)
馬——古滇國突進(jìn)刺客(在象棋中,“馬”更適合在后期發(fā)力,在定位中更像刺客。)
炮——古滇國重型士兵、較壯的角色(在象棋中,“炮”在前期具有很強(qiáng)的進(jìn)攻和保護(hù)能力,但后期乏力,用處不大,這與重型士兵移動不便的特點較為相似。)
兵——古滇國士兵(古滇國在兵卒方面并沒有明確的職業(yè),在戰(zhàn)時農(nóng)民等人便會拿起武器,項目團(tuán)隊決定將兵卒塑造為這樣的形象。)
相——古滇國舞女(祭祀時需要陪襯祭祀的人員,“相”便以舞女的形象出現(xiàn)。)
仕——古滇國主祭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按照等級制度劃分,主祭司應(yīng)以祀為主。)
4 數(shù)字雕塑技術(shù)與3D打印在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制作中的應(yīng)用
?數(shù)字雕塑是利用計算機(jī)數(shù)字化三維軟件制作數(shù)字雕塑數(shù)據(jù),然后通過CNC設(shè)備或3D打印機(jī)等成形技術(shù)制作出雕塑實物[5]。?它是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的產(chǎn)物,是技術(shù)與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一個突破。
21世紀(jì)為數(shù)字雕塑的發(fā)展提供了非常廣闊的平臺。數(shù)字化軟件不斷更新,不斷地適應(yīng)當(dāng)前時代發(fā)展,輕巧高效的數(shù)字化軟件充分體現(xiàn)了高科技性。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依托云南省高校數(shù)字化藝術(shù)創(chuàng)作重點實驗室先進(jìn)的設(shè)備,以ZBrush數(shù)字雕塑造型軟件為造型手段,以光敏樹脂材料的3D打印為成型的技術(shù)和材料。3D打印又名增材制造技術(shù),與傳統(tǒng)的產(chǎn)品生產(chǎn)工藝不同,它是一種以數(shù)字模型文件為基礎(chǔ),運(yùn)用樹脂等可黏合材料,通過逐層打印的方式來構(gòu)造物體的技術(shù)。
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模型由ZBrush軟件制作完成,將模型導(dǎo)出為STL格式,再通過切片加支撐軟件將模型文件制作成3D打印機(jī)所能識別的切片文件,如此3D打印機(jī)便可以根據(jù)切片文件,通過層層堆積的方式將模型完好地制作出來。3D打印所制作的模型在精度、效率、質(zhì)量、成本等方面都較為規(guī)范,打印成品表面也呈現(xiàn)光滑、圓潤、規(guī)整的技術(shù)與工藝美感。在小批量或個性化生產(chǎn)過程中,3D打印所呈現(xiàn)的優(yōu)勢是傳統(tǒng)制造業(yè)無法比擬的,這樣的優(yōu)勢使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研發(fā)周期大大縮短,減少了投入成本,為產(chǎn)品樣板的二次編輯、修改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3D打印和數(shù)字雕塑技術(shù)以新的科技手段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方式,其制作效率高、造型準(zhǔn)確、產(chǎn)品材質(zhì)多樣化等優(yōu)勢創(chuàng)新了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制作過程。
5 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制作感悟
數(shù)字化技術(shù)和3D打印在古滇青銅器系列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制作過程中起了關(guān)鍵性作用。在無法真正接觸到實物的前提下,項目團(tuán)隊僅通過照片和其他圖片資料便能將青銅器模型較好地復(fù)原出來,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獨特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通過多次操作3D打印機(jī)制作產(chǎn)品小樣,根據(jù)小樣模型反作用于數(shù)字模型,如此反復(fù),以調(diào)整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中不合理的地方。制作團(tuán)隊通過不斷實踐,以實際行動擴(kuò)展了3D打印技術(shù)的應(yīng)用范圍,以實踐促進(jìn)了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新時代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融合創(chuàng)新,實現(xiàn)了以全新的數(shù)字化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手段來弘揚(yáng)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6]。
藝術(shù)的延續(xù)在于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藝術(shù),一旦脫離了創(chuàng)新,與時代脫節(jié),終將不復(fù)存在。通過對古滇青銅器紋樣的借鑒和運(yùn)用,充分體現(xiàn)項目團(tuán)隊對古滇青銅文化的理解和對數(shù)字雕塑技術(shù)、3D打印技術(shù)的掌握,生動地傳達(dá)了古滇青銅文化所呈現(xiàn)的造型美、內(nèi)容美、形式美和意蘊(yùn)美,積極展現(xiàn)了古滇青銅文化在新時代的新面貌,豐富了科技在繼承和弘揚(yáng)傳統(tǒng)文化中的應(yīng)用實踐。同時,此次創(chuàng)作實踐也讓項目團(tuán)隊對數(shù)字雕塑、古滇青銅文化有了更多的思考與想法,更加確信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介入可以豐富古滇青銅器文物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展示方式。在文物展示上,可以使用三維掃描技術(shù)掃描文物,文物就擁有了虛擬形態(tài),虛擬文物展覽也可以就此展開。人們無須移步到展廳,便可以通過手機(jī)、電腦等設(shè)備在虛擬空間360°全方位地欣賞文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這種虛擬展覽的方式有助于人們接受文化的熏陶。在文化創(chuàng)新上,可以直接對掃描模型進(jìn)行二次創(chuàng)作,再通過3D打印技術(shù)使之成為觸手可及的實物,傳播古滇青銅器本身所擁有的藝術(shù)美感,為古滇青銅文化的傳承、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提供一種新的形式。而這種以科技作用于藝術(shù)的形式也豐富了“數(shù)字云南”的創(chuàng)新成果。
6 結(jié)語
文化需要創(chuàng)新,不斷地創(chuàng)作出更多具有鮮明特色的藝術(shù)作品,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科技也需要不斷地與藝術(shù)交融,才會使藝術(shù)發(fā)展進(jìn)步,從而產(chǎn)生更多的藝術(shù)種類、藝術(shù)形式。古滇青銅文化亦是如此,項目團(tuán)隊一方面從實踐的角度出發(fā),借鑒古滇青銅器人物造型語言,以古滇青銅雕塑最為淳樸的風(fēng)格改善數(shù)字雕塑語言。探索古滇青銅器人物造型,更新數(shù)字雕塑的創(chuàng)作方式,構(gòu)建出結(jié)合古滇青銅文化淳樸語言風(fēng)格的新型數(shù)字雕塑創(chuàng)作方式;另一方面從弘揚(yáng)和保護(hù)民族文化的角度出發(fā),對古滇青銅文化進(jìn)行數(shù)字雕塑創(chuàng)作是為了更好地傳承青銅文化,喚起大家對傳統(tǒng)文化的興趣,廣泛傳播古滇青銅器所擁有的情感、創(chuàng)造與智慧,為古滇青銅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提供一種新的形式。
時代的進(jìn)步需要創(chuàng)新發(fā)展,運(yùn)用數(shù)字化技術(shù)將古滇青銅器的造型語言與數(shù)字技術(shù)相結(jié)合,使古滇青銅器藝術(shù)以文創(chuàng)的形式傳播和推廣,項目團(tuán)隊實現(xiàn)了科技與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的偉大探索,為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參考文獻(xiàn):
[1] 常銳倫.繪畫構(gòu)圖學(xué)[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7:221-222.
[2] 姚鐘華.古滇青銅器畫像拓片集[M].昆明:云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8:55-56.
[3] 張增琪.滇國青銅藝術(shù)[M].昆明:云南美術(shù)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270-271.
[4] 沈?qū)?云南石寨山文化紋飾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17-18.
[5] 張盛.數(shù)字雕塑技法與3D打印[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9:6-10.
[6] 張仲夏,李異文.“七彩云南”彩車創(chuàng)意構(gòu)思的文本解讀[J].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2019(4):97-99.
作者簡介:姚世珍(1999—),男,山西太原人,本科,助理實驗員,研究方向:數(shù)字雕塑。
程港龍(1997—),男,安徽潁上人,本科,助理實驗員,研究方向:數(shù)字雕塑。